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内文配图由作者提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
我之所以叫“馒头大师”,虽然和馒头本尊没什么大关系,但我小时候确实爱吃馒头。
确切地说,是“肉馒头”——在上海话里,“包子”和“馒头”是一个意思。根据馅料不同,前面要加定语:“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黑洋酥馒头”,如果没有馅,也有定语:“淡馒头”。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住得比较远,我和几个家里同样住得远的同学(住得近的就回家吃饭了),中午会一起去复旦的教职工食堂吃饭。我们去的那家食堂供应各种面食,但我们独爱吃那里的肉馒头。
那里的肉馒头个头不算大,我们称之为“中包”。皮薄肉香,一口咬下去,一汪汁水,打耳光不肯放。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我们,其他什么都不买,水都不用喝一口,每顿一口气吃六个。
后来有段时期,我们几个同学陷入了“谜之内卷”:中午一定要把上午的作业全都做完,越快越好。于是我们就会每人六个滚烫的“中包”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揣着飞奔回学校,到教室里拿出做业:一口馒头,几行做业,边吃边写——估计那时候老师批到我们几个的作业时,应该总是能闻到一股肉香。
在回学校路上,我们谁都舍不得啃一口包子,是一定要带回学校一起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回学校路上,一个小伙伴一定要给我模仿《圣斗士星矢》里冰河的绝招“曙光女神之宽恕”——双腿岔开,双手握拳(捏着装肉馒头的塑料袋)高高举过头顶,大喊一声绝招名字,猛然下坠双手。
那天的肉馒头新鲜出炉,滚滚烫烫,其实已经几乎把塑料袋底部烫穿了。他猛地向下一甩,六个比命还珍贵的肉馒头从他的胯下依次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上,然后歪歪扭扭都滚进了旁边的下水沟——远看,就像他撅着屁股下了六个蛋。
那天中午,我吃了三个,他吃了我匀给他的三个。
因为那家食堂做的肉馒头好吃,所以我格外珍惜那家的饭票(当时要凭复旦的饭票买的)。有时候我每天会节省下来一毛两毛的饭票,时间长了,也积攒了近十块钱——当时对我而言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当时的想法是:哪天中午,我吆五喝六、大摇大摆地带着几个同学走进那个食堂,把一摞饭票往窗口前一拍,转头对大伙说:“今天馒头敞开吃,我请客!”
那时候正痴迷看《基督山伯爵》,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看中了放学回家路上经过的一片工地旁的几块石板。我决定每天都把攒下的饭票压到其中一块石板的缝隙下——那种刺激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埋一个重大的宝藏。
大概两个月后,我又一次去到那个工地准备“藏宝”,发现那几块石板已经被人搬走了。
一阵风吹过,原先摆放石板的沙地上只有几根倔强的小草在轻轻摇摆。
还有在风中凌乱的我。
2
有时候午饭吃完,作业做完,我们就会结伴到校门口的小摊贩那里买零食。
当时我们校门口的小摊贩属于“寡头垄断”,一般只有两个摊位,我们叫“老太婆摊位”和“老头子摊位”。
相比较之下,“老头子”那里的货更偏向于“玩”:粘纸,香烟牌,火药枪,山寨“变形金刚”等等。而“老太婆”那边主打是“吃”。
所谓的“吃”,其实千奇百怪,不少都是她老人家自制的。比如我记得有一种,一根竹签串了一个螺蛳肉,外面裹一层炸过的面粉团,放到酱油里浸一浸,一串一毛钱;还有一种薄如蝉翼的脆饼,我们叫“蛋饼”,一张一毛钱,折成几折,放到嘴里,一口就融化了。
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一种叫“琴糖”的东西。一般我们会说“来个一毛钱的”。老太婆就拿出一根竹签,一掰二,然后打开一个陈旧的饼干桶,里面是一坨咖啡色的黏糊糊的东西,她用两根竹签搅那么几下,绕那么几下,然后弄出一团递给你。
你要说这“琴糖”有多好吃,真的未必,但可能重在整个过程。我和几个小伙伴总会一人弄个一毛钱的,然后到学校教学楼后面的乐园,大家坐在转盘上,每个人拿着两根小竹签搅啊搅,舔一口,搅两下,聊两句——那幅画面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几位少妇在村口唠家常,每人手里在打着一坨毛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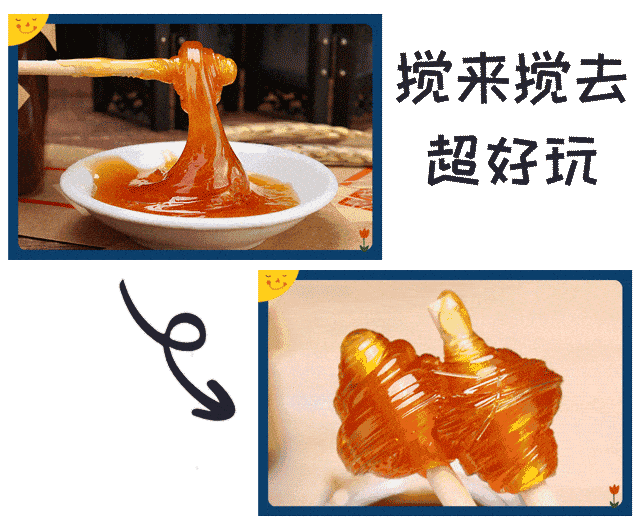
我读小学的那个时代,零食其实是很匮乏的。我记得当时出来不久的“太阳”牌锅巴,大家都很爱吃,但要7毛5分一包,只能偶尔解馋,不可能一直拿来当零食。能吃到炒货摊上的一些瓜子、花生米(一般用报纸包一个三角包给你),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神秘兮兮告诉我,他发现了一种“零食”的吃法。
当时我们放学后肚子会饿,经常会去买大饼:甜大饼是圆形的,里面有点白砂糖,一毛钱一个;咸大饼长条形,里面抹了点盐和葱花,一毛五分钱一个。
一个大饼其实不经吃,三口五口就没了。而我这个同学想出的办法是:
用地道西安人撕羊肉泡馍的纯正手法,将一个大饼撕成极细极碎的小块,然后放到衣服口袋或裤子口袋里,一点点用食指和中指撮出来吃。
这种天才的“化整为零”的方法,顿时打开了我的格局。原来一个大饼只能吃2分钟,现在一个大饼够我放学一路走回家吃上一个多小时。
直到有一天我妈看到我,问我扣扣索索从裤子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在吃?当她发现是大饼碎屑时,瞪大了双眼,不知是恼怒还是怜惜还是内疚,竟然楞在当场,半晌说不了话。
到了初中,校门口的摊贩就明显多元化了,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摊位,永远是烤串摊。
那时的烤串摊,只有一个品种:一串串自行车钢圈上拆下的钢丝,串上比小拇指甲盖还小的几块肉,放在煤炭架上,用不知道哪次刷墙报废的油漆刷抹上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油,撒上几把不知道是盐是胡椒是孜然的粉末,用不知道是不是从《济公》剧组直接拿来的蒲扇猛扇几把——滋啦冒油,腾腾喷香。
一串一毛钱,多多少少同学们都买得起。如果有人跑到摊位前一下甩出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面额的钱已经在几年前停止流通和兑换了),一把20多串(老板有时候还会送一串两串)攒在手里,满嘴冒油地在那边啃,肯定是会引来众人的啧啧赞叹。当然,如果能分出几把请同学们一起吃,那就更值得歌功颂德了。
只是吃得嘴角冒油的时候,大家总会讨论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肉到底是什么动物的?
一般结论来自一对“天敌”:要么是猫的,要么是老鼠的。
双方都会摆事实讲道理,有时还会提高嗓门争论几句,但结局总是只有一个:
猫鼠一家,入胃为安。
3
饮料和冷饮值得单列一段来讲。
我们这代,是经历过上海“正广和”汽水的那一代,我们叫“橘子水”。在那时候,洋饮料属于绝对奢侈品。
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隔壁小伙伴家玩——他的妈妈是第一批买了股票认购证的。当她打开冰箱,露出一排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请我拿一罐喝的时候,我竟然茫然不知所措,半晌不敢伸手,仿佛人家是要我接受的是一张100万元的支票。
往后几年,可乐、雪碧、芬达开始普及了,但易拉罐装的还是舍不得喝的,更多喝的是一种所谓“可口可乐经典瓶”的那种小瓶装。我一直怀疑中国大陆应该有一条隐秘的地下生产链条,不然这种小瓶装凭什么要比其他款型便宜很多?
有一段时间,“七喜”是我们小伙伴中的宠儿,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广告里的那个小人很“酷”。我一直以为他叫“非洲DIDO”,想大概那里十分干旱,所以要喝饮料,后来才知道人家叫“Fido Dido”,跟非洲没半毛钱关系。

至少在我们那片地区,似乎很少见到过“健力宝”的身影,但有种可乐,我们初中时踢完球是经常喝的,一喝就是一整瓶——用装啤酒的瓶子灌的。一瓶也才2块钱,比可口可乐便宜多了。我一直以为叫“天应可乐”(应是繁写体),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天府可乐”。
到了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喝“维他奶”,软包装,1块5一包。那时候我天天在学校参加晚自习,就会去学校小卖部买一包维他奶,放在课桌前,做几道数学参考题,就轻轻抿那么一口——一包维他奶能抿上两小时。
但有时候碰上一道题解不出,抓耳挠腮,越想越气,恼羞成怒,几口就能吸干一包。
相对于饮料,冷饮不解渴,纯粹属于解嘴馋的。
那时候五角场翔殷电影院对面、55路终点站附近有一家卖冰霜的,5毛钱一小杯,菠萝味。我当时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冷饮?
每次都舍不得吃一口完整的,挖一小勺,用上嘴唇去慢慢抹,抹一点,抿一点,直到苦心节省下来的冰霜都化成了冰水。
大名鼎鼎的“光明牌”中砖,在我们那时候是属于奢侈品,一般不吃的。我们吃的最多的,是1毛钱一根的橘子“棒冰”,以及1毛5一根的奶油雪糕。橘子棒冰其实比较解渴,但不能吮吸——一吸,就把里面的糖精乃至色素全都吸出来了。吸时一时爽,最后留下一截白花花没有任何味道和颜色的冰块,也只能硬着头皮啃下去。
价格再往上一点,当时有传统“三件套”:4毛5分一根的“娃娃脸”雪糕:挺好一个人脸,越舔越融化,五官越变形,总让人想起《雪孩子》;4毛5钱一根的“鸳鸯雪糕”,贵有贵的道理:人家是“双子星座”,有两根棒子两截雪糕,可以一拗二分着吃的;再贵一点的我们叫“紫雪糕”,价钱忘了,就是奶油雪糕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皮,当时已经是很惊艳了,属于雪糕中的“贵族”,轻易不吃的。

我记得有段时间各大冷饮店还推出一种长棍状的奶油雪糕,镶嵌着葡萄干或菠萝,名字叫“冷狗”——我也不知道这和狗有什么关系。价格不贵,分量又足,所以一度很受欢迎。

有时候,“冷狗”刚从冰柜里拿出来会非常冰,如果旁边恰好有女生们在,有些男生就会把舌头舔上去——低温会造成舌头黏在“冷狗”上拔不下来。这大概也算一个节目,因为这时候往往女生们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冷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舔狗”倒有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4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下馆子”三个字对我们很遥远,是大人们的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小伙伴一起到一个同学家去玩,到了中午饭点,他妈妈居然关照他:“去吧,就去弄堂口那家饭店,请你同学好好吃点。”
我们当时就震惊了:这是要下馆子?!我们一般去同学家,也就家长煮点馄饨下点面条啊……结果那天不仅下了馆子,那同学还点了一桌子菜。我人生第一次吃的“松鼠鲈鱼”就是在那次吃到的,至今印象深刻:世界上怎么能有那么好吃的菜?
到了高中,“下馆子”就比较常见了,但都是校门口的那种小馆子。
我记得高中校门口有一家叫“柳林饭店”,老板和老板娘人很好,菜给得足,价格经常抹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月总要去那里吃几次,每次基本四个菜:椒盐排条,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蒜泥空心菜。有时还会一起分享一瓶啤酒——嚯,当真是有大人的感觉了。
高三那年,因为提前保送,自然要请客,在那家饭店包厢摆了一大桌,请了十几个要好的同学,点了无数菜,喝掉两箱啤酒,总共花了280元钱——记得清楚,是因为当时对我而言是笔巨款了。
因为我家也经常去那家吃,所以后来那家老板夫妇和我们家也成了朋友。那家夫妇挺会做人的,记得有一次托我妈办件什么事,来家里送礼,顺带把他们女儿带来了我家。那时他们女儿五岁左右,我就在房间里教她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画画,她画了好几张,我都帮她起好名字存了下来。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不肯走,还哭了鼻子。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萌发念头:如果以后有个女儿该多好。
其实高中时候,洋快餐已经在上海很普及了,但对我们那时候而言不便宜。
相对于麦当劳,我和几个同学更喜欢肯德基——当时肯德基调研中国人爱吃鸡是有道理的。
我们吃肯德基,是很有仪式感的:那时候每年成龙都会出一部贺岁片,我们会相约一起去电影院看,散场后到影院旁的一家肯德基聚餐。一般是一人一个套餐:一个汉堡,一包薯条,加一对鸡翅,大概14元~16元左右。一对鸡翅是肯定不够的,只是刚把馋虫勾出来了而已,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就这样推门离开了——不是意志力坚强,而是囊中羞涩。
至于麦当劳,更多是一个聊天和看书的地方。刚读大学的时候,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红遍海峡两岸的年轻人圈子,麦当劳在他笔下被赋予了一层特别的含义,已经超出“饮食”的范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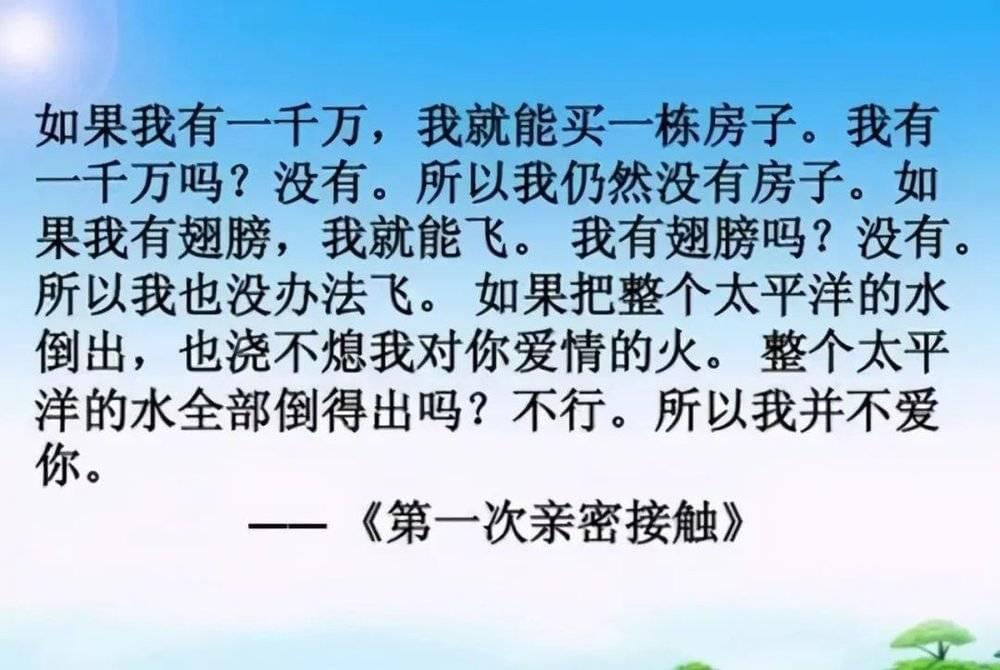
现在的肯德基和麦当劳比原来的品种要丰富多了,我相信口味肯定也不会下跌,而现在真的可以轻而易举点上一大桌了。
但现在已经基本不吃了,即便偶尔吃,那种味道也回不来了。
5
洋洋洒洒,已经要5000字了。
写着写着,各种关于吃的本身,背后的故事和人就会源源不断冒出来。其实还没写的有很多:方便面,干脆面,“鼻头污”(沪语俗语,其实就是盐津枣),万年青饼干,动物饼干,自制蛋卷……以及第一次吃自助餐,吃日料,吃西餐,吃粤菜,各种关于美味的回忆扑面而来。
先搁笔吧。也想看看大家的留言。我相信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的——有相同的,也会有不同的。
不过你们应该会发现:只要你不是真正职业意义上的美食家,那么当你回忆某款美味的时候,总是会难免想起吃这道美味时所处的环境,当时的事,相伴的人……
回忆嘛,怎么可能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期待你们的精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