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 (ID:njupress),内容节选自《论诱惑》,有删改,作者:让· 鲍德里亚,翻译:张新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对游戏的痴迷是否来自一种梦的境地?
即人们在梦中摆脱了现实,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离开游戏?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游戏服从于某些规则,做梦可不是这样,人们不会丢开游戏。
游戏所建立的秩序是约定俗成的秩序,它与现实世界的必要秩序没有共同的尺度:它既非伦理的秩序,也非心理的秩序,对它的接受(对规则的接受)既非屈从也非被迫。只是在我们精神和个体的感受中不存在游戏的自由。
游戏不是自由。它并不听从自由意志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假设的辩证法,属于现实和法则的领域。
规则的激情
任何玩家都不应该比游戏本身更加伟大。
——《滚球大战》
这是《诱惑者日记》中所说的意思:诱惑中并没有某种策略的主人主体,而策略呢,当它在完全知道其手段的情况下展开时,它还是受制于某种超越它的游戏规则。作为法则(loi)以外的礼仪戏剧,诱惑是一个游戏,也是一种命运,正像其游戏对手被带向各自不可避免的目标那样,并不违背规则(règle)——因为正是规则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其基本的义务:必须让游戏继续下去,即使付出死亡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有一种激情将游戏者与规则联系起来,规则又将游戏者联系起来,没有这个规则,就没有可能的游戏。
我们共同生活在法则的秩序中,甚至生活在废除法则的幻觉中。我们只能在对禁忌的冒犯或取消中看到法则的彼处。因为法则和禁忌的格局(schème)控制着冒犯和解放的反向模式。然而与法则抗衡的东西绝不是法则的缺席,而是规则。
规则(Règle)是在任意符号的内在连接上做文章,而法则(Loi)则建立在必要符号的超验连接之上。前者是约定程序的循环和重复出现,而后者是在不可逆的持续性上建立的一个行为体。规则属于义务的范畴,法则属于约束和禁忌的范畴。因为法则设置了一条分割线,它能够也应该被人冒犯。相反,“违反”一条游戏规则没有任何意义:在一个循环的重复出现中,没有需要跨越的分界线(只需走出游戏,句号,事情到此了结)。
对于法则,不管是能指的法则,还是去势的法则或社会禁忌的法则,它想充当话语的符号,一种合法结构体的话语符号,一种被掩盖的真理的话语符号。法则到处设置禁忌和压抑,因此也是对明显话语和潜在话语进行的划分。
由于规则是约定俗成的,任意的,没有被掩盖的真理,它不会经历压抑,也不会有明显和潜在的区分:它仅仅是没有意义而已,并不走向任何地方;而法则却有明确的目标。规则的无限可逆循环与法则的线性目标连接形成鲜明的对照。
符号在规则和法则中不具有同样的地位。法则属于表现的范畴,可以通过阐释和解译来证明。它属于命令和陈述行为的范畴,其主体不能无动于衷。它是一个文本,会在意义和参照的打击下倒地;规则没有主体,其陈述的方式并不重要;人们不会解译它,这里不存在意义的快乐——唯一重要的是对它的遵守和这种遵守的眩晕。这样也区别出游戏的仪式性激情,其强度,还有与服从法则紧密相连的享受,或与冒犯紧密相连的享受。

为了抓住礼仪形式的强度,我们无疑应该破除这样的想法,即任何幸福都来自大自然,任何享受都来自某个欲望的实现。游戏,游戏的领域则从反面向我们揭示了规则的激情,规则的眩晕,来自某种仪式的威力,而不是来自某种欲望的威力。
对游戏的痴迷是否来自一种梦的境地?即人们在梦中摆脱了现实,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离开游戏?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游戏服从于某些规则,做梦可不是这样,人们不会丢开游戏。游戏所创建的义务与挑战的义务属于同一范畴。丢开游戏可不属于游戏的做法,不可能从内部去否定游戏。这种不可能性形成游戏的魅力,使它区别于现实范畴,同时创建一个象征公约,一种没有限制的遵守约束,把游戏进行到底的义务,就像把挑战进行到底那样。
游戏所建立的秩序是约定俗成的秩序,它与现实世界的必要秩序没有共同的尺度:它既非伦理的秩序,也非心理的秩序,对它的接受(对规则的接受)既非屈从也非被迫。只是在我们精神和个体的感受中不存在游戏的自由。游戏不是自由。
它并不听从自由意志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假设的辩证法,属于现实和法则的领域。进入游戏,就是进入一个义务的礼仪体系,其强度来自它的秘传形式——绝对不会来自某种自由的效果,不会像我们一厢情愿所想的那样,通过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斜视效果,处处将目光偏向那个幸福与享受的、唯一“自然的”源泉。
游戏的唯一原则,就是规则的选择助你从法则中解脱并走向规则,然而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当作普遍真理。
规则没有心理学或形而上学的根基,也没有信仰的根基。一条规则,谈不上相信它或不相信它——人们只是遵守它而已。这种信仰的模糊领域,对覆盖整个现实的信誉的要求,都被汽化在游戏中——于是便有了非道德性:做下去但并不相信它,约定符号和无根基规则的直接迷惑在其中大放异彩。
债务也一笔勾销:这里不能赎买任何东西,不能与过去结算任何账目。出于同一原因,可能与不可能的辩证法也与规则毫不相干:与未来也不能结算任何账目。没有任何“可能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在其中游戏,一切都在其中解决,没有交换方法,没有希望,一切都在即时的逻辑中,毫不留情。因此人们不会围着扑克牌桌嬉笑,因为游戏的规则是冷的,然而并不从容不迫,而没有希望的游戏永远也不会是诲淫的,永远也不会取笑什么。游戏肯定要比生活更为严肃,这在以下反常事实中可见一斑,即生活可以成为游戏的赌注。
游戏并不怎么建立在原则之上,正像它不怎么建立在现实原则上一样。其原动力就是规则的迷惑力,由规则划定的范围的魔力——然而这个范围完全不是幻想的范围或消遣的范围,而是另一个逻辑的范围,人为的和入门的逻辑,生与死的自然决定在其中消失的逻辑。这便是游戏的独特性,这便是它的赌注——想把它废除在经济逻辑内将是徒劳之举,因为经济逻辑参照于有意识的投资,或废除在欲望逻辑中也是徒劳,因为欲望逻辑参照于一种无意识的赌注。有意识或无意识:这种双重决定将对意义和法则领域产生价值,而对规则和游戏领域则不产生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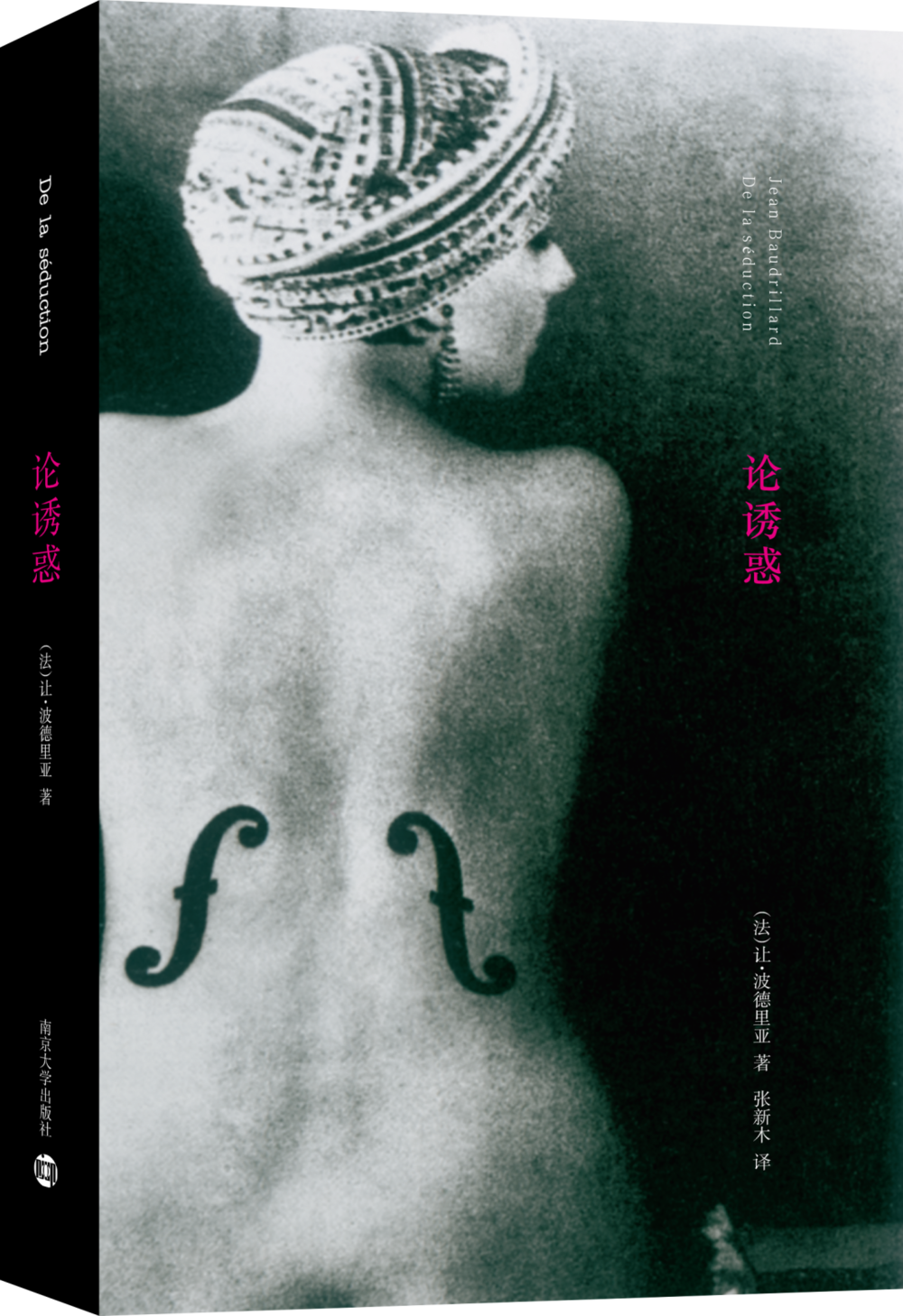
(法)让· 鲍德里亚 著
张新木 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 (ID:njupress),内容节选自《论诱惑》,作者:让· 鲍德里亚,翻译:张新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