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泛滥成灾,“传播过头”了。一个中世纪的虔诚教徒一生才听3000次布道,而如今一个普通美国人一生要接触700万个广告。
让一些人服从另一些人,离不开心理操纵。因而可以想见,宣传的历史源远流长。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独立作家西闪,以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出发,思考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关系。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用视角的新奇治愈习惯的慵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 (ID:njupress),本文节选自《巴黎综合征》,作者:西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马克·吐温说,当真相还在系鞋带,谎言已经跑遍了大半个地球。作家的话意蕴丰富,我试着展开一二。
谎言之所以比真相跑得快,一个原因如作家所说,那是由于真相要“系鞋带”,它在传播之时,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然而,仅凭光着脚丫抢跑,谎言就足以胜过真相吗?还是说,存在更多的理由?
表面上看,真相也好,谎言也罢,它们都是信息。而只要是信息,就得遵循信息传播的规律。可是,如果我们简单地以为,信息传播只是一个由传播渠道、媒介和传播代码构成的线性过程,那就错了。因为在信息接收与反馈的那一端,往往对应着一团奇异的神经细胞:人脑。
拜自然所赐,人类的大脑卓尔不群,但这个思维的器官绝非无所不能。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大自然对人脑的信息处理机制进行了“改造”,来应付环境的巨变。所谓系统1与系统2的区分就是这么来的。通常情况下,帮助我们处理信息的是快捷的系统1,它是自动化的、无需意识参与的低功耗模式。只有在复杂状况下,我们才会动用高功耗的完整模式,也即自主控制的、有意识参与的系统2。
毫无疑问,大自然的改造非常成功,使人类具备了高度的环境适应性。然而就像任何生物的演化一样,这种适应不是没有问题的,它导致人类成为过于倚重系统1而舍不得动用系统2的“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即便不算缺陷,这一认知功能的特点也更有利于谎言而非真相的传播,尤其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认为,与谎言一样,现代宣传的基础就是对“认知吝啬鬼”的充分利用。这只“鬼”在认知上的简单、懒惰、偏见、刻板、情绪化、自满以及自圆其说的天性,统统都是宣传最需要利用的东西。
当然,阿伦森并没有鲁莽地把宣传与谎言完全等同起来。但就像他指出的那样,宣传的目的不是为了信息接收者的利益,更不是为了传播真相或知识。这一关键点,把宣传与谎言捆在了一起,而使它和教育区别开来。事实上,阿伦森给宣传的定义很明确,就是娴熟地运用图像、标语及其他象征符号,作用于人类群体的偏见与情感的“心理操纵”。它是一种主导现代社会的大众劝导,宣传者利用这种方式,其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接受他的想法,还以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
或许是因为“执行力”“自控力”“影响力”等概念很有市场,阿伦森与安东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 Pratkanis)合著的Age of Propaganda(宣传时代)被中国的出版社翻译成了《宣传力》,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一本管理学或成功学的书。其实不然,作者重点讲的是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一种运作方式。这种方式有各种名称——宣传、营销、广告、公关、劝诫等等,实质上都是基于信息传播的心理操纵。
让一些人服从另一些人,离不开心理操纵。因而可以想见,宣传的历史源远流长。不过“宣传”(Propaganda)这个字眼出现得比较晚。1622年,针对宗教改革运动造成的人心浮动,罗马教皇创立了一个最高级别的宣教机构,名为“圣道传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即今天的万民福音部),首次用“Propaganda”来表达劝诫和教育的含义。在拉丁语中,这原本是一个农业术语,意思是播种或繁殖。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借汉语里原指政令传达宣布的“宣传”对译了“Propaganda”。当然,在新教徒看来,这可算不上褒义词。
直到近代,源自宗教的宣传概念才逐渐具有了政治含义,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的使用频率相当低。宣传一词在战争期间及之后盛行,本身就说明国家权力越来越强大的趋势。相较于传统的统治者,现代国家要对大众施以无远弗届的动员、管理和规训,没有宣传怎么行。
有意思的是,《宣传力》一书不认为1622年对于宣传有多么重要,反倒认定历史教科书上不怎么引人注目的1843年才是现代宣传的正式“生日”。因为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沃尔尼·帕尔梅(Volney Palmer)的年轻人在费城开设了第一家广告代理公司。作者似乎在暗示,当褒贬不一的“宣传”被中性十足的“广告”代替,真正的宣传时代才拉开了大幕。这让我想起刘海龙在《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里说的话:“从宗教到政治再到商业,宣传概念的含义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的转移。”
连著名的广告人阿尔·里斯(Al Ries)也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泛滥成灾,“传播过头”了。一个中世纪的虔诚教徒一生才听3000次布道,而如今一个普通美国人一生要接触700万个广告。还有一则新闻值得一提:《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2016年年度词汇,这个词的使用率比2015年增长了2000%。所谓“后真相”,难道不就是谎言的委婉说法吗?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讲的那样,《宣传力》的重点不在罗列种种宣传现象,而在于揭示宣传中最紧要的一环:受众心理。因为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发现,谎言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接收者收到信息时的心中所想。而那些人当时的想法,就“认知吝啬鬼”的特征而言,原则上是可以把握的:大脑有限的认知能力使得我们在处理信息时偏爱直觉、依赖经验,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包装得圆满合理。只要围绕这些东西做文章,宣传既不神秘,也非难事。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宣传)的效果在极大程度上必须瞄准情感,而只有非常有限的部分针对所谓的智力。我们必须避免对公众智力有过高要求。大众的接受能力十分有限,他们的智商很低,但是他们极其容易遗忘。基于这些事实,所有有效的宣传必须被限制为少数观点,并且必须对这些标语反反复复老调重弹,直到公众的最后一个成员都参悟到你通过口号想让他明白的东西。”虽然手段有些过时,但希特勒显然很早就明白,谎言必须利用人脑才能起作用。
《宣传力》细致地揭示了谎言赛过真相的理由,可是就像作者哀叹的那样,欺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和资源去一一揭穿。怎样抵御谎言,如何警惕宣传?300多页的书,只拿出了十几页来讨论,这实在太单薄了。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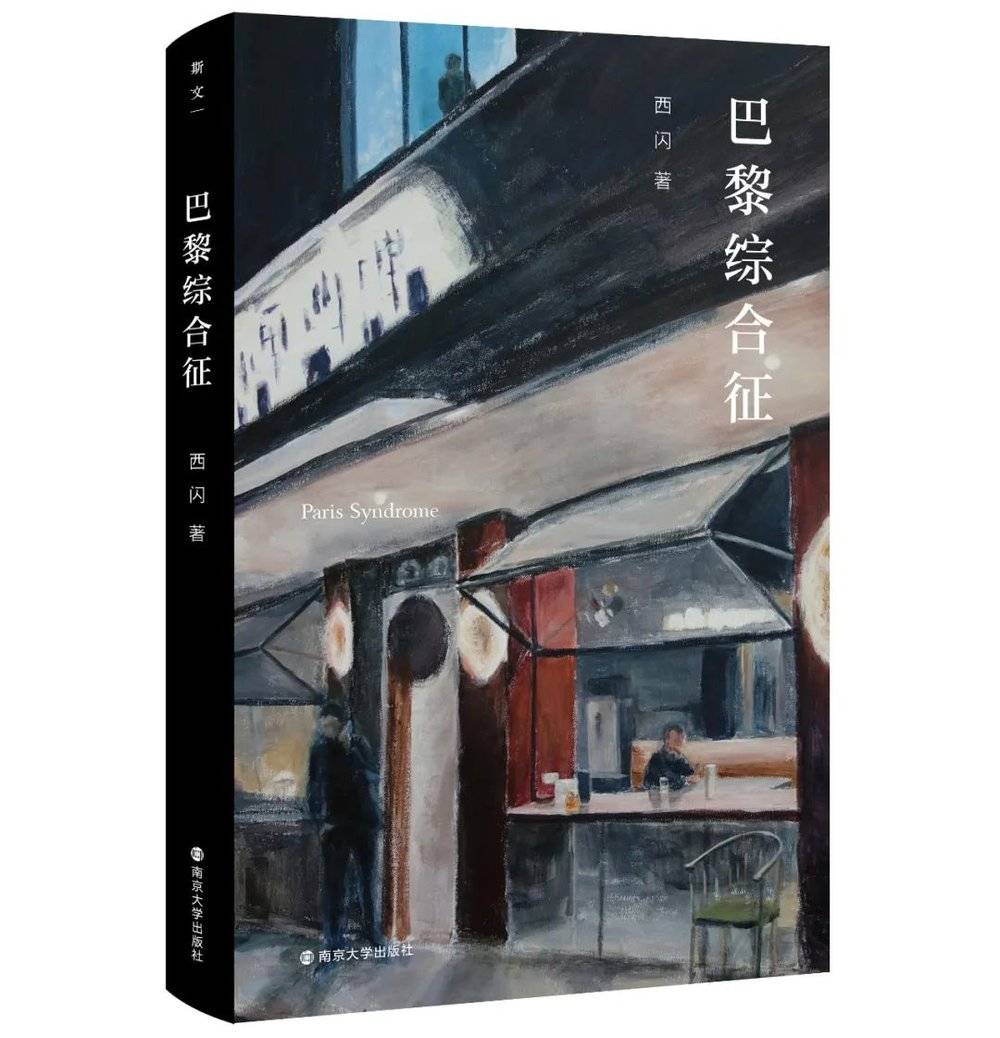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 (ID:njupress),本文节选自《巴黎综合征》,作者:西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