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作者:李亚楠,原文标题:《我迷恋火车,就像男孩爱上挖掘机》,头图来自:李亚楠
关于火车,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那就难免落俗的从小时候说起。
我出生于1988年。这一年,中国铁道部与苏联签订贸易协议,引进8G型电力机车,共计100台,全部配属于山西太原铁路局。对于我生长的这个北方重工业城市来说,火车的历史比我年长了许多。我爸爸就在这样被规划好的城市里过着一种看似也被规划好的工厂里工作。不过作为工厂的采购,他在90年代能到处出差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
我对火车的情愫也从90年代初开始的。由于爸爸的工作,我们经常要去火车站接送他。我家一直在太原的迎泽大街边上,太原站横卧在迎泽大街东端的尽头,坐1路公交车经过五一广场之后,通过那个缓缓的上坡就能看到太原站的全貌。小时候,这座火车站在我眼里很辉煌,具有苏联味道的对称建筑物给人以威严感,不容辩说的严肃,两座钟楼在整点会播放《东方红》的音乐,伴随着敲钟声在城市里弥散开来。
很多次我都是这样在1路公交车上远望着太原站,送爸爸去坐火车。那些我没有听说过的目的地,在心里统称为远方。
那时我年龄太小,对火车没有一个整体的清晰概念,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车厢的连接处,爸爸抱着我,灯光昏暗,斑驳的绿色油漆布满这个拥有圆角方窗的狭小空间,到处都是金属硬朗的线条。这个“铁房间”容易让人遐想,他会带着爸爸消失在视野里,又在某一天,带着爸爸回来,手里拿着远方买回的玩具。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去火车站看火车。
只要有亲戚朋友来太原或者离开,我都想去火车站送他们,只想多看看那个绿色的“铁房间”。新疆的亲戚有时会从遥远的阿克苏来太原,他们一路转车数次,历经几天几夜才能到,我对于那些遥远耗时的旅途没有共鸣,只是更喜欢他们带来的葡萄干,那是我从未吃过的美好。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绿色的神奇“铁房间”带来的葡萄干。
3岁时,爸爸说一定会带我坐一次火车,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全家人选择了青岛作为目的地。对于青岛的栈桥、大海,我现在已经没有一点记忆。那趟旅途只有两个画面至今清晰:第一个画面是在摇曳的夜晚,火车不再晃动,停在了一个低矮的站台上,车窗看外面的世界总是被框选,我躺在床上,只能看到外面有一个黝黑的水塔,水塔下面有一个白炽灯在夜晚晃动,特别明亮。车厢内传来列车员的声音:“石家庄”。
过去的太原交通不便,出省道路单一,我们被太行山、吕梁山紧紧包裹,对于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虽然那条通往石家庄的铁路已经修建了将近一百年,我却是第一次“出省”。这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可对于我来说还很朦胧,只有那盏晃动的白炽灯在我心目中一直代表着“石家庄”。
第二个画面是在青岛的招待所里,两张铺着白色床单的窄床。爸爸用白色的搪瓷缸给我泡了一缸清汤寡水的方便面。
我有一个姑姑住在太原市内一座通往工厂的铁路线旁边,每次去她家的乐趣就是跑到阳台看火车。火车来的时候很是张扬,地动天摇的,带着些许跋扈和笨拙,晃晃荡荡的走来。阳台上很快被火车吐出的白色蒸汽遮蔽,尤其是冬天,蒸汽在空中肆意的飘荡变化着形态,阳光从缝隙中在墙上快速播放着灵动的光影。
上初中时,我喜欢偷偷跑去太原站周边看火车,和我初中最好的哥们儿,俩人骑上自行车,从太原站旁边的小路绕到站台上,看着一趟一趟火车离开又到达。我们都是那个年代“被家里寄予厚望”的北方重工业城市出生的孩子,除了学习,几乎不允许有“课外时间”,不允许一个不正当的爱好。喜欢火车就是不正当的爱好,课余时间在城市乱窜,就是“二溜子”,一种没有希望的人,所以我们只能偷偷去看火车。也许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压抑”,我反而更珍稀每次看火车的短暂时光。
我那时熟知太原的每一次列车,那些让我陌生的城市名字也逐渐熟悉了起来,只是对于它们的样貌我还一无所知,脑子里盘算着,终有一天我会看清那些城市的样子,不再是车厢水牌上几个干瘪的文字。
到了高中,因为厌烦课业,我经常在晚自习前休息的那一小时骑车到铁路边看火车。当时就只是觉得轻松,看上一两次列车从面前经过,觉得生活很真实。那时除了绘画和看火车,我觉得没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有一次学校运动会,我叫了几个哥们儿骑车去太原南部25公里的小城榆次,在榆次站前合影。班主任一个电话通知了家长,说我逃学,到家迎接我的就是一顿毒打。第二天班主任问我为什么要骑车去榆次,我说为了运动,他说想运动就要发挥在运动场上,我说运动场上没有骑自行车这个项目。其实我至今都挺恨他。
逃学、早恋,伴随着整个高中,我是家长眼中没希望的孩子,破罐子破摔。初恋和我不在一个学校,我也不去找她,有空都去看火车了。但某一天她和我说,她们学校有一个男孩也喜欢火车,我不为所动,心里觉得这么奇怪的爱好不会再有别人。但还是在某个契机,终于在她们学校见到了这个朋友,从此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可能的世界,原来全国有这么多人同样喜欢火车,他们还建立了bbs,在上面发帖子,分享全国各地的火车。
我曾经多么羡慕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局这些客流量巨大的铁路局,有那么多我没见过的火车,有那么多我光听名字就激动的目的地。我仿佛进入一张如饥似渴的大网之中,疯狂汲取和填补我在火车知识上的未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这种爱好叫做“火车迷”。
然后我离开了太原,终于出了省,终于离开了父母,那些火车水牌上我不曾知道样貌的城市,我没有走过的铁路线,都在我可以掌握的世界里了。大一时我带着女朋友去南京长江北边的浦口火车站瞎溜达,那是一座民国时的老火车站,在没有南京长江大桥时,火车过长江要在浦口站登渡船,再去江对面的下关站(现南京西站)继续去往上海。后来浦口站废弃了,只停一些没人搭理的破车皮。站台上的梧桐树是这里的标志,秋天会铺落叶。直到现在她都拿这事儿茬我,只会带姑娘去看火车。
大学时真是我看火车的“黄金时代”。我走遍了全国能通达铁路的所有省份。在嘉峪关的西郊荒山上,向西远眺兰新线(兰州-乌鲁木齐),荒漠上一辆DF11(东风11型内燃机车)拖着后面的车厢缓缓驶来,我仿佛一眼可以看到河西走廊的末端,可以看到荒芜戈壁滩背后的新疆。我激动地向新疆方向大喊,直到深夜才跳上一辆去往哈密的列车,在寒冬中开启未知。
那时的身体真硬朗,去拉萨都是一趟一趟硬座车扛过去,几十个小时不在话下。我的铁路类论坛一直使用的ID是T166,那是2010年代上海去拉萨的火车车次。只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如今这些火车迷的bbs都无力支撑或已消失。
我曾坐T28次从拉萨一路去往北京,身上只有10块钱,在漫长的硬座上熬了几十个小时,停靠在西安已是夜晚,有种走出西部、进入大城市的期待感。那时的西安站还是老站台,低矮昏暗,站台上有贩卖食物的小推车。再熬一晚就到北京了,可是饥饿难耐。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花5块钱买了一根可能被苏丹红染过色的鸡腿,另5块买了一瓶山寨的百事达可乐,“达”字写得特别小。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却填饱了肚子。
然后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老旧的铁路全部被翻新了一遍,为高铁动车新建的铁路线不再沿着地形蜿蜒,而是嚣张地在山间打洞,在平原上架桥。速度越来越快,火车站却越修越远。过去面对面的座位已经被规律的前进方向禁锢,火车上没有了天南海北的交谈,听外地的奇闻异事,人们早已习惯沉浸在自己的手机屏幕里。
我还记得大学时和哥们儿从成都坐火车出来,30多个小时的火车上没带烟,我俩就在那儿瞎扯艺术,对面坐着的兄弟听得提起了兴趣,从行李中拿出一条烟,我和哥们儿相视一笑,烟解决了。如今的火车站过于统一,没有了乱糟糟的小贩,没有了那些看起来很地下的行业。烟火气远离了火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因此疏远,缺少了某种能让人遐想的邂逅和文艺气息的暧昧,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和流程化的快速步伐。火车站也不再售卖站台票,站台上挥手告别的场景早已被拒之门外,铁路线全部被铁网高墙封闭,火车彻底成了一个孤立的世界。
这并没什么对错,只是远离了属于我的火车时代。
而后,我坐火车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经常被飞机取代。那些我羡慕的水牌上的城市名字都被电子显示屏毫无感情的展示着,那些城市的样貌我也看腻了。我甚至也坐过了很多发达或落后国家的铁路,但再也无法与我产生共鸣。
我对火车的喜爱已停留在过去。那一列列需要机车牵引的火车,行走在与山川河流关系亲密的铁路线上,外面的现实世界被带圆角的方形车窗框选,既真实又不那么写实,带着某种属于火车的特质。深夜里最感动我的画面,仍然是空旷深邃的黑色里,一列在地平线上飘过的亮着灯光的方窗。普通火车很土,很旧,但它们如同我曾路过的一个东北小站的名字——“一面坡北”,土得带有大地的气息,带有深沉的诗意。
于是我开始在各种工作出差的间隙,用一套老旧的645去拍摄我儿时印象中的普通火车,去走我还未走过的老铁路线。时隔这么多年,我又开始拍火车了。那些火车是可以带着爸爸离开又回来的普通火车,是停靠在小村庄和城市中心火车站的火车,人们可以为之动情,可以驻足停留的普通火车。我想重新捕捉到我第一次坐火车时,一盏白炽灯就代表了石家庄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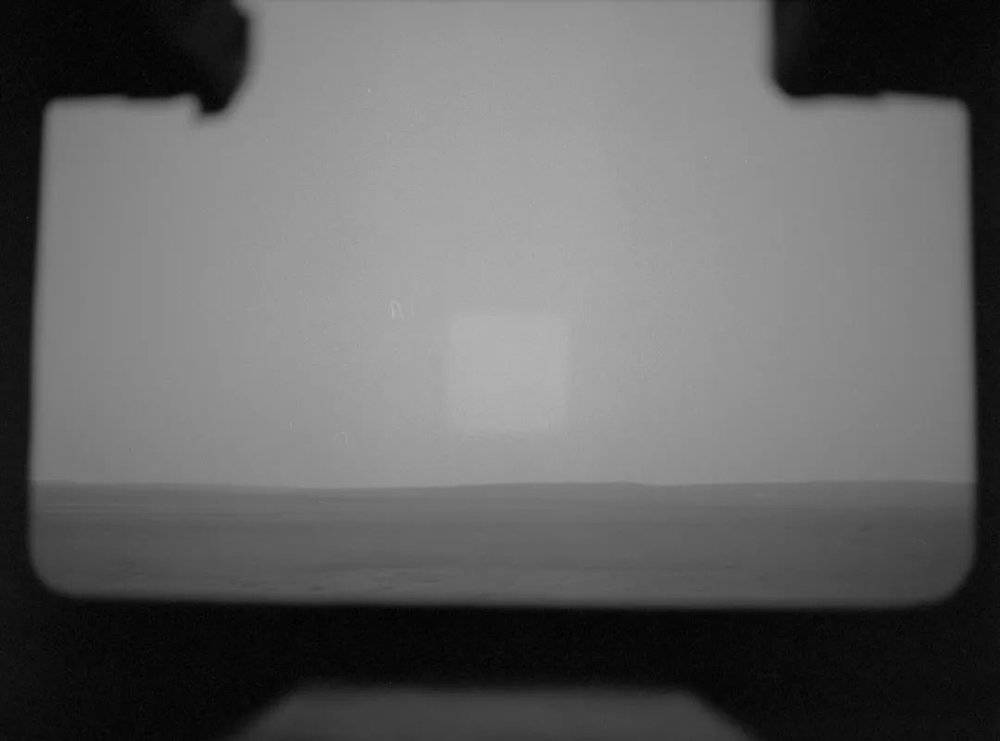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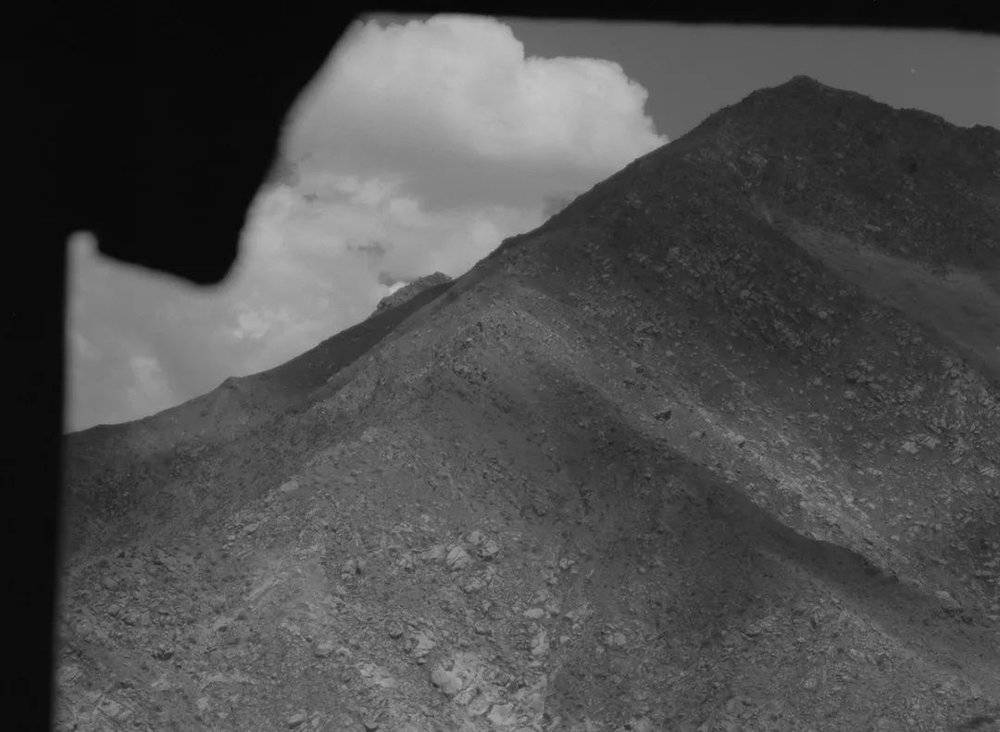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作者:李亚楠(自由摄影师,艺术爱好者),图片:李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