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作者:[日]广松涉,翻译:邓习议,导语:南大社,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区别四周的存在和我们自身的身体,同时自在地理解这种身体的自己寄寓着所谓精神的自我。
“外物-身体-精神”这种三分地区别的构图,可以说有着前近代泛灵论的世界观的背景,进一步来看,恐怕还有着太古以来的“世界像”分节的根基。
对于日常的、实用的意识生活而言,不用说,不可能真正放弃这一构图。但是,其中隐藏着某种重大的陷阱,由于从存在上截断外物和身体、身体和精神(意识)而产生一系列悖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必须首先自为地重新把握这当中的事情,试行“既成观念的批判”。
《世界交互主体的存在结构 》是广松涉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意义》(两卷本)的入门书或精华本,在批判“主体-客体”的传统二元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其自身具有原创性的关系性认识论。书中,广松涉对其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代表性理论如“四肢结构论”和“交互主体性论”做了初步构建和基本阐述,同时也包含其关系主义和物象化论的理论精髓。
以下为节选自《世界交互主体的存在结构 》的内容。
这里,也不打算能专题性地讨论“自己”(自分)与“他人”(他人)的关系,只想考察“他人的身体”问题,确认身体的自我的存在样态。通过这一作业,我们当能开拓“身—心”问题的新视座。
众所周知,在日常意识中,人们一开始原本就将自己和他人从存在上加以截断地理解,倾向将“自我”和“他我”的关系表现为单子性的两个实体的关系。只要是以这种既成观念为公理的大前提,就必将产生“哲学上”的一系列无理难题。然而,不管从中产生怎样的难题,倘若自他的单一的截断合乎真相,我们就不能随意地排斥它。实态又是怎样呢?
当从发生论来看时,新生儿恐怕不存在以皮肤为界的自我,身体的自我每次或膨胀或收缩,被推测为向来放大至不定形的母亲的身体(乳房或手等)。他通过摇动手脚或头脑,以及发出哭声,而摇动放大的身体肢,即乳房或大手等。虽说脐带已被切断,但从第三者来说,新生儿与母体是相融合的,犹如畸形的连体双胞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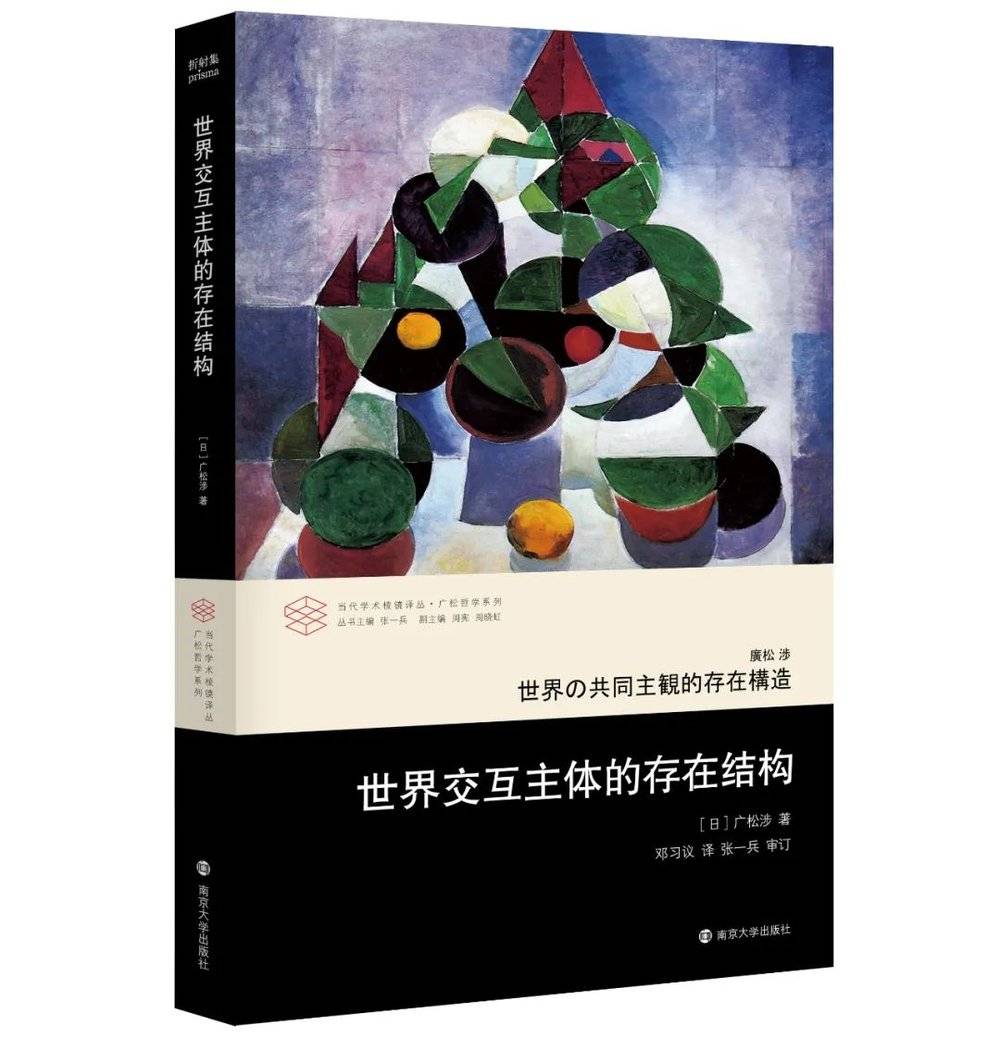
(日)广松涉 著
邓习议 译 张一兵 审订
当这样来论述时想必马上有人反驳。这岂不是对认识与存在的混同?“新生儿不过是尚未自我觉醒,不知道自己身体的限界,作为存在来说他已是独立的主体”,云云。论者们或许还会补充说,“母亲也许确实移情地与小孩产生共鸣,但是,那终究是母亲的意识,不是小孩的意识”,云云。——这种反驳,不过是“自我是以皮肤为界的自我完结的存在”这一既成观念的另一种说法。不过,因为我们正是要尝试重新探讨该教条,这里不必直接收回前面的观点。为了联系实态进行反批判,我想再稍微提示一下我们的见解。
连体双胞胎式的存在方式决不限于新生儿。例如,当管弦乐队的指挥者自在地指挥众多的演奏者、乐器时,对他来说,在前一小节所述意义上,可以说乃至演奏者们的身体和乐器都成为他身体的自我的分肢。他“体感”着小提琴的音色、鼓的声音。
这一点,不光是指挥者,对于每个乐团成员也都可以这么说。通过各人直接分担的演奏,通过指挥棒、通过声音(类似于新生儿以哭声操纵乳房这一“分肢”)而操纵他的乐手。当中展开的演奏者的世界,形成放大的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的一体系。在那里看不见“自我-他我”(自我-他我)的自为的区别。那是浑然一体的一种能知=所知(能知-所知)。
这种“协存体”当然具有其内部透视性的结构。并且,乐手有着各自不同的透视。对第一小提琴来说,敲鼓手在左后方,对鼓手来说,小提琴手在右前方。但是,包含这种透视的差异的情况,并不能导出自我否定连体双胞胎式的结合体这一情况。连体双胞胎中哥哥所具有的知觉的透视与弟弟具有的知觉的透视是有差异的。哥哥右手感到刺痛,不是说转移到弟弟的右手,而是终究从场所,即从弟弟一侧来说位于左后方的第三只手所感受到的吧。哥哥和弟弟其知觉的现存样态,是各不相同的。当哥哥闭上眼睛时,虽然弟弟感知到哥哥闭上了眼睛,但弟弟的视野不可能消失了。
这样,兄弟各自占有对知觉地现存的世界的透视的特殊位置。在管弦乐演奏者的情形中,在结构上也与此类似。管弦乐当然不是肉体的单一主体。但是,通过奏音(空气振动),同时通过指挥棒的运动(反射光线),队员进行着生理、物理的接合,如果说听诊器或眼镜作为身体的自我的构成因而被承认,那么即使神经纤维并非直接连接,也仍应允许主张连体双胞胎式的“合一体”这一情况。就此而言,管弦乐中队员们的存在方式,从一般化来说,关于“协存体”的存在方式,我们主张推及连体双胞胎式的存在结构。
但是,人们通常并非合唱或合奏。连体双胞胎式或珊瑚类的协存体,对人类存在来说难道不是例外的存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进行探讨,这里我想回应前面遗留的可能“反驳”。
抱持既成观念的论者主张,我们所谓的“连体双胞胎式的存在方式”,不过是自我意识的缺乏态或移情的忘我状态。为了明确论点,让我们假设如下场面。带小孩的女性受到拷问。现在在她面前,正要用火筷子去烫小孩的手。当看到火筷子接触小孩的手的瞬间,她感到手一阵剧痛,而不由得将手缩回去。生理学家也许会说“那不过是幻觉”。
但是,在她看来,感到剧痛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反思性地来看,虽然所感觉的地方是自己的手,但确实是小孩的手被摁住的那个位置。作为肉体的手即使被反绑在后面,但她的身体的自我的“手”却延伸到小孩的手的地方,并在那个位置感觉到剧痛。
当然,她的手和小孩的手,的确并非合体的。小孩感到的疼痛和她感到的疼痛有着不同的视角。明确地说,当看到火筷子碰触到的时候,较之于小孩的疼痛,母亲感到的疼痛更为剧烈吧。总之,她俨然感到在自己小孩的手的地方,并感受到自己小孩的(手的)疼痛这一意识事实。

生理学家的“不过是幻觉”这种批评,不能推翻这一“现象学的意识事实”。这时,我们要铭记的是,在小孩的手(的位置)中感到疼痛的事实。若是看到火筷子碰触石头、插入火盆的情景,便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正因为她的身体的自我放大、延伸到小孩的地方而成为连体双胞胎式的“结合体”才感受到小孩的手的疼痛。
如前所述,我们并不主张那是小孩感到的疼痛本身。即使连体双胞胎哥哥和弟弟的知觉的透视的也有不同,同样地,她和小孩的疼痛的透视(在扩大单纯的空间的象征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是不同的。但是,在她与小孩分开的场合,即在小孩不在她的身体的自我的扩张范围的场合,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东西,只有在她与小孩的“连体双胞胎式的结合态”的场合,才是在此意义上的透视中而感受到的东西。
论者作为事实而承认的充其量是“那种感觉到的事实”吧。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若暂且承认这种事实的话,后面则是“花见劫”(围棋术语。指对己方胜负而言无关痛痒,但对对方来说攸关生死。故己方尽可以赏花的心情打劫)。
论者们说“那实际上不过是幻觉”。从“常识”的生理学家之流的标准来看,也许确实如此。在论者们看来,由于上例的女性并未被给予与痛觉相对应的物理刺激,她应该不会感受到真正的痛觉。因此,她主观上感受到的痛觉不过是幻觉吧。以论者们的作风来说,当头脑受到电子冲击而感受到的色彩感觉或音响感觉也是幻觉。因为“适应刺激”的光或声音并不存在。
同时,用一只眼睛看风景也有远近感,用一只耳朵听声音也有方向感,这也是幻觉!因为单眼的感觉不明远近,单耳不明方向。在论者们看来,那是混入了记忆的想象(幻想)的幻觉吧。然而,若是采用那种讨论,一般被称作“感觉”的东西就几乎全部成了幻觉。实际上,若根据眼睛的光学的结构来看,外界的正立看法恰恰是幻觉!无需援用格式塔心理学便可知,刺激和感觉一对一的恒常对应性原本就并不成立。因此,“不过是幻觉”这一论者们的指责,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的观点。
我们当然也在“日常的意义”上承认感觉与幻觉的区别。通常,视觉上的光刺激的辐辏体,听觉上的音源体,触觉上的接触性刺激体现实地赋予皮肤的身体,包括但不限于人们的动物,由于该对应性,便以感觉为指针处理身体。因此,外在刺激物与感觉的身体的区别变得重要,设定准概念化的抽象的“身体图式”,感性的体验就被看作在这一准皮肤的身体的内部自我完结。
但是,“通常”发现的对应性,是指概率大,而并非“必定总是”。因此,在无法发现对皮肤的身体的外在刺激的直接对应性的场合,便习惯于将其当作“幻觉”来处理。但是,这即使是“生物体的自然的智慧”,从原理上说,也不过是权宜的处理方式。
所谓“真正的感觉”与错觉、幻觉的区别,在机械论的“刺激—接受”这一维度原本是无法规定的,后来即使以此为第二性的分类的前梯,也不得不首先定位于当事人的意识实态。基于这种原因,我们从原理的场面拒斥论者们的批判。
这样,我们是在承认与所谓“幻肢”的感觉(即被切断手腕或脚的伤病者所感受到的“手”或“脚”的感觉)同样的权利中,在放大、延伸至他人肉体的场所的身体的自我,在这种连体双胞胎式的“身体图式”中立论能知的所知=所知的能知。
那么,自己与他人的区别,以及能知的主体与所知的对象的区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区别并不是自己的身体与外部的存在的简单的物体性区别。因此,为了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阐述——在当前的问题维度能够言及的范围内——被人们称作“精神的自我”的东西。
(节选自《世界交互主体的存在结构 》,有删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ID:njupress),作者:[日]广松涉,翻译:邓习议,导语:南大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