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林小溪、梁振,原文标题:《当“敬老”变成“恐老”:我们如何应对衰老和死亡?》,头图来自:受访者供图
68 岁的陆晓娅第一次感到衰老的残酷,是在妈妈身上。
她的妈妈年轻时曾是新华社的驻外记者,法语很好,离休时还和朋友一同编过一本法汉词典。但在妈妈 77 岁那年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后,陆晓娅再和她聊起熟悉的巴黎,妈妈的回答已经令人啼笑皆非。
-“巴黎你最喜欢什么地方啊?”
-“睡觉。”
-“你喜欢日内瓦还是巴黎?”
-“第一次嘛,大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为了照顾妈妈,2013 年, 60 岁的陆晓娅从自己一手创办的公益组织中第二次退休。
她一直是一个对生命满怀热情的人,退休那天,还请来了职业生涯规划师帮自己规划日后的生活。她还想去讲课,去旅行,去写作,但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而一度陷入停滞。
2021 年 1 月,她的《给妈妈当妈妈》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她分享了陪护妈妈的经历和心得,她写,“我怕的其实不是陪着老妈,而是怕‘耗着’,什么也不做地耗着,让时间,宝贵的时间,宝贵的生命,就这么一点点地耗尽。”
在这本书里,陆晓娅如此鲜活和真实,她的挣扎和抵御也清晰可见。她写自己不惧怕容貌衰老,但恐惧精神和心智的荒芜;她讲自己不避讳谈论死亡,但面对母亲一步步走向死亡,却又难以做任何决断。
这本书不仅仅是陆晓娅的故事,字里行间的,是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从“敬老”到“恐老”
陆晓娅曾经在养老院里遇到过一位年轻的姑娘,静静地低着头划着手机,这是来养老院实习的大学生。陆晓娅好奇地询问她学的专业,得知是“老年照护”。但姑娘紧接着便补了一句:“毕业了我不会干这个的,毕竟……太残酷了吧!”
姑娘的话让陆晓娅的心中翻腾,“残酷”的背后便是当今社会上对老人普遍的看法:衰弱、疾病缠身、被死亡的阴影笼罩。
但老人的形象并非一开始便是如此。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是智慧、经验与成熟的象征,备受尊崇。在古希腊,五十岁以上才能成为陪审团的一员。罗马元老院“Senate”一词源自代表老年的“senex”。十七世纪的欧洲男人会为了看起来老些,戴上撒了白色粉末的假发。
在推崇孝道、以老为尊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老”更是代表了对一个人最高的敬意和肯定。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学家 Stevan Harrell 在中国香港采访一位老年女性时,出于恭维,猜测对方年龄时故意说小了十岁。但出乎他意料,老人并没有感到被讨好,先是嘲笑了他的观察力不行,又自豪地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年龄。
在 Stevan Harrell 的调查中,年纪越大的老人,在说出年龄时会感到越自豪。在他们看来,老年是一个人在结束了一辈子的辛劳工作后,终于可以“享福”并获得晚辈们爱戴的时候。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由“敬老”转向了“恐老”呢?
敬老文化的瓦解源于社会形态的改变。美国学者理查德·A·波斯纳在《衰老与老龄》给出了他的答案。
在无文字或以农业为主的“静止社会”中,老人的记忆和经验弥足珍贵,因而地位更高;而在走向现代性的“动态社会”中,老人的社会价值大大降低了:工业劳动对体力的要求,是老人无法达到的;大众教育降低了老人记忆与经验的价值;医学的进步虽然延长了人的生命,但也增加了抚养比,养老的压力也随之加大了。
除此之外,医疗进步导致的“老年病理化”,也是“恐老症”产生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以后,受医学革命的影响,看待老年的方式开始大大转变。将“老化”看作是人类自然生理状态的想法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老年系医学问题”的观点,而且人们认为,这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
1951 年,“高龄死亡”从美国的死亡证明书上删除,从此没有人能因年老而死。这样的做法无疑促成了老年的病理化。
而现代医疗和卫生观念确立的“健康”和“洁净”的规范,也让老化的、衰弱的身体被异常化,遭到隔离、排斥和贬低。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 年,上海曾爆发过一起当地居民抵制在小区内建养老院的新闻。业主担心房价会因此下跌、老人会给小区居民带来公共卫生的风险,甚至拉出了“死人院滚出小区”的横幅,规划中的养老项目因此停工。
此类事件近年来在深圳、杭州等较发达的城市中屡有发生,老人成了“危险”“晦气”和“死亡”的象征,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不怕老,又怕老
年过六十的陆晓娅从不惧怕容貌的衰老。
55 岁退休的第一天,她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染发。
在人类学家看来,头发的颜色可以传达特定的印象和信息。商家们早就学会了利用人们的年龄焦虑来宣传染发。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染发刚开始进入日常生活中时,法国欧莱雅兜售的染发剂广告图上便写着:“再无白发,永远三十岁(Not one more white hair ; forever 30 years old)”。
在陆晓娅这个年纪,通过染发来遮掩白发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朋友们互相交流哪一款植物染发剂好用,苦口婆心地劝她:“你不能放弃自己”,希望陆晓娅能早些悔悟。但陆晓娅不肯妥协,在她看来,应该接受自然地老去。
有时候,很久不见的朋友突然见到陆晓娅,会惊叫起来:“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她便笑眯眯地说:“你多看两眼,多看两眼,看久了你就习惯了。”身边的一些朋友跟随她,慢慢也不再染发。陆晓娅感到高兴,觉得自己做了个好榜样。
身体上的衰老从未限制住陆晓娅,她对想做的事依然充满热忱。
《百岁人生》中关于人生阶段的看法,便是陆晓娅的写照:随着人的寿命变长,传统的三阶段人生(求学、工作、退休)将变成多阶段的人生,年龄不再与阶段挂钩,人的选择更加自由,一生可以从事不同的职业。
60 岁她第二次退休时,陆晓娅特意请来了职业生涯规划师,帮她一起规划退休生活。
规划师带她画下一棵大树,生长出四根树枝:一枝是照顾妈妈,一枝是讲课,一枝是旅行,还有一枝是写作。站在 60 岁的人生刻度上,这些都是她想做的事情。
去年秋天,她一个人去四川旅行,作为四川人,她把登上剑门关当作此次入蜀的一个仪式。那是一个湿淋淋的雨天,工作人员见她年事已高,劝她不要在雨天上天梯栈道。但她还是爬了上去,一路上没有遇到第二个人。她感慨有青山相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这个老太太也如是。”

看《乐队的夏天》,她爱上了摇滚乐,拉上同龄朋友一起跑去长沙参加草莓音乐节。在现场,她和年轻人们一起“躁起来”,为喜欢的“五条人”乐队欢呼。音乐节现场没有座位,她站着,从第一首歌听到了最后一首歌。年轻的小妹妹看她有趣,与她攀谈,甚至在音乐节结束后,还特意开车送她和朋友回旅店:“两个小老太太听摇滚很酷。”
怀着独自出国旅行的心愿,63 岁那年,她开始学习英语。现在已经看过了十本英文书,其中有小说,也有传记。她给自己定下了努力的目标:希望在 70 岁那年成为一名英文翻译。

但在母亲身上,陆晓娅还是看到了“衰老”的可怕。那是在人的容貌和身体之外的掠夺:心智的退化与精神的荒芜。
曾经对自己学习能力十分骄傲的母亲,生病之后,别说读书看报,连日常的交流都已经成为问题。随着病情的一步步加重,从不愿意听命于人的母亲,甚至要按照旁人的“指示”才能顺利完成吃饭、穿衣、上厕所这些最基本的日常事务。
老年的母亲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这是陆晓娅在想象自己老去时所难以接受的。
在《给妈妈当妈妈》中,她是这样描写自己恐惧的,“我不太在乎头发是否白了,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几条,但我真的在乎怎样‘活着’,害怕余下的人生成了所谓的‘垃圾时间’。”
可以谈论又难以谈论的“死亡”
在活着的时候谈论死亡,适当地引发“死亡焦虑”,是陆晓娅自我成长的一个工具。
52 岁那年,因为挚友的离开,她写下了人生的第一份遗嘱。自 60 岁起,每年生日,她都会重新修改一次遗嘱。
她觉得,“修改遗嘱的过程就是自我对话的过程。我会想,我到底能够活成一个什么样,我是谁。”遗嘱不光是为了交代后事,还在逼着她向死而生,对有限的人生进行规划。
正如她非常喜欢的一位心理治疗师,美国的欧文·亚隆所言:“有引导的直视死亡,而不是压抑那种恐惧,会让人生更加珍贵、更加深刻、更加有活力。这种走向死亡的方法为人生指明了方向,最终聚焦于如何减轻死亡恐惧以及如何识别并利用觉醒体验。”
2012 年,快 60 岁的陆晓娅在北师大第一次开生死课时,就把“不是减轻死亡焦虑,而是适度引发死亡焦虑”当作自己的授课目标。

在课上,她和学生们谈论自杀、丧葬、临终关怀和濒死体验。去年疫情期间,她给学生们写了一个问题清单,里面有 25 个问题,询问他们在疫情中的恐惧、家庭受到的影响以及是否在危机中得到成长。
有学生来信告诉她,上完她的生死课后,重新捡起了画笔;立即报名去学了架子鼓。她觉得这是她的课最大的肯定。
但是,她也发现,比起和年轻人谈论死亡时的自如,和老人谈论死亡,会是一件困难甚至被认为“不敬”的事情。
在陆晓娅妈妈居住的养老院中,许多老人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却连财产处置都没有文件安排。大家都在回避死亡这一件事,仿佛不提起便不会发生。一旦突然去世,留下来的问题就会非常复杂。
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如今在重症监护病房中,医生们可以使用各种高科技机器来延长病人的生命,干预死亡。何时“确认死亡”,成为了一件可以人为决定的事情。
人类学家莎伦·考夫曼表示,如今的“技术至上”已逐渐成为“道德至上”,病人家属把过多的医疗干预视为了道德上的一种必要。家属们在希望亲人实现没有太多医疗干预的“好死”、“尊严死”和不要亲人离去的想法中苦苦挣扎。
在《最好的告别》中,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认为,当生命接近终点时,“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这个角色无论对于逝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都是生命最重要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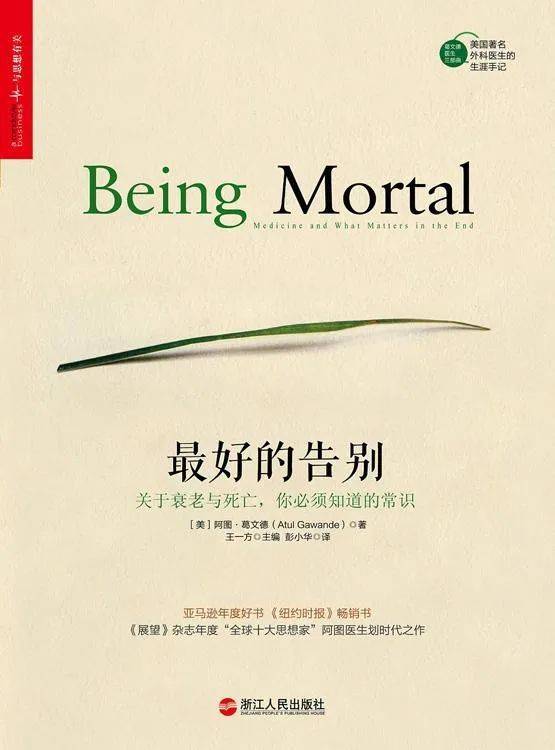
而程序化的医学治疗,则剥夺了临终病人的这种权利。许多老人在接受过多的医疗干预后还是去世了,甚至没有时间和家人说话道别。
在这样的反思下,生前预嘱(living will)被提出和推广。它指的是人们在清醒状态下签署的,对于生命末期的各种事项提前做出的选择。作为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理事,陆晓娅早就签署了这一文件。她希望在自己临终时,不要切开气管上呼吸机,不要进行心脏按压、输血,甚至包括较高级的抗生素,也不要开。
然而,在面临母亲走向死亡的问题上,多年从事生死教育的她依然感到非常困难。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会逐渐失去身体的机能。开始是忘记怎么吃饭,到晚期会忘记如何吞咽,怎么呼吸。如果介入医疗机器,也许可以再活两年。但也只能是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借助呼吸机和鼻饲管来维持生命,靠导尿管来帮助排便。到最后,身体会一点点地挛缩枯萎。
陆晓娅曾经无数次和弟弟妹妹商讨,当母亲进入阿尔茨海默症晚期,无法吞咽以后,他们该怎么办?要不要给妈妈插胃食管?是选择生命的质量,还是生命的长度?她甚至为此向国内外认识的老年科和缓和医疗领域的专家们咨询过不下五六次。他们一致的建议是:不要插。
作为子女,这是最难的一个选择。她有一位同龄的朋友,因为不忍看到高龄的父亲太过痛苦,最后同意撤下呼吸机。但在父亲去世后的两年里,他都感到非常自责,认为是自己杀死了父亲。
母亲是在 89 岁那年,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因为颈椎弯曲,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母亲都不能平躺,只能侧身而睡。但离世后,她的身体放松了许多,平静地安躺了下来,这让陆晓娅感到了些许宽慰。
她还觉得,某种程度上,妈妈帮助他们逃过了一些艰难的抉择。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周云译《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 (美)欧文·亚隆著,张亚译《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年。
[3] (美)阿图·葛文德著,彭小华译《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4] (英)安妮·卡普芙著,王方译《关于变老这件事》,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5] (英)琳达·格拉顿、(英)安德鲁·斯科特著,吴奕俊译《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
[6] 陆晓娅著《给妈妈当妈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
[7] 郇建立问,(美)莎伦·考夫曼答:《老龄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6 卷第 1 期。
[8] 吴心越:《“脆弱”的照顾:中国养老院中的身体、情感与伦理困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110 期。
[9] 陆晓娅:《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什么》,2020.5.21。
[10] 陆晓娅:《2020,打破幻觉之年》,2021.1.1。
[11] David I. Kertzer & Jennie Keith, Age & Anthropological The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林小溪、梁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