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去了,日本作家三浦紫苑的小说《编舟记》还在被改编、拍摄、讨论。今年2月,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编舟记~我要编纂辞典~》是它的第三次影视化,而早在2014年,电影版《编舟记》就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这个叙事里,日本影视界诚恳地表达了对一个“除了编辞典什么都不擅长”的人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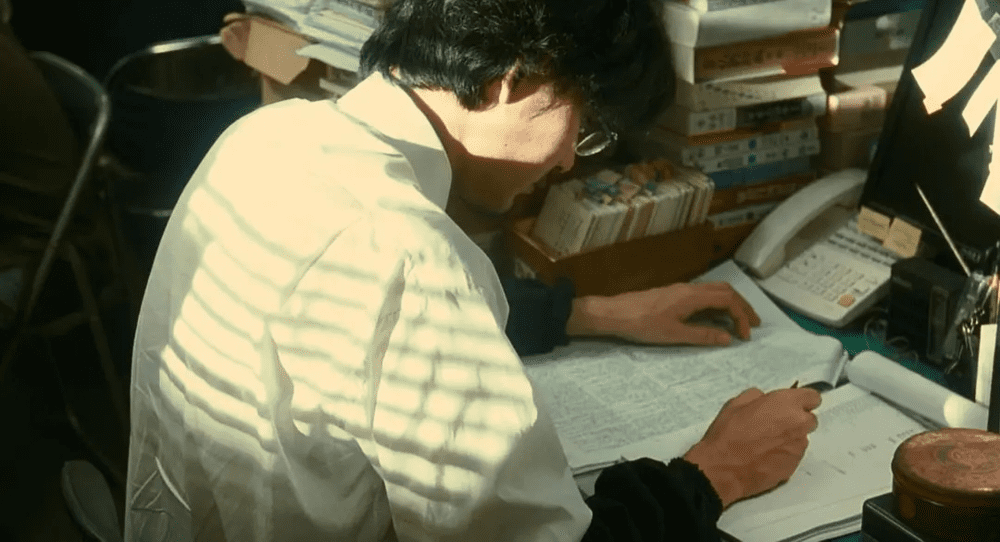
(图/电影《编舟记》)
反观中国,我们也有大量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着案头文字工作的人——中华书局编辑俞国林花13年时间整理历史学家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日记,南京图书馆原古籍部副主任、研究馆员沈燮元花18年时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但大众对他们感到陌生。
2013年,电影《编舟记》导演石井裕也在谈起编辑这个群体时,不由得对一种日式热血般的讲述感到焦虑,“都是一些像什么热情啦、爱啦、诚实啦这类容易给人一种假大空印象的词语”。
他们存在于纪录片里,一闪而过;谈到他们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尊敬,转头又不以为意地忘记。这个群体被捧上神坛、涂上玫瑰色的同时,面目也被涂抹了,被笼统地归入“搞文艺的”。
埋没他们,似乎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漫长的编辑部的故事
以辞典编辑为例,光是列举数字,就能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枯燥。
《日本国语大辞典》耗费十几年编成,有3000名工作者参与,收录了45万个词条;《言海》由大槻文彦投入一辈子的时间完成,他以一己之力编纂、收录了3.9万条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编舟记》中虚构的《大渡海》,包括马缔光也在内的4个编辑,共收录23万个词条,厚达2900多页。
但是,只要让一个辞典编辑从个人的角度解释某个字——比如什么叫“右”,他这整个人就变得出类拔萃起来了:
“如果解释为‘握笔和拿筷子的手’,则忽略了左撇子。也不能解释为‘没有心脏的一侧’,因为据说有人的心脏是生在右边的。那么,‘面向北方的时候,东方所在的一侧’这个解释比较妥当吧。”《编舟记》原著小说中写道。
他们翻页翻到指纹几乎被磨平,连东西都抓不稳。编辞典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方便读者查阅,还为着揪出辞典中长久以来存在的对于性别的僵硬视点。比如,岸边和宫本讨论“女”这个字的释义,发现旧辞典里采用的是“非男性的性别”这个说法,大失所望。他们觉得,需要考虑一下自我认知为女性的跨性别群体。
他们执拗到哪怕是拆掉那扇老掉牙的门,也自觉讽刺:“它凭什么被只工作了四五年的我卸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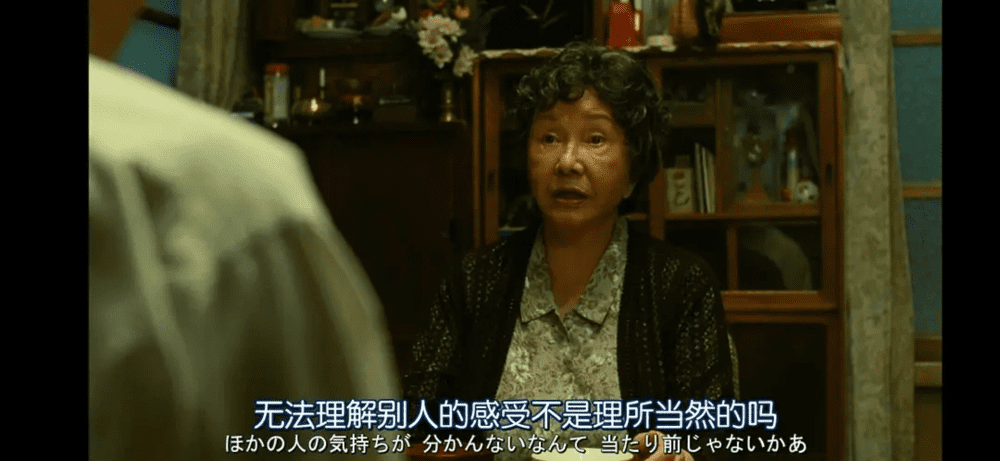
(图/电影《编舟记》)
《编舟记》是虚构的,但像男主角马缔光也这类人确实存在。比如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编辑陈欢欢,她在流行MSN和“偷菜”的年代就开始担任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作品《无尽的玩笑》的编辑工作,直到2023年3月,书才下印。眨眼间,12年就过去了。
这不是一个比编纂辞典轻松的活。《无尽的玩笑》长达100万字,共有267个人物,大量的生僻词、专业名词、俚语、自创新词藏在长句里,这些长句甚至需要抄在纸上演算,才能弄清其结构。在统改稿件时,陈欢欢得右手操作电脑,左手单手翻着几百上千页的稿件。
就像《编舟记》里戳破辞典长久以来偏男性的视点一样,陈欢欢也近乎偏执地钻到字词里:
比如,华莱士用一种叫“Kaopectate”的止泻药来形容天色和某人的脸色,她本以为是白色与粉色中的煞白,直到第969页,“房间窗光已经暗成了Kaopectate的颜色”,才发觉应该是粉色。
她几乎就像个辞典编辑一样努力了。比如,书中有“父亲本人”“妈妈们”这两个说法,译者原本把“妈妈们”译为“母亲大人”,以和“父亲本人”对应。但在七百多页时出现了“孩子们对他们母亲的叫法是‘妈妈们’。似乎她不止一个一样”这个表达,“母亲大人”无法体现“似乎她不止一个”,为了前后一致,于是陈欢欢把“母亲大人”全部统改为“妈妈们”。
所有人名都需要到原文中查到所在位置,再到译稿对应的位置进行统改,这些人名的出现次数,从几次到几百次不等。
只不过,我们很少能像《编舟记》那样,长篇地、惟妙惟肖地描摹陈欢欢们。
冷门的职人叙事
如果不是非常必要,人们几乎不会想起陈欢欢们。日本影视界对他们的态度则正相反。
日本人不厌其烦地拍摄坐冷板凳的各种群体,仔细数一下,有《编舟记》中的辞典编辑、《校阅女孩河野悦子》中的校对专员、《哪啊哪啊神去村》中的伐木工人、《Chef~三星级营养午餐~》中的小学供餐食堂师傅、《五个相扑的少年》中的相扑选手、《机器人大爷》中的电器公司职员,甚至还有《武士的家用账》中为武士敲打算盘的会计。
他们全都近在咫尺,却又不被注意,就像马缔光也一样,没什么存在感。可是,这样的剧集和角色,却奇异地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和收视率。
2009年,电影《入殓师》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电影讲述一个沉闷的职人,他的工作就是为遗体穿衣、刮脸、化妆、套上佛珠,借助这部电影,被疏忽的工种终于也有了曝光度和讨论度。
只有拍得内行,才敢叫职人剧。尤其是在日本,导演会放大每个工作者琐碎的事项。
比如《编舟记》中,辞典编辑部的一次会议,几个人在讨论“怃然”这个词。同事开玩笑说让西冈做个“怃然”的表情,荒木条件反射般,一股脑讲出其释义:“失落、失望、沮丧、因惊讶而愕然的样子”。
或者《入殓师》中,入殓师拿棉布净身,谨慎地刮脸,一手提着白布,擦拭时挡住皮肤,把逝去之人的僵硬的手拢到腹部,上粉底、涂口红、抬起遗体,当冰凉的药水触到手臂,本木雅弘扮演的男主角会打寒颤。
入殓师的镊子、剃须膏,辞典编辑的词例卡、袖套,在这些影视剧中几乎被当成一种审美对象加以叙述。就像纤维布料之于《内衣白领风云》、木材之于《哪啊哪啊神去村》、蔬菜之于《Chef~三星级营养午餐~》,以及纸张之于《编舟记》——辞典用纸的手感,既要随着手指的动作吸到指腹上,顺当地翻起,又不能一翻带起好几页。纸页必须像干透的砂,爽快地落下来。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日本有比其他民族更进步的分析品位和批评精神,声音、颜色、气味、质地一个不落,他们“有一整个宝库的词汇(拟态语)用来表达这些感受”。
有足够的词汇去触达,就意味着被重视。

(图/电影《编舟记》)
它不再是甜宠、婆媳、豪门等类型戏里的一个人设。诚实的职业剧,就该拍出长达14年的编辑过程是怎么完成的,或者关东煮怎么做、卖电器怎么吆喝、编审怎么一字一句地确认。
他们身后虽然没有权威的聚光灯,但也不至于彻底地失语。《编舟记》中有这样一段:
“就算资金匮乏,也不依靠国家出资,而是由出版社、由作为个人的我和你,孜孜不倦地编纂辞典。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为所有希望自由航行于词汇这片大海的人,打造一艘船。”
参考资料:
1.《纪录片<书海编舟记>对出版工作者的启示》,电影评介,曹洪刚,2020.7.30
2.《从电影<入殓师>解析日本职人文化》,传媒论坛,李雅菲,2019.5.25
3.《新世纪以来日本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当代电影,金卉,2016.3.1
4.《用12年的时间将大胆的设想变为现实》,文景,陈欢欢,2024.1.31
5.《从<编舟记>看平成年代的“职人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李忱,2016.7.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花淇心,编辑:谭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