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再次出现幻听。28日清晨,她在大衣口袋里塞进一块湿石头,自沉于她在英国萨塞克斯郡罗德梅尔村寓所附近的一条河流。
“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如此富裕,另一个性别群体却如此贫穷?”1928年,在英国第一所寄宿制女子学院做主题演讲时,伍尔夫抛下这个问题,背上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的“罪名”。
她拒绝接受曼彻斯特大学的荣誉学位,反击英国对妇女一贯的歧视,因为她深知,一个男性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仍会写下“论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的劣根性”这样的标题。
杀死女人的“劣根性”有多不容易?伍尔夫抵御着来自《蓓尔美尔公报》《星期六评论》《每日新闻》的含沙射影:有伤风化、狭隘、年老的感伤主义。她恨透了男性将女性指斥为“劣根”。

1902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男性学者曾霸占着伍尔夫的扶手椅,啰嗦长气,侃侃而谈,而她那句“男性天才无法忍受的冷漠,到了女性身上,全都变成了敌意”,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资源。
但是,伍尔夫不能仅仅被口号式地概括。
女性主义不等于伍尔夫
伍尔夫更倾向于“雌雄同体”,她反对文学笔法当中处处是女性主张。
比如,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强悍地进入男性文学圈,小说中布满了性别反叛意识,她在《简·爱》中控诉:“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阁楼上的疯女人”由此成为文学史上轰动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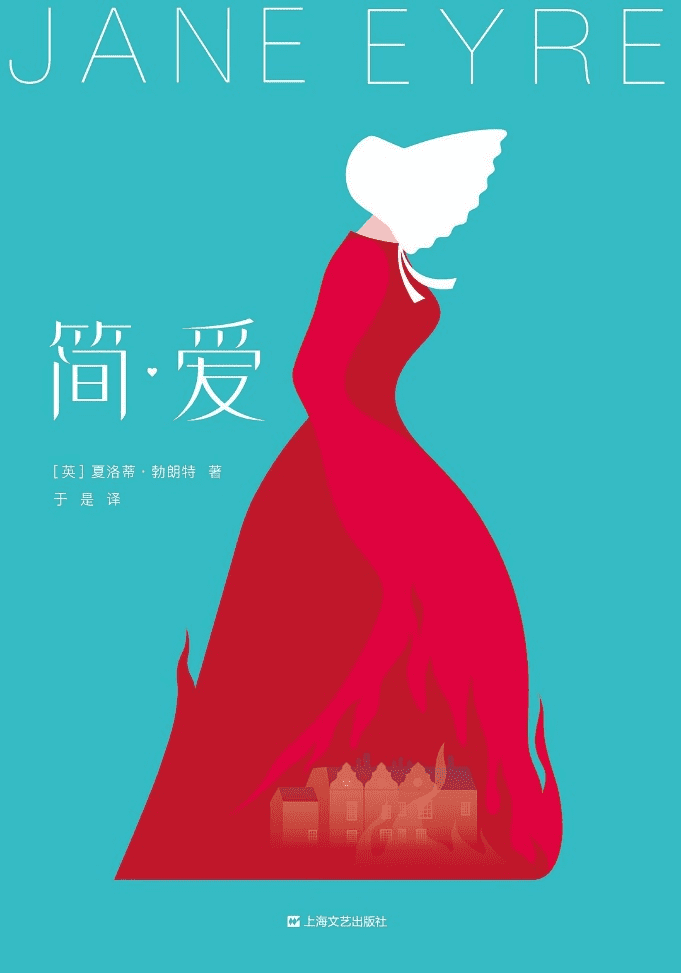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于是译
大星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7
但伍尔夫指出,这个身影暴露了勃朗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缺憾:“她的书变形、扭曲了。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
女性总是被打断、被指使,要么去补袜子,要么去看锅炉。从《简·爱》生硬的转折来看,勃朗特当时也许是在一片鸡鸣狗吠中完成小说的,她不得不先写出匆忙的、突兀的句子。
勃朗特挣不到每年300英镑的收入,没有“自己的房间”。女性不仅贫穷,还要忍受男性批评家的嘲讽——“女人创作就像狗用两条后腿走路”。伍尔夫感觉得到,39岁就逝去的勃朗特被愤怒干扰了。
相比之下,像乔伊斯、弥尔顿、高尔斯华绥这样的男性作家,则有大把时间坐在大厅里激情说教。
男性一遍遍地谈论法庭和议院,炫耀自己的巨著被首相摆在橱窗里,热爱书写斗争,卖弄文笔,字里行间自命不凡。“这让我联想到公立学校里乳臭未干的小男生,他们足智多谋、能力突出,却也过分自大和自私”,伍尔夫同样反感这种“公山羊”气质。
整个西方文学史都有瞧不起描写妯娌、编织、客厅的传统,推崇史诗和宏大叙事,甚至像托尔斯泰一样厌女。评论家们要么男人味昭著,要么带着不悦评点女性作品,就像《威斯敏斯特公报》那样。
于是,在一个纯粹的男权社会里,女作家逐渐走向模仿,像男人那样说话,盛气凌人地把眼光放远。在伍尔夫看来,这不叫雌雄同体,而是被男性批评家的喋喋不休给动摇了。
“任何一位作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包括勃朗特、乔伊斯、弥尔顿,伍尔夫认为,重复女性的愤怒、宣泄男子的气概,两个方向都背离了文学,而且注定凸显笔法的缺陷。
只有实现“雌雄同体”的作家,比如莎士比亚、柯勒律治等,才会让伍尔夫反反复复地读。
在1925年4月8日的日记里,伍尔夫再次痴迷于普鲁斯特的字句,“他像羊肠线那样坚韧,又像振翅的蝴蝶那样短命。我想,他既能感染我,又能影响我,让我嫌弃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句子”。
1927年,伍尔夫在小说《到灯塔去》中勾勒出一个双性的灯塔;1928年,她写出小说《奥兰多》,主人公“在马裤和衬裙之间换来换去”,同时享受着两个性别,极其强健,又极有诱惑力。
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几近结束时,女性决意要进入男性社会,尖端永远是男性,伍尔夫清楚,整个文学史都布满了男性,她觉得不对:“若是女人像男人一般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连看上去也像男人,这真是太可惜了。”
光是“女性主义”四个字概括不了伍尔夫,因为她还有诗性。
“死亡,我总感到死亡正在逼近”
在伍尔夫的小说里,她很少正面描述“性”,自杀前夕,她仍然想起6岁时被同母异父的兄长杰拉尔德猥亵了。
用“性冷淡”来解释伍尔夫太过粗糙。小说《远航》里,理查德·达洛维偷吻雷切尔,紧接着便发噩梦,畸形的小男人长满麻子,她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像死去那样,伍尔夫的笔触由此变得痛苦。

《远航》,[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黄宜思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
2014年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中记载的性侵案例持续上升,而林奕含也熬不到出版第二本小说了,“什么人都有点理由,连奸污别人的人都有心理学、社会学上的理由,世界上只有被奸污是不需要理由的”,性对于受害者来说——包括伍尔夫,是一种罪证。
从13岁开始,她的脑子就被精神病刺穿了,狂躁的时候会幻听,1921年8月18日,她写道:“像我这样的妻子得关在笼子里,外面用把锁锁着。”跟侍者说句话,她也感觉要导致一场爆炸。
《达洛维夫人》是她尝试描述精神异常症状的一本小说,在构思《海浪》的时候,她感觉大脑出了问题,“它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化成了蛹”,伍尔夫打算写下这“废话、细节和肮脏”,主人公说:
“你们曾经用你们那龌龊的爪子,从我身上抢去一个钟点至下一个钟点之间的那段清白的时间,把它们卷成脏污的一团,丢进废纸篓里。”
现实中,伍尔夫因为发病也经常需要躺着,什么都做不了,像一团疲惫的肌肉纤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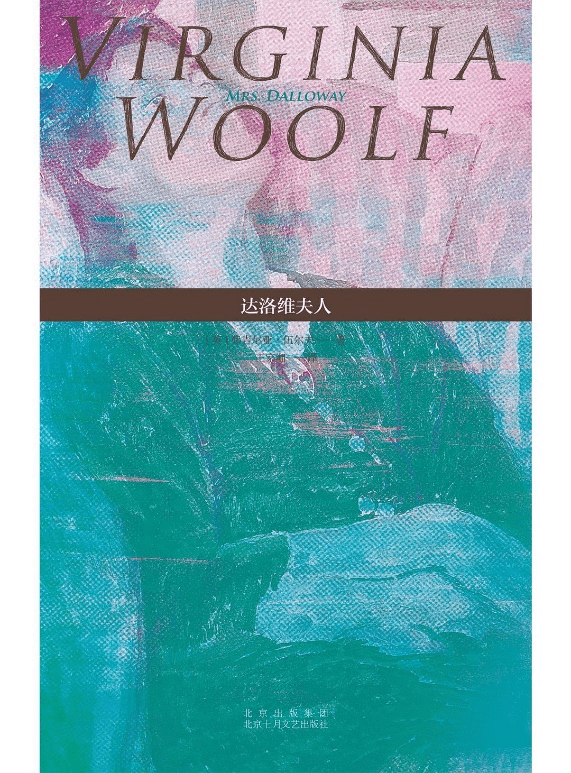
《达洛维夫人》,[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家湘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5
死亡是令伍尔夫精神崩溃的另一件事。她经历过如此多的死亡:13岁时是母亲,15岁时是姐姐,22岁时是父亲。伍尔夫曾尝试从窗口跳下去,她感觉“一个人就这样被打发掉了”。死亡像是极不可能却板上钉钉的事情,让她出现幻觉。15岁的伍尔夫说,仿佛死亡是违背法律的,击打在她的蝶蛹上。
她不断地发病,这个季节是躁期,那个季节是郁期。有时感到整个英国都很糟糕,无法阅读,无法写作;有时飞快地给所有椅子、桌子赋予辞藻,滔滔不绝,视线模糊,手抖个不停。她要求自己写日记,为的是确认脑子里那堆可怜的神经还能不能支撑她写下一部小说、下一篇评论。
《墙上的斑点》《海浪》《到灯塔去》,这几部作品几乎都来自她的躁期,意识流“这儿、那儿地忙忙碌碌”;到了郁期,她再像用湿梳子梳头发一样,把段落理顺、吹干,最好赚300英镑,快乐地计划着盖个浴室,砌一个热水炉灶。
1925年的新年伊始,伍尔夫说,“我的英雄主义只体现在文学领域”。
对她来说,“骑士”不是历史书里的男性,只有女性才生发得出一种“骑士”般的保护情感,她一头扎进躁郁的湖泊里,奋力描写女人。1929年8月19日,她结束晚餐,纪念《妇女与小说》完稿:
“你会感到有个小东西正拱起脊背不断地向前奔跑。”
参考资料
1.《伍尔夫日记选:思考就是我的抵抗》,弗吉尼亚·伍尔夫,2022.9.20
2.《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弗吉尼亚·伍尔夫,2019.10
3.《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与小说美学》,向婉,2014.5
4.《伍尔夫“雌雄同体”思想研究》,孙碧茹,2017.10
5.《伍尔夫的躁郁症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苏中美,2019.5.2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许峥,编辑:谭山山,校对: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