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5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现年64岁的挪威作家、诗人和戏剧家约恩·福瑟,因其“以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为不可言说之物发声”。
和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相比,约恩·福瑟的名字对读者们来说更显陌生。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上有一项“你是否读过约恩·福瑟作品”的投票,只有9%的人选择了“读过”。
约恩·福瑟本人的反应,倒是符合人们对诺奖得主的想象。他在接受挪威公共广播公司NRK采访时表示,得知获奖消息,“我很惊讶,但同时也不惊讶”,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谨慎的准备”。
中国戏剧界跟约恩·福瑟的交集,可以追溯至2005年。彼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路生读到一本英译本挪威剧作集,他看中了其中由约恩·福瑟所写的《有人将至》,并交给该院英语老师邹鲁路,希望她能翻译出来。
2014年、201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秋之梦:约恩·福瑟戏剧选》——这也是截至目前唯二的福瑟简体中文作品,译者正是邹鲁路。
事实上,得益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积极推广,中国剧迷们对这位剧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诺奖结果公布前,译林出版社、世纪文景已有推出福瑟作品的计划:译林出版社计划推出“约恩·福瑟作品”,包含福瑟偏爱的小说《晨与夜》、近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七部曲”(《别的名字:七部曲I-II》《我是另一个:七部曲III-V》《新的名字:七部曲VI-VII》);世纪文景则即将出版福瑟小说代表作之一《三部曲》,译者是李澍波。
李澍波现居挪威首都奥斯陆,我们请她撰文谈谈约恩·福瑟其人、其作,讨论“不可言说之物”到底有没有答案。
(以下为正文)
福瑟(Fosse)是一个地名,位于挪威西部哈当厄尔峡湾之侧的一个小镇,居民数百人。约恩·福瑟生于斯,长于斯。
用姓来标识和家乡的联系,是挪威艺术家强调自己来处的一种做法。1889年,一位20岁的年轻人把本姓“图尔森”改为家乡的名字“维格兰”,他就是日后的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
约恩·福瑟的“福瑟”倒是本姓,他祖上三代都住在这小镇。爷爷乌拉夫驾船把干鳕鱼卖到卑尔根,爸爸克里斯朵夫在镇上开百货店。长子出生时,克里斯朵夫想用父亲的名字给儿子命名,但乌拉夫想把自己的弟弟——7岁就夭折的约恩——的名字给长孙。双方讨论的结果,就是这孩子叫“约恩·乌拉夫·福瑟”,在福瑟镇,大家都叫他“约恩·乌拉夫”。后来,约恩·乌拉夫成了作家,大家改口叫他“约恩·福瑟”。
一个人的姓名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过去、属于纪念、属于对过去某人某地的回忆,是福瑟作品里经常玩味的主题。《三部曲》的男主人公阿斯勒干下杀人害命的勾当,改名换姓,改名“乌拉夫·维克”。
“维克”(Vik,“小海湾”之意)也是挪威最常见的小镇名字,漫长的海岸线和峡湾沿线,每几百里就会有一个叫“维克”的小镇。而《七部曲》里的成功画家阿斯勒也有一个同名重影:另一个落魄画家阿斯勒。
当姓名和个人的关系不再那么天经地义、牢不可破,而是可撕开、可玩味时,许多看似天经地义、牢不可破地附着在个体身上的不可言说之物,也就松动开来了。
一、“不可言说之物”究竟是什么?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福瑟的理由是“以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为不可言说之物发声”(for his innovative plays and prose which give voice to the unsayable)。这里的“不可言说之物”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固定答案。
许多事物在被言说之前,都曾是不可言说的,比如女性在父权社会家庭框架中的感受,在多丽丝·莱辛之前可能是无法被言说的,直到莱辛赋予其文学语言。同样的话,可以用来形容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体验和托妮·莫里森的关系。
而在福瑟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社会现实的维度,而是被抽象简化提纯后的“个体内在”和“人与人之间”这样一个场域,个体的呼吸和沉默,两人之间互相影响的呼吸和沉默,或者加入第三者后的呼吸波动和沉默,这些都是福瑟在戏剧和韵文作品中所赋予表达的对象。
把“prosa”翻译为“散文体”不但不够准确,而且可能有些误导。瑞典语和挪威语里的“prosa” 并不像英语里的“prose”那样是诗的反面,并时刻准备向说明、讲理奔去,“prosaic”更是平庸、拖沓的婉称;“prosa”更接近无韵之诗,可能不按韵脚,但是有口述的声韵和节奏。福瑟把自己的小说称为“prosa”,也就是以注入了诗性、音乐性、哲学感受、身体感受的叙事来构成他的文本。
福瑟的学生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即《我的奋斗》作者)为其获奖欢呼雀跃,他说福瑟是真正的艺术家,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终究颁给艺术了。
不过挪威大众甚至挪威媒体不像克瑙斯高这样热爱现代主义文学,文化大报《日报》(Dagbladet)在很长时间内都对福瑟视而不见。在1988年福瑟的第二本小说《关闭的吉他》被瑞典大出版社伯尼尔慧眼识珠,翻译成瑞典语后,得到从评论家到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之前,《日报》甚至没有登过一篇关于福瑟作品的书评。福瑟第三本小说《船库》在挪威和瑞典同时出版,此时代表挪威文学圈风向的《日报》才肯定了福瑟,给其敲上一个“可推荐”的章。
福瑟拿诺奖以后,《日报》文章的标题是“福瑟:一个瑞典的发现”,把福瑟形容为“在挪威还是一个难读的、受众较窄的作家”。文中引用瑞典文学评论家维克托·马尔默的说法,“诺奖该颁给另一个挪威作家”——也就是挪威文学评论重要阵地《阶级斗争报》一直看好的达格·索尔斯塔。当然,文章作者也不会扫大家的兴致,以“总之祝贺就好!”收尾。
二、“诗性独白”
福瑟是不是瑞典的发现?答案是肯定的。
上世纪80年代把福瑟小说陆续译成瑞典语的作家、译者斯蒂夫·森—桑德伯格,就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之一。
90年代初,瑞典戏剧界最有能量的女性之一——贝丽特·古尔博格读到了福瑟的剧本《有人将至》,她在里面听到“一种清澈深沉的音色,那闪耀的洁净、脆弱、黑色激情、幽默,让人想到洛卡、辛格、贝克特,似乎看到爱德华·霍普的画,似乎能听到由现代爵士四重奏演奏的赋格”。
古尔博格和福瑟的伟大合作由此拉开序幕,她把福瑟推荐给瑞典的戏剧出版社,他的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丹麦语、法语、德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至于福瑟的翻译和推广为什么没有从某家挪威戏剧出版社开始,是因为当时挪威没有戏剧出版社。
一个瑞典独立剧团排了福瑟的戏,带到巴黎的法国喜剧节;古尔博格成功地把福瑟推到英国的实验剧场。世界像一个牡蛎那样,朝福瑟打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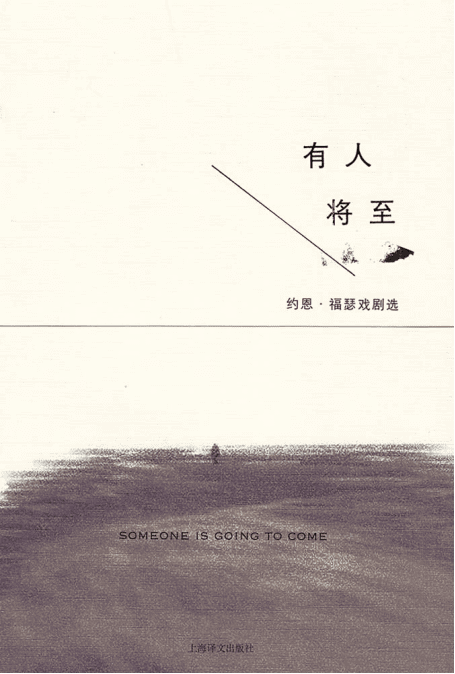
《有人将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封面。
福瑟的作品是本质主义的、极简的。福瑟的小说和戏剧在本质上都是诗性独白,它的一些场景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轨迹:《三部曲》《名字》里未婚先孕的小两口和《关闭的吉他》里的单亲妈妈,多少影射出福瑟20岁就当爹,和女友、孩子在卑尔根学生城里住了8年,边读书边带娃的情况;《三部曲》和《七部曲》都在卑尔根(旧称卑约格文)展开。
在一些最基本的设定后,作家的关注就投向物质层面以外之物。他写小说时,被称为“描写状态的作家”;写剧本时,被称为“静默高手”。他的作品已经尽量剥离了外在的属性,只余那些最本质、最存在主义的——平静与不安、死与生、对孤独的渴望或焦虑、对不孤独(或者一起孤独)的渴望或焦虑,各种形式、各种节奏、各种氛围的静默包围着寥寥对白和微乎其微的动作,构成了他独特的戏剧空间,使观众沉溺且抽离。
他的戏简单而深邃,简单到连孩子也能演,深邃到通向始料不及的、一种闪耀的黑暗中——因着那闪耀,黑暗才得以被看见。
三、“爱戏剧的人往往写不出好戏”
福瑟的戏剧被搬演到别国舞台上的主要优势,一是他对各种非语言表达的精妙运用,二是他的戏本身就把非本质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剥离得相当干净,有效降低了文化转译的难度。
当福瑟作为来自挪威的剧作家在各种国际戏剧节上备受关注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挪威得到的受众和媒体追捧倒相对有限。
福瑟在挪威感受到的阻力和助力,和他使用的新挪威语有很大关系。新挪威语是19世纪一些比较激进的挪威语言学家提炼出的一套保存各地方言特点,又体现和古挪威语历史联系的本土语。它和书面语(或曰“巴克摩挪威语”,Bokmål)是两种通行挪威语。
挪威官方语言还有萨米语,受宪法保护,但是使用者集中在北挪威萨米人居住区。使用巴克摩挪威语的人占挪威总人口的85%~90%,就是在以使用新挪威语为主的西挪威,不少市县也声称中立,在政府公文中使用相同比例的书面语和新挪威语。
福瑟出生、成长在西部,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过程里,都使用新挪威语。
他深深认同这种语言,其写作和翻译工作也在回馈它。福瑟用新挪威语译介的作家包括卡夫卡、汉德克、乔伊斯、贝克特、伯恩哈德等,他的写作也把新挪威语带入了一个新的水平。他以全新的方式,使用新挪威语的淳朴特质、音乐性和古老关联。

卑尔根被冠以“欧洲文化之都”和“世界遗产”的名号。(图/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
但福瑟坚持用新挪威语,也导致其作品的声誉在上世纪90年代前局限在以卑尔根为文化、商业中心的西挪威。另一方面,挪威政府对弱势语言和文化多元性大力扶持,鼓励更多使用新挪威语的书籍、戏剧、媒体问世。
卑尔根国家剧场的戏剧总监苦于新挪威语编剧的缺乏,组织了一个10天的编剧班,邀请8位作家新秀参加,福瑟身在其中,但并不活跃,甚至有些被动。
这个小镇青年是高中以后才被老师带去看戏剧现场表演,他感受过剧场的魅力,但不算太热衷。10天课程结束后,他表示:“我衷心觉得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写一出戏。”日后,他写了很多出剧后依然嘴硬,说道:“假如不是开始有对戏剧的恨,我也写不成这么多戏。很多爱戏剧的人往往写不出好戏。”
也许正是因为缺乏对戏剧的仰慕和崇敬,福瑟在尽情玩弄戏剧这种表现形式时,没有一点心理障碍。福瑟接受国家剧场的邀约写了剧本,成功售出,发现写剧本是很好的收入来源。在西挪威和奥斯陆,都有专演新挪威语戏的剧院,缺的只是好编剧。
1996年,百年来只上演过四次新挪威语戏的奥斯陆国家剧院邀请四个新挪威语剧作家写一部向易卜生致敬的戏。四人里,有的太忙,有的自杀,有的拖稿,只有福瑟按时交付。福瑟一向认真负责,绝不辜负那些垂青自己的人。
从当年学生报征文比赛时认为“他的天才一眼就能看到”的评委西西莉亚·洛维德,到曾是他的出版社编辑、后来的挪威文学推广基金会主席马吉特·瓦尔索,再到瑞典人贝丽特·古尔博格,连同所有那些一路对福瑟大力扶持的人,在10月5日诺奖宣布时,都该觉得功德圆满了:他们凭着本心和期待所作出的选择,被一路加强并放大了,迎来了文学作为一种本真声音的凯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李澍波,编辑:谭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