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在人们惯常的眼光里有着全方位的体面。
他们研究某个学科,经常谈论普通人读不懂的话题,把“读书”这件事从考场延续到案头,贯彻它的终极意义,有着传统认知里备受尊重的刻苦、智慧、奉献这类难得的品格。
不必朝九晚五地服从于打卡制度,“看起来不像一份工作……为某个社会科学项目进行民意调查,或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挖掘档案”,环境单纯,在学历阶梯的尖端玩着一门智力游戏。
“但这几个小小的场景几乎是大众想象的全部了”,这句话出自《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一书。它试图为这种文化上的刻板印象祛魅。
该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卡特林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拿到古典学博士学位却自称“学术难民”,羞耻、焦虑、恐惧的混合情绪几乎要压垮他。但是,从中退出却貌似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因为,“离开学术界感觉像是在证明你的学术能力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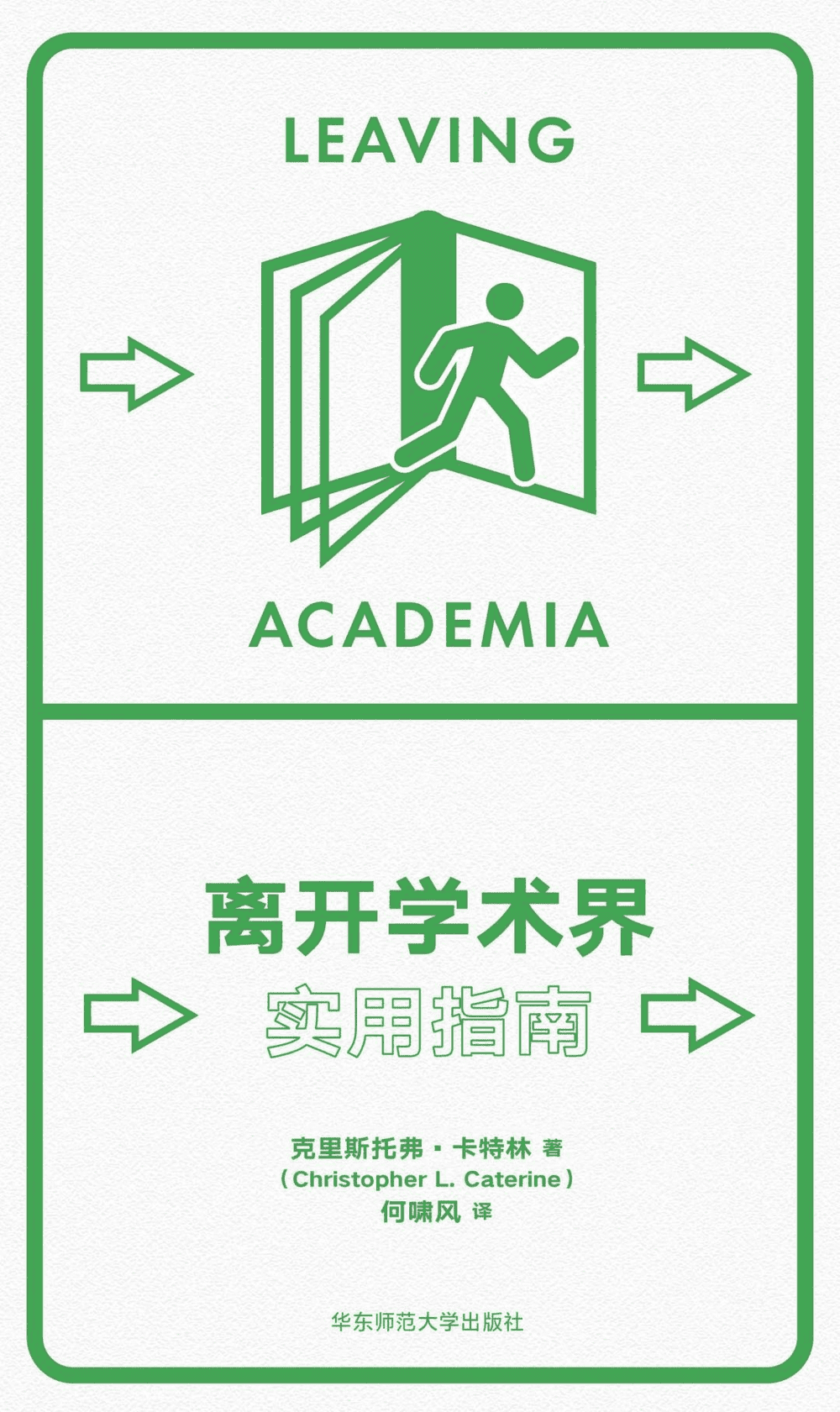
《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 [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著 何啸风 译 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9
结束学术生涯,不是你的错
这种下意识的印象背后,其实有一个冷酷规则,叫“非升即走”。
比如克里斯托弗·卡特林的妻子马洛里,如果不在头6年内发表数篇文章,甚至出版一本专著,她就有被解雇的可能。哪怕这个职位名为“终身教席”,脑袋上也随时悬着倒计时的时钟。
卡特林把它称为陷阱,当一个人疯狂地为了续约而找课题、写作并发表,这6年时间就是“无比漫长的”,它包含着混乱的生物钟、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拒稿信、偏僻住所、心理问题。
从数据上看,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与有限的教席之间,像一组流沙的漏斗,能留下来的人极少。
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所登记的博士在校生有509453人,而10年前这个数字为271261人。几乎翻番的博士生增长速度,显然不是高等教育体系所能覆盖的,更别提“985”“211”级别的高校。
把问题移到卡特林所做的统计里,就更加分明了:
“我不得不用各种关于高等教育的统计研究得出这个数字。今天在美国,只有约1.2%的艺术类和人文类博士项目的学生可以在顶尖院校得到终身教席。即使不限定是顶尖院校,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凡是拥有终身教席的人,只占读博人数的2%-7%。”
“从另一个角度看,10名学者中至少有9名没有从事大多数人起初攻读高级学位时希望从事的行业。”
僧多粥少,这在学术界与非学术界都是铁板钉钉的现实。能否留下,混杂着运气与实力,而不能就此认定“你不行”,更别说具体的数字难以言明各类隐形歧视、纷争、冷酷与缺陷了。
在“她乡电台”某一期对学术圈的讨论中,嘉宾们就提到类似“这个系统不在乎我们”的感受。尤其在高智力环境中,少数族裔、女性、残障人士等都曾面临不公平问题。
比如,耶鲁大学哲学系要求博士生在英语之外,还必须懂德语、法语、希腊语或拉丁语。曾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袁源去询问中文能否做第二研究语言时,系里给出的解释是:“中文跟哲学研究没有太相关。”
袁源觉得这句话带有文化等级偏见,“言下之意是中文没有哲学价值?中国哲学几千年,凭什么认为中文跟哲学研究不相关?”她据理力争,最终促使系方改掉了规定。
而这类偏见在学术领域并非个例。需要进行漫长的斗争,大脑必须时时做出判断并付诸变革,否则就要被迫处于袁源的一个同学所描述的微妙处境里——“每次下课都要跟在一群很高大的男人后面走路的那种感觉”。它有多么讨厌,只有弱势方能瞬间理解。
被迫从学术界离开,有时是概率问题,有时是不公问题,但是很多人归咎于自己的能力问题。
学术劣币如何驱逐良币?
豆瓣话题#你是如何对学术感到幻灭的?#底下那些焦虑的跟帖,浏览量达258.3万次。
“以学术为志业,否定时却好像把自己的前半生否定了,这种否定能摧毁一个人”;“有的人在极度杰出并且幸运的情况下拿到一个偏远地区的学术工作(还不一定是教职,有可能是临时Post-doc)”;又或者是,虽然雇不起心理咨询师,却常常收到系里发出的防自杀邮件。
课题方向“错误”、论文投稿被拒、遭受学生质疑、基金申请失败、大龄脱产身份等,都有可能将他们推向学术统计数据不乐观的那一侧,直到某天彻底打破波西米亚式生活理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连江曾在个人公众号上引用黑格尔的话——赢得他人承认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而在学术界,“赢得其他学者承认尤其困难”,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
“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是萦绕在所有学者头脑中的紧箍咒,翻译得直白一点,则是“不发表就毁灭”。
水特是海南某大学讲师,他在拿到教职的同时也收到了任务书:“发表多少篇文章,发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一清二楚,如果没有达标就把你退掉或者转岗。我们学校已经算是要求比较低了,有个在双一流大学读博士后的朋友,两年之内达不到副教授的要求就会被清退。”
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忍受学术期刊冷漠的挑错,还要目睹一些经过包装、蹭了热点的学术垃圾得以发表,由此逐渐走向自我怀疑——是我不够聪明?还是我应该装作像其他人一样关心既定的话题?
甚至在投稿反复被拒的情况下,连错在哪了都不知道。就像在读哲学博士生莫古所说:“目前我看到过拒稿的回信都是模板,还没看到过活人回的信。”
学术评价走上了一条单向度的路,篇数、字数、刊物级别等评判标准,像马鞭似的抽打着学术神经,李连江把这种“俱乐部”规则形容为“聪明人刁难聪明人的高级但未必高尚的智力活动”。
莫古认为这会导致异化:“一旦‘发表’而非‘研究’成为目的,那么学者通过某种套路在较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之后,他或她将不断重复这种套路。且不说这会让学者自身的发展受限,谁又能保证权限巨大的编辑与审核本身,不会沦为权力的游戏?”
于是“被自愿”的内卷开始了,搞比赛、交材料、开大型学术会议、学已有的话语范式,前提是想办法留在这套评判体系里,而后才有空间思考如何做出令学界增加高度的课题。
当大量时间被倾注在某个学科之上,离开学术界便几乎不可能,就像卡特林所担忧的,职场动态与学术常规有天壤之别,而“学院之外几乎没人能将维吉尔之后的罗马诗歌知识,或18世纪法国小说中的性别建构进行变现”。
与此同时,承认“其实你是想离开的”,也变得尤其困难。
相较于学术,生活才是统治力量
马克斯·韦伯于1917年11月7日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当中提到“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很多不被这种遴选制度选中的人,学术才干其实并不差。
“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
韦伯将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解释得清清楚楚,而后提出:“唯有单纯为事业献身的人,才具备学术领域的‘人格’。”如此便不难理解,豆瓣小组中对学术感到幻灭的人们早已不谈使命。
有的幻灭来自外在,比如“徒有知识却没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博导”“外行指导内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冗长而‘必要’的论文包装过程”;有的幻灭来自内在,比如产生抑郁倾向,“人生和学术混在一起,好像人生也完全失败掉了”。
摆在眼前的最大警戒线是年龄。准备申请博士后的小温理了一条大概的线:“学术成熟期一般在40~50岁,往后身体机能下降,状态肯定没30多岁时好,可能很难做出研究成果。50多岁以后就开始偏向于总结性的东西,60岁就退休了。”
在一篇题为《离开田野,离开学术》的帖子里,作者打算花半年时间到贵州一个村子里调查社会变化,撰写一篇民族志报告,却时常感受到“一种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感以及道德上的自我谴责”。
最后,这位作者几乎读不进任何海外的中国研究资料了,怀疑那到底是真正的关怀或只是抽象的幻想。“如何让学术界的知识发挥实际作用”,这是他被一个农妇无意间调侃之后持续困惑的问题。
当现实因素一年年地入侵学术道路时,突然在某天,发现职业上的哲学意义崩塌了,有人继续理想主义的钻研,有人则考虑离开学术界,比如卡特林。
作为一个研究冷门罗马诗人的学者,当卡特林发现自己整整10年都只是在试图与全球仅有的50位受众展开学术讨论,以及逼着学生记住拉丁语法的细节时,他最终决定转换一个生活逻辑:“把对于世界的影响,与支撑这种影响的赚钱方式区分开来。”
又或者是像小温一样,把“志业”当职业:“别把自己从事的东西太当回事,我们可能研究的是比较形而上的领域,但它未必就超凡脱俗了,这只是一份现实中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超越性或者绝对的崇高性。”
当我们剥离知识对生活的统治之后,事情也许就不用看得那么严重。
退出这一体系,当然不意味着“你不行”;而留在学术界,所谓“不发表”也未必代表着你“就毁灭”了。
参考资料:
1.《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2.《作为系里唯一的女性,还是有色人种,是怎样一种感受?》2021-12-31,她乡
3.《离开田野,离开学术》,2019-05-20,Lumières
4.《影响学术生涯的心理和性格因素》,2023-02-23,李连江
5.《沿街托钵已成中材学者的宿命》,2023-03-28,李连江
6.《挤出那片属于自己的研究空白》,2023-09-08,李连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苦苦,编辑:谭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