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萧奉,原文标题:《接吻的中国史,比你想象中更生猛》,题图来自:《梦华录》剧照
如果你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感兴趣,那一定要知道胡文辉,他的《现代学林点将录》盘点一百多位学者的学术生涯,广搜异闻,识见敏锐,被称为现代学术的“梦华录”、现代学人的“思痛录”。
如果你对陈寅恪的生命和思想有过好奇,那么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也是必读的书。他不仅仅熟悉陈寅恪,在学林掌故与近现代史上也用力极深,能把学者的著述、遭际与时代变化相勾连,写出了一部沉痛的诗史。
现在,他推出了一本新书叫《接吻的中国史》:从《易经》咸卦说起,广泛搜集历代诗词曲歌小说、出土文献、汉墓画像石、明清春宫画来说明古代中国人也接吻并且善接吻,其中还有接吻的语言学、游戏文学、东西方比较、口臭问题的解决等研究。
相比学术史上的大事和大人物,接吻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有什么好研究的?
胡文辉解释说:“古代中国人之于接吻,虽不及西方人那么热衷、那么高调,却绝非不存在,也自有其‘吻的文化史’的。在日常生活中,在影像世界中,中国人今日已司空见惯者,在史学上却无人问津,这是一个悖论。所以有此作也。”
一、每个普通人都做的事,就值得研究
新周刊:关于此书的缘起,你在后记中谈到,这是2008-2009年间读赵翼《瓯北集》时发现“却渐老去风情断,方与佳人接舌来”一句,由此想到中外接吻文化之差异,开始随时记录相关史料。当时为何觉得接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胡文辉:研究历史问题,或许可以说有两种不同的入手方式:一种是你觉得某个问题重要,然后就围绕这个问题来读书,来搜集材料;一种是你发现了某些有意思的材料,然后就从这些材料开始继续积累,并注意相关的领域或学科状况。
我研究接吻史,应该算是后一种类型,就是材料优先。当然,就算是材料优先,材料本位,前提也是我觉得这些材料涉及的问题是有意思的,具体到接吻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是认为,从历史上来说它不但有趣味,而且是值得研究的。
至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这个值得多说几句。我觉得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当然是事件史的,有关的人、事、物或制度,对天下大局影响巨大,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研究对象;还有一种是生活史的,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比如衣、食、住、行、性,这些我们过去往往不将它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但这是当时每个普通人都做的事,你说它不重要吗?接吻问题就属于这样的研究对象。
新周刊:为何接吻在中国史学上长期无人问津?你也提到,曾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过去是不接吻的,你在书中用很多史料及研究反驳了这一点,也提到了张竞生、周作人、叶灵凤对接吻的讨论,但他们当时的讨论还很粗浅或很偏颇。
周越然1937年在《晶报》也译介过西方与中东文献中关于接吻的材料,对中外的接吻文化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他似乎是比较早的从生理和人伦上指出,在中国“接吻一事,实与开天辟地同时”。但在这之后,相关的历史研究甚至讨论似乎都很少。你如何理解接吻史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胡文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关接吻的史料很少,所以很难展开历史性的研究。相反,我现在之所以会写成一本书,也正是基于史料的积累。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嘛,史学当然不只是史料,但史料是最根本的。
至于接吻史在学术上的意义,我倒不认为有多大,就像我在书里说的,“接吻只是一件小事”。不过,至少这是情爱史、日常生活史、风俗史不应缺少的一环。

《倩女幽魂》剧照。
新周刊:本书正式撰写是在2020年,一个不鼓励接吻的时期,让这个研究别有意味,令人想到潘光旦在1930年代译介《性心理学》,陈寅恪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当时写这本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胡文辉:那段时间正在隔离,我正好一个人住在放书的地方,有时间写较长一些的东西。而正常的时候,我需要两头跑,有近一半时间住在父母家,需要帮忙带小孩。
二、最适合接吻的地方,是远方
新周刊: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接吻是在电影里。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说:“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
在你的观影史中,你记得第一部看到吻戏的作品是什么吗?当时是什么感受?
胡文辉:帕慕克的话很有意思,也提醒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看见的接吻,绝大多数其实都来自影视或图像。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我,大约只见过路边的陌生人接吻,但没见过熟人在我面前接吻。我肯定看过《庐山恋》,但完全没印象了,包括接吻镜头。印象最深的吻戏,当然是《天堂电影院》那段“吻戏片段合集”,这几乎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罗马假日》剧照。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接吻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爱情象征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就是在流行文化和大众电影的推动下才形成的。在西方,亲嘴、亲脸也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时期都流行的社交风俗,罗马皇帝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接吻,认为接吻有害道德和卫生。为什么是亲嘴式的接吻成为了全球性的、爱情的象征,而不是吻手、吻脸或者更单纯的亲密动作?
胡文辉:首先当然是因为西方的强势,它的技术、文化乃至军事力量,使它成为近几百年世界的中心。我们当然更容易接受“中心”的影响,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古代的中国是东亚的绝对“中心”,所以朝鲜、日本也更容易接受中国的东西,正如我们今天接受西方的东西一样。所以,西方的风俗和文化往往成了世界的样板,接吻只是这些样板之一而已。
相对来说,形而下的东西,比形而上的东西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物质文明,也包括接吻这种大众性的习惯。

《胜利之吻》,历史上最著名的接吻照之一,为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拍摄于美国时间1945年8月14日的纽约时代广场。
新周刊:中国从中古以后,爱情观和性爱观为什么趋向开放?
胡文辉: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即陈寅恪所说的“胡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讨论了这种风俗文化的“胡化”。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贵族阶级的消解,贵族阶级所讲求的礼仪也随之消解,整个社会变得更为世俗化了。
但所谓“走向开放”这一点,恐怕也不能夸大,在中古以前,是不是就一定很保守呢?也许只是性爱方面的史料很少保存下来而已。
新周刊:虽然接吻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亲密行为,但在现代以前,中国的接吻行为一般都是私密状态的。留洋学生应该是中国第一批学会公开接吻的人,除了书中提到的张竞生,还有哪些人是“饮头啖汤”者?
胡文辉:我研究接吻史,重点是古代,价值也主要在古代,越到后边,材料越多,我就无力涉猎太多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
我的书印出来之后,我才搜到一个帖子,是几年前发表的论文,《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由这篇论文,我才知道,二十年前已经有了一本叫《不吻你可不可以——中国亲吻亚文化》的书,我的书已不算是第一本接吻史了。
那本书在古代方面比较薄弱,主要是综合前人的东西,但明清小说和民国作品的例子都很多,比我掌握得丰富。至于那篇《西方接吻文化》的论文,因为写得比较晚,已经有了新的搜索条件,所以民国的材料更加丰富。所以,关于近代以来这个时间段,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这两种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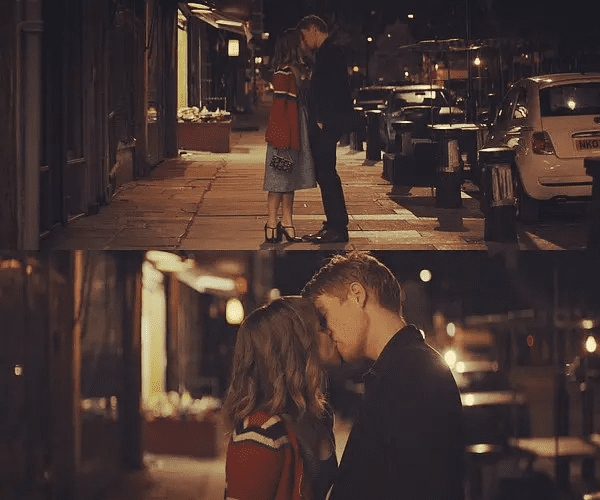
《时空恋旅人》剧照。
新周刊:接吻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城市化的产物和标志?在中国,接吻的流行和城市化是同步的。
作家夏天敏在《接吻长安街》中写过一个农民工,他的愿望是与自己的恋人在长安街接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在某种意义上,当初的留洋学生就是中国最早的进城者。有意思的是,城市可能提供了一个适合公开接吻的环境,即使在今天,乡村地区的接吻仍然是私人状态下的。
胡文辉:《接吻长安街》这个文本,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觉得它的重点,不在“接吻”,而在“长安街”。在长安街接吻,只是代表了他能跟恋人相聚在北京,相聚在大都市。我觉得城市人接吻,也大多数是在私人状态下的。最适合接吻的地方,恐怕不是城市,而是另一座城市,是远方。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三、跟着兴趣走,跟着问题走
新周刊:本书讲完接吻史之后,还有一个外编《中国人的口臭问题及其解决——接吻的关联性研究》,也很有意思。接吻从私密行为变成公开行为,个人卫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是决定性因素。
不只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似乎也是这样,周作人曾引用罗马诗人Martialis的一段记录:“外出十五年后,回到罗马来,它给我这许多接吻,比勒思比亚(Lesbia)给加都路思(Catullus)的还要多。各个邻人,各个毛脸的农夫,都来亲你一个气味不佳的嘴。织布匠来逼你,还有洗染店和刚才亲过牛皮的皮匠;胡子,独眼的绅士;烂眼边的,和有稀臭的嘴的朋友。这真不值得回来。” 谈谈你对口臭问题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
胡文辉:接吻与口臭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了,每个想接近异性的人都知道的。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难只难在怎么去研究它。
以我所知,确实没有太多现成的研究可以依赖。研究最多的,似乎是刷牙和牙刷的起源问题,还有关于口腔卫生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些是属于医疗史范围的;还有的人专门研究《金瓶梅》,因而研究了里面的“香茶”,也就是当时的口香糖。但“正经”的医疗史研究,大约不会从“口臭”这个很世俗很日常的角度入手,所以这个“外编”,对于口臭和相关的口腔卫生问题,可能是做了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综合。
新周刊:在中国,接吻的去性化,似乎和体育运动有关系。蒋子龙在一篇《谈“吻”》的文章中说道:“自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运动员获胜后有一个非常抢眼的动作,那就是吻。或吻运动衣胸前的国徽图案,或蹦着高地双手向观众抛飞吻,或一次又一次地吻自己的金牌,或拥吻教练员……大吻特吻,吻得比西方运动员还溜乎,这个中国人以前喜欢在私下里进行的动作,开始公开张扬。”
胡文辉:这个我觉得不是因,而是果。
新周刊:有的心理学和性别研究认为,“相较于女人,接吻似乎对男人来说并没有非凡的意义,他们只是将接吻看作亲密关系的一种日常行为,甚至只是当作亲密行为的前奏”。你认为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一直没有认真看过《老友记》,可能是因为里面基本都是对话,广州人说的,“口水多过茶”,不是很对我的胃口。前几天我试着从头看了几集,第二集开头恰好讲到男人女人对接吻态度的不同,里面有个男生就说:“接吻就像一个出场秀,你得忍着看完这段出场秀,然后才能看到真正的表演。”这大约可以印证心理学家的看法吧。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于接吻,相对来说,女性更容易受文化想象的影响,而男性更容易服从本能。

《老友记》剧照。
新周刊: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接吻的用语,考证出了“接吻”乃汉语原有的词,这一词先传入日本,日本人用来翻译kiss,然后再传回中国。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似乎曾经用过别的词来翻译kiss,比如周越然曾提到“开始”,即kiss的音译。这个翻译倒也颇有趣味,恰好表示kiss是性爱或恋爱的开始。方言中有一些别的说法,比如粤语有时称之为“打茄轮”。关于接吻的语言学,还有看到其他说法和材料吗?
胡文辉:形容接吻的方言,各地都有,我也见到有一篇专门的论文,但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范围,也超出了我的能力。
最近知道成都人将接吻叫做“打啵儿”,但写成书面时,往往写作“打吅儿”。这个“吅”字,本来并不读“啵”,所以我认为成都人是有意借了“吅”的字形,以表示口口相接,这跟明清小说里的“做个吕字”是差不多的手法。
据乔纳森在直播里介绍的,西方有著作专门搜集了关于接吻的词汇,洋洋大观。还有日本也有关于接吻的辞典,但这些我更加没有能力讨论了。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新周刊:你的研究兴趣很广泛,早期做过中国方术史,后来研究现代学术史和陈寅恪,再后来广泛涉猎各类文史考证,还做过金庸小说研究,最近几年对诗词似乎也花了不少功夫,写了很多古典诗。看起来相当驳杂,但感觉又很胡文辉,比如有一篇小稿子分析老外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中国女人。
能否说说,你的研究趣味是如何形成的?在选择研究题目、决定什么值得搜集史料时,你有没有一个偏好和标准?
胡文辉:或者有人觉得我很“博”,或者有人觉得这其实是“杂”,但对我来说,只是本当如此,我只是跟着兴趣走,跟着问题走。只要觉得发现了新的问题,或者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或新的材料,那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来继续研读,继续跟进,这样往往就会介入不同的领域或学科里。
领域和学科本来就是一种“路径依赖”,它是有用的路径,但绝不是唯一的路径,问题本身是不分领域和学科的。
当然,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肯定有些更重要,有些不太重要,有些更有趣味,有些更有关怀 。肯定有人会觉得,研究接吻问题是无聊的。比如传闻康生说过:“我用脚趾头夹着笔来写字,都比郭沫若写得好。”
我以前为此写过一篇考证文章,追溯这一修辞的来历。然后,就有个历史学家觉得我这样很无聊。
就像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钱锺书就觉得很无聊。还有人觉得,伯希和研究了很多不重要的问题。我以为,伯希和、陈寅恪并不需要我们来为他们辩护。我也不用为自己辩护。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我有很多的题目可以写,先写一本接吻史,确实是考虑到这个题目更加应俗。
新周刊:现在除了一些小题目,你还有在进行一些比较大的研究吗?什么研究在你看来应当写成札记、论文和专著?
胡文辉:大的题目不容易有集中的时间去做,而且我兴趣太多,所以近期基本都是写一些小题目。写成多大的篇幅,是札记、论文还是专著,自然应该以内容的新意来决定。只有一点新材料、一点新意见,就不必大费周章地综合成一篇论文,如此类推。

胡文辉的书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早年曾有媒体到你的书房进行拍摄和采访,很多读者对你的藏书量感到震惊。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你的藏书量还在增加吗?
胡文辉:买书是一件骑虎难下的事……
新周刊:你现在每天的阅读习惯、写作规律是什么样的?
胡文辉:跟孩子在父母家,就多翻书;在自己放书的地方,就多写东西。
新周刊:最近有没有读到一些有意思的新书?
胡文辉:我很少读刚出版的书。新书往往等到5折时才入手,入手了也往往放了很久才看,看的话也往往看得很粗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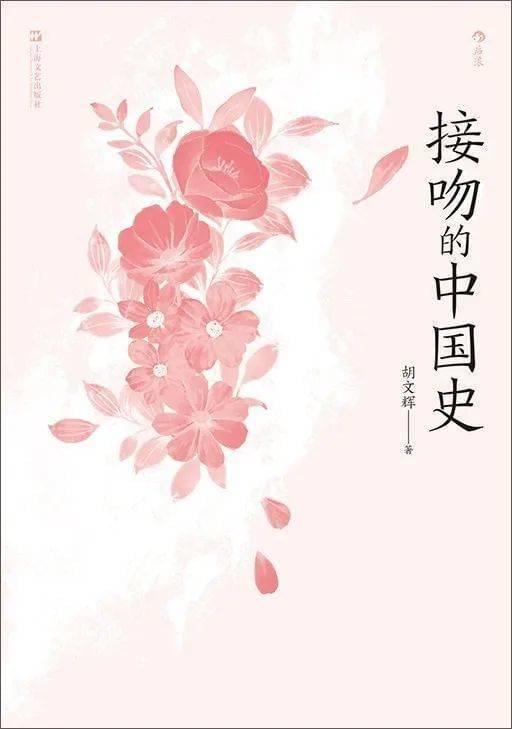
《接吻的中国史》
胡文辉 著
后浪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萧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