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王一恪,编辑:张文曦,题图来自《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说起塞林格,很多人都会想起那本一度被列为禁书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其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一样,塞林格自己的人生同样叛逆:他不满学校的教条式教育,三度退学。在《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青年追捧的圣经后,塞林格用得到的稿费买了一座小木屋,过上了隐居生活。2010年1月27日,J·D·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自然离世,享年91岁。许多人惊讶于这个与海明威同时代的作家居然活到了21世纪。塞林格在1967年之后就并未发表过新作品,而是选择了隐居。
当下的人们越来越喜欢把佛系、躺平放在嘴边,与其说是摆烂,不如理解为是与世界的格格不入。直到现在,不少人还是在现实中追问意义,试图寻找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恰如塞林格在作品中写尽了人与世界的撕裂感,或许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阅读塞林格。
1. 重返麦田
塞林格是一个对于中国的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许多人都听过出自他的短篇小说《破碎故事之心》中的名句: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951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在书店中常被摆放在名著区域,同一书架上往往还有《巴黎圣母院》和《复活》。《麦田》讲述一名生活在纽约的16岁少年霍尔顿从学校退学之后两天的故事,他满口脏话、酗酒、滥交,对成人世界的虚伪深恶痛绝,评价他在好莱坞取得一定成就的哥哥“在好莱坞当了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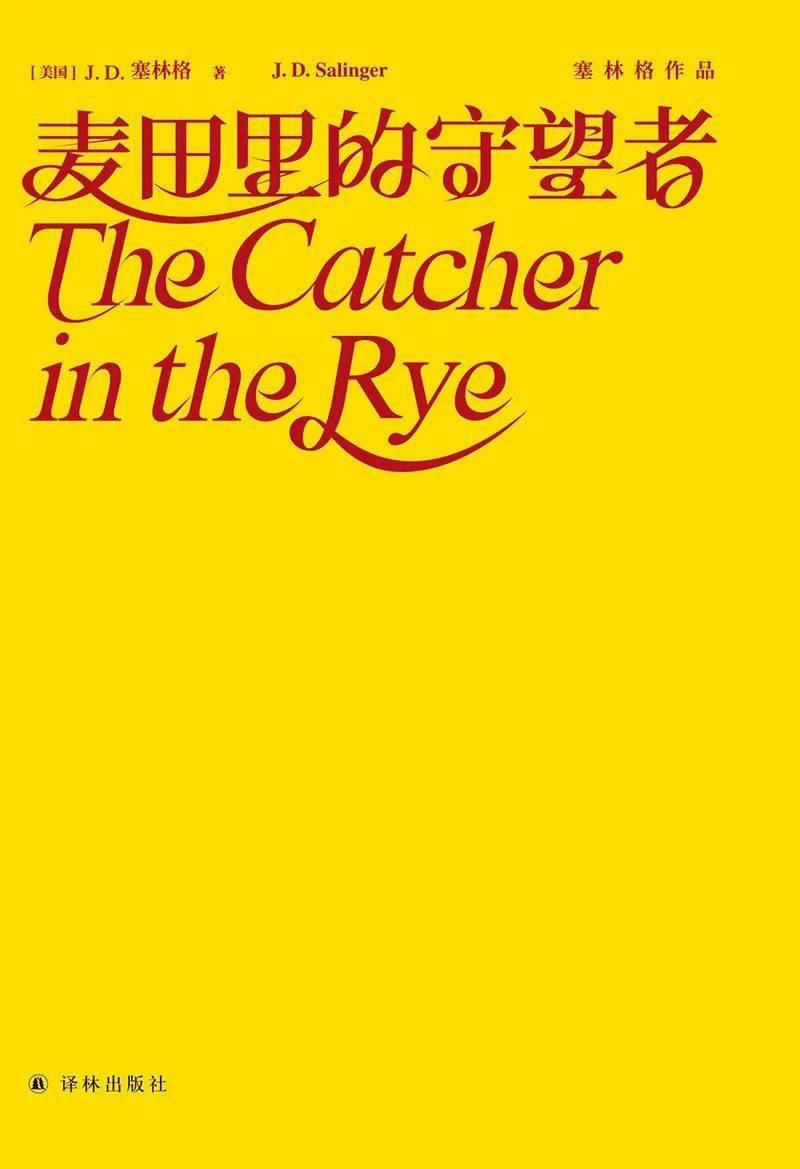
[美] J. D. 塞林格,施咸荣 译
译林出版社,2022-3
尽管塞林格有一个姐姐,家庭和睦,生活条件优渥,但他曾表示《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一定程度上有自传的成分,这里更多可能在暗示他成长过程中内心的挣扎。
塞林格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他曾上过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纽约大学主修特殊教育,半途辍学。之后被做肉类生意的父亲送去维也纳学做肉品生意,但也未能进行下去。后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写作的晚间课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塞林格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几个月后入伍,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的几场战役。在战中,塞林格在巴黎与当时任战地记者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见了面。海明威十分喜欢塞林格的作品,认为他有着惊人的天赋。后来塞林格加入反间谍工作,这段经历也为《九故事》中最著名的一篇小说《为艾斯美而写——有爱也有污秽》提供了创作的灵感。

此外,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也受到了十分广泛的欢迎与甚至超越《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评价。这部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由陆续发表在《纽约客》等文学杂志上的九篇小说组成。书中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48年的《逮香蕉鱼最好的日子》令塞林格崭露头角。1953年,塞林格发表了《九故事》的最后一篇小说《泰迪》,同年《九故事》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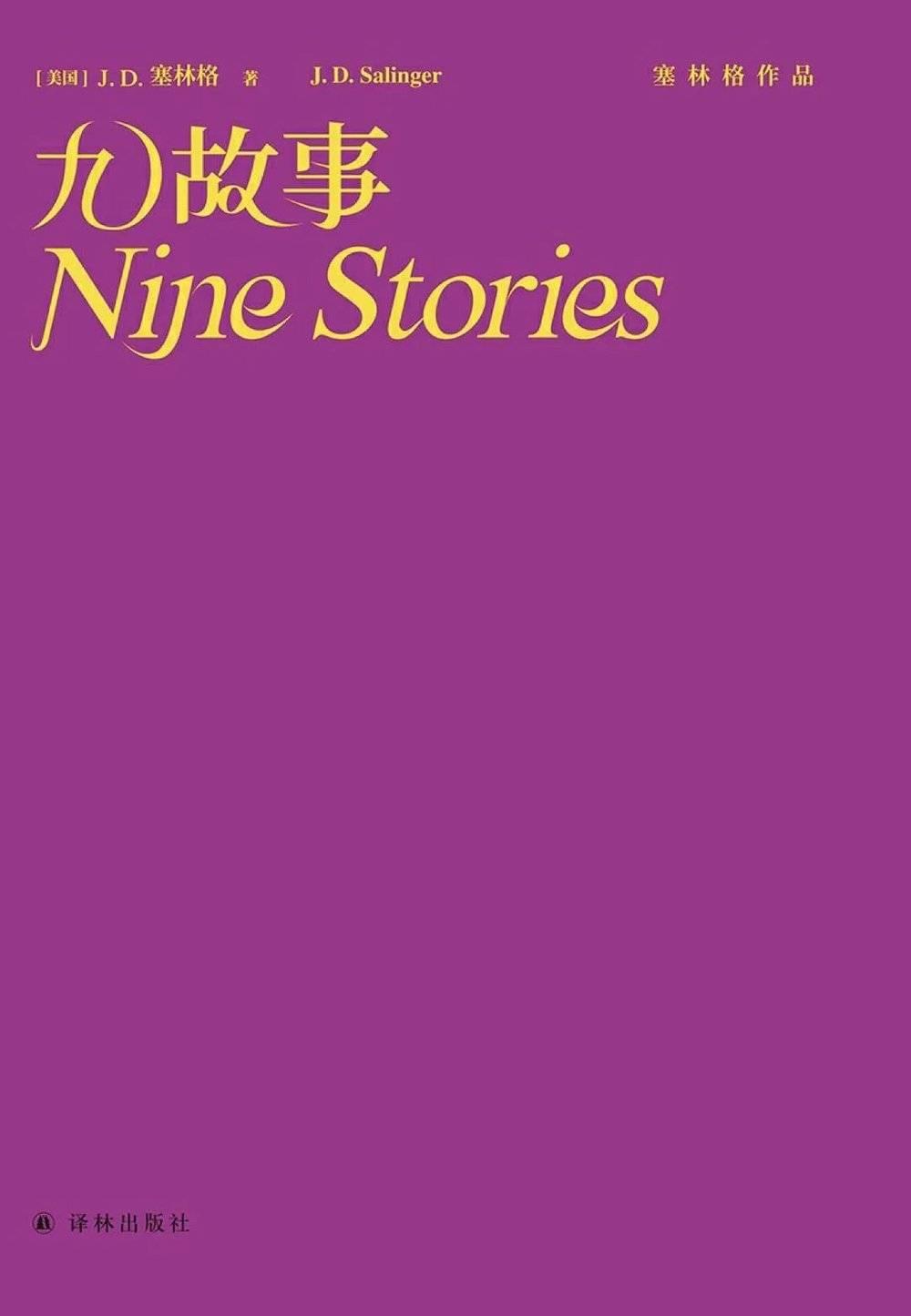
[美] J. D. 塞林格,丁骏 译
译林出版社,2022-3
这些小说的主题无一例外,都是在描写孩子与成人世界之间的互动。在这部以两个天才的死亡为首尾的小说集中,塞林格的小说开始出现关于“禅宗”的元素。
“双手击掌之声人尽知,只手击掌之声又若何?”这则禅宗公案被塞林格置于九个故事开始之前,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塞林格留给读者理解《九故事》的钥匙,“人总是习惯于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与身份,所以此生此世终有牵挂与纠缠,希望失望都在这里面酝酿与消解,确切与虚无也都会在这里面沉浮隐现,反反复复地在此中求我,在他人的眼与心中找我,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发出自己想要的声音,而这样一路下来的结果,最后恰恰是失了我,失了我的声音,所谓纠缠越深,离道也就越远了。”
2. 隐入“格拉斯”
霍尔顿对于成人世界的嗤之以鼻和《九故事》中儿童少年的纯真、机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大获成功以后,塞林格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镇,过上了远离车马喧嚣的隐居生活。
在这之后,塞林格发表的作品只有寥寥数篇中短篇小说,其中一部分结集成册出版。《弗兰妮与祖伊》与《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这两本书中收录的中篇小说都是关于一家姓“格拉斯”的人的故事。许多塞林格的死忠粉丝认为,“格拉斯家族”的故事是真正能作为映照其人生“代表作”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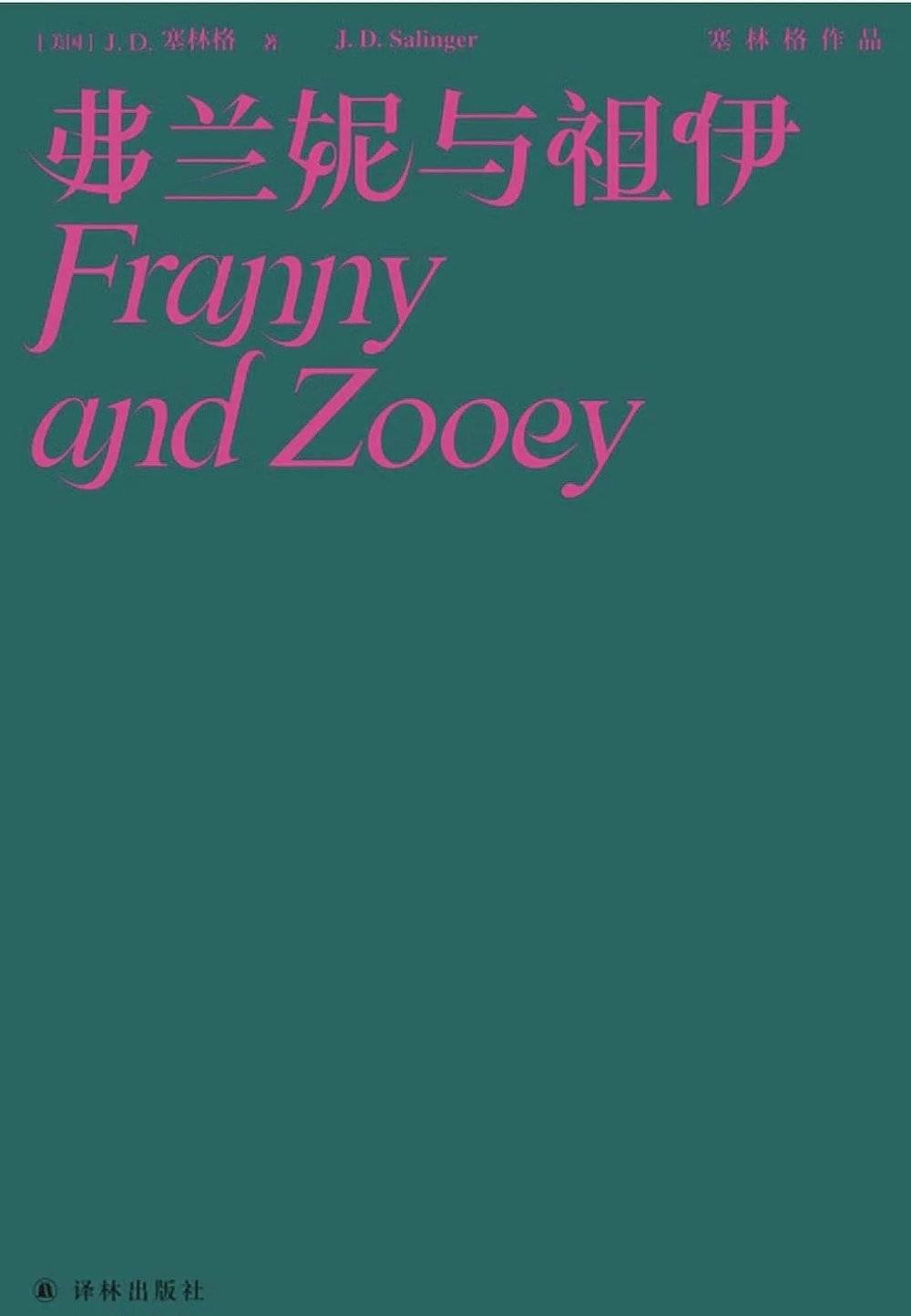
[美] J. D. 塞林格,丁骏 译
译林出版社,2022-3
塞林格退伍后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麦田里的守望者》使塞林格一举成名,但也令他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在格拉斯家族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塞林格对于隐居的向往。
“格拉斯家族”是塞林格在小说中虚构的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大家庭,这个家族出现在8篇小说里。其中大哥西摩·格拉斯是这个家庭中的灵魂人物。七个兄弟姐妹在童年时期都参加过一个广播节目“智慧之童”——一档由有着超出自己年龄的智慧的孩子们参与的谈话节目,和他们交流的时常是学者等社会意见领袖。
塞林格十分擅长创造早慧、出众的青少年形象,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自己的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演化成精神上的危机。对于这些危机,塞林格为格拉斯家的孩子们安排了不同的结局。

在《逮香蕉鱼最好的日子》里,参加过二战的大哥西摩·格拉斯在度假时选择吞枪自杀;老二巴蒂·格拉斯一个人搬进没有通电话的小屋中写作,但形容自己为“文学娼妓”。在《西摩:小传》中,塞林格暗示巴蒂就是那个文学世界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沃尔特在战争中因为意外死亡;老五波波·格拉斯走入了寻常的婚姻生活,过着“主流”的生活;最小的妹妹弗兰妮·格拉斯,在祖伊的帮助下走出信仰的危机。
有许多人认为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就是塞林格本人的化身,他们是塞林格将自己的生活分割成一片片后,重新拼贴的结果。这样的拼贴与他的写作手法也有着共鸣。格拉斯家族的故事横跨1919-1965年。塞林格十几年间陆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像一块块拼图,将格拉斯家族的往事拼凑出来,用当下时兴的话来说,塞林格创造了一个“格拉斯宇宙”。
这些不同的路径或许是塞林格曾经想象过的人生道路,比如像祖伊或者弗兰尼一样做一个演员,或像巴蒂一样进入大学教书,或者和沃尔特一样以一种荒谬的方式死在战场上。

塞林格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单篇小说往往发生在一段很短的时间之中。《麦田里的守望者》发生在两天两夜之内;《抬高房梁,木匠们》是西摩婚礼当天发生的故事;塞林格最喜欢的小说《祖伊》则有着类似传统戏剧的结构:封闭的场景,大量的对话,主人公在短短半天之内经历极大的内心冲突。
塞林格另一独特之处在于,读他的小说颇有解谜的感觉。《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开头称关于主人公背景的介绍是“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在他的短篇小说,特别是《九故事》中收录的小说里,这种“废话”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
读者常常因此一头雾水,在知乎“《九故事》”的标签下的问题,多是寻求其中某一篇或整本小说的寓意。塞林格的作品一面在故事结构上极其简洁,许多人用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来解读他的作品;另一面却絮絮叨叨,格拉斯家孩子们之间的长篇信件出现过多次,人物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日常的琐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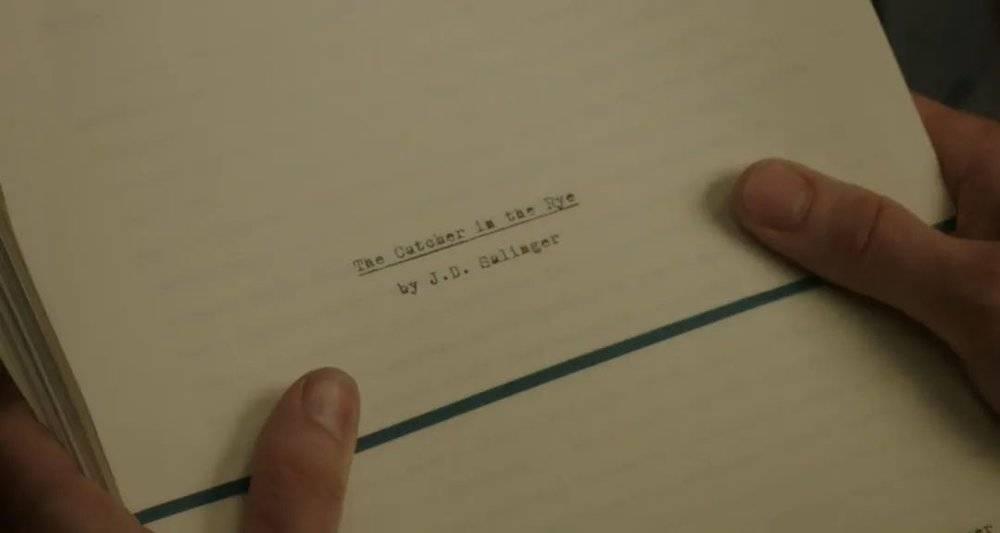
1965年,塞林格公开发表了最后一篇作品《哈普沃斯,16,1924》,占据了当期《纽约客》绝大多数版面。这是一封来自西摩·格拉斯7岁时写给父母的一封长信。自此,塞林格再未公开发表过任何作品,也极少与外界往来。
3. 塞林格的咒语
塞林格在194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到东方哲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后的美国青年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的答案在人们的眼中逐渐模糊。无法摆脱战争带来阴影的塞林格同样十分渴望一份心理的安宁,但是从他小说中提出的近乎偏执的问题看来,安宁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求。
1955年,塞林格发表了《弗兰妮》。

这部短篇小说中包含的问题十分尖锐,弗兰妮对于文学、自我、爱情的疑惑一步步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此时她又因一本书经历着信仰上的危机。塞林格持有的态度或许是悲观的。
“这群年轻小伙一开口都是清一色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腔调,不管轮到哪个说话,没一个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陈词,就好像是在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极端有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大学外面的那个世界一筹莫展,已经瞎忙活了几个世纪。”
没有留下任何回答,甚至回答的尝试,小说以弗兰妮的昏厥戛然而止。第二部分《祖伊》发表于1957年,塞林格试图通过祖伊对于弗兰妮的开导来解释一种观念:天堂就在人的心中,而不在任何于自我之外的地方:“我们他妈的又笨又多愁善感又这么没有想象力,所以才看不到天堂”。孤掌何鸣?塞林格从《九故事》到《祖伊》中一直在试图给出他的解释。他在自己编造的迷宫中不停地寻找着一个出路,在《弗兰妮与祖伊》中,塞林格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说法。

塞林格的作品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不仅仅是“经典作品“的光环,而是关于意义的困境在当下依然存在,甚至更为突出。互联网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浪潮、去中心化技术兴起及贡献了众多科技奇观的人工智能都冲击着这一代的人们,没有人知道未来将要走向何方。许多在时代潮头的人们的手机上都有冥想软件,试图从已在硅谷风行多年的佛学,特别是禅宗中找到一些安宁,或者说是答案。
塞林格对于东亚的文化十分了解。在《抬高房梁,木匠们》的开篇,西摩用“伯乐相马”的故事哄弗兰妮睡觉。《西摩:小传》中对中国、日本古典作品的大量引用也表明了其对东亚文化的研究。对于东方文化,西方人通常认为这其中有着难以跨越的底层思维的壁垒。德国哲学家奥根·赫立格尔曾在日本学习禅,在他的记录《箭术与禅心》中,他写道:“禅理藏在不可见的黑暗中,就像是东方的精神生活所酝酿出来的奇妙谜语:无法解释而又无可抗拒地吸引人。”

百年之前人们的困扰和忧虑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减退,依然有许多获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们沉浸在身心灵的修行中,寻求一些他们也说不清的东西。于是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对塞林格充满着好奇和认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王一恪,编辑:张文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