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蓝观 (ID:mic-sh366),作者:李昀/吴妮/澍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来没有一种药,像辉瑞的Paxlovid一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从医药圈人士处破圈到中国二三线城市的老百姓。
2022年岁末,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后,巨大的感染基数,重症人数的增多,让Paxlovid这种迄今为止效果最好的新冠口服药以“救命药”和“特效药”的面貌,成为中国民间的高价疯抢的“标的”。
在过去一个月,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完全没有储备Paxlovid,有货的医院,数量极少。广西某县城的一家公立医院,只有一盒Paxlovid,药剂科主任不敢告诉呼吸科主任,被问起时,回答:“只能院长批准才能用”。在民间,一盒医保价只有1890元的Paxlovid,一度疯涨至过万元。
但医院里的Paxlovid,和民间千金难求的Paxlovid的命运却几乎一致:有严格适应症的药,有的被用在不该用的病人身上,私人千金购买的药也因为缺乏当地医生的指导,而不敢给感染者服用,而束之高阁。
Paxlovid的被浪费和被错误使用,不仅存在于医疗资源不甚发达的地区,甚至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也大量存在。
即便过去半个月,Paxlovid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新故事:因价格问题未进医保、它市场上而非疗效上的竞争对手要么进医保,要么初次定价就遵循最新文件,默沙东的莫努匹韦价格是Paxlovid的一半;另外,一些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陆续到货Paxlovid或阿兹夫定,但P药的炙手可热依旧没有改变。
在大多数人们都会加入一两个的“买药群”里,黄牛依然活跃。只是默沙东在中国获批了以后,P药黑市价立刻下降了一些,由1万多元下降到9000多元,默沙东的M药只有不到一半——3000多元。
但即便如此,一般求购者首选还是辉瑞原版,买不到的话才买默沙东、阿兹夫定,以及辉瑞仿制和默沙东的仿制药。
直至春节前,P药仍呈现一药难求的局面,然而,不仅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就连广西、东北等地区,这些“来之不易”的P药,并没有真正送到需要者的手里,甚至有被扔掉的现象。P药滥用的背后,也有一些医药行业发展不完善的影子。
北京:许多P药用于危重症和住院病人
2023年1月中旬,北京已是中国Paxlovid供应最充足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医疗机构,Paxlovid使用起来限制颇多。
北京的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已经投入使用Paxlovid,不仅要求患者满足65岁以上、有慢性病、处于发病前五天等条件,还需要是该社区的居民。
问题是P药没有覆盖所有的北京社区医院,这意味着一些社区的群众还不能通过这一渠道获得P药。北京一家没有P药的社区医院表示无法提供用药指导,建议患者咨询能够提供P药的社区医院。
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急诊分诊台的医护人员表示,除非住院,门诊很难开出Paxlovid。
买到P药后,合理使用十分关键。
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提到,P药的适用人群是发病5天以内的轻、中型且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年患者。对于初次诊断重型新冠患者,和新冠症状出现5天后的患者,Paxlovid的循证依据都不足。
如今,P药的临床投入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P药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依然存在。
但一方面是医院在临床中发现P药存在新的适用情况,《中日医院成人Omicron病毒感染初始诊疗方案》提出:对于发病超过5天的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推荐基于核酸检测结果进行。如果核酸持续不转阴,可延长给药时间。不过,也有医院坚持在发病5天内使用抗病毒药物的建议,各大医院的诊疗方案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临床是动态的,重症患者家属可能抱着殊死一搏的心态,央求医生开P药。广东某医院的一位ICU护士说,即使医院不开,患者也会自己买。有的患者住院自带P药或者P药仿制药。患者去世后,这些没有发挥作用的P药被遗落在医院,我们只能销毁。
上海:被“荒诞”的规定浪费的P药
近日,上海社区医院的辉瑞口服药Paxlovid资源已经呈现出供应紧张的状态。据了解,一些社区医院的P药库存已经见底,甚至断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沈璐(化名)在很多人看来是幸运的。她的母亲今年76岁,感染了新冠,但户籍所在地的崇明区长兴镇社区医院还暂时有P药储备。
然而,老人却没法通过这一渠道获得药物。
一开始老人没有任何发烧、咳嗽等最常见的新冠症状,只是觉得胃部不适,感到恶心。到消化科就诊后,由于考虑到家中成员除老人外都已感染新冠,医生推荐老人做肺部CT检查,怀疑胃部症状是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检查结果显示,老人已经出现肺部感染症状。
尽管出现显著症状的时长是在5天以内,但老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老人已经虚弱到没法下床了。在联系各大医院寻求住院未果后,沈璐最后托熟人在浦东区一家二级医院找到了床位。住院后,沈璐发现治疗药物大多为抗生素一类抗炎症的药物,缺乏针对病毒本身的治疗。
沈璐听说P药有阻止病毒复制的效果,而且母亲符合P药用药人群范围。她希望医院能开一些,但医生却表示,现在医院已经没有这种药了,需要病人自己去找货。
根据目前上海市政策,65岁以上且发病时间在5天以内的病人,可以到户籍所在的社区医院申领P药。但现在老人正在住院,无法本人到场社区医院开药——这成了获得P药的最大障碍。“医生说你住进来了,就不可以随便出去。要出去就必须办出院手续。而且现在开药都是跟着住院记录走的,你在什么医院就必须在这里开药。”
长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表示,像沈璐母亲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没法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开药必须本人到场,不可以家属代领。我们这里一共就还剩十几盒药,怎么能随便地交给一个不符合领药条件的人?”
沈璐感到很矛盾。“我们当时是靠关系进去的,现在又闹着要出来,这算怎么回事?这还不是最麻烦的。现在床位这么难找,我们一旦离开医院病房,就意味着要自己负责老人的病情了,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实在承受不起。为了一盒P药,值得么?”沈璐声音疲惫地说。
在思想斗争的几天时间里,沈璐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一些消息,让她最终决定放弃寻找P药。
“我弟弟咨询了几个相当权威的专家,都说P药有很大的副作用,我们担心母亲会吃出什么毛病来。而且我朋友家的老人,虽然吃了P药但没有明显好转,最后发展到了重症。”
之所以这些消息对沈璐而言如此重要,是因为她并不信任住院医生对P药使用的建议。老人入住的是骨科病房,三张床位里有两张都收治的是新冠病人——由骨科医生负责。
“现在医院各个科室的病房都在收新冠病人。虽然我听说他们这些骨科医生接受了新冠治疗的培训,但是感觉这些医生还是差点水平。我们问医生要不要用P药,感觉对方也是模棱两可,搞得我们越来越拿不定主意了。”
当沈璐回顾这一道P药选择题时,忍不住发出感慨:“本来我和家人的预想都是很理想的,觉得现在社会上有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真的经历下来之后,感觉一切都特别混乱。有床位的地方没有药,有药的地方没有床位。”
沈璐本来还想着要不要通过网络上的渠道买一点P药,但一想到有可能引发副作用,而且到货了可能老人已经过了最佳使用阶段了,就决定不再执着了。“我就觉得算了,太折腾了,还不如安安静静地守在老人身边,随时注意她病情的进展。”沈璐说。
然而,即使是既有床位、又有P药的三甲医院,也没法在最佳时间使用P药。
即使是作为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上海市浦东医院,在使用P药的初期也存在不合理情况。据统计,2022年4月至6月,浦东医院使用Paxlovid的病例共计203例,其中136例用药不合理,用药不合理率达67%:浦东医院有16例首诊为重型、危重型患者使用了Paxlovid抗病毒治疗。3例患者在症状出现5天后用药,最长在第10天开始用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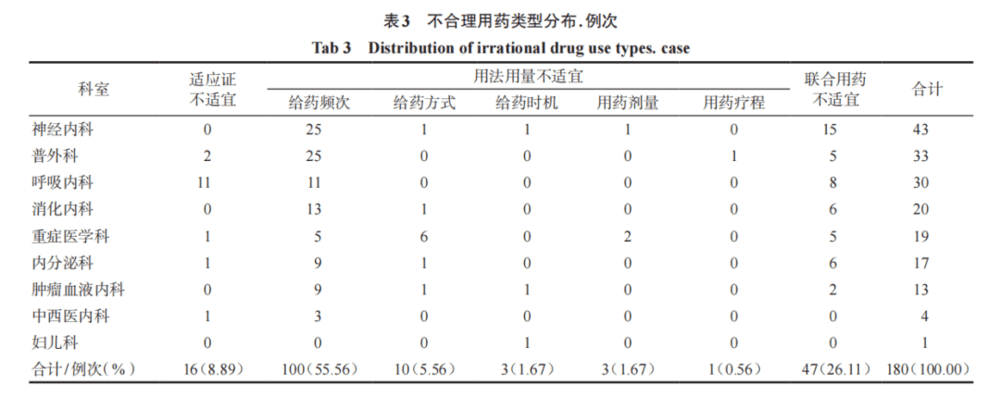
上海一名著名大三甲的医生表示,虽然P药的最佳使用时间是发病5天以内,但有些病人时间超过了,或者已经是重症的,核酸还能测到阳性的,也会因为机制上的合理性而为病人使用。
“比如我接了一个本部过来的病人,就看到他医疗记录里,最开始并没有用,可能各方面原因,然后6.7天复查CT,报了肺部进展,把P药给加上去了,其实并不是最科学的。”这名医生说。
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情况,让医生没有办法根据诊疗方案中的推荐标准进行开药。上述医生提到,理想情况是:病人一般出现症状之后立即做核酸或抗原检测,医生可以比较准确判定发病天数。但是“有些病人即使出现了症状,屏了好久,再去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灵活的范围了。”
出现症状和核酸阳性之间存在时间鸿沟——这个问题不只是患者个人的检测意愿导致的。“我们其实只是做了抗原,然后结合CT结果,认为老人是得了新冠。实际上,我们住院的时候,医生根本没有要求我们去做核酸,他说就按肺炎来治就行了。”沈璐说。
沈璐的母亲现在下不了床,家属甚至不知道医院里哪里可以做核酸,没有医生建议主动为患者进行检测。沈璐推测:“我估计跟乙类管控有关,因为测血常规就是能判断是不是受病毒感染,现在就是稀里糊涂。”
广西县城:P药只有一盒,要院长同意、必须是ICU病人才可以用
小杨(化名)的父亲70岁,有高血压、高尿酸等基础病,之前几次冬季感冒都曾发展到肺炎住院。生活在广西某县。
抗原阳了之后大约七八天,小杨的父亲仍然头痛,咳嗽还加剧了,于是住进了离家近的中医院。CT显示肺部感染明显。医生开了炎琥宁注射液,还有止咳化痰药。
小杨之前听说过P药,向呼吸科主治医师咨询父亲能否用。主治医师表示自己没听说这个药,看过小杨用手机查到的相关信息后,她说可以试试。
小杨在网上看到一份有P药供应的全国公立医院名单,发现其中包括本县人民医院。打电话去问,医院却只承认有阿兹夫定,不承认有P药。她又通过在医院工作的熟人打听,答复是“确实有一盒辉瑞”,但被预订了、不能轻易动。
“我就心想先转过去,边治边说,反正有阿兹夫定保底。”小杨当时想。
人民医院呼吸科已没有病床,辗转之下,小杨的父亲住进了其他科室的病房,由呼吸科医生指导该科室医生治疗。
成功转院第二天,小杨再次找医生谈。“科室医生很耐心,说有这个药一定帮我开,但是查了几次内部系统都没有辉瑞这个药,问我是不是了解错了,让我去找呼吸科医生确认。”她回忆,“呼吸科医生说并不知道医院有这个药,也查不到,让我去药房确认。”
“药房一开始说没有,我很确定有,让他们再查一下。可能有人查到了,就有些言词闪烁,说这个药他们药房没法做主,要问药剂科主任。”
最后,药剂科主任与呼吸科主任电话沟通后给出答复:P药全院只有一盒,要经过院长同意才行,而且必须是ICU病人才能用。
“能用上阿兹夫定已经算很幸运了。”医生宽慰小杨,因为阿兹夫定供应也非常紧张。
最后,父亲服用了6天阿兹夫定,身体好转,就停药了,很快出了院回家休养。
后来,小杨自己转阴后一直咳嗽,去发热门诊就医,医生说没有新冠特效药,给她开了3盒治疗带状疱疹用的阿昔洛韦。
北方某县级市:没有医生知道怎么用
一位92岁的老人,身患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她属于新冠疫情中最高危的人群。她的儿子、儿媳都是当地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获取医疗资源和信息相对容易。当她出现感染症状时,情况并不严重,只是有些低烧。因为当地送到医院去的是高烧不退乃至昏迷的老人,因此,儿子和儿媳并没有太当回事。
但她在外地工作的孙女,了解老年人感染新冠后的“沉默性缺氧”,表面上症状并不明显,但如果血氧度低于90以下,需要住院。她的一位朋友的奶奶,也是92岁,当天只有一些轻微的咳嗽,第二天一早就过世了,她印象很深。她让父母用紧急买的血氧仪检测奶奶的血氧,已经降到了80多。因为医院住院人数爆满,家里正好有氧气瓶,赶紧给老人用上。
在此期间,孙女花三千多元从朋友处抢到的辉瑞P药也寄到,她的父母紧急问医院的同事,呼吸科主任。但不管是呼吸科主任还是急诊科主任,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这种药,更不知道怎么用。因为医院并没有这个药,因此更不会有相关的培训。
一个热心的医生,仔细看了说明书,看到用药禁忌,而恰恰这位老人服用的药属于其中,需要减量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医生建议不用。因此,高价买到的辉瑞P药,仅仅被用了一次,就束之高阁。
一家人在极度的焦虑中,观察老人的血氧饱和度。老人的血氧上上下下,相熟的医生也没了主意,推翻“不用”的建议,让家属自主选择——这距离老人出现症状已有一周的时间,已错过了感染五天之内使用的建议。幸运的是,老人最终的血氧饱和度回复到了90以上。
美国:另一种意义上的浪费
在美国,治疗新冠,医生需要严格遵循诊疗指南。轻症患者使用的是被紧急审批的辉瑞P药,默沙东的M药也在诊疗指南上。但在现实中,因为两者的数据相差甚大,绝大多数病人使用的是辉瑞P药,只是少数不能使用P药的才使用默沙东。
而在危重症患者治疗上,美国的诊疗指南推荐的是瑞德西韦。“在病毒学的概念中,感染五天内是病毒复制期,过了5天之后,是炎症反应期,Palovid在5天后就没什么作用了。”南加大重症室主任乔立人表示,在危重症治疗中,没有医生会给病人使用辉瑞P药。
2022年7月,FDA修改了Paxlovid的紧急使用授权,药剂师也可以开出此药处方。
美国政府也以每疗程约53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数百万疗程的Paxlovid,这是辉瑞的批量采购折扣价。
有症状的民众可以登陆一个网站,经过线上问诊开方,免费获得P药,线上护士问一下出现症状的情况,出现了多久后,不用问询者出示任何测试结果,就可以开出P药,民众可以到附近的CVS等药房里取。
因此,一些并没有症状的患者为了安全,也会上网站上谎报症状拿药。药对民众是免费的,药房和开处方的护士或医生也能赚到钱,开P药非常简单。但很多民众囤了免费的P药之后,也没有用上,就当垃圾扔掉了。“反正买单的是拜登政府,没有人会心疼这种浪费。”一位医生开玩笑说道。
为什么在中国对P药的使用无统一标准?
在中国,医生开药并没有一套限定死的方案。医生开药首先遵循的是“循证”,这类文件一般由行业协会或者各种医学组织指定的治疗方案,通常叫XXX治疗指南。因为是一种全国通用型的版本,所以这种治疗方案常常以保险和安全性为原则
但指南大多是时候起到的是教科书式的作用,并不能完全覆盖掉临床药物的使用。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用药风格,而真实世界里病人情况千差万别,也不是一两套诊疗方案能完全限定死的。所以,医生在临床上到底会如何开药,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指南+经验的结果。
医生的主要KPI是治病救人和学术晋升,“学习新药前沿知识”并不直接体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医生除非遇到“无药可用”的情况,否则不会主动去了解一款新药的临床使用。因此,某个治疗领域的指南发布距离临床大面积应用,中间隔的时间往往按年计算。而推动一款新药在临床使用的主要推手,其实是制药公司。
回到P药的临床教育上,前段时间有新闻提到,北京和上海一些类似医联体的机构在线上培训Paxlovid的使用。这种学术会议大部分是学会发起,但是牵头者是药企,医药上市公司高额销售费用里有很大一块比例就在于此。
而另一边,虽然早在2022年3月份第九版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纳入了Paxlovid,但一来彼时中国还未完全放开,新冠患者人数规模本就不大,重症患者几乎没有。院内基本也没有P药的用武之地,制药公司也就没有推广的场景和必要性,医生也就压根不了解P药到底该如何用。
二来,此次疫情防控的调整比较突然。对于辉瑞本身,立即招聘相应的医药代表,让代表进院教育以及在各市县区组织学术会议都需要大量时间。此外,疫情高发导致的科室内从早到晚连轴转,也减少了医生去接受P药具体用法的接触场景。
当然,辉瑞可以在短期内通过砸钱、砸人力来大幅提升学术教育的活动。但一来供货情况严峻之下,短期大规模投入很难得到什么大的回报;二来,价格和医保带来的可及性这两块,都存在压制因素。辉瑞缺少动机。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次新冠疫情重症感染书骤增,大量病人涌入急诊病房,以至于很多其它科室也不得不加入到呼吸重症的治疗当中,其中甚至出现妇科和儿科的病床用来住新冠肺炎患者。呼吸科和感染科对P药也都只是“初见”,其它科室更是因为机理不同,理解起来虽然不说有千差万别,但也有不小的障碍。
种种原因,造成现在很多临床医生虽然是新冠患者的直接救治方,但具体对于一款新药的适应证、用药禁忌、服药细节、不良反应处理等等,完全做不到面面俱到。
这背后的一个宏观原因,一方面还是“临床诊疗”是一个很难被标准化的过程,需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另一方面,我国在诊疗标准化的路上,做的工作也不够。
在医药代表进入中国之前,医生要学习新药知识,只能每年申请中华医学会一年举办一次的用药培训会议,很多医院的名额只有个位数。后来随着制药行业逐渐成熟,各种年度、季度学术论坛遍地,每家药企也会牵头去开科室会议,但这需要一家一家去做,没办法在全国范围内一劳永逸。
很多时候,一款创新药物进医保两到三年后,在一些小地方的三甲医院甚至看不到这款药;不少像心血管、糖尿病等慢病领域的产品,用得最多的还是上个世纪的品种。
这是药品流通领域的难题,也是医疗体制的历史难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蓝观 (ID:mic-sh366),作者:李昀/吴妮/澍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