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陌生人的力量》 ,作者:[美] 乔·基奥恩,译者:傅岳竹、孙敏唯,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原文标题:《序言:出租车里的陌生人》,题图来自:《与陌生人共舞》剧照
首先,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陌生人的故事。
几年前,我有幸在楠塔基特岛上度过了两周,参加编剧家们的一个活动。我和另外三个作家共居一室,磨炼写作能力,和同行见面交流。此间,我们抽空参加了各种聚会,悠闲自如地享受美酒佳肴。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的聚会刚结束,四个人走到外面,等着搭出租车回去。我告诉几位作家,尽管我从事的纸媒体可能真的江河日下,逐渐被人们遗忘,尽管我的未来、我的希望以及我的梦想一片渺茫,但我也不会牺牲这种体验来换个行当,因为这份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既可以和陌生人交流,也能顺道养活自己。
我接着说,和不认识的人说话时,你会发现他们都有金子般的闪光点,每个人至少会有某个观点或给你带来惊喜,或让你不禁莞尔,或让你感到震惊,或让你深受启发。陌生人通常不需要什么激励就会告诉你一些事情,有时候这些事情会让你走向深刻,让你重新获悉人类多彩而富有魅力的经历,抑或让你设身处地地体味到他人的痛苦。陌生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展现了他们独立的精神世界。当你被允许走进他们的世界时,你可以内化其中的养分,让自己获得成长,由此变得更有智慧,更能感同身受、理解他人。
出租车终于出现了,司机是一位老妇人。我们几个迅速挤了进去。我刚才说过,我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现在我想让朋友们看看我的本事。(如你接下来所见,我对出租车司机有一种特别的好感。)于是我开口问女司机在楠塔基特岛生活的情况,她娓娓道来。接着我问了些其他事,她对答如流。谈话渐入佳境,她对我们的交谈感到舒适。短短20分钟的车程,她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她出生于曼哈顿上西区,生来便享有荣华富贵。当她还小的时候,当地上层社会盛行一种病态的风尚,家家户户随大溜,纷纷捆绑孩子的小腿,而她的父母也不外如是。她解释说,当时人们认为,小孩子的腿要是没有被捆绑过的话,就显得不够优雅。社会名流如果被人看到和这样的孩子待在一起,则会深感羞辱。凡此种种,不过是为了让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免遭羞辱罢了。
父母出于无知捆绑了她的小腿,她却因此落下残疾,不能正常行走。我不禁开口问道:“当你的父母意识到问题时,他们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吗?他们咨询过外科医生或理疗师吗?他们试图弥补他们所造成的伤害,让自己的亲生女儿恢复正常的行走能力吗?他们为此向你道歉了吗?”
出租车司机说:“没有。”
“那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带我去上舞蹈课。”
“天哪!”
我惊讶道,“他们为什么让你去上舞蹈课呢?”
她回答道:“因为他们想教我更优雅地摔倒。”
读者朋友们,我的祖父、父亲和兄弟都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爱尔兰天主教殡葬师。这样的成长背景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幽默感,我种种情绪皆源于此。我想说,关于人类的悲惨境遇,我这辈子从未听到比这更精妙的总结了——就在这个夜里,这个陌生人向我讲述的一个发生在大西洋小岛上的“搬起石头砸到自家孩子的脚”的故事。
那次交谈后,我开始思考关于陌生人的种种问题。为什么我们不与陌生人交流?我很好奇。我们什么时候才会与陌生人交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实际上,除了工作需要,我在外确实没有和陌生人交谈过。我有这份工作,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所谓的去平衡工作和生活经常感觉像是一场消耗战。我几乎没有时间在可以与陌生人交谈的场所驻足流连,也没有精力去和他们细细交谈。即使我真的挤出半个小时待在酒吧或咖啡馆,我也不跟人开口攀谈。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事与愿违。
我估计是因为我的大脑有点短路了,对此,有小孩的父母估计都深有同感吧。我通常独处一隅、畏葸不前,要么翻看闲书,要么一直内心毫无波澜地浏览着手机信息,几分钟后,我就完全记不得在手机上刷了什么了,这种感觉很不好。结果是,我不再和他人说话,哪怕眼神交流都觉得多余,因为眼神交流让人感觉像是一件苦差。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让自己从与他人的交流中退出真是易如反掌。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毕生都在研究城市,他一直提倡一个叫作“摩擦”的理念,也就是促使你和陌生人互动的低效率事件,比如向屠夫询问烧烤技巧,向路人问路,或者打电话订比萨。这些行为看起来微不足道、多此一举,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与陌生人的互动越发没有必要。
我怀疑,这样的技术进步正在削弱我们的社交能力。我自己便是个典型。即使便利店收银员那里没人排队,我也总选择自助通道结账,这是为什么呢?当店员问我打算买些什么时,我为什么会烦躁不爽?虽然我很清楚,陌生人会告诉我的事情通常比推特上流传的蛊惑人心的信息泥石流有趣得多,但为什么我还是沉溺在自己的手机世界里,不和陌生人聊天?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不大清楚,但我确实没再和陌生人交流。对此,我的感觉并不太好。
尽管如此,在一些时候,我最终还是选择和陌生人交谈,就像在楠塔基特岛上,我们相谈甚欢,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从中学到新的观点、了解到有趣的见闻、领会到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当然,也听了一个好故事。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这让我如释重负,尽管这话说出来很奇怪,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我的脑海,甚至渗透到我的日常工作中。有一次,当我采访演员艾伦·阿尔达(Alan Alda),问他怎么向科学家传授沟通技巧时,我就提到了那次与陌生人交谈之后奇怪的解脱感。听到这一点,他面露喜色。“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我来说特别明显,”他说,“以至我想知道为什么与他人交谈不是一种正反馈。为什么我们不能本能地去与人交流呢?”
是啊,人们为什么不能本能地去和陌生人交流呢?
人们一听说是陌生人,就感觉来者不善。著名乡村歌手默尔·哈格德(Merle Haggard)没有给他的乐队取名为“陌生人”,因为他想让我们相信乐队成员都是好公民。如果他真的把乐队取名叫“陌生人”,那是他想告诉我们乐队成员很危险。
希区柯克的电影《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讲的并非在火车上邂逅一个浪漫的伴侣,或是认识一个新客户、交到一个新朋友,也不是在旅行中和人展开激烈对话而拓宽了思维。电影讲述的是,如果你不小心,一个外表迷人的精神病患者就将把你卷入谋杀你的妻子、害死他的父亲的阴谋中。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最初的名字并不叫《内心深处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Within),因为被关在一个岛上的痛苦经历激发了英国男学生最好的一面。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陌生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讲述的并非一个阿尔及尔人来到法国,向当地人介绍阿尔及利亚丰富的饮食和文化传统,并过上了美好生活的故事。相反,小说的主人公几乎与世隔绝,甚至对自己都感到很陌生。当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无动于衷。在一次意外中他失手杀了人,他思考着在行刑那天,他面对绞刑架时,一大群观众冲他发出仇恨的叫喊声,这是唯一一件能让他感到不那么孤独的事。事实上,他堪称史上第一个“网络喷子”。
自从有陌生人这个概念以来,我们就一直对陌生人抱有畏惧,即使有些人看起来友好,我们依然觉得他们毫无逻辑、背信弃义、道德败坏、身心不洁。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产生。随着乡村、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这种观念逐渐深化。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一时兴起“陌生人是危险的”这个观念。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也不能免俗,将地铁乘客描述为“一群随机的陌生人,其中一个可能是连环杀手”。甚至在2018年,富饶的佐治亚州哈里斯县的一名警长还当众树立了一个警示牌,上面赫然写着:“欢迎来到佐治亚州哈里斯县,我们的公民都有武器防身,一旦你杀了人,我们就可能会杀了你。我们有1个监狱和356块墓地。祝您旅程愉快!”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难以与陌生人相处。西方正遭遇着广泛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是因为陌生人不断迁移进来,这些人与西方文化并不契合。他们为了逃离战争、连年贫困和当局暴政,来西方寻求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寻找充分发展的机会。这给许多西方人造成了归属感和自我认知的冲击。
随着这些新面孔纷纷出现,我们对陌生人本就有的恐惧变得越发强烈,他们遭到当地人的一致抵制,由于人们缺乏相互理解,反对呼声声势浩大。根据几项民意调查,西方人过分高估了移民的规模,也过分低估了新移民融入新国家的能力。
另一方面,政治两极分化、种族隔离、阶级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已然将一国的同胞变成陌生人。事实上,在美国,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忍受彼此的目光。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目前政治党派对于敌对党的看法比近2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负面”。三年过后,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称,“分裂和敌意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双方党派都有越来越多的拥趸认为对方阵营成员比自己更没有道德,思想更狭隘。双方都不知道如何理解对方,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尝试去理解。
跨越党派的友谊越发少见。两极分化使他们各自为政,双方不仅不愿意开诚布公,而且懒得顾及对手,哪怕细想一下他们那缺乏意志、毫无同理心、没有积极性且低智、邪恶、愚蠢的废物对手(对手甚至称不上人)都会感觉在浪费时间。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的政治环境不断要求我们与同党派的人团结一致,但同时我们也会产生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很危险。研究发现,在美国和英国,有很多人感到孤独,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孤独程度甚至超过了老年人。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孤独对人的危害不亚于吸烟,成为真正威胁公共健康的因素。
孤独的原因错综复杂。当科技减少我们和陌生人交谈的需要时,我们的社交能力就会减弱,同时结识新朋友的能力也在削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我们离开了熟悉的亲朋好友,身边是一群又一群陌生人,这让我们很难与街坊邻居产生联结感。随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数百万人迁移流动,当我们和邻居交谈时,可能就像和身在印度的陌生人交流别无二致。这创造了一种现象,政治学家克里斯·拉姆福德(Chris Rumford)称之为“陌生感”。
“对于那些日常生活中我们亲近的地方,我们可能不再感觉完全为我们所有了。”他写道,“我们居住在当地社区,感觉到街坊邻居生活在一起,但并没有觉得大家有多么团结友爱,这种感觉不像是待在社区……我们不再确定‘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很难分辨谁是‘我们’的一员,谁是外部成员……陌生感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对他人来说也可能就是陌生人。”
当然,不只是大城市有这种状况,小城镇也无法置身事外。在城乡小镇,人口迁移和社会经济因素形成合力,造成深刻的变化,甚至可以使我们的家乡变得面目全非,倒是我们自己,在土生土长的地方竟成了陌生人。可以料想,当环境日益多元化时,和新来的陌生人交谈会让我们焦虑不安,这无关彼此的政治倾向。有时,这种焦虑让我们避免与不同人群甚至是自身群体交流接触。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感到漂泊无根,仿佛脱离了周围的世界。“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的环境。”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生前如此写道,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孤独,“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职业模式、居住模式、死亡模式、社会政策也发生变化,数百万人早已感受到长期的孤独,而世界上许多地方采取的生活方式让这种孤独感更为严重。”
在过去的200万年里,陌生人之间大多关系不善,有鉴于此,有人愿意和他们搭话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我们做到了,我们也必须和陌生人交谈。因为没有陌生人,我们将一事无成,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便是铁证。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当然知道人类彼此造成了何种伤害,我对此深感绝望。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0年后,我再次震惊于这种伤害是多么没有必要,毫无意义和道理。对我来说,智人常常是一种极度混乱、自相矛盾和自带毁灭性的生物。
然而,我生命中一些让我快速成长的经历都得益于和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那是在大学期间,我在费城郊外的一家乐器店里弹着贝斯,这时走进来一个戴着牛仔帽的中年黑人。他看着我,又转头看着贝斯,最后看向我,慢吞吞地说:“你这臭小子,看起来倒有几分柯南·奥布莱恩(ConanO’Brien)的样子。”黑人当即雇用了我,邀请我和他组建的12人放克乐队一起演奏。之后,我们一起去费城附近的俱乐部演出,再后来,我们前往浸信会教堂参与福音演出。我是乐队中唯一的白人。
对一个从白人生活区走出来的20岁年轻人来说,从接受年长音乐家的指导到去教堂演出,再到亲身感受人们对我这位白人异教徒的热情款待,这些经历非常重要,对我界定自己的身份以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毕业后,我在一家书店发现某本书里夹着一张奇怪的传单,传单上写着一个新的刊物在寻找作者。这让我深受触动,所以我给联系人发了电子邮件。虽然这份刊物最后没有出版,但联系人碰巧是一家小型周报的发行经理,我们成了朋友,然后成为室友,他把我介绍给报社的编辑,我开始为报社写作,几年后我就开始经营这家报社,那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所以说,和陌生人交谈有利于做生意,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如果不是那张传单,我根本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如果在此不提那个爱尔兰同事,我就有点愧对良心了。我进入报社大约一年后,一个爱尔兰同事拉着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在现场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后来他成了我的朋友,我又碰巧遇到了他的同事,他这位同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和我4岁女儿的母亲。前几天,当我和女儿谈到“陌生人是危险的”这一话题时,她告诉我:“爸爸,有些人可能害怕你,但我不害怕,因为我认识你很久了。”
此外,我的父亲埃德(Ed)和母亲琼(Joan)都很擅长与陌生人交谈。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交朋结友:家里来客时,假期出游时,在餐馆吃饭时,走在路上时。结交新朋友,联系老熟人,对他们来说是永无止境的。许多老年人也许会消极地坐在家里,社交圈不断缩小,而我的父母却总是乐此不疲地结识新朋友。对他们及其许多朋友来说,人活着就要和陌生人交谈。
毫无疑问,因为陌生人,我才是我,行我所行,想我所想,居我所居。然而,现在我却坐在酒吧里,离另一个人只有几英寸远,低着头,垂下眼帘,沉默不语,把脸埋在手机冰冷的蓝光之中,并且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们为什么不和陌生人交流?我们什么时候才和陌生人交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陌生人的力量》是我寻求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事实上,我发现和陌生人交流让我们变得更加美好、更加聪明、更加快乐,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不再那么可怕,整个世界也变得更加可爱了。大量的新研究发现,与陌生人交流有助于拓宽我们的个人世界,为我们带来新的机会和关系,打开新的视角。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孤独感,增强我们对自己居住地的归属感,即使这些地方正在发生变化。与陌生人交流,无论他们是逃难灾民还是政治对手,都能减少彼此之间的偏见,缓和党派之争,且有助于缝合破裂的社会。
正如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所写的那样,“当一个陌生人不再是想象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地出现在你面前,和你一起生活在人类社会时,你可能喜欢他,也可能不喜欢他,可能同意他的观点,也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如果你们两个都愿意,你们最终是可以理解对方的”。
接下来,我们会一起浏览全书,从小处入手,渐观全局。《陌生人的力量》从心理学家的新见解讲起,讲述当我们与陌生人互动一下时会发生什么。随后,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为什么和陌生人互动一下会让我们感觉很好。为此,我们将回到远古时代人类起源之时,从猿类祖先身上寻找答案。我们将了解到早期人类如何变成科学家口中的“超级合作猿”(the ultra-cooperativeape),这种生物既害怕陌生人,又需要陌生人。
之后,我们将了解到狩猎——采集者怎样创造出与陌生人安全地进行交流的方法,这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随后,我们将了解到,对陌生人的热情态度如何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还会看到,大众宗教真正的变革性智慧在于能够让陌生人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就彼此熟稔起来。我们还将得知城市是如何兴起的,这是因为人们想和更多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而非竭力避免和陌生人接触。
我们将了解到人类文明是如何发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学会了缓解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恐慌,以从陌生人那里获得一些机会。我们会一起探讨所有阻碍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的因素——从技术到政治,再到芬兰这个美丽安静的国家的公民身份。
当然,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陌生人——街上的行人、活动人士和研究人员,后两者试图塑造一种与陌生人交流的文化,以帮助解决一些最紧迫的社会问题,降低其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在主动和陌生人交流时,也会得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变得更善于与人交流。这些沟通技巧我自己也会反复实践,因为我会刻意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社交高手。
《陌生人的力量》始于回溯大约200万年前的故事,最后以今天的故事结尾,我所希望的是,证明我们有理由与陌生人主动交流。多年来,媒体、政治家、学校、警察等一直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是“陌生人是危险的”,但事实相反,对陌生人缄默不言要比和他们主动交流危险得多。与陌生人交谈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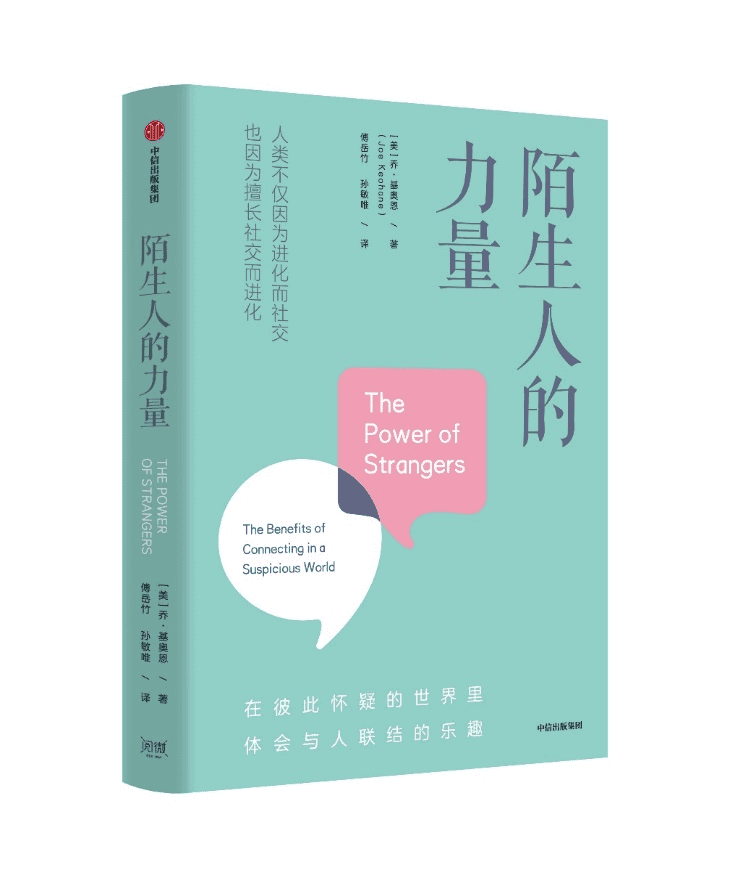
本文整理自:《陌生人的力量》 ,作者:[美] 乔·基奥恩,译者:傅岳竹、孙敏唯,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