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银发世代》 ,作者:[美] 路易斯·阿伦森,译者:蒋一琦、张光磊、周哲,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6年,美国著名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纽约客》编辑戴维·雷尼克为此采访了他。雷尼克问时年66岁的斯普林斯汀:“为什么现在出书?”
斯普林斯汀长叹了一声,然后笑起来:“你知道吗,我想趁现在自己还没忘得一干二净。”
雷尼克开怀大笑。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所以开始有些压力了”,斯普林斯汀补充说,“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采访那时,斯普林斯汀正在做巡回演出,门票预售一空,每场演出时间都极长——连续三个多小时高强度的纵情欢歌,夜以继夜,辗转于世界各大城市。一个月后,他的新书问世,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斯普林斯汀又开始新一轮巡回,更确切地说是两轮:一轮签书会,一轮音乐会。
按他这样的年龄或精力,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还处在中年时期,但艺术家本人清楚地感觉到,无论“老”的定义是什么,“老”在他身上都已经初显,而且至少他自己已经可以看到以后的走向。
但无论是斯普林斯汀,还是小他10岁的《纽约客》编辑雷尼克,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从他们正在讨论的职业细节来看,斯普林斯汀不仅正处于新的高点,而且掌握了新的艺术技能,但他们认为斯普林斯汀的人生已经滑到了一去不返的下行螺旋上。斯普林斯汀数十年来一直作为音乐人为人称道,现在则作为富有才华的作家得到肯定,而这给他的未来带来了新的选择和机遇。
作家不需要蹦蹦跳跳,也不需要沿着舞台劲歌热舞,走入歌迷之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人都这样。斯普林斯汀也可以坐在钢琴前弹琴,或者坐在凳子上弹吉他,或者只用一个麦克风,打一小束聚光,让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的脸、词和曲上。那就不是典型的斯普林斯汀演唱会了,但那样会难看吗,或者说只是不同?那样做是会破坏他一贯的风格,导致他的歌迷流失,还是会吸引更多歌迷,以此显示他的受众更广、适应能力更强?他可是发过民谣专辑《爱情隧道》(Tunnel of Love)的人。
重点是,像许多人一样,斯普林斯汀有选择的余地,只是他的选择和大多数人显著不同。举办不同形式的音乐会,演唱改编的歌曲或演奏不同类型的音乐,只是他的选择之一。他也可以坐在家里,拿着鼠标键盘,或者纸笔,或者录音机,或者一边口述一边请人记录,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只有对这种分类做一成不变的理解,这种过渡通常才被归为退化。若以对人类生命周期的理解对其进行建构,那么它看起来更像是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其他形式的过程。
即便不是接近古稀之年,斯普林斯汀也肯定处在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老”的范畴。纵观两三千年的历史,从西方的苏格拉底和雅典帝国时期,到更早之前的中东和亚洲,人们给老年划分的起点是六七十岁。
在美国,1935年启动了社会保障计划,把65岁当作整个联邦区分中老年的分界线。制订该计划的总统经济安全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ecurity)选择以65岁为界,一部分原因是,这是当时普遍退休年龄方面的数据所显示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当时已有的美国国家养老金体系中,50%选择了这个年纪(另外50%选了70岁)。
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退休标准、寿命和保险方面的统计结果已经发生变化,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65岁要么是一个严格的分水岭,要么是进入过渡期、走向老年的标志。
在大多数人身上,老年的早、中、晚期差异显著。在我们目前关于“老”的概念中,生理退化和选择丧失是它的必要条件。即便大多数更年轻的人很快并明确地把他们归入“老”那一类,许多人也不认为自己老了,直到生理退化和选择丧失这两个方面变得无可回避。
当到达通常所认为的“老年期”时,人们有时会觉得无所适从。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进入老年的这种过渡其实是在几十年内逐渐发生的,从20岁时就已经开始。这种变化利弊共存,只是我们总倾向于关注它的弊端。起初,那些生理退化和选择丧失悄然不觉,然后是容易忽视,接着也许是退而避之,最后是避无可避。
斯普林斯汀表示,他意识到了自己身心的负面变化。人到了一定年纪,很难不扪心自问:是我的心智先衰退,还是身体先衰退?是身心俱衰,还是会出现奇迹?衰退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多快?
衰老始于出生。在童年时代,人的变化巨大。在最初的几十年里,活着与衰老的含义无法画上等号。我们先看到的是关于儿童发育的表述,接着是成年早期的忙碌和社会意义上的重要节点。我的一个朋友搬到了美国另一个州,之后我有9个月没有见到她的小宝宝,再见面时,小婴儿已经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除了严重疾病或残疾,儿童发育的各个阶段都是可预测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分界点。
随着人生不断展开,各阶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虽然人们会争论生命的起点是受孕时还是出生,但童年的起点都是从呱呱坠地后大口呼吸的那一刻开始的,这是生命伊始的统一形态。然而,生命的终局就没有这么明显了。10岁时永远是孩子,但到了18岁,既可以是青少年,也可以说是青年人,关键要看他们的表现。有些人在十几岁时身体、情感和心智就已经达到成熟,有些人则是在20多岁时。女性往往比男性早熟。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在长达数年的同一时期内长为成人。
随着20岁的到来,发育速度似乎变缓,像毛发生长或冰川融化一样不易察觉。从婴儿期进入儿童期、从青少年进入成人期的那种变化似乎停止了。但是看不见或者注意不到,并不等于没有发生。变化贯穿人的一生,无论是身体、功能,还是心理,莫不如是。
在某个节点,我们进入了“中年”的疆域,发现变老并不只是那个被称为“老年”的神秘之地的特征。有时候,我们愿意迎接进化,因为它带来了更大的自我满足、更深层的自信和对过往与当下更多的安全感。与此同时,身体变化不断积累,可能会以复杂、令人不安甚至使人穷困的方式发挥作用。人对自身的认同感可能会受到挑战。
即便那几十年里变化看似缓慢、几乎无关紧要,它也依然存在,依然重要,而且持续发生。在我30多岁时,我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因为我有幸在十几岁戴上了牙套,并且坚持看牙医。到了40岁出头,我的下门牙开始向交叠的方向生长,似乎因为已经过了太久,以至于它们忘记了早年金属牙套、头套、颈套、橡皮筋对其的训练。沿着叠长的下门牙的边缝,我看到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喝了几十年早餐咖啡、偶尔来一杯红酒以及日常食物残渣的侵蚀。
但我的牙医说,我的牙齿看起来很不错,她可以看出我在老老实实刷牙、用牙线。但我知道,她真正的意思是,我的牙齿状况对50多岁的人来说很不错,但不是像以前一样好,或者绝对意义上的好。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有条件的解释慢慢就变成无声的了。
到了明显衰老的年纪,曾经十分遥远、所谓“老”的秘境对我来说不再陌生。每天,我的膝关节都会提出抗议。有时只有一条腿响,但更多的时候是两条腿一起咔咔作响,如同新的背景音乐,伴随着我的每一步。我时不时在三副不同焦距的眼镜之间切换,因为每一副功能不同。我有一个基因缺陷,有癌症史,有七道可见的手术疤痕,现在还在渐渐丧失几个不重要的身体零件。
如今,当身体抱恙时,我不光考虑治疗的问题,还担心无药可医,担心新的衰弱之兆不但会持续下去,还会引发一连串的伤病和额外的身体失能。我脑海里回响起童年的歌谣:“脚骨连着腿骨,腿骨连着髋骨……”虽然还不清楚以后的光景,但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我=老”,只是有时,眼看着自己在这个广阔领地无情地挺进,我仍然觉得意外。
这些身体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但它们只是生命长河的其中一段。对我来说,生命这个传奇的余下部分更像是这样:尽管我还没成为“老龄”国度的永久居民,但我已经对它的文化和习惯颇为熟悉,而且充满期待。
我想象着,如果幸运的话,早期老龄可以长达数十年,而且极似中年的最佳时期:我坚定地知道我是谁,明白我想如何度过光阴,那些容易与空洞、虚荣的社会认可混为一谈的野心减弱,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关怀和关注他人,有信心坚守自己的信念,有令人振奋的新目标,对生活有深切的满足感。全世界步入老龄的人普遍有类似的情绪。
童年时期,我们会庆祝重要的成长节点。而在此之后,我们也许会惊讶于继续成长的安静,甚至感到有些不安。一位将近40岁的朋友发现一个荒谬的现象:他的同龄人不愿意听到他自称“中年人”,而他显然已经步入中年。我打量他一番,表示同意其他人的看法:他一点也不显老,但是显然也不再年轻——他介于两者之间。
我母亲则在成年的另一端,她说变老并不尽然是件坏事,除非年届八十,在那之后情况才会急转直下。她说这话时,我们正在护理院吃晚饭。她住进护理院是因为我当时尚在人世的父亲需要有人照应,而不是她自己状态不佳。几秒钟后,因为没人来送水,她耐不住性子跳了起来,抓起我们的杯子就奔向餐厅另一头,往杯子里倒满了水。她的身体不复从前,但在我看来,也不像是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人。但对她而言,她已经越过那一道槛,进入了风险更高、更加脆弱的阶段。
迄今为止,即使是最不固定的分界线,也把成年和老年划分得清清楚楚。如果身体健康、运气好,有些人直到将近80岁,才开始或自认为显出老态,有人还要更晚些。相比之下,一些主要的压力因素,比如无家可归、贫困或监禁,会加快衰老的进程,使50多岁的人老态尽显——他们的细胞变化与慢性病和死亡方面的风险,与年长他们几十岁相对健康的老人不相上下。
尽管如此,对50多岁的人使用“老”这个词仍然可以打上引号。我们将“年老”定义为生命年表上的一个确切位置,有时还把它解释为一种生物—心理—社会学状态,但主要是这二者的结合。按照这种逻辑,一个虚弱的72岁老人可以被称为“老”,但一个跑马拉松的72岁主管则不能。事实上,两者都属于老年人,哪怕这位主管到了80岁高龄仍能保持目前的各项活动,他也是老年人。
因为变老是个漫长而隐秘的过程,一个人步入老年与其说是突然转变,不如说是悄然跨过了一系列不甚明确的门槛,而这种转变往往是由局外人首先注意到的。大多数30岁以上,当然还有那些40多岁的人,都还记得第一次被称为“先生”或“女士”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从而立之年进入不惑之年,衰老似乎在加快。
等到知命之年逐渐届入花甲,定义成年人生长的身体变化日积月累,不再无法察觉,而是出现一些微妙的征兆:眼角生出鱼尾纹,发际线后退,右膝不大听使唤,朋友中有人得了癌症,同龄人开始谈论疾病和临终的老年亲戚。如果不是从更早的时候开始,那么最晚等到花甲之年慢慢走完,这些变化就已经无法否认了。
再过不久,变化更加显著,每一个10年过去,生命的轨迹看起来都比前一个10年更加清晰。一天天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过了1年、5年或10年再回首,我们会发现,变化竟是如此显著。
各个时代都有老年人的身影。在公元前2800年的埃及象形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佝偻的人倚着一根棍子。从公元前775年开始的900多年里,希腊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衰老的理论。他们留下的遗迹显示,古希腊人建造了系统、道路和高效的污水处理系统。他们的卫生条件良好,大部分繁重的劳动由奴隶来完成。
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已经注意到,奴隶们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但得到的食物不足,而且经常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使他们比所在社会的其他公民衰老得更快。亚里士多德认为,衰老是由时间推移、“精力”丧失、体内的热量和精气逐渐消耗所致。因为身体需要一定量的这些元素,而老年人的摄取量较少,导致他们更容易生病。尽管奴隶比学者更快地消耗这些元素,但最终每个人的元素都会耗尽。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人们并不期望变老,而那些期望变老的人往往比他们的孩子活得更长久。在儿童和年轻人居多的社会中,老年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所以在建造房屋、制定法律、设计城市、培养劳动力或培训医生时,考虑他们的意义不大。
现在,大多数出生在发达国家的人都比较期待老年生活,而且老年人的数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老年也会持续更长时间,维持健康的时间也更长。许多老年人(数量空前)正在或将要在老年阶段做的事,与较为年轻的人所做的大部分相同,只是有时方式不同。如今的老年人还会完成许多其他在生命早期或寿命不够长时不可能做到的事。
在那些通过传统、历史和宗教形成认同的社会中,“老年人在出生时更接近神圣的过去,在临终时更接近圣贤先祖的权力之源”,因而享有威望和明确且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今,人们认为过往无关紧要,死亡更像是结局或深渊,而非与上帝同在的机会,于是“变老”失去了魅力,甚至连中年也是可怕的。在一篇名为《惧怕衰老》的一句话微故事中,作者莉迪娅·戴维斯完美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
在28岁时,她渴望回到24岁。
与此同时,在我50多岁时,我认为回归24岁的想法很可怕。我并不怀念那时的压力、不安全感或者装腔作势,一切在当时常常看似有潜力、力量和机遇,实则不然。
老年有界限和地标,它们真实存在,但又取决于如何被解读。在变老之前,我们有数十年时间“年轻不再”,而不同的人和文化对“长期”的定义也大不相同。
就像色情文学一眼即知,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老态龙钟。但是,中年和老年之间确切的转折点很难定准。考虑到过多的生物学标记以及它们无法预测的行为和相互作用,无论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我们这个物种而言,想明确地区分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难以捉摸的等式中,文化也不是唯一值得注意的部分。
什么是“成年人”变成“老年人”的标志,关于这个边缘地带的特征,不同人的解读各不相同。我母亲在60岁时被诊断出癌症,她选择听天由命,说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她已经老了,已经走过了幸福的一生。25年后,她回忆起当时的想法,意识到几十年间她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她的老年生活本身也发生了改变,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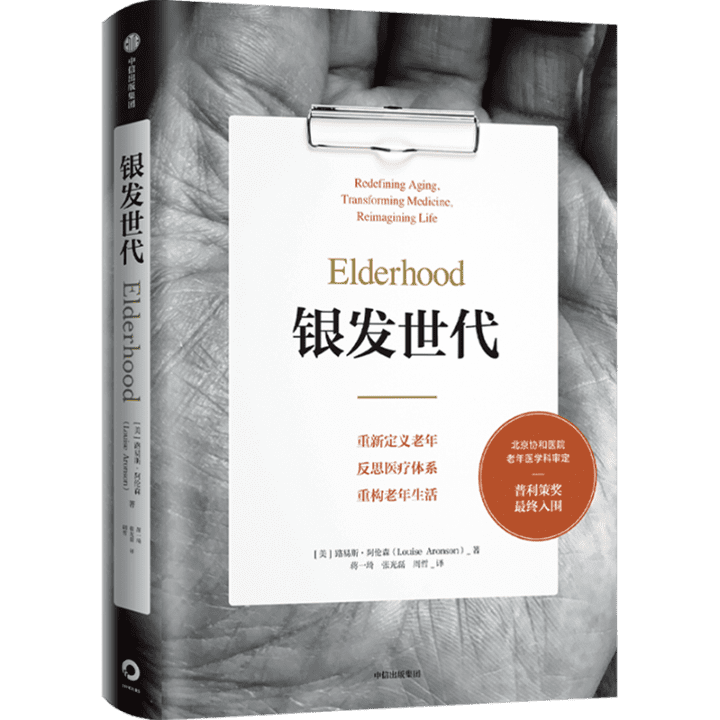
本文整理自:《银发世代》 ,作者:[美] 路易斯·阿伦森,译者:蒋一琦、张光磊、周哲,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