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王亚奇,题图来自:《使女的故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现在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使女的故事》原著在剧版走红后成为畅销书,阿特伍德的名字也传遍了大江南北。但多数人不了解的是,反乌托邦题材只是阿特伍德作品的冰山一角。
她的创作不拘泥于任何形式、题材,她曾出版过诗集、写过现实主义的小说,她的评论集也充满了智慧的闪光。
阿特伍德俨然已经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这也是她的作品值得被铭记的原因。看见这个世界的残缺,并把它记录下来,阿特伍德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做到的事。
1939 年11 月 18 日,时值加拿大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格蕾杯”足球赛后不久,整个世界正面临着笼罩上亿人的战争阴云,法西斯在欧洲加速进军,被军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于两年前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印度、东南亚、越南、非洲、伊比利亚半岛也深陷在昨日世界消失的恐惧中。而北美是一片相对宁静的土地,风暴降临的前夜,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来到尘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名字“玛格丽特”与妈妈重名,为了区别开来,她被家人昵称为佩吉(Peggy)。
阿特伍德曾说,她有两个名字,所以有双重身份,玛格丽特负责写作,而佩吉负责其他的一切。
分身写作,可以作为理解阿特伍德的钥匙。她写作勤恳,想象力丰富,大胆地进行不同体裁的文学实验。在阿特伍德的作品里,读者既能看到精灵、哥特、女巫、灵性写作的一面,也有正面强攻型的女性书写与政治寓言,还有一些轻快的语言实验、悬疑、科幻和反乌托邦,阿特伍德仿佛拥有一个巨型的胃,吞吐着大量素材,当她荣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的终身成就奖时,授奖词的一段话颇具有概括性:“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20个女人、30个女人。作为作家,她拥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
作为一位全能型作家,阿特伍德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戏剧、评论、漫画、音乐、时尚,她曾凭借诗集《圆圈游戏》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还为一首名叫《弗兰肯斯坦怪物之歌》的摇滚乐写过歌词,与此同时,她积极参与公共议题,为性别暴力受害者发声,她创作了《为被谋杀的姐妹而歌》;身份政治与辩论自由的议题发酵时,她与J.K.罗琳、福山等人联名签署了呼吁辩论自由的“公开信”;多年来,阿特伍德没有说为了爱惜羽毛、营造作家的神秘感,就放弃对于争议话题的介入。

新世界的推演者
如今,她最知名的作品是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但她早期其实是一位诗人,迷恋神秘主义、泛灵情结和中世纪艺术风格。
《圆圈游戏》展现了她隐喻的天赋,这部诗集的文学性强于她的许多小说,比如早期的《可以吃的女人》《人类以前的生活》《神谕夫人》《肉体伤害》,而她的小说技艺在短篇集《蓝胡子的蛋》中走向成熟,随之《使女的故事》出版,阿特伍德涉足反乌托邦体裁大获成功,这种对于未来的推想,超越地域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极大地考验作家构建一个世界的能力,却可能是阿特伍德感到最自由的领域。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7
《使女的故事》的辛辣讽刺,也寓言了女性的处境。“在未来世界里,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伴随着核事故、化学污染、病毒试验及其引发的生态污染危机,全球人口出生率骤然下降。美国部分地区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 Gilead(基列国),女性被当做国家财产,失去作为正常人的权利,她们中有生育能力的人被称为‘女仆’,沦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
《使女的故事》不是幻想,而是阿特伍德对女性生存现状具有切肤体会后的文学书写,一种以反乌托邦形式进行的“现实再编码”。

在这方面,厄休拉·勒奎恩的写作对阿特伍德深有裨益,勒奎恩在《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中展现了小说作为“思想实验”的方法,阿特伍德沿着她的步伐继续迈进,她擅于将神话、宗教、寓言、历史案例和科幻元素融合,创作出诸如《证言》《盲刺客》《别名格蕾丝》《羚羊和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等作品。

[美] 厄休拉·勒古恩 著,陶雪蕾 译
读客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2
但和专注于纯粹想象、不去指涉现实的作家不同,阿特伍德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介入现实的野心,女权主义、身份认同、气候危机、极权主义等,阿特伍德的作品具有高调的政治性。
阿特伍德曾经在2010年秋与勒奎恩有过一次公开对话,勒奎恩在对话中区分了“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fantasy):前者是“关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测”,而后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值得推演的存在。阿特伍德意识到“科幻小说”的优势,比方说借着科幻的壳,言现实所不能言之事,在这方面莱姆的《机器人大师》是杰出的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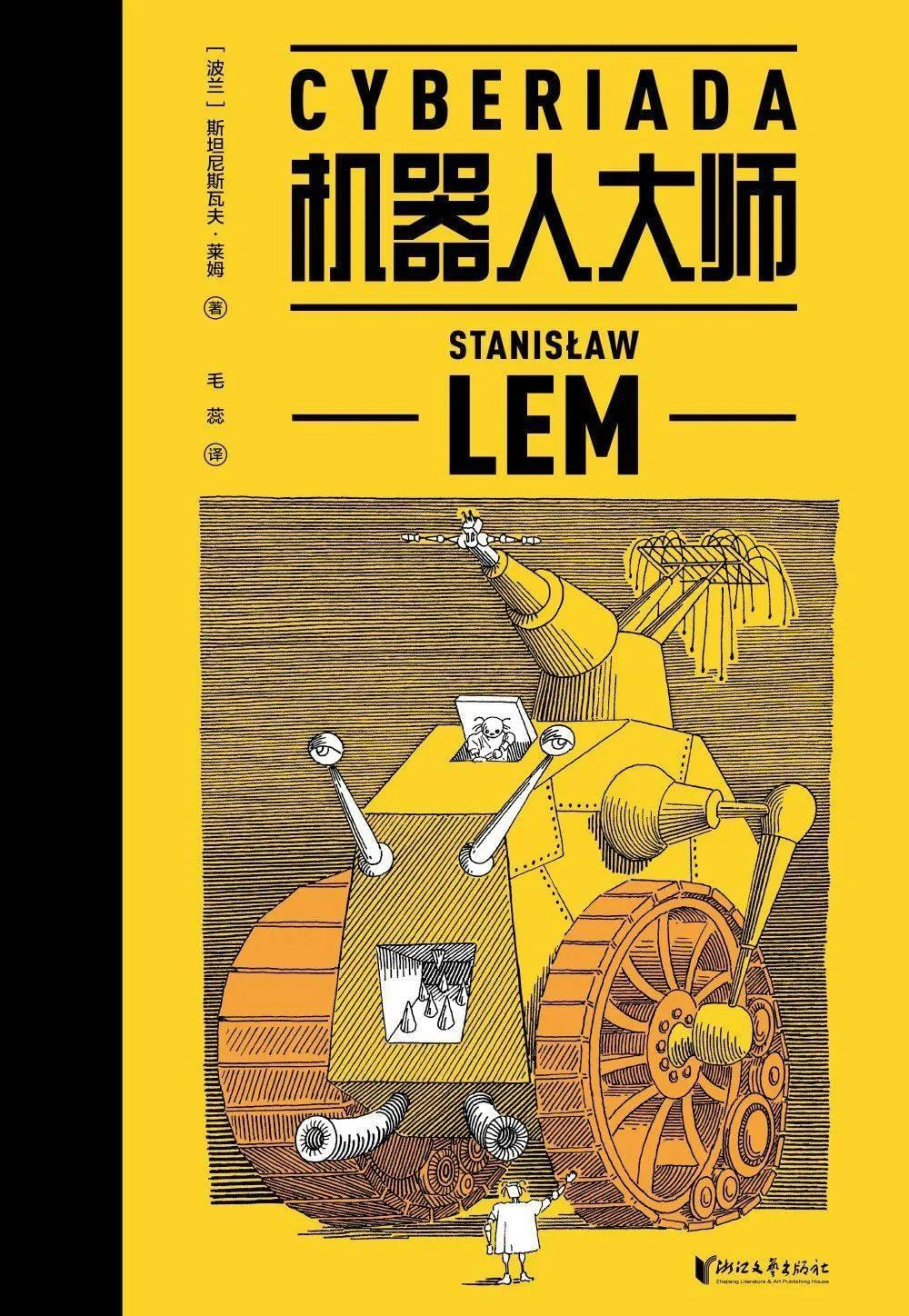
[波兰]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著,毛蕊 译
果麦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4
科幻小说可以大胆地推演人类进化的形式、未来社会的生态,用科学知识与想象力去探究文明演化的边界。她也意识到“科幻小说”的局限:沦为点子文学的风险、对于设定的依赖、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等。
相较而言,幻想(或谓之“推想”)是一种更不受限制的写作方法,更接近文学的内核,那就是自由与运用自由的能力。不是为对抗什么,而是为了创造什么,不是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对抗者、技术主义者的角色,而是在打破限制中,创造一个新的、湛蓝的世界。
我们不妨说阿特伍德是一位杰出的“推想写作者”,推理、想象、对正反乌托邦(ustopia)的合理演绎是她长篇小说的优势。她对于权力关系格外敏感,在这方面她仿佛是福柯理论的文学演绎者,她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被客体化的进程,也能在精妙的结构里,表现出乌托邦灰暗的一面。

可以说,阿特伍德是21世纪将推想与文学融合得最好的作家之一。阿特伍德在她的论文集《在其他的世界 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中分享了自己大量阅读科幻小说后的思考。从科幻小说与神话、宗教之间的关系,到漫威、《哈利·波特》、《阿凡达》,从对于乔治·奥威尔、厄休拉·勒奎恩的讨论,到对于人体冷冻术、人工智能、控制论、女性生存现状的剖析,阿特伍德慷慨地分享她的见识,在她的大脑里仿佛装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她展现出小说家与时俱进的能力,那源自于广阔的好奇心、精准的问题意识、结构能力和对于人类情感与社会演进的洞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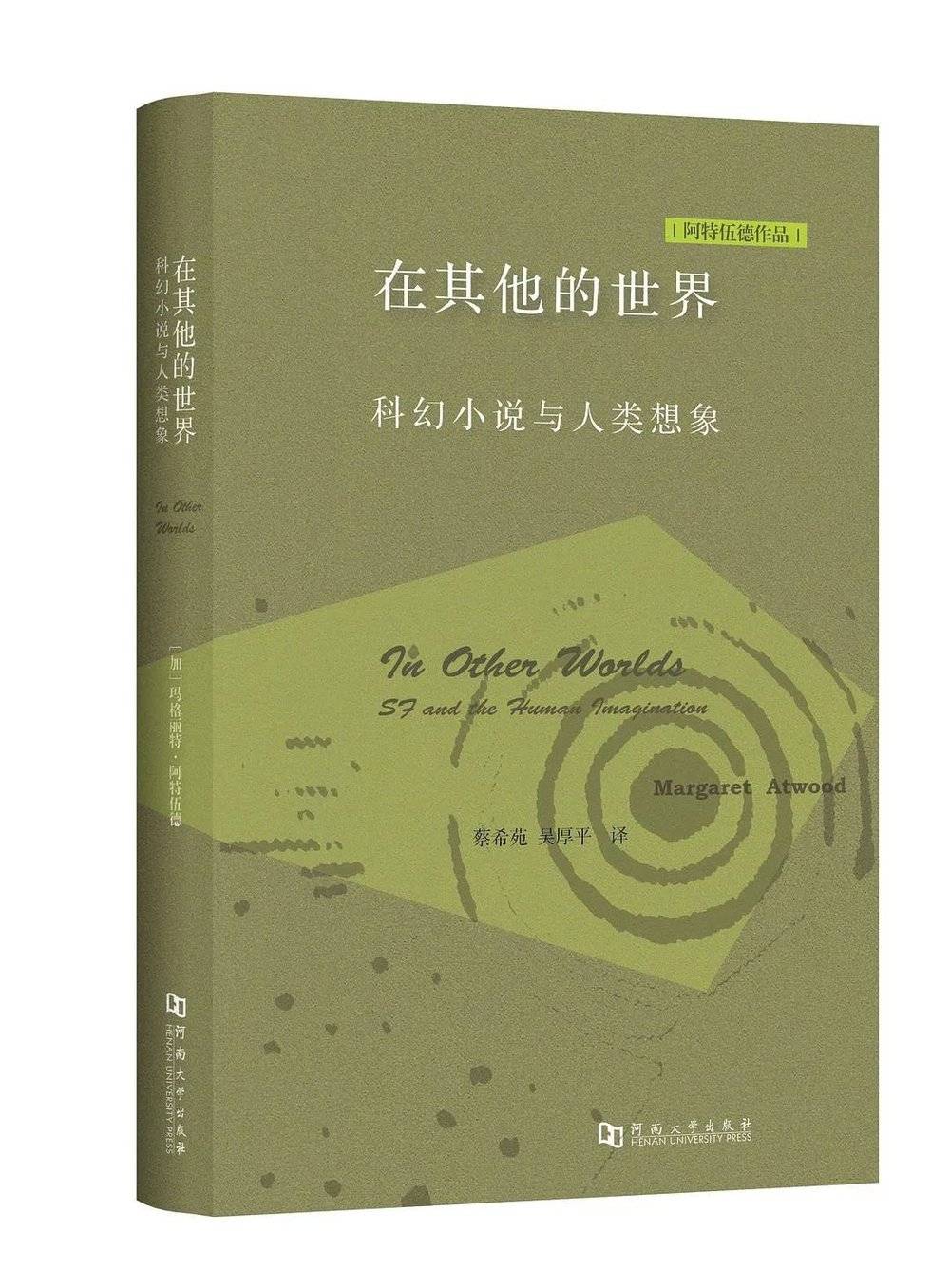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蔡希苑 / 吴厚平 译
上河卓远文化 |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4
书中,阿特伍德写到:“在文学作品中,每一处风景都是一个思想,而每一个思想也能由风景塑成,正反乌托邦亦是如此。”
反抗凝视
阿特伍德并不许诺一个左翼蓝图的玫瑰色幻梦,也没有滑落到“存在即合理”的保守说辞。其实在反乌托邦作品之外,阿特伍德也写过隽永的回忆流小说,例如入围布克奖决赛名单的《猫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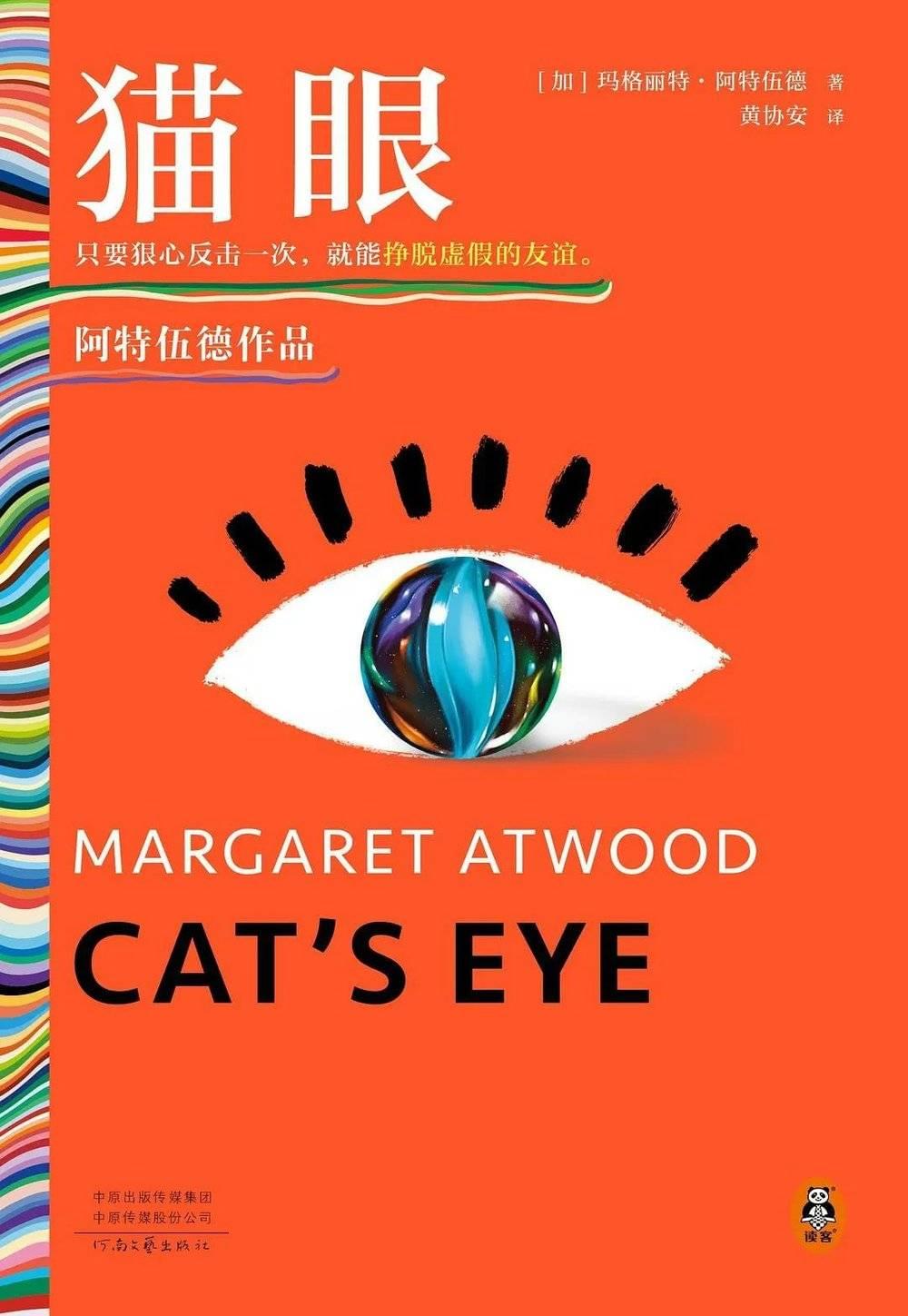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黄协安 译
读客文化 |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4
《猫眼》创作于1988年,彼时的阿特伍德已经年近50岁,岁月使她的阅历更加饱满,也让她的笔触更加细腻悠长。《猫眼》彰显了阿特伍德耐心讲述女性故事的能力,小说从一位女画家回多伦多举办画展说起,她在故地重游中回忆往事。阿特伍德在这种过去和现实交织的叙事中,诚恳地探讨女性的友谊、亲密关系、身份认同、父权制对于女性潜移默化的影响。
《猫眼》讲的其实是女性的主体性如何被塑造,在这塑造的过程中,有多少是自我的,有多少是社会文化与周遭目光、权力关系潜移默化的规训。小说中伊莱恩与科迪莉亚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起初,童年时习惯了游牧生活的伊莱恩在随父辈回到城市后,很不习惯人类主流秩序里的目光和规范。在女孩们的世界里,伊莱恩如同一个闯入的异类,一个不守游戏规则的野蛮人,为此以科迪莉亚为首的女孩们试图戏弄她、惩罚她,令她服从既有的相处规范。她们把她埋进后花园一个新挖的洞里,令她在黑暗中感到被孤立的恐惧。又将伊莱恩的帽子扔进溪谷,命令她自己捡回来。
她们是女生,却在男权社会的浸泡中习得了男权的控制术而不自知,或者享受上位者的感觉,在权力和情感操控中无形中内化了男权。当伊莱恩终于习惯了父权社会的法则,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她开始用画家的视角重返记忆的现场。

整部《猫眼》,其实就是阿特伍德用文学写的《凝视与反抗凝视》,是她通过具体的故事入手,告诉我们父权社会如何通过密集的凝视规训一个女性的心灵,再到通过伊莱恩的笔触,展现女性自我的凝视,用女性的笔触,去拆解一切冠冕堂皇口吻下的控制、物化与将女性视作客体的手段。正如书中所言:“渐渐地,我开始想要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东西,辫子,睡衣,钱包。一个世界在我面前慢慢打开。我看到了一个女生的世界。”
这让人想起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两位作家都敏锐地感受到女性关系之中微妙的角力。阿特伍德很细心,她尽量避免对关系的刻画沦为狗血,而是耐心地铺陈女性交往中的暗流。出身、力量、兴趣、交往对象、对比、嫉妒、渴望、权力关系的拉扯,直到她们长大,更强力和懂得运用世俗规则成为宠儿,另一方相比之下似乎暗淡,但强力的一方知道,那蛛网般与后者共享的记忆,始终是她身体里的软肋。

2017年,阿特伍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图书俱乐部的访谈中谈到:“我们感知时间的方式完全是主观的。除此之外,时间如同一个迷宫,错综复杂地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并为我们的未来铺平道路。因此,时间的概念从来都不是直截了当或线性的,而是‘方块形的’,它崎岖、朦胧,充满了由我们制造的障碍。”
在时代的浪潮中
需要看到的是,阿特伍德是一位关心新技术的作家。她的小说阅读感受很契合当下的场景,一个由流媒体、影视剧、元宇宙、互联网等元素构成的“叠影时代”——一个我们被层叠的影像和错乱的信息包围的时代,源源不断的“观看”正在发生,每个人都在宣称自己看到了真实。
在《别名格蕾丝》《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小说里,阿特伍德捕捉到不同叙事者对于故事讲述方式的影响,影视剧的节奏也影响到她的创作,她的语言善于快速捉住观众,在精彩、快节奏的故事中,提供一种潜在的唤起能力——唤起读者内心被压抑的某种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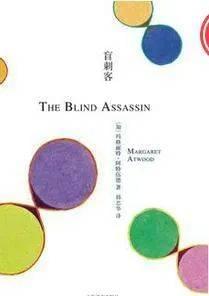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韩忠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
在《使女的故事》《证言》里,阿特伍德冲击了“男人关心的才是政治的、公共的”这种陈腐观念,她把女人关心的、恐惧的放在小说中心,用寓言的方法揭开女性面对的森严世界。阿特伍德看见了文学和政治的交叉性,但在文学创作中,文学仍是第一位的,不是政治或热点的附庸。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于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7
和门罗专注于一个领域几十年如一日的打磨不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思维敏捷、精神充沛的杂食作家,她将公共议题与严肃文学融合,在不同文体的穿梭中打破层层森严的戒律。
阿特伍德展现了文学作为思想方法的可能、与现实周旋的新的方式。阿特伍德的小说既是好看的故事,也是具有严肃文学内核的作品,她怀着充沛的激情投入到虚构这门艺术,在虚构的世界里,她又足够冷静、沉着,将世界的部分真相隐藏在幻想瑰丽的文字中。
阿特伍德对写作者的启迪不是文体创造层面上的,而是推想的层面,是文学如何进入公共议题,又不折损深刻性这一面,也关乎在这个时代,如何书写一部好看且耐人寻味的小说,在故事中安放某些难以概括的复杂情感、日常生活中惊心动魄的瞬间。在这些层面,阿特伍德是当代的杰出表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王亚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