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王亚奇,原文标题:《重建日常的第一步,走出去》,头图来自:电影《迷失东京》
作家李静睿出生于川南小城自贡,长大之后拥有了旅居世界各地访学和写作的机会。李静睿既写小镇,也写城市。从《小镇姑娘》到《微小的命运》,她笔下的人物亦如她自身一样,无法和各个地方脱离关系。
作家大头马酷爱旅游,“不安分”的她曾经在世界尽头南极跑过马拉松,去冰岛看过冰岛马。她最近出版的新书《东游西荡》把旅行的故事写得像是一份私人游记,书里几乎很少对景点有赞美之词,更像是一本行游世界的旅行吐槽笔记。
她们的旅途截然不同,写下的文字风格也大相径庭,“在路上”如何构成她们的写作灵感,又如何改变了她们的作品?今天的刀锋图书奖秋季论坛,我们和李静睿和大头马聊聊旅行文学。
“东游西荡”的工作与生活
硬核读书会:大头马老师刚刚出版了《东游西荡》,里面的旅行经历特别有意思,你开始旅行的契机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从写虚构类小说转来去写旅行文学?

大头马:其实这些文章大概都是2015年到2018年写的,我差不多是同时在写小说跟写非虚构,并没有一个突然转向。一开始旅行的契机是我从2015年开始跑马拉松,经常去国外参加比赛,就会顺便玩一下,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晚上回来之后,我总觉得应该写一点什么,不然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所以就会自然地开始写一些文章。
硬核读书会:李静睿的旅行动机应该和大头马不太一样,您之前做过八年的法律记者,过程中有没有去过什么普通旅行者几乎没有去过或者很少去的地方?
李静睿:我觉得我的旅行不太能称之为旅行,它就是工作。在工作中我去的地方应该都不是游客会去的地方,完全跟旅游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第一次出国是2005年,那时中国放开了私人护照的申请。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去柬埔寨,因为我跟着世界无国界医生组织去柬埔寨去给孩子们发治疗疟疾的药。当时也都是去的柬埔寨最穷困的地区,村里的孩子都是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
我和香港的一位无国界医生聊,他说我们送去的是大规模研制的治疗疟疾的药物,以前传统的疟疾药物一针的成本大概要几十美元。
所以我去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在广州,因为做法律记者,所以都是跟着公安、纪委去外地。我一打开《东游西荡》这本书就震撼了,因为南极、马拉松这些事情都离我太遥远了。

硬核读书会:之前做法律记者时候的经历对你后来的写作有产生什么影响吗?你虽然做过记者,但是并不进行非虚构写作。
李静睿:我写过一些书评。其实作为作者的话,所有的人生都对自己产生影响,可是具体到法律记者对我的写作到底产生什么很具体的影响,我觉得我不太说得出来。
因为我在做法律记者的时候,我的工作很硬,就是和各种法律法规、各种案件有关。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文学,也没有人知道我喜欢看这些书。我的生活是分割成两个部分的。那时候和同事们聊的都是人大要修什么法律之类的内容,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聊文学。在《新京报》的时候,阿乙、阿丁和我们在一层楼,他们当时好像是体育记者,大家都是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地干自己和文学有关的事情。

硬核读书会:你会想体验一下大头马那样的生活吗?
李静睿:完全不想,一想到每天都要住在酒店里,要去见那么多陌生的人,我已经提前开始焦虑了。
在工作上我很愿意吃苦,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再苦的地方我都愿意去。我们以前为了采访,还跟着中纪委爬过墨脱,我觉得很少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时5000米的雪山,连摩托都没有通车。
到山上之后,东西也煮不熟,生的面我都吃了三碗,路上也不能洗澡。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太陌生的经历了。自从爬过那次雪山之后,我再也不想爬任何雪山了。最后报社觉得我太苦了,还给我发了3000块钱,可对我来说这就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当我可以选择的时候,我肯定是选择找一个五星级酒店躺在那就不动了。
为了工作我完全可以克服困难,可是为了生活的话,我更愿意待在家里。

你在哪,世界的中心就在哪
硬核读书会:那大头马老师,你写旅行文学时创作习惯是怎么样的?你书中写到一个细节,在冰岛得知自己的相机找回来之后,开始在青旅里写三个月前的日本游记,所以你是旅行之后才写下文字吗?
大头马:其实我那几年出去玩,本质上也是为了逃避当时的现实生活。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做编剧,编剧是一个非常辛苦、没有任何尊严的工作。
我这些旅行的时间都是在一个项目和另外一个项目之间,我觉得我不行了,必须要出去玩一下,然后才能继续回到现实中。我记得去冰岛那次,我是先去了斯德哥尔摩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再去冰岛,一路往北。
当时我手里正好有一个项目还没有做完,非常焦虑。在那趟旅程里我记得我哭了好多次,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因为不得不去参加之前就报名的马拉松比赛,同时手头上又有很多工作。其实去到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天我就已经非常不想跑比赛了,斯德哥尔摩是一个纬度很高的地方,它的直射光非常强烈,中午的紫外线光照会让你的皮肤很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比赛很难,觉得自己可能跑不下来。
在比赛前一天,我一个人在老城区逛,走到一个咖啡馆里坐下来就开始哭,因为我觉得我第二天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比赛,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差点迟到了。不过也跑完了,而且好像当时还跑了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
我在冰岛写日本的游记,因为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写自己的东西,有时候只能在旅行的时候才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写一些之前要写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硬核读书会:你书里面有很多关于细节的描写,还有一些跟人物的对话,如何去还原这些在记忆里可能已经模糊的场景呢?
大头马:我记得大概的内容,可能对话不一定记得非常准确,但是大概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因为也不用特别准确地去把每个人说的话给写下来,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
这个问题应该李静睿更有发言权,因为做记者的肯定经常要面对怎么去回头去写稿的情况。
李静睿:我们都写的是案件什么的,跟你写的旅行游记完全不一样。我在日本住了整整半年,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对我来说,出去玩是一件完完全全放松的事情,这些东西可能最后会消化到我的小说或者别的东西里面去,但你要让我为这个东西再去写篇文章,我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

大头马:而且如果你住到一个地方,反而没有想要去写的动力了。我是有自己的写作规划的,有目的性想要去练习写非虚构。我和李静睿有一个共同的好友月亮,他写过一系列和纽约有关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受到了这些内容的影响,我也想去进行旅行文学这类稍微严肃一点的写作。
因为我从小学、中学时期就开始写文章,那个时候写的是更接近于杂文或者是豆腐块似的随笔。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影评。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了,就暂停了这类非虚构类的创作,开始去写小说了。
非虚构写作对我来说,是以我的感受为中心,处理我对于世界的认知的一种写作方式。我还是想要去进行这样的创作,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不知道有什么素材和题材可以写,我的工作也不要求我去进行这样的写作,所以我就有意识地想要去探索一个更细分、更精准、更垂直的创造方式。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可以去进行旅行写作,然后就开始写了。

硬核读书会:在李静睿老师那本《微小的命运》里,主角林薇薇分裂成两个自己后,故事分别平行发生于纽约和自贡,两个城市虽然有巨大落差,但是两个林薇薇的故事又是相似的,“城市和际遇带来不同,却并没有那么不同,因为人心的相似带来更多相似”,在您去各地的旅途中,有没有试过在两个很不同的城市中有相似的经历或感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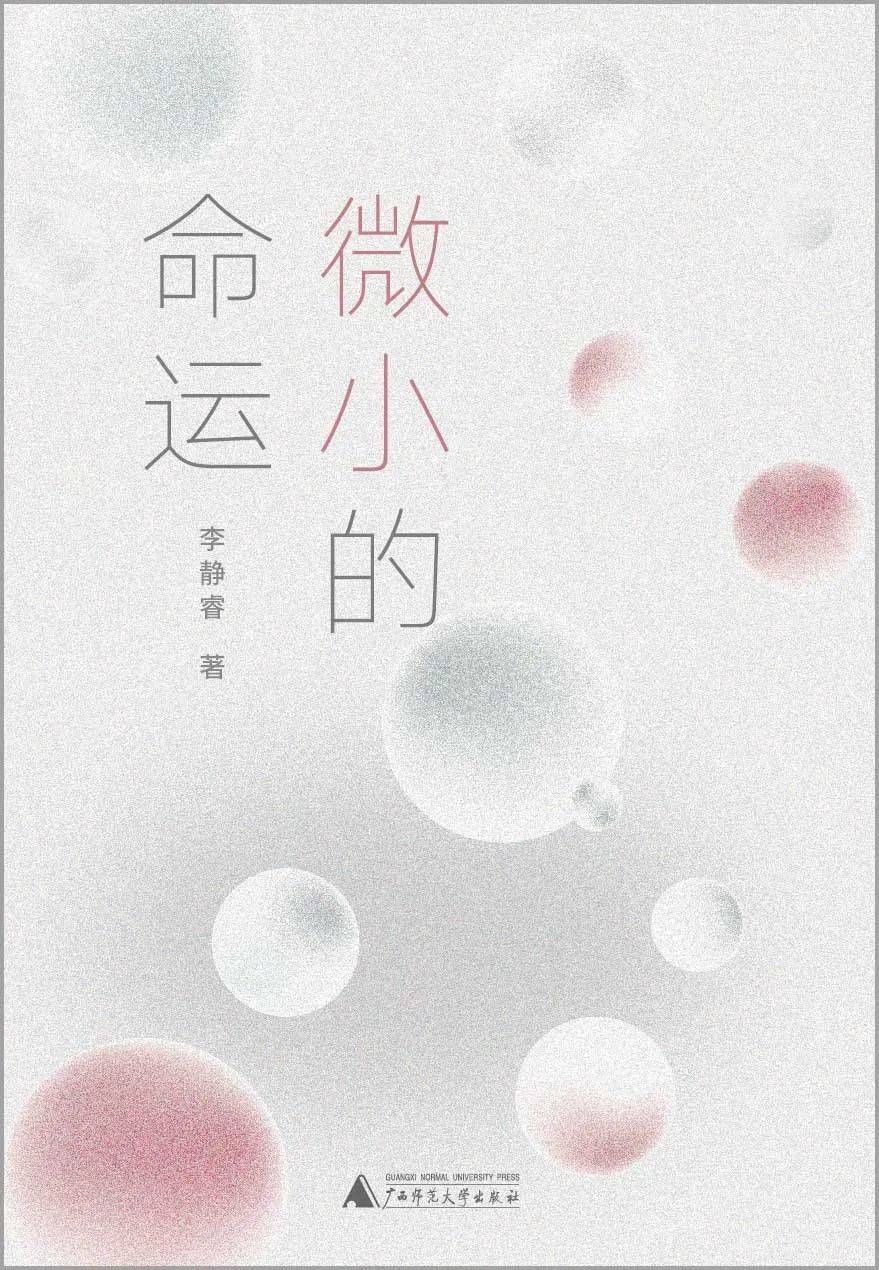
李静睿:写《微小的命运》的时候我30岁,正好结束记者的工作,跟着我丈夫在纽约住。那时候我一下子脱离了一个体制化的生活,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只是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个专栏。对我来说,那段日子很自由,又过于自由,那种感觉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不太确定你当时到底是快乐,还是觉得迷茫。
那时候我就开始写这个故事,其实当时我想表达的是:人的这种自由意志可能会强于一种命运的安排,当时可能是这么想。可是10年过去了,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我对这个想法并没有那么确定了。
我从小在自贡长大,后来去南京读书,长大后先是在广州工作,后来又去北京工作,在纽约住过,也在东京住过,这些城市对我来说本质上的差别并不大。我觉得我在哪过的生活都很相似,不管我在哪里,我都是先去把菜市场在哪先搞清楚,先把一大堆调料先搞好,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要自己做饭,然后偶尔出去吃饭。
城市带给我的变动很小,我没有因为城市的不同而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
硬核读书会:但是在您的作品里面还是有写小镇和城市。
李静睿:对,因为我是从小城市出来的,我现在每年也都会回小城市去住个一两个月,我也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彻底搬回小城市去生活。
我觉得人应该尽可能地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去看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到底在哪里,对你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阿摩司·奥兹写《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他那时候就觉得耶路撒冷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就觉得写作的人就应该像狄更斯一样写伦敦,或者像哪个作家一样写巴黎。
![《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 著,钟志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16-10<br>](https://i.aiapi.me/h/2022/11/30/Nov_30_2022_09_52_33_633574550881513.jpeg)
他很疑惑,他说,我想写作,可是我生活在耶路撒冷,那我能写什么?
他说后来我就明白了,作家整个世界是围绕着你写作的那支笔来转的。也就是说你在哪里,世界的中心就在哪。我觉得他那句话说得很好,虽然没有大头马去的地方那么多,但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去过更多的地方之后,地域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反而消解了。不过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出去看一看。
硬核读书会:大头马老师说很多旅行都是在两个项目的间隙时候去的,对于很多旅行者来说,旅行本身已经足够累,更何况要再分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到写作上。你会觉得在旅行中写作是一种负担吗?
大头马:在旅行中写作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因为没有什么其他时间,而且我不是那种把自己旅行的日程安排得很满的人,我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我出去旅行也非常随意。因为对我来说,基本上每次旅行都是要先跑完一场比赛,比赛一跑完,我就觉得我已经完成了一件正事,剩下的时间就无所谓了。
所以我特别随意,当我到一个地方,才会临时开始查这个地方有些什么景点或可以玩的,我就去逛一下。也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哪里或者一定要把所有的地方都看完什么的,如果我觉得累或者怎么样我就不去了。

硬核读书会:李静睿老师现在每个月都会去北京郊区旅行,这和你之前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李静睿:这三年的生活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我当时辞职和汶川地震后我做前线记者采访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当时的记忆对我的心理冲击特别大。从汶川回来之后,我就开始不想再做这些事情了,那个时候就想留在家里面,不太想出去看这个世界了。
那时候我认为经历了汶川地震后,我这辈子不会再遇到更大的事情。但这些年我看到了另外的事情发生。
以前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家里写作时,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我有一个很舒适的小环境就足够了,我可以写小说和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这一年的生活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尽可能地多出去看一看,哪怕是我小区外的世界,我都要去看一看。
城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凝聚了你的人生
硬核读书会:你们对自己故乡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静睿: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城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凝聚了你的人生,它凝聚了你过去的回忆和情感,这些东西是城市使之为特殊的东西。
我现在每次回老家都很开心,在北方待久了我会很喜欢南方,看到树、看到河还是很开心,这是出于大自然对我的慰藉,可是城市本身的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大头马:其实现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差异已经越来越小了,每个城市看上去都差不多,尤其是像中原的一些地方。我现在暂时住在南京,觉得南京跟合肥差别也不是很大。

硬核读书会: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城市和机遇带来不同,但并没有那么不同。那两位老师你们平时会特意看一些旅行文学作品吗?
李静睿:我很喜欢看奈保尔的书,最近我在重看他的《信徒的国度》,他把印度的国民性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写得特别好。他不能算专门的旅行作家,可是他的书是常看常新的。
![《信徒的国度》[英] V. S. 奈保尔 著, 秦於理 译新经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2014-8](https://i.aiapi.me/h/2022/11/30/Nov_30_2022_09_52_40_633580935148780.jpeg)
奈保尔好像在一个非洲国家待了27个小时,就写出了成名作《大河湾》。奈保尔的书的很多主题都是围绕着一种文化和一个制度之间产生的冲突来谈,《信徒的国度》其实也是他写伊斯兰教和改革之间的冲突的部分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比较喜欢看这种文学性和思考性结合的作品。
我前段时间也看了一本特别好看的书,叫《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作者从家乡科隆往东走到巴尔干半岛,再向南翻过高加索山,抵达他父母的故乡伊斯法罕。他把克里米亚、乌克兰的事情写得很清楚。我今年还看了《中亚行纪: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旅》,它是政治文化与国民混到一块写的,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德] 纳韦德·凯尔曼尼 著,李双志 / 王博 译索·恩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br>](https://i.aiapi.me/h/2022/11/30/Nov_30_2022_09_52_43_633584483612147.jpeg)
大头马:我特别喜欢《忧郁的热带》。我喜欢的也不是单纯的旅行文学,而是多少算所谓的一种跨界或者是一些学术著作,当然不是那种特别严肃的学术著作。或者是一些小说家写的和旅行有关的作品,比如《萨哈林旅行记》。
![《忧郁的热带》[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著,王志明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09<br>](https://i.aiapi.me/h/2022/11/30/Nov_30_2022_09_52_45_633586526530418.jpeg)
硬核读书会:在中国,旅行文学不是一个非常大众、主流的文学类型,有人评价说旅行文学是精英专属的文学体裁,两位老师认可这个说法吗?为什么?
大头马:我以前接触的人教育背景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这两年接触到了更大众的群体。我先是在公安刑警大队待了可能两三年,现在是在一个动物园当志愿者,我的同事大部分看上去也都是那种跟文艺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但是,有一天我在跟我的两个做动物保护的同事聊天,我就说在动物园志愿者经历结束之后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已经想好了,叫做《禅与动物饲养艺术》,其中一个同事立刻就说你这题目也是抄别人的,他读过那本《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我就特别惊讶,我说你怎么会读这本书?
在我的认知里面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日常会有阅读习惯的人,所以我现在觉得还是应该谦卑一点比较好,不要有那种刻板印象。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作者: [美]罗伯特·M.波西格 著,张国辰 译华章同人 | 重庆出版社,2011-9<br>](https://i.aiapi.me/h/2022/11/30/Nov_30_2022_09_52_48_633588964179394.jpeg)
硬核读书会:请两位老师推荐一些和旅行有关的作品给读者,可以是书,也可以是电影。
李静睿:奈保尔的整个旅行系列都很好看,写印度的、写伊斯兰世界的、写加勒比的,最近还出了一本他自己选的精选集,叫《我们的普世文明》。
![《我们的普世文明》[英] V.S.奈保尔 著,马维达 / 翟鹏霄 译 新经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2022-8<br>](https://i.aiapi.me/h/2022/11/30/Nov_30_2022_09_52_50_633591638474314.jpeg)
大头马:如果让我推荐旅行文学的话,我会推荐金庸的小说。我现在去回忆金庸的这些小说,大脑里会跟地点关联起来。比如《神雕侠侣》一开头是在嘉兴,我对这些故事的记忆都与这些地名有关。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去读金庸的小说都会有新的感悟。
李静睿:金庸的小说既是很好的旅行文学,也是很好的历史读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王亚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