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钟毅,题图来自:《极乐迪斯科》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为游戏站队。比如在泛游戏论者、人类学家斯蒂芬森眼中,游戏是使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存在。
斯蒂芬森声称:“游戏是每个人的佯装出游,它将现实世界的纷扰与义务抛诸脑后;游戏是每一天的生活插曲,它与日常生活与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在他看来,游戏就是在纯粹地传播快乐。
虽然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进入过主流理论的圈子里,但是水管工的蹦跳和投掷红白色精灵球时产生的快感,都在再次确认人的娱乐天性。
而比斯蒂芬森更早、人类学家赫伊津哈作为第一位深入系统研究人类游戏的学者,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就已认为,文化存在于游戏之中,游戏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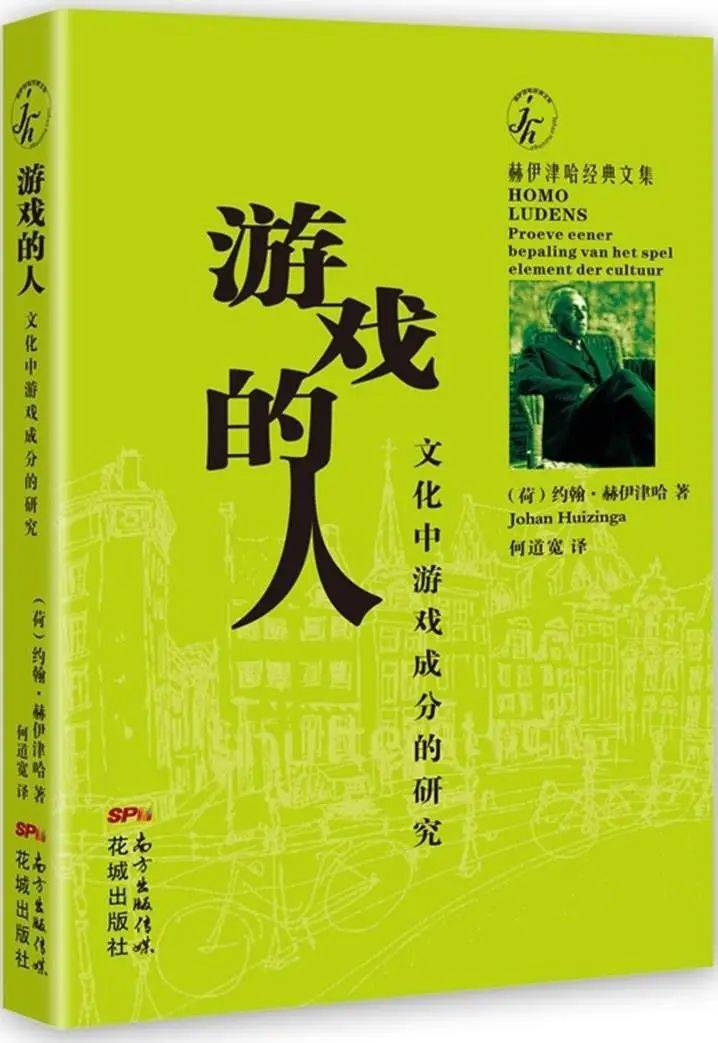
[荷]约翰·赫伊津哈 著,何道宽 译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2017-1
他从文明视角看待游戏并将其特征归纳为三点:自由自主的、不同于生活的、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人们脱离了日常生活,自发主动地进入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世界,开展能够热情投入却无利可图的行为,且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中按规则展开。
和以往物质匮乏的时代相比,现代人曾经被压抑的游戏欲望被解放了。
有高校开始开设游戏艺术和电子竞技专业,2021年11月份EDG夺冠的消息也在各类社交媒体上刷屏。
游戏开始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央,否定游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游戏本身,早已不只是街头霸王的街机娱乐。在大家彼此隔绝的时期,《动物森友会》给予了玩家线上相聚的温情、《只狼》《双人成行》《人类一败涂地》等游戏也风靡全网。
如今的游戏中不仅包括了动作、任务、操作,也包括了情绪、知识、价值观和交互性。
作为第九艺术的游戏,也开始通过调动人们的参与、沉浸与反馈,在文学呈现上占据一席之地。
二、当文学遇见游戏
早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登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提到“所有的文学都具有交互性”。但是,文学的交互性充满着隐晦色彩,作者埋下的伏笔和留白,都不是摆在台面上的内容。
私认为,文学并不讲求有多少互动感,无论读者或观众是否与内容互动,剧情都会继续推进下去。
因此,文学更像是作者单方面的撒播和表演。即便是后来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理论一度将解读的权力交还到了读者手中,作品还是一定程度上依赖作者的存在。而游戏区别于前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必须依靠玩家的互动和理解才能推进,它召唤玩家在探索中走向叙事的完整。

那么,游戏是否能成为文学的栖身之所,或者说,当文学与游戏相结合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文学+游戏”的配置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文本性、哲理性强的游戏,另一种则是叙事游戏。
先说第一种,一些文本性强的游戏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带有强烈交互性质的小说。
要举例子自然是在2019年包揽TGA(游戏界的奥斯卡奖)四项大奖的《极乐迪斯科》,它原本就是根据爱沙尼亚语小说改编的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玩家会发现整个游戏的背景被拆解成不同零碎的部分,玩家需要自行搜寻和拼接线索,高度的开放性让玩家可以很快地沉浸入游戏世界中。

而在通过媒介特性将受众吸引进入游戏世界,是游戏的第一步。场景、动作等要素,无一不是为了游戏文本所服务。
“你闭上眼,听见狗在吠叫。一个孤独的女人坐在工厂窗户旁边,梦想着陨石撞击这个星球......旧南城里,一个没有眼睑的男人在微笑。春天来了,到时间了。”
“下方,城市随着余下的灯火一起颤抖。人们赶回家,离开家,抽烟,睡觉,边洗澡边唱歌。在灯光熄灭之前,餐桌边缘、手,还有围裙都在窗户里闪烁。”
“当你掷出骰子的时候,会发现它每次都给出相同的结果——‘上帝是冷漠的’——这就是我们的诅咒。”比她说得还要糟。上帝已死——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遗忘的年代。”
如果把这些话单拎出来,读者或许会认为这些是从哪本文学作品里摘录下来的片段,实际上这些都是游戏中的对话或者旁白。
以一个尚待破解的凶杀案为线索,铺天盖地的文本就此展开——在文字体量巨大的对白和主人公哈里的个人思索中,玩家通过点击选择不同的思维走向塑造不同的人格,关于艺术、真理之路的思考被迫进行。

如果说《极乐迪斯科》属于是那种文本性强的游戏,那么像《全网公敌》《游荡者: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我在七年后等着你》这类则是在情节的故事性上取胜的游戏。
这类互动叙事类型的游戏可以理解为“用游戏的方式讲好一个故事”的典范。
“讲好一个故事”是这类游戏的最终任务,达成这一目标也有不同的方式。
《全网公敌》《我在七年后等着你》都偏向纯剧情类型。在《全网公敌》中,玩家需要扮演一名解密的黑客,依次解决看似五个独立的事件,被监视对象的每一个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甚至是银行卡支付信息都无所遁形。通过在海量的信息中抽丝剥茧,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故事开始跃然于水面。

而《我在七年后等着你》则直接被一些玩家评价为“根本不像游戏”“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故事”。游戏设计者收窄了玩家的自由程度,玩家基本上只能根据剧情行动,按照游戏设计的环节一步一步地踏入故事线。
数个故事不断堆叠,以男主角春人寻找丢失的记忆为主线,高度的体验感让玩家最后走到结局一刻时几乎无一避免地代入到了男女主角回溯时间只为再次遇见对方的情感中。

与以上两种相对的,在《游荡者: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节选改编自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玩法则更加自由:玩家只需通过点击屏幕在场景内探索道路,而场景内也具有极强的互动性:选择吃完腐尸之后,游戏画面会短暂地停留在黑色的画面,原本富有生命力的自然场景变得黑暗恐怖;吃下花朵后,游戏画面则会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除去精美的画面制作,故事的叙事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亮点。游戏讲述了一个想要寻找自己,却最终在沉默中消亡的故事。

被创造出来的怪人思考在黑白世界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和三个小男孩踢完足球之后,怪人“跟在他们后面,因为不再孤单而欣喜若狂”,然而当他跟着三个小男孩遇见了镇子里的大人时,大人拿起武器站在镇子里的每个入口,开始驱赶这个“怪胎”。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怒不可遏,我必须远离那些叫做‘人类’的生物。”遇见了喜欢的人之后,他原本以为可以不再孤独,摘下面具之后爱人却毅然离去。而这个改编自原著的游戏最后的几种结局皆是悲剧——报复人类、走入冰川或抹杀自己。
游玩过程中的孤独感向读者说明,哪怕色彩在某一瞬间非常鲜艳,都改变不了这个故事悲剧的底色。
如果是阅读原著,读者只是一个目睹悲剧发生的旁观者。而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即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人,NPC的每一次冷眼、每一块投掷的石头,都扔在自己身上。
三、“所有文学都具有交互性”
陪跑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次接受《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过程中说道:“当下, 游戏可能是最适合文学的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像纸质文学和数字化文学的改变,因为内容并不是简单地从纸上迁移到了数字平台,而是更深层的——文学的边界被直接地突破了。
在这种跨媒介叙事中,一种崭新的互动系统诞生了。受众可以直接地身处特定的世界中,解读各种各样的符码,纯粹地享受共情和扮演的乐趣。
《极乐迪斯科》里骷髅头辛迪站在被炮灰摧毁的二楼,将一罐红色颜料倾倒而下,巨大的刷子上写满了对世界的祈愿,倾诉艺术的本质是让大多数人感到愉悦,不远处,穿着绿衣服的有钱女人在自己的船上打着精明的算盘。
《游荡者: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怪人走向一片白茫茫的冰川,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摆脱名为孤独的怪物。
《行尸走肉》的末日世界中,克莱曼婷在做完关于生命的选择后,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准备独自一人穿过面前的僵尸群。

以上的这些故事情节和画面如果只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其冲击力和画面感远不及游戏的交互性所带来的强烈。
在游戏打造的赛博世界中,内容由文本变成了超文本,作者和玩家从阅读关系变成互动关系,故事的结局和走向甚至还会取决于游戏者的选择,由作者决定论变成了作者和玩家共同创造。
游戏与文学并不必要成为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线。《极乐迪斯科》主创团队爱沙尼亚游戏工作室ZA/UM的名字就来源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阿列克谢·叶利谢耶维奇·克鲁奇尼赫,这个词由俄文的前缀“зá”(超越)和名词“умь”(思想)构成,并无确定的含义,却象征一种超验式的诗意。
在争论游戏是否有资格进入文学殿堂时,实际上也在把文学画地为牢。
许多在叙事或文本上出彩的游戏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甚至一部分还走上了影视化的道路。这些都证明了,吞噬文学的诗性的并不是某种媒介,而是想象力的局限。就像当时ZA/UM其中一位小说家Kaur Kender 找到正在酗酒的Robert Kurvitz ,说道:
“不要再写作了。如今已经没有人看书了。要不要试试电子游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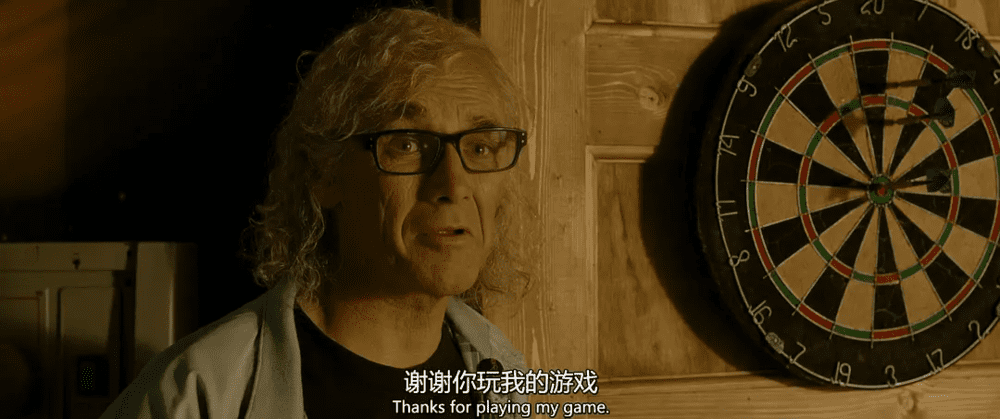
参考资料:
1. 陈洁雯、胡翼青《从斯蒂芬森出发:传播游戏理论的新进展》
2. 熊超琨《电子游戏超文本叙事研究》
3. 喻国明、杨颖兮《参与、沉浸、反馈:盈余时代有效传播三要素——关于游戏范式作为未来传播主流范式的理论探讨》
4. Gamesradar,The making of Disco Elysium: How ZA/UM created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RPGs of the decad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钟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