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怎样观察ta的世界、思考ta的经历、描写ta的生活?作家王梆今年出版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写她对英国底层生活观察的《贫穷的质感》,一部是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
她的文字时而疏离、冷静,时而热烈、酣畅。并不顺遂的经历给了她更加敏锐的观察力与反抗性。读过这篇对谈之后,或许你会更加理解,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优秀作者,是如何“锤炼”出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宋爽,头图来自:《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奇特的是,和王梆聊天,让我猛然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这句话:“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至少在王梆的表述中,她的人生过往和“优越条件”不怎么沾边。她的生活,从年少开始,就注定走向两条道路:要么出走,要么溺水。
但世界运转的方式往往以令人惊异的姿态展露出来。我们总会说,一个幸福的童年会让人获得更幸福的人生,但也经常忽略掉,一个幸福的、几乎毫无坎坷的早年生活,也容易让一个人无须思考过多——简言之,容易停留在较为肤浅的思想层面。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
我要说的是,那样甜滋滋的生活全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苦难稍多一点的生活也有可能将沙砾磨成钻石,在一片荒芜之中发出一些光芒来。

这种光芒很刺眼,这个形容用在王梆身上再合适不过。她的文字和表述绝非星光熠熠、溜光水滑的,那些稍显奇特的文字和她本人的遭遇一样令人不适。但这种硌人的不适感在她看来,是有价值的。
她的笔下出现了各式女性,虽然面貌各异,但核心都没什么二致。她们是一群强硬、执拗和不屈的女性,在生活展现出的万千姿态中,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还不是苟活”。
以下是《新周刊》与王梆的对谈实录:
一、身体内外自带一层隔离膜
《新周刊》:《假装在西贡》里面的对话并不多,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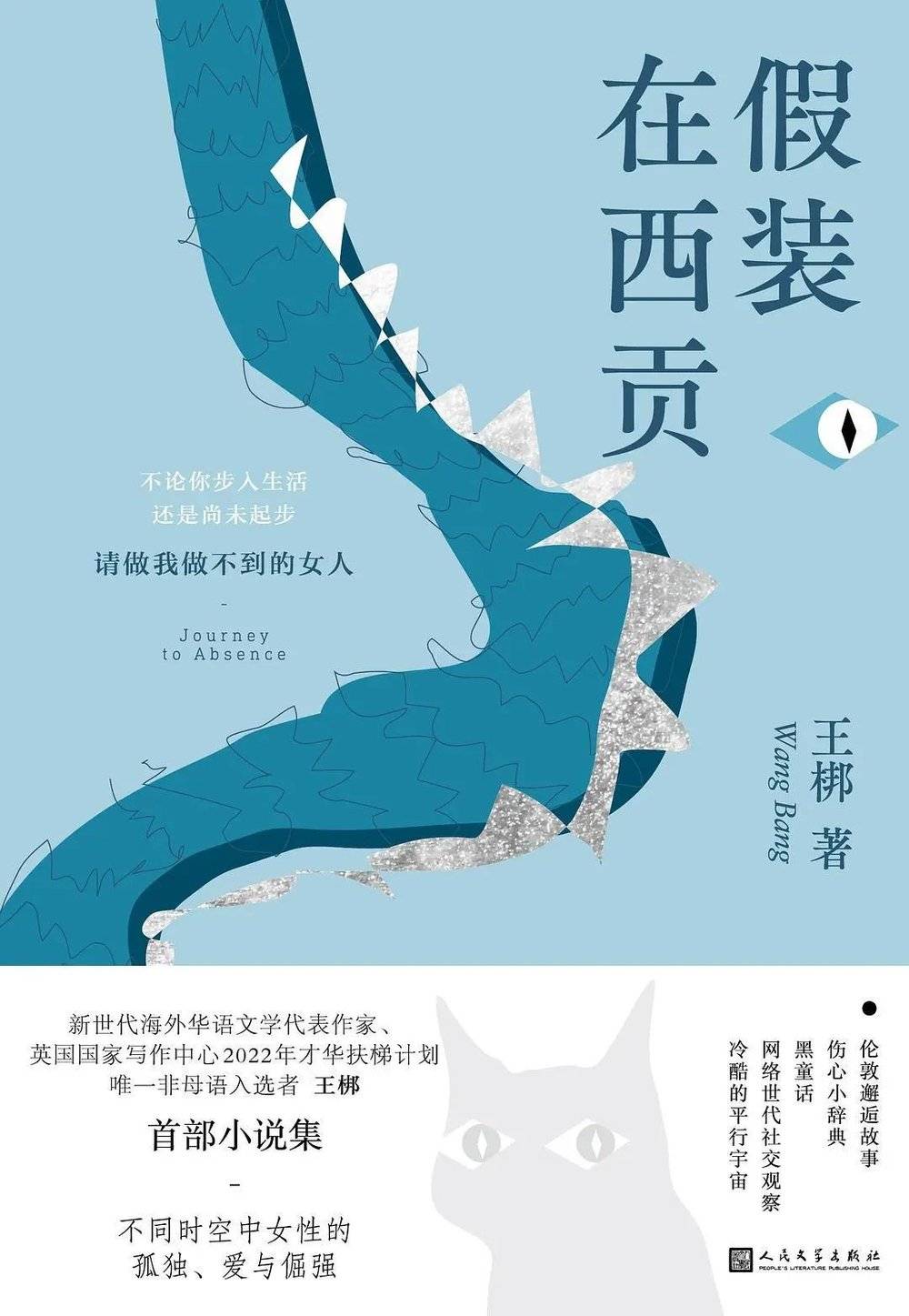
《假装在西贡》王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8
王梆:对话太难写了。我是南方人,我的故事主角来自五湖四海,对我来说要准确把握方言的魅力非常困难。
对话体要求作者能够精准描绘出某个地方来的人说话的腔调,就像你也是在那里出生一样。你现在听我说话,就知道我是地道的南方人,有很重的南方口音。所以我为了避免自己在方言掌握上的缺陷,就只能少写对话。
《新周刊》: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作家,他们会认为自己不论写哪里的人,都会选择用一种口吻去表达他的语言,而不会在乎方言这个问题,因为作家会认为人性是共通的。
王梆:2022年我入选了英国国家写作中心一个叫“才华扶梯”的项目,我的导师——曾获得布克奖提名的英国小说家伊薇特·爱德华兹(Yvvette Edwards)对我说:“对话要体现出人物的生存背景。”
比如我手头正在创作的这部英文小说,就写到偷渡客、外来新娘以及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工。导师希望我笔下那些初来乍到的华裔移民工,即使用英语对话,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他们是华裔。

后来我去唐人街的中餐馆,边吃饭边竖起耳朵听员工们讲英语,发现他们说的英语确实有一种规律。中国劳动人民的英文语法是朴素的,简、快、平,不拖泥带水,不加复数,不发后缀音,我得把这个规律写出来,让人一看到这个对话,就知道是他们说的。
《新周刊》:你小时候是在大院里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大院?
王梆:我们住的大院,规模比王朔笔下的大院要小得多,但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企事业大院,比如《看上去很美》小说主人公方枪枪住过的那种大院的痕迹。
最典型的痕迹就是“等级”,大院无论大小,都隐藏着森严的等级,谁可以欺负、谁不行,取决于谁有个怎样的爹。
所以,我的中篇小说《天青》(收录在《假装在西贡》)会花很大篇幅描述某个有点权势的爹和他的“爹学”。我对这种“爹学”和文化环境非常熟悉,可以说我一进去那里,就知道他们(大院里的人)会怎么做,会怎么说话。

我们那一片的大院有一种苏联的氛围,老旧的红砖房、游泳池、篮球场,一应俱全。一些大院长大的孩子,因为父母对自己特别苛刻,所以从小也比较势利眼, 再加上又都有那么一点小文化,故而对人、对事比较刻薄。当他们聚拢起来,围攻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会很具杀伤力。
《新周刊》:你个人似乎和这个群体格格不入。这种相对隔绝的生长环境,容易让人多少有些傲慢,而且不屑于食人间烟火,但同时也会让人对外界、对市井生活产生极大的好奇。
王梆:是这样的。从小到大,我都比较叛逆。我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大院里,谈不上合群,我可能还从武侠电影或小说里学了一些小小的冷暴力,虽然不会用语言或行动去攻击谁,但身体内外自带一层隔离膜,令那些特别霸道的孩子不好接近。
总之,我对自己的生长环境很抵触,尤其是对那种表面上看起来特别乖,但背地里其实很有心计的人比较反感。

我有几个好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其中一个朋友得了红斑狼疮。小时候我们很亲密,后来她去了一个重点中学,然后就得病了,16岁时走的。我们大院里,还有一个少年,游泳时溺水,也没救过来。所以溺水的记忆会出现在《天青》里,我会反复写一个池塘,那个池塘非常深、非常暗,就像我们的早年记忆。
尽管我们的少年时代,不像偏远农村的孩子那么艰辛,但我们经历了很多悲伤的故事,我想在《天青》里,把这种伤感的、青春的记忆写出来。
《新周刊》:你个人似乎和这个群体格格不入。这种相对隔绝的生长环境,容易让人多少有些傲慢,而且不屑于食人间烟火,但同时也会让人对外界、对市井生活产生极大的好奇。
二、完美的生活都是一种修饰,甚至是一种粉饰
《新周刊》:你刚提到,你有时会专门去观察人群,你小说中主角的原型一般都从何而来?
王梆:我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自身的反射。
大学毕业后,我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年,大都市繁花似锦,却也光怪陆离,人们那种普遍对成功感的追求,比小地方的人还要明显得多。因此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非常清醒的孤独感。
中篇小说《假装在西贡》,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清冽的孤独。一个都市女性,为什么会陷入那样的境地?是因为别人让她走的路,她都不想走。正常恋爱、结婚生子、养房养车……你给她什么,她都不想要,你让她随波逐流,她偏要逆流而上,除了对抗,也没有其他方法,所以自然就会孤独。

我身边充满了这样的人,有舞者,有学琴的,有诗人,他们都是跟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一拨人,但这种格格不入又是必须的。我觉得那种对生活的所谓的甜蜜感非常腻,那种极度甜蜜、完美的生活都是一种修饰,甚至是一种粉饰。
《新周刊》:我想知道你刚提到的这些女性在对抗,她们到底是在对抗些什么?比如你刚说了,给她什么,她都不要,那么她在反抗什么?
王梆:作为一个非常关切女性生存状况的人,我会在人生中面对很多问题,比如是否愿意过我父母为我安排的生活。

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严谨的家庭,我的父母会觉得,你不要读那样的书,不要看那样的电影,不要听那样的音乐,这些都是我要对抗的。在一个社会里没有对抗,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新周刊》:为什么要起《假装在西贡》这个名字?
王梆:它来源于一个叫“假装在纽约”的微信公众号,“假装”成了一种青年生活的固定时态,假装在某地,是对“不在此地”的一种存在主义式注解。
比如现在很多社交平台开始显示IP,你就会突然发现,很多人根本不在签名所显示的地方。《假装在西贡》应该就是受了这样一种亚文化氛围的影响。选择西贡(西贡是旧称,现已改名为“胡志明市”),是因为我在那里晃晃悠悠过了大半年,对每个角落都很熟悉,所以我自然就想到它。越南虽小,你却可以在它身上看到一些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
《新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非常关注女性议题的?
王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吧。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厌女的家庭里,父亲对我和弟弟并非一视同仁。在父亲的观念里面,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他会认为,女人要做女人分内的事情,像洗碗等家务这些;坐要有坐相,腰要直,要低眉顺眼,穿衣服不要外露。
但是,他虽然不尊重女性,却会尊重他的母亲。女人在他眼中,只有成了母亲,完成了生产和男权社会分配给你的任务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尽管如此,在出现婆媳矛盾时,他还是会对我的母亲恶言相向。
我童年的背景音,基本上就是父母的吵架声。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始终未能从这样一种被侮辱的环境里走出来,虽然她和父亲离了婚,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独立生活,但她依然会延续父亲的那套话语,她会说:你穿这么暴露,是想要色狼在你背上划几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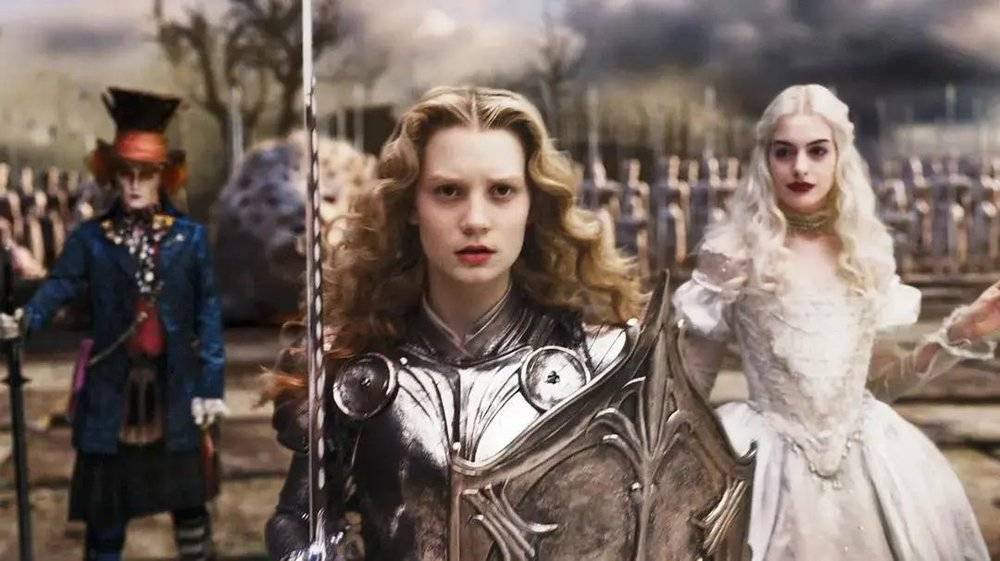
《新周刊》:我现在突然明白你笔下的女性十分决绝、不善媚术的原因了。
王梆:是的,我从懂事的那一刻开始,就在立志做一个和我的母亲不一样的人。因为我没有出路。要不就做一个乖女儿,以一生不自由为代价,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是不假思索的,是本能的。
《新周刊》:这也是你的写作对象都是女性的原因,对吗?你会不会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使命感,一定要把视角对向女性?
王梆:我喜欢描述女性生活,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此外,我对姐妹情谊亦有一种饥渴感,因为自己没能从母亲那里获得这种情谊,所以长大后,见到坚强、慷慨、勇敢的女性,就会有一种想要靠近的欲望。

《新周刊》:会有人认为,女性作家就爱关注女性写作,而男性作家的视角可能更广阔。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梆:是吗?我觉得他们如果看了我的英国观察《贫穷的质感》,或者我给杂志写的时评专栏,如果不是事先得知我的女性作者身份,恐怕会以为它们出自男性之手吧。不少人觉得仿佛只有男性作家才会涉猎时政话题,这是一种偏见。
三、继续生活下去,而且还不能是苟活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贫穷的质感》,为什么你会选择关注英国的贫困阶层和边缘群体?

王梆:英国有15%~20%的贫穷人口,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正好被“空降”到了那个群体里面。作为一个作家,肯定要先关注周遭的生存空间,这并不等于说我对贵族和上流社会就毫无认知的兴趣,只是我至今没有机会进入那个阶层而已。
新周刊:你所观察到的这个阶层,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王梆:我当时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房子在装修,有很多来自东欧和本地的油漆工,一边刷漆一边大放音乐。我仔细听了一下,他们听的都是像Coldplay(酷玩乐队)、U2等乐队的那些歌曲,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像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听郑智化的歌曲或《我的滑板鞋》那样。无论在哪里,工人阶层似乎都喜欢通过激荡的音乐,舒缓自身的疲惫和苦难。

此外,读书也是一点。我们的小区有一个读书会,事实上几乎每个小区都有,来参加读书会的人有油漆工、水管工等各类人群,我们会一起阅读和分享历年来比较流行的、获奖的书籍,而这些书是各个阶层都会阅读的,并不只是中产或上层社会才会看。
《新周刊》:你如何形容自己的语言风格?
王梆:我比较喜欢异质化的语言。我觉得语言要有陌生感,陌生即美,那些被用烂的、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我会觉得比较cliché(陈词滥调)。所以我有意要避开,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更陌生化一点。
《新周刊》:你在英国待了这么久,会影响到你的语言风格吗?
王梆:像汉语一样,英语非常优美,博大精深。我尤其偏爱它里面的动词,它的很多动词极具速度和力量感,让人很想生搬过来。我也喜欢英国的思维方式,它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的色彩在里面,自我、奔放,像脱缰的野马。

《新周刊》:写作的时候,你最着迷的是什么?
王梆:它的虚构性。不像非虚构的现场采访,写小说时,我可以躺在床上,哪都不用去,然后故事就在你脑中的巨大屏幕里展开了。
《新周刊》:你认为你的作品底色是什么样的?
王梆:我的作品荒诞、苍凉,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色彩。但在这种叙事里,你仍然要非常坚定,像水中努力游向对岸的豹子,保持上扬的体态,继续生活下去,而且还不能是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宋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