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穷人起初凭借工作,后来凭借消费,似乎总在洗牌,又似乎岿然不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题图来自:《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贫穷和懒惰总是肖似一对孪生兄弟。而勤奋工作往往站在它们的对立面,似乎天然拥有着“伟光正”的英雄姿态。
贫穷源于不工作,潦倒应该归咎于懒惰,这种看似理性的论调实际是后天才创造出来的“工作伦理”: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此获取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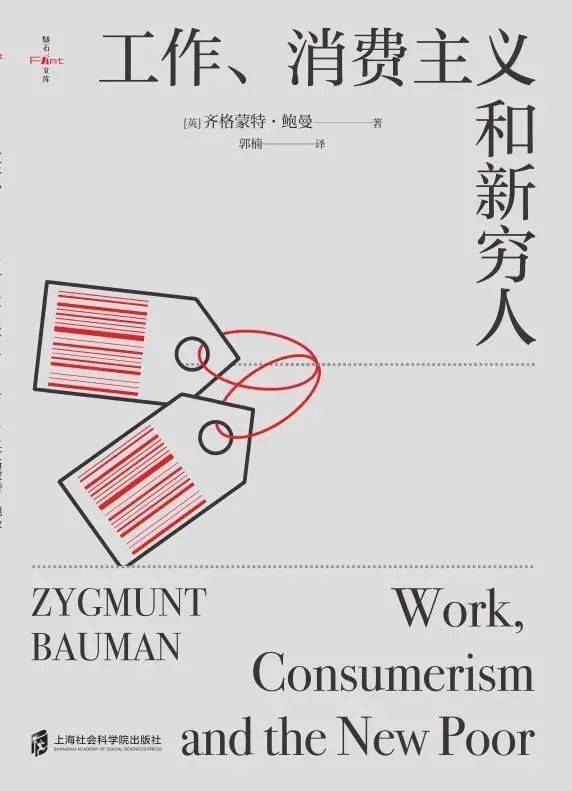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郭楠 译
燧石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9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工业化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到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口号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似乎和现在资本方“画饼充饥”的行为如出一辙。这种志在引领愚昧大众走向理性和智慧,实际上瓦解了当时的工匠和自身原有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
鲍曼说,后来进行的道德改革运动,试图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绩效,但是这些追求,是过去的工匠在自己掌握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却被工作伦理所破坏的。
1. 有关穷人的工作伦理
英国学者约瑟亚·柴尔德(Josiah Child)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
在鲍曼的理解中,“工作是‘人对上帝的责任’”这则观念暗示了,把穷人限制在贫穷状态是一种道德要求,“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忙不迭地立即证明,当工资保持在低水平的时候,‘穷人会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生活得更好’,而他们领取高工资时,他们就迷失于无所事事和聚众闹事”。
而现代智慧的代表者之一杰里米·边沁,更激进地表示,身处贫穷的事实就说明穷人并不比不守规矩的孩子更有资格获得自由,他们不能管理自己,只能被管理,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要对付善变又愚蠢的穷人,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
对于此类曾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现今更可能招致谩骂的“坦率”哲学,鲍曼提出,“尽管存在大量的反面证据,人们还是顽固地认为废除普遍的以工代赈是造成贫困的首要原因,解决贫困问题应当着力于引导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若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公共政策,那就是: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在那时,工作被塑造成是穷人被社会接纳、寻找社会定位的重要途径。穷人变成了工业世界的储备劳动力和稳定秩序里的一分子。
学者基斯·麦克利兰(Keith McClelland)曾指出,许多人认为体力劳动是必要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值得称颂,因为它将为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为工人带来道德上的提升。
尽管工人们对“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深有体会,对粗暴、残酷、规律性的制度极度厌恶,也不得不加入其中,相较更加糟糕的贫困境况,微薄的工资也拥有了吸引力。

与此同时,提倡工作伦理的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鲍曼解释,“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在工作伦理盛行的时代,穷人拥有了社会劳动资源的“光明”身份。在穷人和富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的宗教光环之外,穷人也得到了一种实际不公但听上去正义的“庇护”。
2. 工作之于生活,是一种“基准”
在鲍曼眼里,工作首先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而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鲍曼总结:“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中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被分配的工作类型。工作类型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它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过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决定了预期的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正是这个‘独立变量’让人们塑造自我,并准确预测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确定了工作类型和职业规划,其余的事情就水到渠成,需要做什么也基本确定下来。总而言之: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工作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构成。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男性的绝大多数可支配时间、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写道:“在这里,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形成自己的‘社会性格’(至少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社会性格)。除大规模征兵(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
除此之外,进入工厂的广大男性以“养家糊口”为绝对权威建立起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也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鲍曼分析道:“在家庭内部,丈夫和父亲被要求扮演监督或管教的角色,类似工头在工厂中,或校尉在操场上发挥的作用。正如福柯坚持的,现代的规训权力,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和延伸,将心脏泵送的血液传导到生物体的每一个细微组织和细胞。家庭的父权将秩序生产和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传导到圆形监狱无法触及的人群。”
在社会生存和繁荣问题中,工作也被赋予了决定性作用——资本的活跃和就业的增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也是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
3. 新穷人,也是“有缺陷的消费者”
如果说在工作伦理盛行的时代,穷人可以通过劳动力这个身份获得被社会接纳和认可的机会,那么,在工作伦理式微的今天,穷人的处境似乎更加江河日下。
现在,企业倡导的是劳动力精简,减少劳动成本,穷人作为劳动力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迫切需求。“把穷人培养成未来的劳动者,曾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有意义。它促进了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完成了‘社会整合’的任务——秩序维护和规范管理。”
“然而,在‘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这两种意义都不成立了。”鲍曼说,“工业社会是以权力冲突拉开序幕,那时的人们为自治和自由而斗争。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
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鲍曼认为,过去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如今已经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经济水平变成衡量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准绳。

社会已经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并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鲍曼的陈辞,和目前消费主义即正义的现状几乎无缝衔接,“穷人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信用卡和美好前景,他们达不到要求。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
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吸入任何靠近的东西,吐出的只有麻烦。
体面、正常的社会成员,那些消费者,他们对穷人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期待。穷人是完全没价值的,没有人(真正有身份、有话语权的人)需要他们。对穷人应该零容忍,没有他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没有人需要他们,所以他们最好不存在。他们可以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会因此懊悔或内疚”。
在工业社会早期,穷人是“不工作”“道德沦丧”“社会蠹虫”的联想词,在消费社会中,穷人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也消费,只是消费得远远不够。在重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穷人起初凭借工作,后来凭借消费,似乎总在洗牌,又似乎岿然不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