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期待下一个余华、莫言和刘慈欣,只是文学巨星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程迟,头图来自:《活着》剧照截图
出版界常会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的青年作家,很难重现余华、莫言、刘慈欣等前辈作家的销量奇迹?
青年作家的写作水平并不差,近年来也诞生过诸如双雪涛、班宇、林奕含、陈春成等销售成绩较好的例子,但严格来说,除了双雪涛和班宇的小说得到明星推荐和影视改编的加持,以及林奕含的作品因社会热点被关注到以外,大部分流行青年作家,其实都属于小范围热门,不像余华、莫言、刘慈欣,能够跨越老中青三代,获得家喻户晓的影响力。

或许我们自己听过陈春成、双雪涛,觉得他们已经很出名了,但一问起父母,或者问其他行业的人,他们就未必知道,可是一提起余华和莫言,大部分人显然都听说过。
横亘在青年作家面前的问题是,除非有一个重大公共事件的推动,否则当代青年作家很难靠作品本身来跨越圈层阻隔。
或许有人会说:“拿青年作家与成名作家比较,并不公平。”但《活着》写于1992年,那一年余华32岁;《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那一年莫言31岁;焉论出名趁早的张爱玲,24岁就写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他们都是在青年时期写出了成名作。有趣的是,上一个能激起各阶层讨论的青年作家,已经是萌芽一代出身的韩寒和郭敬明,现在他们都去拍电影了。
一、余华的销量神话有历史原因,今天无法复制
早在2020年,余华《活着》的单本销量就已经突破两千万册。他2021年出版的小说《文城》,首印五十万册已全部卖光。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由读客策划、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自发布后居于当当新书总榜第一、抖音上架两天销量破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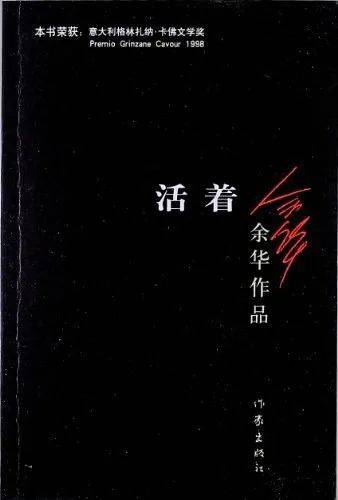
出版界每年推出不少新人作家,但蓦然回首,年终榜单熟悉的名字还是余华、莫言、刘慈欣、张嘉佳,像林奕含和陈春成这样的青年作家能位居其中,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事。


比方说在当当2021年的虚构畅销榜上,国内新人作家的作品仅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入围。
而在京东虚构畅销榜和微信读书榜单上,高居前列的依旧是东野圭吾、村上春树、余华、刘慈欣、张嘉佳等老面孔,陈春成这样的新人跻身其中,在新人作家里实属难得,而大部分新人作家仍要面对回应者寥寥的境遇,他们或是短暂被讨论,又如秋风扫落叶般被遗忘,或是干脆被区隔在主流的话语之外,以一种地下作家的身份寂寞地游戏。
林奕含在去世后才被人熟知,创作了《大象席地而坐》的胡波也重复了这样的命运。如今被豆瓣读者津津乐道,书写了《寂寞的游戏》与《送行》的袁哲生,也早在2004年匆匆离开了人世。在时代的幸运儿之外,大部分作家或是独行一生,或是在死后享有迟到的殊荣。

当然,自不必美化青年作家的道路,这是求仁得仁的事情,坦率来说,至少能被我们知道的写作者,哪怕只是小圈子里流传的,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比大部分工人要好,因此无需自恋地粉饰作者的痛苦与孤独,而不妨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为什么今天的青年作家,很难再复制余华、莫言那样的幸运?当诸多新人作家难以被看见,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阻碍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的成就是个人努力和时代进程的总和,作品能引起怎样的反响,不是作家能左右的事。比如约翰·威廉斯1965年创作《斯通纳》,他想不到这本小说蒙尘五十年后,会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成为畅销书。
同样,余华写作《活着》能引起全民讨论,固然是因为作品本身出色,但如果没有八十年代那个全民讨论文学的氛围作为铺垫,九十年代文学依然是重要的大众消费品,《活着》也不可能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
我曾经跟一位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编辑聊天,他说:“那阵子,我们的刊物有几十万人在看,现在不行了,只有几千甚至几百人。”余华自己也说:“《活着》为什么现在受欢迎?也是三个字‘运气好’,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余华这是自谦之词,但的确,如果《活着》在今天首印出版,它可能会像《夜晚的潜水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样,成为小范围的畅销书,但很难达到家喻户晓,你爷爷奶奶都知道的地步,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众休闲消费已经细分的市场。
八十年代有文学全民热,是因为平民百姓的娱乐选项尚不发达,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综艺节目、选秀节目、短视频,更谈不上“网文”,阅读诗歌和小说成为大众消遣的主要方式。大学里不读一本北岛或顾城,不闲聊几句马尔克斯或米兰·昆德拉,都不好意思自嘲“文艺青年”。
但是从九十年代互联网出现以来,文学的大众消遣功能就被慢慢淡化了,文学界也日益分野为“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传统的期刊杂志文学和互联网上兴起的网络文学,文学写作者又逐渐细分,例如早期的先锋派余华、格非、苏童等人,转型到古典写作或现实主义与先锋技巧混合的写作风格。
由韩东、朱文推动的“断裂”写作运动,以王小波为代表的启蒙写作和对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反思,还有陈染、林白、棉棉的女性主义写作,于坚、韩东、张枣、西川等人的进一步诗学探索与各自不同的纵深。
由此可见,九十年代后,文学已经在快速细分和部落化,文学所承载的大众消遣功能,也逐渐被互联网、歌舞厅、蹦迪场所、综艺节目和唱歌节目所分流。这是一条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才是一个幸运又偶然的产物。
在千禧年以后市场化的浪潮中,文学一度呈现出泡沫繁荣——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兴起,三毛、安妮宝贝(后改笔名“庆山”)、韩寒与郭敬明等作家被全民讨论,仿佛八十年代那股全民关注文学的热潮又复苏了,舆论也一度认为文学的读者群在迅速扩大。
但沉淀过后会发现,新概念引起的文学热,并没有为严肃文学培养出一个坚实稳定的阅读群体。
媒体把焦点放在若干个明星作家的身上,媒体投放的资源、大众的兴趣点,是郭敬明《小时代》所引起的争议、韩寒的历次笔战、安妮宝贝或其他作家所引起的高雅与通俗之争,而不是真正以文学质量作为基础的讨论。
大众对明星作家的热情,并没有反哺到严肃文学中,而是反映为通俗文学的销量数据,它并不像文学基础和市场细分已经做得较为出色的英、法等国家,有一个稳固的中间阶层,作为严肃文学的消费者。
也没有借助对热点的讨论,提升读者在文学鉴赏和文本细读上的耐心,反而是随着互联网媒介的二次革命——纸媒衰弱、自媒体崛起,短视频取代文字成为弄潮儿,而文学在短暂成为舆论焦点后,再一次回到它边缘的位置。

或许,文学边缘化才是历史的常态。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会给人一种错觉,觉得那是一种正常的文学表现,但把时间拉长,在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文学都不是大众关注的中心。
当今青年作家无法复制余华那样的销量奇迹,既是时势使然,也是文学细分化和部落化的结果。
在今天,文学写作者很难作为大众偶像或公共意见领袖存在,互联网话语的平民化、下移化,也让作家和知识分子一呼百应的氛围被扫入历史的坟茔。人们讨厌被教育,喜欢被迎合,以流量和用户兴趣为标准的算法,加剧了这种“作者为平台和读者服务”的趋势。
以文学为职业的写作者,在今日的定位犹如打磨一个个陶器的工匠,他们是手艺人,是造梦者,但在作品交付之后,他们只能等待编辑、出版商、平台和市场的裁决,在这个生产链条中,新人作者处于卑微而被动的角色。
二、再见,作者中心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验写作者,或者说是中国语境下的先锋写作者会更加艰难。
自八十年代先锋热消弭以后,现实主义再度成为国内文学的主流,读者的阅读趣味、接受程度,仍然以现实主义文学为基础,而市场并没有培养起一个稳固的、足以支撑广大实验写作者体面生活的购买力群体。
换言之,读者会喜闻乐见于巴尔扎克、福楼拜继承者的艺术作品出现,如果是继承自世情小说,如《金瓶梅》或《海上花》笔法的,读者也会拍手称快,但如果是继承自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那样的现代主义笔法,或者法国新小说派的实验小说,它们的阅读群体就会大大缩小,成为小范围文学爱好者敝帚自珍的读物。
这些年,中国并不缺乏新潮的、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笔法的写作者,例如业已蜚声中外的马原、残雪、阎连科、余华、格非、孙甘露,已经写出代表作的路内、林棹、刘亮程、霍香结,以及近年来冒出的青年作家周恺、黎幺、孙一圣、彭剑斌、慕明、李唐、郑在欢等。
这一名单如果仔细罗列,还能列出一长串,他们未必认领“先锋写作”的标签,写作风格也不局限于一脉,但他们都彰显出冒犯传统、敢于实验的小说气质。
然而,因为实验小说的读者群体在中国有待扩展,大众媒体也更乐于推广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们很难看到一部实验小说能卖出六十万册,并斩获国内最高的文学奖项,而这在法国已经发生。
2020年,“乌力波”团体的作家埃尔韦·勒泰利耶(Hervé Le Tellier)凭借《异常》(L’Anomalie)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截至2021年2月中旬,这本书已经卖出了63.3万册,仅低于当年杜拉斯的《情人》。
![《异常》[法] 埃尔维·勒泰利耶 著,余中先 译,海天出版社,2021-7](https://i.aiapi.me/h/2022/01/22/Jan_22_2022_20_30_42_29885612735036734.jpeg)
值得一提的是,自普鲁斯特、塞利纳以来,法兰西不乏新潮写作者同时被市场和奖项所青睐,例如罗布·格里耶、乔治·佩雷克等,法国读者对于小说的语感、创新性、冒犯权威的能力格外挑剔,他们重视语言和风格更胜于故事,而在国内,大部分读者仍强调故事是小说的第一要素。
1960年代,法国先锋写作者曾经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名叫“乌力波”(Oulipo)。所谓“Oulipo”,即“L’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汉语翻译为“潜在文学工场”。他们以探索文字表达的可能性作为宗旨,鼎鼎大名的雷蒙·格诺、乔治·佩雷克、卡尔维诺、埃尔韦·勒泰利耶等,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员。
他们曾有一个主张,那就是用“机器”的角度来看待创作,而不再是把一部作品的完成,归咎于天才的灵光一瞬。“文学机器论”认为:作者可以是作品这台机器的发生装置,但并非它的完全主宰,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绝非灵感或才情的突然涌现,而是日复一日的缜密思考与理性计算,是理性和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作品也绝非在作者完成后就宣告结束,实际上编辑、读者乃至整个文化生态、政治生态,都在参与对作品的创作。
这实际上寓言了作者中心制在当代的步步消亡,在今天,尤其是在影视剧、游戏开发等前沿领域,作者越发成为整个系统中的零部件,而不再是昔日作者神话中被天神眷顾的人。作者中心制的消亡,其实也是当代作家不复往昔号召力的重要原因。
三、让更多新人被看见
在文学边缘化的局面下,缺乏有力的、具有共识性和稳定读者支撑的严肃写作平台,以及在业界取得广泛认可的青年扶持奖项,让青年写作者很难以写作作为自己谋生的主要手段,也让那些真正缺乏背景、缺少关系的写作者要比别人付出更大代价,才能获得一次被看见的机会。
现今,一个“局外人”作者要发表小说,要远远难于成名作家或正当红的青年小说家。而在传统文学杂志之外,市场化,且支持严肃文学创作的平台正日渐缺乏,目前仅存的,如单读、ONE、小鸟文学、豆瓣等并没有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刊物类似的影响力,而豆瓣阅读也转向通俗小说创作了,而老福特、晋江、起点早已是通俗小说的天下。
因此在今天,写通俗小说并不缺发表平台,通俗小说借由影视化被看见,例子比比皆是,如紫金陈的《长夜难明》、阿耐的《大江大河》系列,但一个“局外人”写严肃小说(或所谓“纯文学”),大概率要承受漫长而孤寂的历练。
当然,近些年国内有过一些可贵的尝试。比如由“鲤”“腾讯大家”“理想国”联合主办的“匿名作家计划”、《收获》发起的“《收获》双盲写作大赛”、《青春》文学杂志发起的“青春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对于野生作家的发掘,以及像小鸟文学、ONE、单读这些市场化平台的坚持,乃至后浪文学等出版机构多年来对华语文学、国内小众青年作家作品的出版。
它们并不完美,就如野生写作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但至少它们真的在做,试图一步步打破圈层的隔阂,发现有待被看见的面孔。
就如同日本有用于嘉奖纯文学新人的“芥川奖”,以及用于表彰优秀通俗文学作家的“直木奖”,一个成熟的文学系统在细分之后,也应当在细分领域具有得到大部分同行共识的、公平公正的新人扶持机制。
但很可惜,国内的新人扶持机制仍然亟待完善,文学共和国号称包容,内部其实分野明确,不同文学派系彼此彬彬有礼又暗自隔绝,基于偏见所产生的鄙视链则划分出一道道冷漠的高墙,将热忱的文学之心挡在门外。
曾经,文学界并没有“纯文学”和“类型文学”这样死板的划分,写何种文学体裁,也不是佐证作家优越性的理由,所谓严肃和创造力,应基于作品内核,而非外在的标签,但在时下的文学舆论场,标签成了比作品本身更受热议的东西。这使很多具有天赋的写作者,早早离开了文学道路。
让勤恳创作、热爱文学的人不被辜负,文学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让新人与老人平等地较量,一个不以论资排辈、地位与人脉为标准的文学场域,才能成为新鲜文学力量的沃土。
如此,越来越多风格多样的青年作家起来,接受读者的检验,一个更为有趣、更有创造力的文学生态,就会慢慢培养出来,而它其实需要每一个在乎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守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程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