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袁长庚(人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任教于南方科技大学),主持人:郝汉、易莲媛,原文标题:《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是“社科热”的解毒剂》,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以“如何像xx学家一样思考”命名的出版物,正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们似乎迫切地需要关于世界的各种解释,以高效地指导行动。在人类学者袁长庚看来,“社科热”背后的“解读焦渴症”其实源于一种“经验的焦虑”——在短短十来年间,面对变动、纷繁、崭新的社会经验,中国人普遍感到不知所措。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虽然能够提供一个看似包罗万象的强势解释,而它们不但不能缓解焦虑,反而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
袁长庚认为,在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所真正稀缺的是“人类学的感受力”,人类学通过展示人类经验,理解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对一切斩钉截铁的理性假设的怀疑与打破,能够让自认清醒的现代人感到自己或许从未现代过。

[英]马修•恩格尔克 / 陶安丽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21-8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作者马修•恩格尔克进一步认为,“人类学让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并揭示着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在保守、去全球化、本质主义盛行的世界里,人类学正充当着“地球村”理想的捍卫者。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袁长庚,和我们聊聊人类学以及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以下为节目内容的文字节选:
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
郝汉:如果给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它会是什么?它和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有哪些区别?
袁长庚:这个问题挺难的,我们同行之间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现在做的事情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明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缺乏共识。一般来说学生如果这样问我的话,我就会说人类学是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老师同学都说我们要好好做人,要学习做人,但做人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有很多最基本的面向和构成。
我个人并不认为所谓“社科热”是真实的,因为在公共舆论的讨论中,我并没有觉得大家有意识地去贯彻或者是去应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但是我能理解热的表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它与其说是社科热,不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非常普遍性的经验的焦虑,商业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顾客在想什么,文化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受众群体想要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决策和行动。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一个问题,中国从1978年以后的迅速发展,在意识上得益于一种态度,就是“暂时搁置争议”。
搁置对于一些经验上的东西的模糊性讨论,先一切向前看,这样的东西其实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结果就是,中国人确实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没什么怀疑的。但是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不可能有谁能够持续性地不追问自己的经验问题。
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我们开始变得不解,而且这种不解开始困扰我们。比如我上课经常跟同学举一个例子,你今天或许想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美国人,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有很多的材料,但是你回家,比如说这个假期,你爸爸妈妈突然开始跳广场舞,然后疯狂地迷恋各种养生知识,这个东西对你而言可能是不好理解的,而且问题在于,你受的教育和你所在的文化环境里并没有太多的工具能够让你走进你的爸妈,走进他们在夏天里发生的事情,这种经验性的焦虑伴随着新一代人的自我焦虑,然后他们向外不断地去寻找一些所谓的知识或话语试图穿透它。我能理解这背后的驱动可能是很真诚的,但是它离转化成为一种有效的思考还是有一定距离。

人类学在以前其实跟文化研究很像,只是说我们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人类学关心一些小社区,一些所谓的未开化或者是欠发达社区当中的人的文化。以前人类学处理文化的方式是研究表征,我把你的文本符号包括你的解释收集起来,然后给出一个系统性的书写。举个例子,早期人类学像埃文斯·普里查德研究非洲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他就是到那个地方看你们仪式上都有哪些基本元素,然后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重要,你怎么实践它解释它,这是比较传统的或者经典意义上人类学的做法。什么叫表征危机,就是后现代以后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别人的表征其实是西方学者通过书写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就充满着你西方人的权力和偏见。你把别人写成那个样子,是因为你有这个可能性,不管你讲得再好,再贴近这些人,但实际上你还是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书写。

[英] E.E.埃文思-普里查德 / 褚建芳
商务印书馆 / 2017-3
我可以比较具象地讲一下,可能大家就能明白人类学跟社会学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社会学,作为一个博士生,你开题的时候一定是关注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社交媒体在大规模运动中起到的作用,你确定核心问题以后大概会找到几条线索,这些变量可能很重要,有些人是通过测量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做一些访谈或者线上文本收集,无论如何基本的问题框架是相对确定的。框架相当于研究者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来自于他的阅读和理解,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先有一个框架,然后找材料把它各方面丰满起来。
人类学恰恰相反,人类学也会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我对于西非某一个城市里抗击某种疫情的过程很感兴趣,但是在出发之前我会想,我可能会涉及到某些问题,比如宗族问题,身体观宇宙观问题。通常一个成熟的人类学研究经常会出现,你带着问题进入到田野,但田野会改写你的问题,它会告诉你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或者你要想回答问题的实际问题在问题。
所以经常出现,我们写的研究计划其实是为了在田野中修正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太相信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把别人的经验打造起来。社会学并不是这样,社会学有些时候也会修正,但是相对而言还是会强调这个框架本身的稳定性,你不能随便动摇这个框架。所以人类学的体验当中会发现一个问题,学者本来是沿着传统的问题意识去的,结果发现别人生活当中的逻辑是大于你研究的逻辑的,我们的任务等于说,你必须要顺着别人的逻辑走。当然,也不是说这种东西就一定先进,但是它有一种很明显的学科意识。
人类学我经常讲一点,就是人类学家其实很奇怪,我们一方面非常强调书写的重要性,比如民族志的写作,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又很不相信语言,所以总在找在语言可表述和不可表述之间的那些东西,至少现在表征的强调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说,我告诉你这些符号,这是一套系统文本什么的。很多人会强调,你看我今天观察到一个现象,他怎么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买东西,这种碎片式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对话,也会发生被观察者自己的解释,但是实际问题是,我作为研究者是要去想,在他的生活内部,整个从表述到决策到行动的过程为什么能成立,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对方未曾觉察的一部分。
很多人说你们人类学写作越来越像文学,但是你们的解释越来越像哲学,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对那种非常成体系的,认为自己能够给社会建立一个框架,然后把某些问题支撑起来的理解方式是保持怀疑的。
最初的人类学,本来是寻找特例
袁长庚:人类学在发展历史上,本来是去找特例,它本来是告诉西方人,我们西方人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是因为可能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只是我们今天处于工业时期。所以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的定位是去寻找那只黑天鹅。

早期,西方殖民世界在扩张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因为殖民势力扩张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宗教的扩张,所以对基督教文明而言,它面临着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到底要不要承认这些人是人,所以其实人类学早期知识上的启蒙,跟所谓博物学或者早期的探险家是一样的,它们其实都是在收集关于人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奇闻异事,只是它服务的大的目的是想要明确,人类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它们就像今天的化石研究一样,找到一个个时期的某种生物,然后填在进化序列当中的某个环节里。
人类学早期就是这样,包括殖民当局资助的一些研究,也是希望去搞清楚这些人现在停留在什么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理他们。但是大概发展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开始不安分,他意识到西方人的很多的问题意识其实是错的,比如我们都觉得,一个成熟的文明一定是有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的,但是二战前后,这些欧洲人在非洲研究时发现,那个部落其实很大,有几千甚至几万人,但是它根本不需要一个所谓的整整整齐的国家机器,它就可以通过分散或结合的方式有一套自己的节奏,而且运作得非常良好。
所以,其实人类学是在二战后通过找这种特殊性的方式去回应西方人自己的。但是这个东西到今天又会转变角色。今天很多人是希望看到特殊性,因为这些特殊性就给所谓本质主义留下空间。我跟你不一样,我们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不要跟我谈你跟我是一样的,也不要谈跟我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别人经常就会说,你今天之所以会觉得你跟他不一样,是因为你忘掉一些常识。

所以我们回到存在的层面,回到日常生活层面,你就看出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经验背后貌似都有一套整齐的逻辑,而且互相之间是有理解的可能性的,这就使得今天的人类学角色有一点改变,就是我们当然还是会呈现特殊性的原因和脉络,但是已经不再强调特殊性是人类必然的宿命,我们反倒会在对差异的强调中意识到,可能我们共性的那一面是很明显的,甚至有一个更重要的知识计划是,人类学其实事实上一直是启蒙以来的知识的反叛者,它大概从最初开始就不太相信启蒙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
比如大家意识到,最近这几年对于生态危机这种事情讨论得比较多,人类学参与其中就会发现,我们如果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可能要回到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是这样,你认为它天经地义,但是可能不是这样。人类没有天经地义,这些东西是现代性造就的,可能非常短暂,也就100多年200年的时间。
保健品销售在想什么
易莲媛:作为一个外行,我早期阅读的人类学研究,可能给我特别震惊的经验的,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正好是彝族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呈现的时候,比如关于他们吸毒、艾滋病的这些议题。那本书里面写到,当地人对于得艾滋病这件事并不是非常在意,大部分媒体就会很简单地把它解释为我们常说的劣根性,这是他们的民族性。
但那本书里面的阐释是,对他们的生命经验来讲,艾滋病就是20年以后才会死,人可能也就活到20年、10年以后,所以这个级别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是一回事,因此这并不是民族性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就是这样,这个疾病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如其他的东西,可能还有其他更加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贫穷问题。对于死这件事,当地人和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在理解生命的长度和死亡的感受上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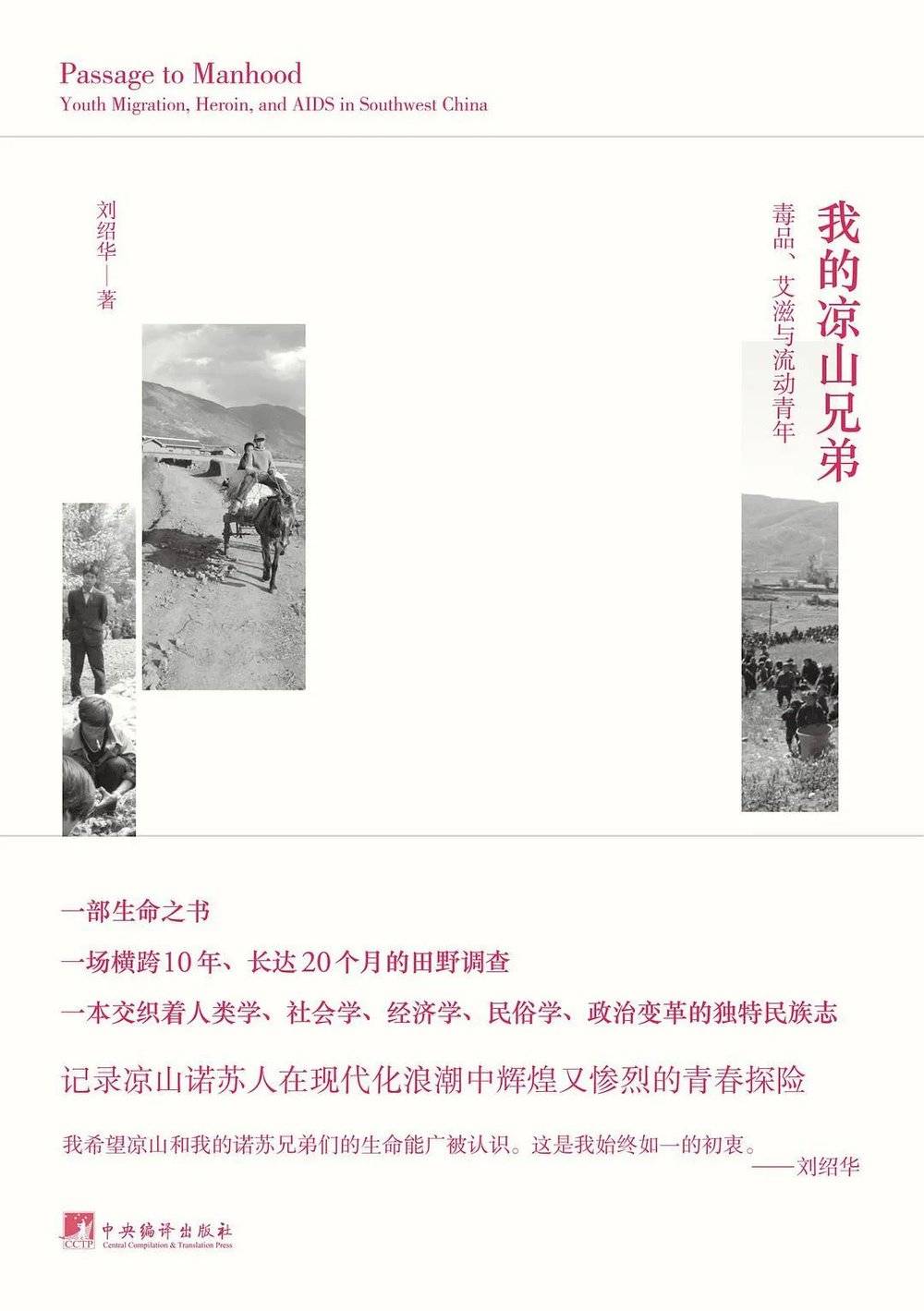
刘绍华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5-9
袁长庚:我自己博士研究做的是保健品销售,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别扭,因为这个圈子里面每天充斥着,学习为什么财富是重要的,几千人的会场告诉你为什么穷。这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罪过,你明知道这些东西表述有问题,但它又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此刻就呈现在你面前。
没办法,因为要完成研究我就一直跟着。但是我的感受是,跟他们的时间越长,我越能感觉到他们其实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他们想追寻到的东西也跟我们一样。
那会儿我在会场上做笔记,每天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小儿推拿,妇科保健,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怎么用营养素做调理之类的。有时候说太快我跟不上,就用英文做标记,那些同伴从我身边走过时,就说你看他多厉害,他会写字,会写英文也会写中文,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中国人的基本能力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后来很多人告诉我说,小袁五年级之后就辍学了,初中上了俩月就结婚了,然后跟着老公在外面跑建材,一跑就是十几年。她说实话跟你讲:我现在能认的字可能就100多个,我到这来之后觉得特别好,因为这里的人都很有知识,我在这又会写了很多字。因为要上台做分享了,他们就特别鼓励你上来展示自己,她说你看我刚上来的时候,一句话都讲不清楚,紧张得也不会做表达,后来我看多了,现在做分享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行业。

其实很多人进去之后,他知道对他的病没有用,但是他就想要大夫给他一个说法,你为什么得这个病,他为什么没得。大夫把中医西医灵修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给你一个非常完整的流畅的表述,我给你下这个诊断,我在价值观上对你有充分的同情。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女性参与进去,因为很多女性在家庭生活里有一些长期性的顽疾。
老公其实对这事无所谓,他会说你承受能力太差。但是她来到这个环境里,这个人就会告诉她,你看我就告诉你,我们团队里这些姐妹们10个有9个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女的在家里太痛苦,整个家里从老到小都靠我们。男人是永远不可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所以你说他能给出什么彻底解释吗?
不是,他使得这个经验有效果,而且他能够非常合法合理地表述,所以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人类学在解释力上有什么了不起,很多人看完论文之后觉得说这不胡扯,什么也没解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因为人类学的整体文化观念经常认为,要素a和要素b之间有关联,要素c不一定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它总在支持这张网,最后就使得我们看到,人人的意义之网到底在哪,现在已经不完全是通过语言来完成了。
比如,妈妈把孩子送到一个课外辅导班,如果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你可能觉得妈妈心狠,或者是激发他,但是如果生活在世界里,你就知道孩子是有养育的现实压力的,不光是说送去让他学数学,让孩子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可去,而且是对自己有所提升的。

所以我们如果隔着很多东西,会使得最后你觉得判断很清晰,但是你越走向经验,越走向他人,你其实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那套解释。有些时候你自己在社会转型期,在社会变化剧烈的年代,就会像一个人掉到水里上下翻腾,然后抓住一棵树干之类的东西。你可能认为他就有明确的求生方案,但其实他没有,他只是想抓住什么。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现在谈论的很多问题,其实在经验层面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人类学在某种层面上讲,就是说的这种反思性,虽然有的时候很招人讨厌,但是我觉得客观地讲,人类学经常会让你走得慢一点,让你不要过分去下结论。这种走得慢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权健公司倒的时候,有媒体来找我做访谈,我实际上是觉得挺没劲的,因为我们对一些现象,实际上几十年来都在重复着一套不太经得起考验的陈词滥调,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会说这些人是被洗脑了,第一反应是说这些人多愚昧,至于他在里面到底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不太关心。
所以这就是面临一个问题,正如我一开始讲到的,中国现在那种经验上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我们时代的一个比较大的困境。我们身边不管是教育体制里,还是文化的生产体制里,很少有不断地打捞现有的经验。而且最近这些年媒体的处境也比较尴尬,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本来应该做这个事情的力量。
虽然现在大家好像都来找人类学和社会学,但有些时候我会比较不客气地认为,你们其实只是想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是为了强化你现在已经形成的认识框架,你没办法真正把他人的经验变成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的起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袁长庚,主持人:郝汉、易莲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