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硬核读书会FM,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话剧《福寿全》在北京刚刚落幕,这部相声题材的原创话剧借长福和延寿这两个小人物悲喜参半的人生故事,串起了相声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的辛酸过往。它是导演黄盈在传统表达探索道路上的新作,也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阎鹤祥本色出演的话剧首秀。
相声演员是否可以脱掉大褂?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作“文艺轻骑兵”的相声有何变化?相声与戏剧的合法性都来源于现场吗?知识分子和大众艺术怎样结合?冒犯是艺术的宿命吗?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谈谈这部话剧,以及相声、戏剧作为剧场艺术所面临的尴尬与可能的未来。
嘉宾:
黄盈(戏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
阎鹤祥(德云社相声演员、话剧演员)
郝汉(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编辑)
董牧孜(媒体人)
以下为内容节选:
相声演员也可以脱掉大褂,专注内容才最重要
郝汉:阎鹤祥老师之前说过,相声演员其实该脱掉马褂。对于艺术的传承而言,这些形式上的传统究竟重要不重要?
阎鹤祥: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形式,不见得是真正的形式。比如刚才你说的穿大褂,穿大褂对相声来说连形式都算不上,因为过去穿便装,大褂是便装,甚至那时候说实话比较穷的相声演员没有好衣裳穿,他可能下台连双正经的鞋都没有。那时候知识分子穿长衫、大褂,相声演员可能觉得上台要穿一件像知识分子的好衣裳,所以他才去找一件大褂、长衫。所以说,你们所认为的相声穿大褂,这些所谓形式上的事情,反而跟艺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大褂跟它的内容有关系吗?显然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真正的形式,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是基本功,你要练贯口、练嘴、练俩人的配合、要练这些经典的段子,这个其实是今天的形式。你们认为的今天的相声内容上的东西,恰恰是我认为相声形式上的东西。其实相声这门艺术传承内容上的东西,应该是他对幽默的理解、他的语言的节奏、他对任何两人对话当中一些应激反应。每个人的语言魅力、组织语言结构的方法,这是真正内容上的东西。
从下九流到艺术家,不得不说的相声往事
郝汉:两位谈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回到《福寿全》这部相声话剧本身,它从1890年开始讲起,一直到1980年左右结束,可以说是讲述了一段由两个小人物串起的相声史诗。记得剧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福的隐退某种程度意味着传统相声的离场,后来改革开放,电视台记者访问延寿的桥段,似乎又正是历史中新相声的崛起。延寿从前被视作下九流,而如今被称作“艺术家”,这其实跟新中国的相声改造小组有关系。如同两位刚刚所说,相声演员从平头百姓的底层形象,在经历新相声改造后,精神上才真正穿起了长衫。

阎鹤祥:如果聊新相声的话,其实在旧社会没有“相声”这个词,“相声”这个词究竟哪一天定义也有待考证,那时候叫“听玩意儿”,根本没有这个词,包括“曲艺”这个词也是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的文化部门为了挽救这些艺人,给这些艺人的地位归类。相声在旧社会很简单,就是一个人站着,靠说笑话让别人给钱,能吃饱饭,到了最后,行业越扩越大,引进一些别的创作,甭管是文人创作还是高雅创作,导致有了些新的内容。
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实际上是新中国的这些艺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就是说旧社会的东西不能说了,如果你还想生存的话,就要说好的东西,要说新社会劳动人民大众能接受的东西,这也是一种自我的改观。如果要说,相声在历史上的改变,那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它所承载的内容,不见得是它本身想承载的,是它简单的形式赋予它的。比如,新中国要宣传“五讲四美”,相声要说新东西,要说新创,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简单,容易承载。
为什么过去相声叫“文艺轻骑兵”?两个人往这一站,针砭时弊也好,逗乐也好,它形式灵活。你看老舍先生也写相声,老舍相声里谈到最多的一个美国人是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写了无数讽刺杜勒斯的事。那个时候,老舍先生写相声是要应付东西方冷战阵营的,所以不同时代可能赋予了相声不同的意义。为什么今天大家会觉得相声值得讨论、值得探讨?因为今天的文化形式多了,媒体形式多了,原本相声所需要承载的宣传需求,被别的艺术形式分走了。我们有时候看相声是不是没落了或者没创作了,恰恰是相声本身不需要承载这么多东西了。
郝汉:我蛮好奇黄老师作为导演在处理这段历史时有什么想法,因为您其实是国内少数具有学院身份的戏剧导演,自己就属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完美结合。

黄盈:我不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在教书而已。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普通大众,您刚才提到说戏里的这五十年,由于延寿跟长福之间的分别,导致这一部分在戏里其实是缺席的。它之所以缺席,不光是因为剧情需要两个人不在一起搭了,还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从189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个八十多年将近九十年,两个人的一辈子,同时也是相声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声史当中能说的东西太多了。最后我决定要把这个戏在两个小时左右完成,才导致新相声这五十年在戏当中有点一笔带过了。
这五十年对相声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从一个老百姓为了填饱肚子,只是靠说话就能吃饱的艺术样态,也伴随着整个中国的发展——告别农耕文明,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相声在街上不光是在说笑话,可能要靠骂街来吸引人,甚至说要靠打徒弟,靠路人怜悯之心,给点钱,挣钱、吃饭是第一位的。
接着的重要时期就是从在“平地抠饼”(指最早的相声表演是“撂地”演出,在市场里拿白粉画个圈,演员站在圈里就说,又叫“画锅”),头上没一片瓦的情况下,相声走进茶园,开始在一个相对较小、封闭、安静的空间里,大家可以踏踏实实坐下来听了,这是一个飞跃。
下一个飞跃,是新中国成立。由于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让相声可以走进剧场。侯大师的相声第一次进剧场是有史可查的。那时候人们去长安大戏院听相声,早上天气不好,有点阴天,将要下雨,那时候侯大师就觉得完了,这票可怎么卖,剧场这么大。他骑着自行车跑到售票处,恨不得乔装打扮去打听票卖得怎么样。我想说相声进剧场可能是有新中国的推动作用的,但是真正一张张票能卖出去,还是在于老百姓对这事的需求。

“德云社相声热”部分得益于网络,戏剧就没这么幸运
董牧孜:到了本世纪初,我们又迎来了一波“相声热”——郭德纲先生以及德云社的火爆。阎鹤祥老师也是在这个时期才来说相声的。您怎么看待这次“相声复兴”?
阎鹤祥:文艺形式的复兴来源于科技的复兴,我们不能单纯地只看相声,1949年解放以后,相声的第一次复兴让我们看到了侯宝林大师,包括马季这一代相声演员,他们属于中央广播说唱团,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半导体话匣子,能听广播,老百姓能听到这些东西。要是没有广播的话,离开北京、天津,陕西、云南、贵州这些地方,可能就听不到相声。
第二次复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电视开始走入家庭,我们家里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后来又有了彩电,那个时候开始有晚会节目,相声都是从那看到的,牛群、冯巩、侯耀文先生等等。第三次复兴就是我师父在2005、2006年的火爆,这其实是源于网络技术的复兴。我们想想那时候多少人听郭德纲先生都是在网上下载资源,连好多人听我说相声,都是从网络开始的。

到今天我们中青年演员再次复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4G、5G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现在随便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艺人。理解相声复兴,我们恰恰忽略的是通信技术改变对于相声传播度的改变,以及艺人群体带来的传播方式改变。所以我的观点是,有时候人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多,科技变了。而且互联网传播没有强势导向,你想听谁,你就去下载谁,恰恰我师傅这种艺术形式是口口相传的,互联网早期的自由给了我师父更热烈的传播方式。
郝汉:戏剧跟相声都是剧场艺术,但又非常地不一样。草莽蓬勃的互联网生态似乎也对戏剧没带来像相声那么大的破圈作用。
黄盈:坦白讲,随着技术革新,其实不少人都希望能够走进剧场,去现场感受戏剧这门原始、传统的艺术样态。我个人来讲,对于戏剧的传播或者说它和新技术的合流,没有那么乐观。你会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20世纪以前的戏剧大师往往都是剧作家,比如莎士比亚、穆里埃。他们不仅仅是编剧,虽然当时没有导演这个说法,但是他们也承担了导演的工作,甚至干了制作人的事情,并且他们本身也是演员。剧本写作其实是一度创作,在舞台上得经过二度创作,戏剧是把白纸黑字变成活生生的形象,变成活人跟活人相遇的这么一门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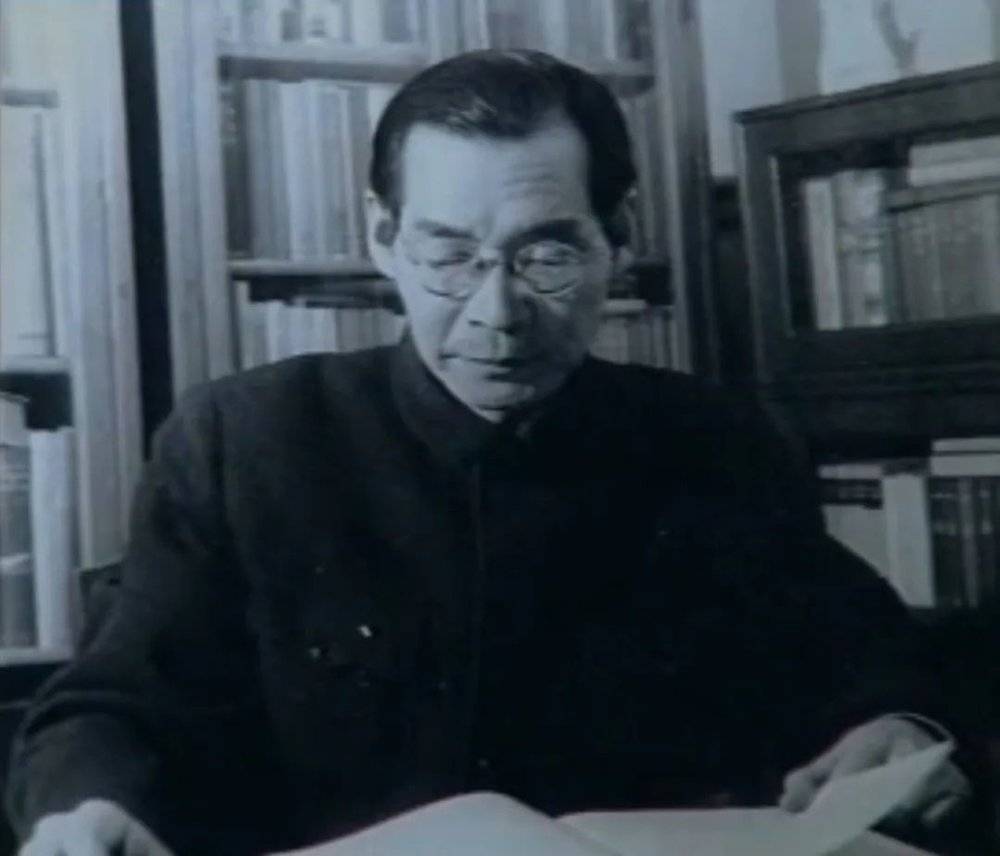
可是这事儿在二十世纪以后就变得不同了,二十世纪之后的大师像彼得·布鲁克,包括我的前辈林兆华老师,以及给中国戏剧本土化探索开山立派的焦菊隐大师,这些大师们往往只是导演。不只是中国,从国际上来讲,导演都渐渐地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甚至超越剧作家成为戏剧史书写的主角。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是因为二十世纪的机械复制影像让我们开始有了电影,慢慢又发展成电视,今天变成网络短视频的形态,真人表演可以被记录下来了。在电影诞生之初,它就和戏剧进行了一次分流。你去看那会儿的大型讨论也好,或者说电影运动也好,它的发展要求它自己这门艺术跟技术强烈结合,它在寻找它的合法性,电影院本身是个剧场,只是大家聚在一起,不再看活人了,而是看事先拍摄好的、经过剪辑的、可以被机械不断放映出来的影像。原来我们看一部剧作的时候,你走进剧场,某种意义来讲,可能看故事就可以满足了。现在要看真人表演的叙事,我打开手机就能看,我凭什么要进剧场看?这给所有剧场工作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就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能让观众走进剧场。
因此,戏剧在二十世纪之后的合法性就是它所一直强调的“现场性”。正是现场性的突显,才让负责在舞台上进行二度创作的导演站到了最前端,成为了领导者。
而相声的问题不太一样,当你只通过收音机听俩人说话的时候,虽然有一大部分的折损,但是它基本上把原来艺术中好的面貌保持了下来,通过电波传达给你。山沟里的人虽然不知道说相声的人的神态,但只听说话,他已经得到了相声的乐趣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相声是幸运的,而戏剧可能还应该继续去坚守自己的老传统。
“这个行业的最低标准应该是自个儿写的东西自己演”
郝汉:我们再回到世纪初的那波相声热,和上世纪末时文人和相声演员的紧密合作不再相似,它好像转了个弯,又回到了相声最初的样态,一个草根的叙事上。
阎鹤祥:对相声的繁荣与发展,我跟大部分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相声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一步一步到今天的。而我恰恰认为相声能传承到今天,是因为一位又一位的大师,比如说侯宝林先生、马季先生、郭德纲先生,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哪个徒弟、哪个后人也传递不了他们的东西。他们对语言、节奏的掌控、对幽默的理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所以,相声教育的核心也正应该是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反复打磨一个人的幽默、可爱。这是相声教学真正要做的事,不是单纯去传承那些报菜名、贯口等等,而是打磨精品。这个精品,不是作品,是有趣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谈什么时期的相声,都没有意义,只是每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牛人。
董牧孜:在创作力方面,没有好相声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的相声剧本,相声也确实是人写出来的。两位老师要不要谈一下“剧本荒”。在天才人物之外,知识分子跟大众艺术的结合必要吗?
黄盈:我刚才提到20世纪之后的戏剧为了强调现场性,其文学性有意无意间地被忽略了。但再强调现场性,我也相信戏剧演出不只是大家在一起“蹦蹦迪”。叙事、剧本依然是基础的、重要的。至于说到底怎么来做,包括刚才聊的话题,相声的发展,电视相声的发展,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些非常优秀的大师,那些打磨出来的人,在自我打磨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许多大知识分子,甚至都是一些不能够用这个说法去涵盖的群体在帮助他们。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相声有一个很大的飞跃?那时候很多相声段子的作者本身也是语言大师,就跟新中国时期的老舍先生帮助相声有一次飞跃的道理一样。许多把自己打磨出来的人,当他们成了名之后,不仅是拿着钱去消费就完了,他们开始主动去结交、能够打开他们艺术事业或者帮助他们成长的人。所以,我觉得打磨人这件事,不只是这一个人的自我打磨就完事了,它其实需要很多人在背后去帮助、去推动。而推动过程当中,从创作出发点来讲,不同事业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攻一件事、搞一个创作的时候,绝对比一个人埋头傻干要强。
像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俗人。我相信很多做创作的人在接地气的同时,先要做的事儿是放下身段,别给自己端起来,先能跟大家一起俗了,俗完了之后,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力有限,怎么能做到雅俗共赏?雅的那部分,其实是更需要能够写剧本的人,或者说更多的文学大家、知识分子在背后和我们组成团队,一起去做出好的作品。
阎鹤祥:我不是搞戏剧的,但我知道现在好剧本确实不好拿,我只说创作上遇到的问题。像80年代的时候,你买报纸的话会发现每个报纸上的投稿板块,都有相声本,那时候全民、作家都在写相声,老舍先生五六十年代也写相声,老舍先生是可以争夺诺贝尔文学奖的那种地位的作家。而今天,你会想到一个具有这种实力的作家去写相声吗?你会觉得很荒诞。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剧作家产出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多,我们能写的作品可能只有相声、小品文,还有对口词,只能写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大家、人才涌向了这种创作,很多大作家都写过相声。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说我们斩断了跟知识分子的来往,而是因为编剧输出的渠道也多了,有几个亿的电影电视编剧等着,谁还来写相声呢?这也暴露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弊端。我向来的观点是好的相声演员应该是可写的,相声能维持下去不能完全依托于知识分子,要是没人给我们写了,我们就完了吗?
所以,你看真正的大家都是自己写,马季先生一辈子写了几百个相声,现在没有这样的天才了。我师父所有作品都没有用过别人的,全是自己写。说得更严肃一点的话,这个行业的最低标准,应该是自个儿写的东西自己演。但是这么多年来,连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我们都没有达到,这是以后该努力的方向。演员可能变不成知识分子、变不成学者型演员,但要努力把自己变成有创作能力的演员,等衡量一个合格相声演员的要求高了,这个行业就好了。
伦理哏、厌女,冒犯的艺术有问题吗?
郝汉:阎鹤祥老师此前谈到过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就是他对传统相声里的伦理哏、相貌嘲讽、旧生活呈现等题材的反思。这些笑料虽说具有“来自生活俗气的巨大魅力”,这是传统相声的灵魂,但它在今天确实面临着冒犯女性、冒犯弱势人群的问题,这其实并非相声面临的问题,所有艺术只要具有讽刺性,都面临“冒犯他人”的风险。
阎鹤祥:相声之所以在传统作品上有过一些类似的问题,是因为过去的听众群体固定,当时女人不让听相声,茶馆听相声,如果有女性在,有些话就不说了,或者说先把她们请出去。相声更像是男人讲给男人听的,它自然会有一些擦边球、偏油腻的东西。但是相声如今变成一门大众艺术,我们就要去做改变,而且得有一些对于女性的关怀,过去女性的相声演员都没能关注到立足女性本身的创作内容,女性相声演员几乎都在模仿男性相声演员。像一些冒犯,包括弱势群体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演员素质的问题,以前的演员都是文盲,温饱都顾不上,也没有上过学。所以,我说演员要提高的素质是什么?是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这样才能创作出雅俗共赏、具有关怀和真正幽默又高级的作品。

郝汉:对,其实也想问一下黄盈老师,您也强调戏剧的文学性,文学求“真”,“真”的东西尊重了生活的事实,但可能是会冒犯到他人。
黄盈:因为我觉得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伦理哏,或者说对于女性不尊重的言论,确实是跟当年的观众群和创作者为谁服务有关系。布莱希特有一句名言叫“吃饱肚子,再谈道德”。当年的相声艺术既然是为了吃饱饭而产生的,那么当一个人饿肚子、吃不饱、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说实话,没有人能够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但随着相声的发展,相声演员们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得挺好的情况下,这就确实需要想一想了,很多传统相声的老段子应该怎么说,而且不光是女性观众走进剧场的问题,其实它也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尊、自爱,需要互尊、互爱。近几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尖锐,甚至说要迎来某种改变。
我们看当年莎士比亚写《威尼斯商人》的时候,坦白讲,你好好看一下这剧本,并不会觉得他在替夏洛克这样的犹太商人树碑立传,而如今文本还是那个文本,今天的创作却解读出了他对犹太商人的关怀。通过演绎,它有了新的可能性,这对相声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启发。很多老段子不见得是要完全把它废掉不演了,而是看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那些过去为了吃饱饭而出现的段子在今天还能展现它的光辉。我一直是一个顺应时代、顺应大众、跟着老百姓一起同呼吸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硬核读书会F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