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维舟,编辑:程迟,题图来自《白银帝国》剧照
如今,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最喜欢的场景之一,便是当年的繁华盛世——比如“万邦来朝”的盛唐,以及“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开封。而那些富贵人家所留下的宅第,更是激发着游客们的想像。
在历史小说中,但凡夸赞富商的奢华富庶,最常用的一个词便是“富可敌国”。这样的事例确有不少,晚清广东巨商刘学询,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暴富后又娶了十二房美妾,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一座极度奢华的“刘园”,号称“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但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像他这样的闽广商人还不是最富的群体。宋代商人分三大群体——北方、南方和四川,到了明代中后期,沿海从事外贸致富的闽广商人才取代了四川商人,而与此同时,晋商控制了北方商业,徽商则主导了长江下游的商业,这南北两大商帮才是明清时代真正“富可敌国”的群体。
一、从盐起家的晋商
晋商之富,在举世闻名的山西大院就可见一斑:他们不仅在致富后留下了连绵的宅院,而且这些院落实际上也是明清时代中国(至少是北方)的金融中心。
如太谷曹氏从明末创业,顺治年间发迹,至乾隆、道光年间鼎盛,到1938年前后八代人,商号发展到640余座,钱财达1200万两白银,雇佣掌柜、伙计达3.7万人之多。
山西本地出产并不多,仅有基本生活资料及所谓“傻、大、黑、粗”类商品,晋商又是如何崛起为帝国商人的?
这其中的秘密或许就在于一种人人必需的商品:盐。
对晋商的研究普遍认为,山西商人群体的形成与明代的“开中法”有着密切关系:根据这一政策,官府鼓励商人将军粮、马匹等物资运送到辽东、宣府、延绥等长城边境地带,凭此换取盐引,准许他们将食盐运销各地。山西不仅在地理上接近这些地方,而且还有出产上好食盐的解州(今运城)盐池,于是晋商依托这一国家政策,开展大规模粮食和食盐贸易,积累起庞大的资金。

这项贸易有多重要,从数字就可见一斑:明万历六年(1578)全国办盐4.9亿斤,各盐运司并各提举司余盐、盐课、盐税等银共100.39万两,占当年太仓银库总收入367.62万两的27%,是最重要的税源。在尚未脱离农业生产的社会里,只有参与政府采购行为才能稳定地获得高额利润。
由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山西因此常在京师左右,加上本地山多地少,被迫要在农业之外寻求出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开放的过程中,山西人就能比以务农为主的河北人更能抓住机会,充分利用交通便利和官商关系,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他们多起家于长距离贩运转售贸易,“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不资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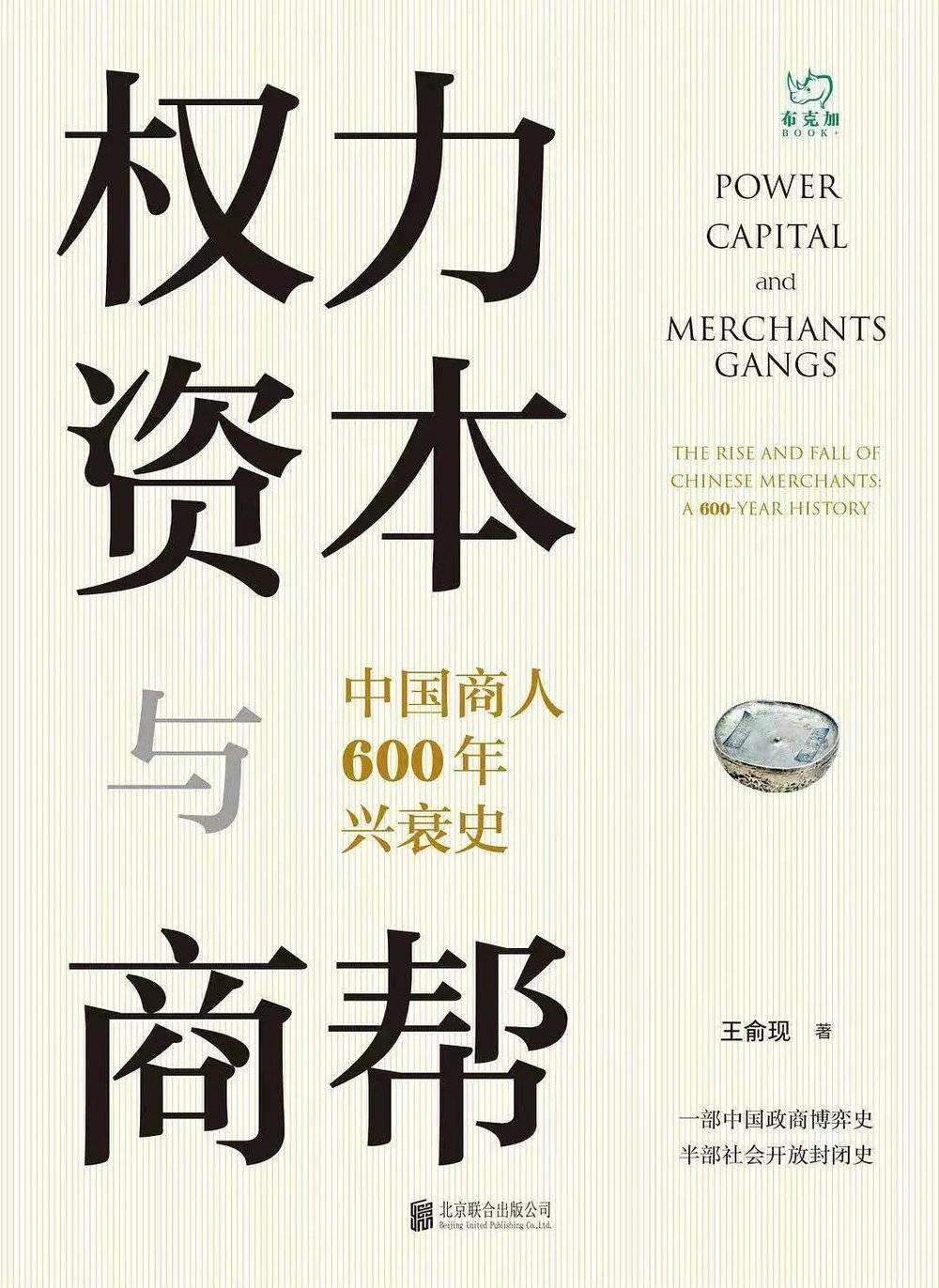
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一书明确指出:明代的晋商主要从事的仍是传统的官盐特许经营,类型比较单一,但清军入关给他们带来了重大历史契机,不仅因为清朝对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强大控制给商人提供了更多发财机会,也因为晋商和清廷实现政商勾结,“商通过贸易,又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抽血,再以股份红利、捐税等形式,把一部分养分输送给居于上层建筑的统治者”,这种信用凭证就是所谓“龙票”。
正是在清代的晋商身上,传统的“官商勾结”取得了“最深刻、最广泛的结合”。

无论是清军出征、还是蒙古王公的进贡与生活需求,都存在大量的商机。清朝对准噶尔的连年战争,耗费5439.5万两,以1715年对准噶尔之战为例,清军兵力5.9万人,给养标准是每人每月24斤粮食(合今28.6斤),当时米价是每石0.72两银,加上到京津的运费,晋商范毓馪向清廷报出的米价是每石0.9两,但将之运到前线却要合计40两,运费是货物本身价格的43.4倍!
这些晋商不仅做生意,甚至还在当地土地开垦、城镇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晋商店铺的字号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往往是当地最早的商栈乃至定居点,大大影响了长城以北城镇的发育。所以历来就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
依托这些商业网络和财富,他们垄断了票号(汇兑行业)、钱铺(汇兑、银行业)等金融业,活动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华北、东北、西北和华中,到1905年前后的清末,北京的金融业店铺中大约一半都是由晋商经营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他就是晋商出身,这实非偶然。
二、称霸江南的徽商
和晋商相比,徽商之富也不相上下:明嘉靖年间曾排过一个富豪榜,标准是“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当时全国共17家入选,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万历年间,全国每年财政收入才400万两银,但徽商的资本总额已高达3000万两,年获利900万两;清代全盛时,扬州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国库存银也不过7000万两。徽商当时号称“一等生业,半个天下”——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占据天下财富之半。
和晋商一样,徽商起家依靠的也是明清时代庞大的食盐贸易,只不过他们的根据地在扬州——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扬州是两淮盐业的中心,所产食盐行销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徽州商人第一次被文献提及,是在建造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时候。
在某些方面,他们确实和晋商有不少相似之处:都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杭州、南京是南方的政治中心);都依靠盐政起家;老家都多山不宜农,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徽州有句著名的俗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中流行着两句土话:“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意思是说出门经商总得带着绳索,身背的行囊坏了、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万一血本无归,还可以用它来上吊。
木材商、盐商、典当商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而徽州商人在经营木材之后,又垄断两淮盐业,积累的资本再进入典当行业。
到后来,他们所从事的门类逐渐形成明确的专业细分: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的木商,祁门的茶商,全都以其巨额的财富和鲜明的地域特征而闻名遐迩。这种劳动分工的专业性还体现在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景德镇瓷器当时行销各地,但事实上,控制着订货、制作和营销等所有流程的也是徽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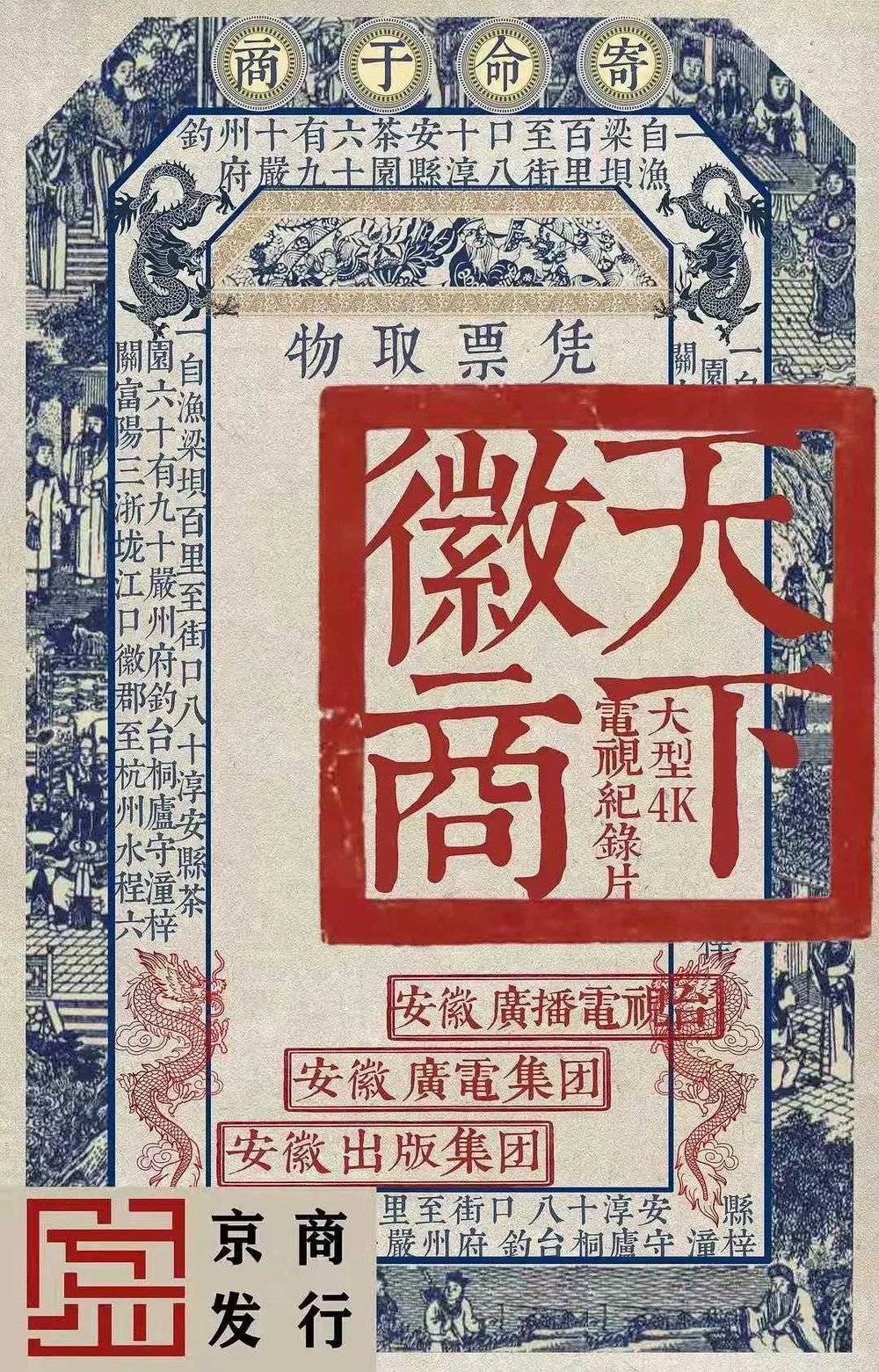
徽商活动的重点区域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河道纵横,因而徽商外出经商的许多路线都是水路。晚明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共记录了水陆路程143条,其中有不少均为水路交通。
水路最大的好处是载重大、运费低:根据黄汴的记载,从镇江往南,船费每20里(11.7公里)仅2个铜板。这为远距离贩运商品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也使徽商能沿内河水路拓展商业网络——据《五杂俎》记载,晚明时北方漕运的大码头、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临清城中,“十九皆徽商占籍”。
但就像黄国信在《市场如何形成》一书中研究清代食盐贸易后指出的,“船运贸易面对诸多交易成本,最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就是寻求与官方的合作”,尤其是从事大规模食盐贸易,若想击败对手,“实现垄断的最佳方式,仍然是与官方合作”,并且这一逻辑“适合传统中国一般商品的贸易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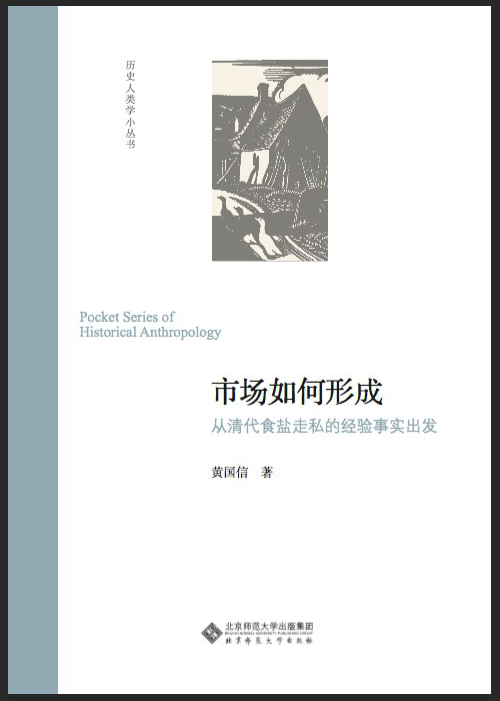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徽商与晋商可谓殊途同归,到最后很自然地汇聚到整个帝国利润最丰厚的两淮盐业上,进而聚集在扬州。早在明末时,扬州就已在许多方面成了一个“徽州城市”,城中最富有的商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徽商。
虽然不像晋商那样和朝廷关系紧密,但他们也表现出很强的依赖性,因为他们的生意其实都有赖于朝廷。
有时候,他们还能有意识、有能力通过结交朝廷要员,间接干预国家决议,促使朝廷制定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淮安人)盐政变法,由开中纳粮改为折色纳银,这样一来,晋商就不再因地理近便而可以在运送粮食上得到边贸优势了。
这给了晋商明显震动,一部分山西盐商被迫迁居淮扬,另一些商贾人家则开始鼓励子弟读书,因为他们察觉到,如果“朝中无人”,到头来最多只能捐官买官,顶不住对手的降维打击。
这也可以看出徽商的一大不同:身处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们的资本化程度更高,不像晋商在清代仍主要从事军粮供应等实物贸易,徽商在晚明就依托大量流入的白银转向货币化。朝廷当时之所以采纳“折色纳银”的政策,与其说是他们游说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因为大势所趋,而江南一带当时正引领着全国走向商品经济。
或许也正因为徽商积累的资本更偏重于流通,他们不像晋商那样将赚到的钱都拿来在老家盖豪宅,相反,他们有一个突出的不同,就是投入到文化领域,即所谓的“附庸风雅”,来为自己积累文化资本。
很少看到晋商有赞助艺术的,但徽商在这方面则很舍得投入:京剧最初是因1790年为乾隆祝寿的“徽班进京”而来,而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徽班”,就是因为最初由扬州的徽商所赞助,并且与安徽的音乐和伶人有关。在绘画领域,据《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一书研究,在16-17世纪“如果没有徽州商人对艺术的收藏和赞助”,那么名垂史册的新安画派“也许就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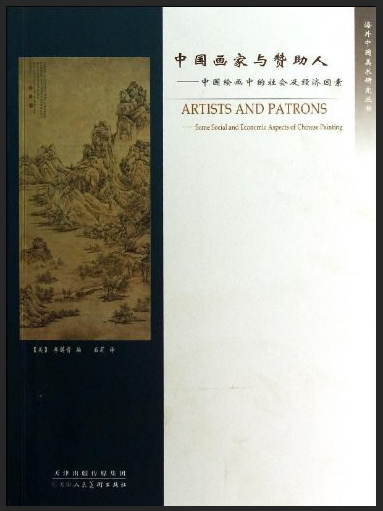
三、衰落的原因
从这些历史也可以看出,无论晋商还是徽商,其财富的积累、增长,其实都与国家密不可分;也正因此,到了近代中国国运衰退时,他们的好日子也逐渐到头了。
首先受到打击的是徽商。英国汉学家魏根深认为,“食盐垄断的取消,再投资的失败,以及外国资本的竞争是徽商在清末衰落的部分原因”。
但实际上,徽商所受到的最沉重打击是太平天国战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一片糜烂,扬州、南京都被两军反复争夺劫掠,徽商的老家徽州也化为焦土。晚至光绪二年(1877),两江总督沈葆桢还说“皖南自兵燹后,遗黎十不存一”——连命都保不住,那财富就更不用说了。

电影《白银帝国》以清末民初富可敌国的山西天成元票号的传承为主线,再现了“中国华尔街”金融业的百年兴衰。
太平天国运动虽未攻入山西,但对晋商仍有重大冲击,因为在“官商一体”的格局下,朝廷任何的额外支出,这些商人都是现成的提款机。
此时正当旅蒙晋商和银号票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咸丰三年(1853)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山西朔州人章嗣衡上奏,列出晋商的财富:“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最终,在这场战争期间,各地商民捐纳3000多万两白银,晋商出钱最多,占37%。
晋商以往虽然富有,但社会地位却并不高;等晚清时稍受重视,却开始了衰落。据《清稗类钞》:“咸同以前,缙绅之家,蔑视商贾。至光绪朝,士大夫习闻泰西之重商,官商始有往来,与为戚友。若在彼时,即遭物议。”晚清国势下坠,晋商也大受牵连,到光绪十七年(1891),建筑豪华,包括院落26座、房屋218间、面积11728平方米的高家崖堡,仅以964两纹银,易主他姓。
但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朝的灭亡,晋商各大票号“昔之以豪富自雄,至时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对象以偿还债务,不足则为阶下之囚,受缧绁之辱”。
垄断外蒙贸易的晋商三大号,在辛亥革命后一蹶不振。这还没完,不出十年,外蒙独立,对其生意造成了釜底抽薪的打击。
除了像战争这样无法左右的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他们的衰落也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正因为他们原先太成功了,高度适应和依赖国家的特殊政策与需求,结果也就使自己捆绑得更深,以至于当局面出现重大变故时,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来对冲这些风险。

到清末民初,局势已逐渐明朗:沿着内陆商道拓展的晋商和沿着内河水道延伸的徽商,都将无法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格局中幸存下来,此时能灵活适应的,是崛起于东南沿海、能积极对接海外贸易网络的商人群体,特别是浙商(宁波商帮)和闽广商人。
这也并不是偶然的。晋商、徽商虽曾“富可敌国”,但他们积累的多是个人财富,却不是地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分工布局。
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长三角、珠三角两地,都是早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专业的市场分工,在沟通国内市场与进出口贸易的基础上,把原先相对独立运行的市场流通连成一体,促进了生产与流通的进一步结合。
这种由各级市场构成的复杂而统一的市场体系,显然能更有力地对冲、回应内外部的风险,大量地涌现有能力的商业人才。最终,真正的经济竞争,已经不是一小群商人所能把持、掌控的了,而取决于当地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备程度。再精明的晋商、徽商也将无法逆转这样的时代变迁,因为这归根结底已经是一场游戏规则完全不同的宏大竞争了。
参考文献:
[1] 刘学询等《考察商务日记·考察农务日记·扶桑两月记·扶桑再游记》,岳麓书社,2016年,叙论第26页
[2] 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93页
[3] 王先明《晋中大院》,三联书店,2002年,第84页
[4] 刘影《皇权旁的山西:集权政治与地域文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5]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第311页,又参[11]见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6] 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7] 《皇权旁的山西》,第201页
[8] 《皇权旁的山西》,第98、第212
[9] 转引自《晋中大院》,第35页。又参见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222页
[10] 《清代旅蒙商述略》,第6-7页
[11] 《清代旅蒙商述略》,第10页
[12] 《清代旅蒙商述略》,第118-120-21、144页
[13] 《清代旅蒙商述略》,第49、130、144页
[14] 《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第75页;又参见《清代旅蒙商述略》,第229页
[15] 《晋中大院》,第50页
[16] 渡边义浩《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李晓倩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42页
[17] 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
[18] 王仁湘《中国滋味:盐与文明》,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5、167页
[19] 《中国滋味:盐与文明》,第15页
[20] 《中国滋味:盐与文明》,第166页
[21] 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第893页
[22] 《徽州》,第30、111页
[23] 《徽州》,第9、第109页
[24] 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等译,三联书店,2015年,第64页
[25] 陈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9页
[26] [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第193-194页
[27] 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8] 黄国信《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2-93页
[29] 《清代旅蒙商述略》,第20-21页
[30] [美]郭安瑞《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郭安瑞、朱星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4-165页
[31] 李铸晋编《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石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
[32] 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第893页
[33] 《清末教案》第二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140页
[34] 《清代旅蒙商述略》,第193-194页
[35] 《晋中大院》,第92-94页
[36] 《晋中大院》,第92页
[37] 《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第92页
[38] 刘志伟《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载氏著《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第140-143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