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枪稿(ID:QiangGaooooo)
作者|李不言
头图|@山河令官微
《山河令》的火爆,再次证明武侠依然是中国人共有的乡愁。
不过,今日的武侠早已不是金庸、古龙们所构建的那方天地,女性创作者和女性消费者正在合力改写武侠叙事,从男性手中抢过那个曾经只属于他们的江湖。
01. 武侠耽美化
《山河令》的名场面基本都出现在两位男主角温客行、周子舒眉目传情、打情骂俏的段落,但凡有这样的戏份,弹幕里就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和尖叫。
而我也能充分理解大家对于两位俊男撒糖的喜爱,毕竟这的确已经是这部戏最好看的部分了。
姑且撇开剧集的整体质量不谈,从《镇魂》到《陈情令》再到《山河令》,一目了然的是,观众不再满足于男人之间的手足情义,而越来越爱看男人之间不挑明地搞暧昧,但他们又不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性取向。
看两位俊俏男子喝酒、吃饭、吵架、护崽、抢娃也就罢了,叫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连其貌不扬的男性配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奇奇怪怪。

例如说,故事中杀手组织头领蝎王在他义父面前如受气小妾般娇滴滴争宠的表现,实在和他出门在外杀人如割草的日常大相径庭。但编剧也无意呈现这个角色从小缺少父爱的另一面,只能理解是为了满足观众消费非常态男性情谊的心理需求。
究竟主要是怎样的观众有这种观看需求?答案毋庸置疑是女性,尤以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女性为主。
腐女们磕耽改剧的糖,其实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层面上的整体弱势,而从纲常束缚中获得了某种特权。
耽美叙事的盛行,其基础在于女性在现代社会、职场中遭受的性别压力,以及愈发狭窄紧张的性别舆论场给所有人造成的焦虑,能够在对耽改剧的支持叫好中得到隐性释放,而且这种释放(暂时)是被当局默许的。
而在创作层面,女性书写同性叙事(耽美作品的作者多为女性),也可以视为是对男权主导的政治秩序的反抗,或者说,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

同时,女性社会权利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让她们得以在文娱市场中掌握了更多的投票权。以《山河令》为代表的武侠故事的耽美化,实际上就是男性叙事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里的女性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河令》为典型,两位男主只搞暧昧,却不挑明关系的原因,除了有关部门的审查之外,也是因为绝大多数女性观众对于真实的男同社会处境及其相关叙事欠缺真正的关注。
《春风沉醉的夜晚》《谁先爱上他的》《叔·叔》这类真·同志影视,应者寥寥,实则反映的是,不少女观众对于男男CP的追捧,更多是出于她们对于这种在禁忌边缘疯狂试探的暧昧性的迷恋,而一旦挑明,一切玫瑰色幻想就会被戳破而变得索然无味;所谓的“甜蜜”,就将走向现实中性少数群体的压抑与边缘。

02. 武的式微,侠的隐退
从小说《天涯客》到剧集《山河令》,有一个值得玩味的改编细节:故事中,建立超级特务机关“天窗”的人,从皇帝变成了要谋反的节度使。
这种思路的本质是要维护最高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不要忘了,传统武侠的核心精神,就是对权力秩序的疏离、怀疑和反叛,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似乎已为当下所不容。
“侠”本身代表了一种精神理想,体现的是普通人对于超脱世俗、抵抗秩序的欲望。侠是普通人,但更主要的是,他必须有常人所不及的处事原则和境界,他可以是纲常伦理的维护者,但更主要是反叛者。
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三侠五义》《水浒传》到否定皇权的新派武侠,侠义传奇的演进脉络,其实就是中国民智的逐步开启。
而回到今天的网文武侠时代,在故事上,它们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庸俗套路上,而且不幸的是,还不具备当时武侠故事的深度与厚度(佼佼者如金庸《笑傲江湖》中辛辣的政治讽刺)。

古龙后期作品《欢乐英雄》,着重描写武林大侠以外平凡人物的友谊与人性,而非大着笔墨刻画传奇。图为尚敬执导的原著改编电视剧定妆照。
一度,新派武侠作者们对传统侠义形式和内容都有反叛与舍弃(如古龙《欢乐英雄》等),而今天一代,最大的革新或许也就是把这些故事“耽美”化,侠客之间的情谊被模糊处理成了友情与爱情兼有又皆非的双重情感。
尽管如此,在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渐渐远去,宗族体系不断瓦解冰消、家庭关系原子化的今天,“看武侠”仍是中国人重温民族性的重要途径,是构建所谓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佳方式之一。
但在一个泛娱乐的时代,观众在卷帙浩繁的历史前望而却步的同时,也对与历史同气连枝的武侠不够跳脱于现实的陈旧形式感到了厌倦,武侠被更天马行空的仙侠、奇幻分流,硬派武侠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
一个例证是,现在的武侠片已经网剧化、网大化,而武侠电影已全面失守。近十年来华语电影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武侠作品屈指可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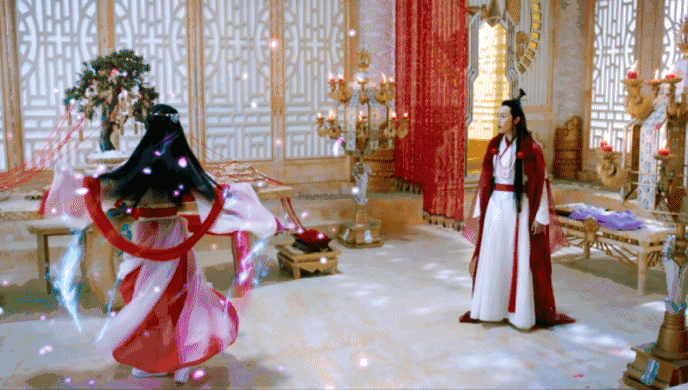
图片源自《香蜜沉沉烬如霜》(2018)
或者可以这么说,《战狼2》才是当代真正的武侠片。侠客冷锋凭借过人武艺,干着大侠们都热衷的惩奸除恶的事业,自由自在的同时还全不受政治、法律的制裁。
因为他身处异国,才得意施展其为所欲为的侠客秉性。(注:此句较原文略有修改)
03. 武侠片与武侠剧
从中国的文化根源上看,或许武侠叙事本不该盛行。
因为我们自古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韩非子直接用那句著名论断“侠以武犯禁”,给侠客们定了犯禁党徒的不法身份。在明清时期的六七百年中,普天之下皆张有官方的禁武令。
只是在社会动荡、国家危急时,人们又会把屁股悄悄挪到传统的反面,开始重武轻文。特别是一百多年前,中国适逢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于是才有了长篇武侠小说兴起和繁荣。
罗斯福当政,美国政府鼓励电影工作者创作能激起美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作品,才有了西部片的辉煌。同理,顺应了中国民众迫切需要建立民族自尊心的时势,武侠片、武侠剧则是唯有中国人才能拍得出、才能领会其内涵的“西部片”。

图为经典西部片《燃情岁月》剧照
不过作为同样源于武侠小说的延伸作品,武侠片有起有落,武侠剧却能一直长销。
民国时代,武侠故事即被多次搬上银幕。到了六七十年代,张彻、胡金铨在香港影坛,与金古梁同步了新派武侠,再到九十年代,徐克、程小东、袁和平等人再将武侠声望推至顶点。之后,武侠片就在华语电影体系中逐步衰落至今。
然而,自从TVB、亚视在七八十年代开始批量改编武侠小说起,武侠剧就一直是当红剧种,到了大陆影视工业兴盛的今天,势头也从来不减分毫。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武侠故事大多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篇幅漫长,电视剧可以凭借其巨大的容量以重现这些要素。而篇幅不够的电影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其二,相比电视剧,电影的媒介属性与观影条件要求更高更强的共情感,更需要与集体情绪的高度契合;而随点随看的电视剧能提供给观众更多的陪伴感。显然,被审查和主流意识形态共同钳制的武侠片,已经无法产出这种足以让观众共情的精神强度,而在主要给予陪伴感的电视剧中,观众并不会在意剧中的武侠精神是掺水货。

其三,电影求变,电视剧求稳。电影更像是一个排头兵,它天生带有探索和冒险的意味,它需要不断自我革新向前发展,拓宽观众的既有审美;电视剧则更接近于一种日用品,像毛巾、洗发露、早餐牛奶一样是刚需,需要安全稳定,无论它怎么排列组合,都是换汤不换药。
电视剧满足的是我们如白雪公主的后妈王后那样每天问魔镜谁最美,并希望魔镜回答是自己的欲求,这种欲求如此稳定,电视剧也就少有变化——至少在国产剧的范畴内如此。
得益于电视剧媒介性质的恒定,武侠叙事在被电影冷落的同时,在电视剧的容器内得以作为某种化石景观保存,甚至允许人们在它陈旧的基底上对其进行各式带有自毁性风险的微雕试验——比如耽美化。
04. 内卷时代哪有武侠
十年前最卖座的电影跟现在最卖座的电影大不相同,2010年《让子弹飞》这种满脸写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匪片”还能成为当时最火爆的电影现象,而如今最卖座的是《战狼2》《李焕英》。
而有趣的是,十年前最火爆的电视剧跟现在最火爆的电视剧却并无质的变化,十年前的剧王是《甄嬛传》,与之对标的是18年的剧王《延禧攻略》。

如果说《甄嬛传》还试图用正史化的拍法,努力将这出宫斗戏从个人叙事引向剧中历史人物所在的那个宏大叙事中去,那《延禧攻略》不仅全然放弃了这种努力,心安理得地相信这世上只有生存和向上爬两件事,并且沉溺于攀附皇权的快感之中无法自拔。
不幸的是,电视剧往往是现实社会运行法则的直接呈现,攀附正统、与权力共舞正是这个内卷时代的主旋律和势之所趋。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出超大型宫斗剧之中。
而《山河令》让皇权消失、令节度使背锅,也正是这种攀附与共舞的结果。当寄托了中国人自由理想的武侠剧,也要向代表权力的主流价值体系靠拢时,那还何来武侠?
金庸曾计划根据《卅三剑客图》写33篇系列小说,但他仅完成了一篇《越女剑》就不再写了。原因之一或许是《剑客图》的第二个主角虬髯客是个唐朝的武林高手,可汉代到唐朝森严的世族门阀体系和武侠的自由、平等、反叛精神是不相容的。虬髯客本想在乱世建功立业当皇帝,结果只因在人群中看了李世民一眼就觉得他才是真天子,还没打就认输了,毫无侠客风范。
看起来,今天的我们,都是精神上的虬髯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李不言,作者简介:文字走狗,电影门徒,理性党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