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文瑾,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就要走到2023年的尽头了。回望这一年的大事记,无论俄乌、巴以冲突,还是其他许多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暴行,都让我们深感人类常常生活在过去的阴霾之下,旧恨时常转化为新仇。
这让我这个以教授外国文学为生的教书匠想起,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复仇女神,她代表了无情的正义;她还有另一个名字,意思是“不可避免之人”。她的存在告诉我们,人类常常是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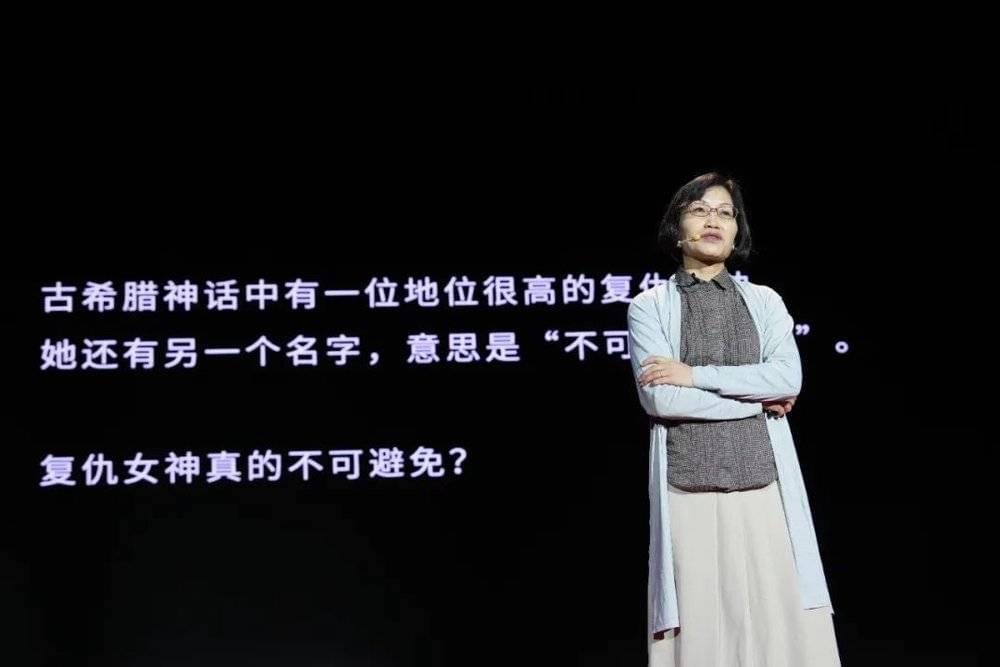
复仇女神真的不可避免吗?生活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宽恕。
宽恕是罕见的
宽恕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原谅,它针对的不是一般过错,而是那些不可能和不应当被宽恕的事情。宽恕内在地包含着一个悖论,因此不容易被理解。在民间认知中,善恶有报才符合三观。
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叫《灰姑娘》的童话,这个童话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团圆结局,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结局还存在不同版本。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又来了。
在1697年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版本中,灰姑娘不但宽恕了虐待她的继母和两个姐姐,还安排她们嫁给了王孙贵胄,跟自己一起过上幸福生活。而在后来1812年德国格林兄弟的版本中,两个坏姐姐则受到了惩罚,被鸟儿啄掉了眼珠。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个版本?
2015年迪士尼出品的电影基本采用了佩罗的版本。宽恕与和解,大概更符合迪士尼的价值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恶人受罚才更符合人们的期待。这也是格林兄弟改编这个童话的意图:他们想教育民众,传递恶有恶报的观念。
当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血淋淋的残忍和暴力时,人们会更加怀疑宽恕的可能。不义与不幸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像地心引力一样沉重和真实,宽恕反而像纸上谈兵。大多数时候罪犯请求宽恕而被拒绝,我们会认为这很自然。
三位选择宽恕的母亲
宽恕是罕见的,但仍然有人选择了宽恕。
2000年,四个来自贫困地区的无业青年在南京入室盗窃,杀害了德国人普方先生一家。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灭门惨案,四名罪犯被判处了死刑。
更令国人惊讶的是,普方太太的德国母亲写信给中国法官说,这几个凶手夺走了她的挚爱,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她十分痛恨他们,但并不希望以死刑来判处他们。
居住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为了更好地表达对普方先生一家的纪念,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改善四个年轻罪犯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基金会认为,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他们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改变这种状况。
2007年,河北邯郸农村一位叫梁建红的母亲在法庭上痛哭,请求轻判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她并非不痛恨凶手,更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另一位母亲不再像自己这样经历丧子之痛。
后来梁建红不顾家人反对,长途跋涉到730公里外的监狱去探望那位罪犯,还送了他一本《弟子规》和200块钱。她知道这个年轻人从小在贫困扭曲的家庭中长大,饱受家庭暴力。她希望《弟子规》能帮助他改好。
梁建红的儿子是因为没有讨到被拖欠的工钱来分给工友,而被急需用钱的工友在一时冲动下杀害的。她说,如果老板不拖欠工钱,儿子就不会死。
2011年,《中国青年报》和《南方人物周刊》都报道了另一位独子被杀害的母亲张艳伟。她在经历了两年多痛苦的心理斗争之后,同样是出于怜悯之心,决定接受法庭的调解,不再坚持要求判处凶手死刑,而是希望他能在监狱里反省。
为什么给予宽恕?
为什么她们会选择宽恕?
从哲学意义上说,宽恕既是对人的道德脆弱性的承认,又相信人是有可能改变的。中国有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会犯错是人的本性,但人性还存在向善和改过的可能,宽恕便基于这种对人的理解和信心。
事实上,宽恕并不存在于所有社会和文化中。在以决定论和宿命论来看待人性的眼光中,宽恕既不存在,也没有意义。因为假如一切都是被决定的,无论被处境、命运还是血缘所决定,都没有宽恕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宽恕体现了一种自由。
受害者给予宽恕不是由于懦弱,而是意味着他超越了人遭受侵害之后通常会产生的报复反应,说明恶和不幸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占据上风,但并不能剥夺人类爱与宽恕的可能。套用一句流行歌词——“就算失望,并不绝望”。这是人们在看到世界存在诸多仇恨与荒谬之后,仍对生活抱有希望的理由。
前面提到的那几位母亲便体现了这种令人敬佩的爱与宽恕的能力。
同时我也发现,她们的宽恕中都包含了一种对自身苦难的模糊认识:她们个人遭受的不幸其实也同社会失序和教育缺失有关,是社会问题以无序方式爆发的结果。当她们以仁爱之心来承受苦难时,她们也默默分担了一份对社会疾苦的救治。
正如作恶是对人伦的破坏,不仅仅是私人事务,宽恕作为对人伦的重建,也同样超越了私人事务。所以,于公于私,宽恕都是一种开端启新的力量。
我们可能听说过“宽恕是一件礼物”,我想这就是宽恕作为礼物的含义。西文宽恕这个词的词根,如法文“pardon”的“don”和英文“forgive”的“give”,都有赠与的意思。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母亲张艳伟,在儿子去世后写了2000多封信,经常在儿子的墓碑前读给儿子听。当她终于做出宽恕的决定之后,她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今天妈妈要告诉你,几天来妈妈真的感受到一点点轻松,过去那种活着的压抑纠结减轻了,少了许多。妈妈也要告诉你,也许是我最不忍心说出的话……可我知道是你最爱听的话,那就是妈妈从现在起,想活好每一天。”
虽然痛苦仍然不可避免,但我们看到了宽恕的医治能力。这是法律的正义和复仇女神所代表的无情的正义所不具备的。
法律的正义作为犯罪后的惩戒与补偿,只是按照公平对等原则,计算并尽可能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无法弥合伤害造成的人们之间的敌意与憎恨。当时机一到,这种憎恨就会被愤怒之火重新点燃。
冲突中处于弱势的那方则经常会由于无辜受欺而遗留下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心态渴望复仇,羡慕强者而鄙视弱者。正是这种受害者心态很容易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内化施害者的逻辑,从而沦为新的施害者,以致造成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局面。
只有宽恕能在道德层面上给生活新的开始,帮助人们对抗如莫比乌斯之环般的命运之轮。
大家都听说过南非传奇人物曼德拉,他为了解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奋斗了大半生,并为此坐过27年黑牢。1994年他当选南非总统,在就职典礼邀请了三位曾在牢里苦待过他的狱警。他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并逐一与他们拥抱。曼德拉的行动让他们羞愧不已。
典礼结束后,曼德拉平静地对他们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曼德拉以实际行动告诉国人,如果南非要掀开新的历史篇章,宽恕的能力至为重要。
宽恕不应当被滥用
然而,宽恕虽然美好,但不能低估其困难,也不应当被滥用。宽恕既非魔法,亦非心理治疗,更不是展示慷慨与仁慈的游戏。
2007年韩国导演李沧东拍摄了一部以宽恕为题材的电影《密阳》。在这部影片中,孀居的女主角李申爱唯一的孩子被一个熟人绑架并杀害了。她在精神极度痛苦中走进了教堂,希望通过信仰来帮助自己摆脱丧子之痛。
为了接近上帝,更是为了自我疗救,她甚至想去探访并宽恕那个凶手。意外的是,那个男人居然平静地告诉她说:“我流泪悔改,被上帝宽恕了。”
这顿时让李申爱崩溃。因为宽恕来得太轻易也太残忍,既不需要受害者同意,也不关心受害者的眼泪。这是真的宽恕吗?
这个戏剧化的电影情节,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宽恕是否应该有条件?是否应当以施害者向受害者忏悔认罪作为前提?
在我看来,电影中那位罪犯自认为被宽恕了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自欺欺人。他在玩弄一个宽恕的骗局。因为人要得到上帝的宽恕,就必须首先请求受害者的宽恕。
《圣经》中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五:23-24)可见上帝是公义的,并不漠视受害者的眼泪。
这个罪犯的角色提醒人们 :理解上帝的良善不能没有对复杂人性的衡量。即便人们有了宽恕一切的良好愿望,也不能低估其困难。这困难不仅是给予宽恕的困难,也是请求宽恕的困难。
我们一般以为,给予宽恕比请求宽恕困难。但其实,如果脱离功利目的,请求宽恕的行为也是罕见的。生活中的道歉大部分是为了减少麻烦,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真的需要请求原谅。
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黑白并不分明,界线并不清晰,人们常常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人们会更多地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而很少会想到可能是自己让别人遭受了不公。在这样的灰色地带,就更加难以承认自己的过错。
时至今日,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忏悔的声音仍是罕见的。他痛心疾首地说:“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
宽恕的困难也包括讲述真相的困难,讲述真相是宽恕的前提。南非图图主教和他所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倡议宽恕时,也强调对真相的调查与公开讲述。
讲述真相不仅是反对遗忘,也是让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拥有某种一致性。在彼此敌对的人中,对过去的记忆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会成为宽恕的根本障碍。
记忆不是抽象的,它承载了人们的爱恨情仇,不会简单臣服于宽恕的指令。当人们的记忆无法达成某种一致时,宽恕便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为了宽恕能落到实处,记忆的修复便如同铺路工程。在敌对双方之间,修复共同的历史记忆比谈论宽恕更为紧迫。二战后欧洲和平的重建,就是从德法两个交战大国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开始的。
应当承认,由于创伤记忆的存在和打扰,宽恕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且创伤越重,宽恕就越困难。尤其当新的冲突发生时,创伤记忆很容易卷土重来,新仇旧恨使事情更为复杂。无论是面对私人恩怨还是国家冲突,宽恕都是一场对自我的持久征战。
集体罪行中的个体罪责
此外,人们应当知道,对于集体犯罪,政府无法代替个人来给予或请求宽恕。
我们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曾有一位南非妇女来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她的丈夫被凶暴的警察杀害了,她表示她本人不打算宽恕这件事情,而且认为委员会或国家政府都不能给出宽恕。
这位妇女的态度表明,宽恕不同于调解或仲裁,也不同于赦免;它首先是施害者与受害者双方之间的事,与第三方无关。宽恕不能成为当权者为了政治利益而抛售的和解辞令。
20世纪后半期,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很多致歉和请求宽恕的声音与行动,例如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著名的华沙之跪。毋庸置疑,这些声音与行动都十分必要和美好,但也容易模糊“宽恕”这个词的界限。
因为宽恕首先应当作为个体的非体制性行为存在。体制性的包办容易使忏悔和宽恕丧失其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个人良知的觉醒,这一点对反思20世纪的社会历史悲剧尤为重要。
20 世纪历史上的重大罪行,往往都是以国家、民族,以及人类进步等宏大叙事为借口。普通个人在这种集体罪行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成为了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人们以某种社会规范或外界环境为由推卸自己的罪责,只肯相信自己的良好意图,而拒绝为行为后果负责。这就是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哲学家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指出的“恶之平庸”的观念。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最重要的执行者之一。然而,当他在法庭上受审时,却声称自己不过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是一个国家机器中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行政性屠杀的典范,认为他的罪行既非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狂热,亦非出于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而是由于人格的浅陋。艾希曼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升官晋爵,此外就是良知的麻木与沉睡。
正是这样千千万万人格浅陋的普通个人,一起制造了史无前例的罪行。针对这些罪行,既无人承担责任,也无人请求宽恕,使人类事务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然而这个怪圈并非无法突破,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西蒙·威森塔尔的故事。
1942年,年轻的威森塔尔被关押在集中营。有一天一位在战争中负伤濒死的纳粹士兵托人找到他,请求他作为犹太人的代表接受自己的临终忏悔。这个士兵深感罪孽深重,并为此痛苦不已,他不想带着遗憾死去,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冒险的举动。
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个举动实属大逆不道,所以他们是默默地在一个像太平间的房间里,做了这样一番交谈。
这个士兵的请求使威森塔尔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当代表那些惨死的同胞来给予凶手宽恕;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切感觉到这个士兵真诚的悔恨之心,和被自己的罪疚感深深折磨的痛苦。
最终,威森塔尔沉默地离开了。后来他幸运地从集中营里生存了下来,他时常回想这件事情,于是询问了很多宗教、精神和政治领袖,问他们自己当时的拒绝是否正确,其中也包括图图大主教。
他将自己的故事和这些人的回复编辑在一起,出版了一本书《向日葵——论宽恕的可能与限度》,专门探讨宽恕的难题。

中译本《宽恕》
尽管威森塔尔坚持认为自己无法代表死去的同胞来宽恕凶手,但这个临终士兵的忏悔,显然让他有所动摇,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士兵不但没有像艾希曼那样推诿自己的罪责,将自己称作一颗服从命令的螺丝钉,而且执意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来向另一个代表受害者的具体个人来寻求宽恕。
这个士兵出身天主教家庭,他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位神父来宽恕他,他也完全可以像《密阳》中那个罪犯那样自认为已经“流泪悔改,被上帝宽恕了”,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找到了一个素不相识且正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冒着十有八九会被拒绝的风险,来向他请求宽恕。我想这就是他的诚意,他拒绝把自己作为“工具”来逃脱,而坚持要作为一个人来承担这难以承受的罪责。
我想,即便他没能获得来自犹太人的宽恕,也至少证明了自己人性的复苏,这或许便是解除“平庸之恶”怪圈和魔咒的关键所在。
有限的宽恕
在现实生活中,《向日葵》中描述的那种临终忏悔依然是罕见的,更常见的是无人请求宽恕,或是请求宽恕的不到位,甚至是将施害者和受害者混为一谈。
面对这种情形,为了解除仇恨的困扰,避免集体创伤记忆转化为报复性冲动,对于20世纪反人类罪行中的受害者来说,十分必要和困难的是接受有限的“宽恕”。
有限的“宽恕”不是以受害者的名义给予施害者宽恕,而是终止父债子还的报复逻辑,承认关于罪恶不存在株连问题。因为每个灵魂都是自由的,施害者的后裔并不必然继承施害者的罪性,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灵魂负责,每个人都将独自面对终极审判。当然,有限的“宽恕”仍然希望人们能够负责任地记住过去。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扬凯列维奇,作为战后幸存的犹太知识分子,他对宽恕问题格外敏感而尖锐。他有一个著名观点:“宽恕在死亡集中营已经死去”。因为他认为在死亡集中营里发生的暴行的极端性不仅毁灭了受害者,也使得施害者的人性荡然无存。对于这种极端罪行,是不可能也不应当给予宽恕的。
多年之后,有一位德国青年给扬凯列维奇写了一封信,他说:“对于纳粹罪行,我是完全无辜的。但这不能给我丝毫安慰。我的心灵难以平静,我受到一种混杂着羞愧、怜悯、屈辱、忧伤、怀疑、反抗的情感的折磨。我总是睡不好,经常彻夜难眠,思索着,想象着。我摆脱不了噩梦的纠缠。”
收到这封来信之后,被称为“顽固不化”“心肠刚硬”的扬凯列维奇也被感动了。他给这个德国青年回复说:“三十五年来我就在等待这样一封信:在信中,一个并不相干的人完全承担可憎的恶行的责任。”
显然,扬凯列维奇的意思不是要父债子还,不是认为下一辈应该背负着上一辈罪行的包袱前行,而是肯定了这个青年看似“多愁善感”、貌似无用的多余的罪咎感当中,包含了一种对于过去的负责任的记忆与良知觉醒。这正是平庸之恶的解毒剂和有限宽恕的期冀。
有限的“宽恕”是让自己理性地面对过去的创伤和现在的责任,心智清明地管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既不遗忘,也不陷入仇恨,以哀悼和纪念来恢复对自我和世界的正确认识。
有限的“宽恕”既可使个人获得品格与德性,也可使国力上升阶段的民族获得精神上的成熟,学会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直面自身和人类历史中的苦难与罪恶,开创和平的未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生活在充满仇恨而缺乏宽恕的现实中。为了迎接真正的新年,为了让过去真正地过去,今天让我们都学会负责任地记忆。
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作者:演讲者:刘文瑾(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策划:恒宇啊,设计:挠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