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被压在床垫底下的《性爱的艺术》,封面是粉色的,长得像尊龙的男人一手撑在床上,暧昧地看向旁边的女人。
打开书,米黄色的纸张上,是黑色印刷体勾勒的各种姿势的简笔画人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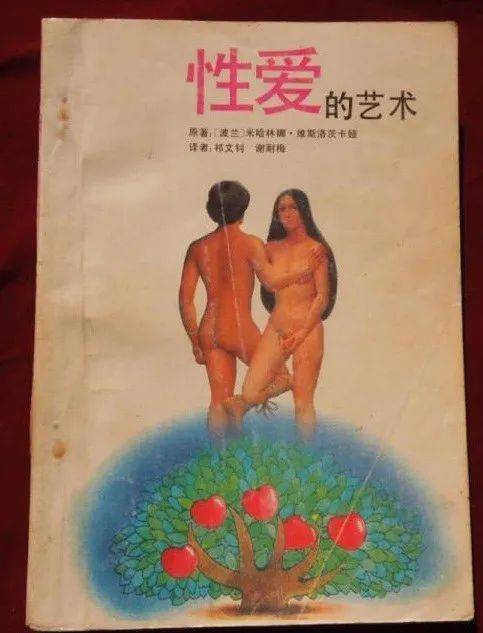
▲90年代的性科普读物。作者: [波兰] 米哈琳娜·维斯洛茨卡娅、出版社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译者祁文钊、谢耐梅。
父母结婚于1990年代,他们正是通过这本书自学一窍不通的夫妻生活,然后把它塞进床垫最底下。
这造成了我极深的困惑,这个藏着掖着的事情,一定是不好的,但为什么大人又喜欢讲那些故事,哄堂大笑?
初中生物课上,我暗暗期待生殖器部分的讲解,年轻的老师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匆匆念完了那一节的文字,来到了下一章节。
生活里,性是羞耻的,性令人难以启齿;电影里,性是美好的,性伴随着爱情而来。
也是长大之后,我才发现,伤害、权力,经常通过性的方式施加。
根据美国儿童虐待预防协会综合全球1980~2008年271份儿童性侵报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预估,在15~19岁的女孩中,有1/20(约1300万)曾经经历过强迫性性行为。
从来没有一个生物行为,像性一样复杂。
它裹着性别、欲望、羞耻、权力、伤害、情绪、亲密、爱……它就像那本《性爱的艺术》一样被尘封在床垫底下,在人们身心深处扭曲、发酵。
今天,性是陈旧的话题,但在实践层面,性咨询师卓月月发现了,“只做不谈”,仍是我们文化里性关系最大的问题。
今年10月,为了写“我们的性”,我来到性咨询师卓月月“以人为本的性表达”团体课。我想了解,如今人们如何进入“性”这个话题,人们来到这个团体课,带着什么样的个人经历?他们期待什么?

▲月月与她的助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那个词很脏
上海的秋天,下午6点钟天几乎全暗下来了。
在窗帘紧闭的空旷舞蹈室里,所有人戴着面具,随着熟悉的流行乐扭动了起来,一向身体僵硬、内缩的中国人,来到这个场合,似乎很努力地打开自己,以至于呈现出滑稽、可爱的局面。
尝试扭动了几下、撞击了几个身体之后,有人退到了一边。这是团体课的热身,脸上的面具让人在一群陌生人中稍微有了些安全感。
接下来,所有人会被渐次发到几张卡牌,人们需要用卡牌上写的词语造句并念出来。我抽到的词汇是阴茎、包皮、阴蒂等,造句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句子乏善可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性教育仍然十分匮乏。
大约发完卡片的时候,两位迟到的女士匆匆进了门来。Cathy穿着白色的棉麻面料连衣裙,很拘谨地找了个地方坐下,我看到她时而盘起自己手上的佛珠。
轮到她发言,她犹豫而严肃地摆放着卡牌,突然,她抽出一张牌,“这个词语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实在说不出口”,最后,她艰难地念出了这个充满了生殖器名词的句子。
Cathy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女性要端庄,这些词汇不是这种教育所认可的。
一直以来,她觉得性应该是圣洁、美好的,在性关系里,她总是被动等待,因为主动的欲望是羞耻的。她期待仪式般圣洁的灵肉结合,面对的却是粗鄙的性,太肮脏。
与她同行的女士Vicky,则用一种不带情感的语气把句子念了出来,好像要极力把自己和这句“很脏”的话划分界限。
Vicky是一位小学老师,由内而外都很得体,她有一个孩子,从来没有体验过性生活的愉悦。但刚开始这门课,就要说一堆“脏话”,这情况显然不符合她的预期。
现场不少人并非第一次接触此类的两性课程,很多人甚至是频繁上课的“上课专业户”。
轩轩同时是另一个以女性为主的两性咨询平台的学员。曾经,男友的出轨让她陷入了痛苦的自我怀疑,于是她跌跌撞撞走进了性课堂。
如今,她早已换了几个男友,从一个社恐、不自信的女孩大变样,就像她在自我介绍时的自我定义:大家好,我是主动出击的轩轩。
家庭主妇秋秋也在遇到关系问题后寻求帮助。
她和丈夫青梅竹马,育有两个孩子,在外人看来郎才女貌的婚姻,内里伤痕累累。丈夫频繁出轨的日子,她像疯了一样到处寻找。被找到的丈夫会认错、回来,然后继续出走,如此往复。
参加类似团体课、寻求性咨询的来访者里,女性占大多数。
她们花了很大力气做好心理准备来到这里,很大比例是因为丈夫出轨、嫖娼,或者是已经无法忍受极差的性体验。她们带着对性的困惑,抱着要学习性技巧、增加性魅力的目标,来到特殊的课堂。

▲爱何以重新学习?(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相比起现场的10名女性学员,4位男性学员则没有认为自己有“明显问题”。月月说,一般而言,最终走进性咨询室的男性,很多抱着猎奇的心态,他们一般不会觉得自己的关系遇到了什么问题。
钓鱼是现场年纪最大的学员,当天晚上,他有点强装镇定地缩在角落。作为一个60后“老人”,在推开门的那一刻,他内心忐忑:现场这么多“年轻人”,有的人看起来甚至和自己上大学的儿子一样大,这把年纪了,我也可以谈性吗?
他出生于1964年,成长于文化上普遍性压抑、性匮乏,不谈性愉悦的年代。
20世纪80年代,钓鱼迎来了青春期,恋爱自由带来了新风向,但彼时拥有婚前性行为的人依然会被视作“流氓”。他对性的好奇和困惑却越发严重,那时候,他经常到书店淘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关于两性的书籍。
在人体医学那列书架上,他读到了各种人体器官的知识,那构成了他最初对男女生殖器以及生殖行为的了解。
在大学宿舍的夜晚,等人们睡去,他总是一个人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这些“禁书”,其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露骨的描写,成了他的性启蒙。
后来,经家人介绍,他和妻子结婚,如今已经20多年,儿子也上了大学。他依然对性的探索充满了兴趣,似乎是对当年性压抑年代的代偿。
只不过,这些探索显得孤独,他一般不会和身边的朋友谈论这些事情,甚至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也不会,谈论性只会让其他人对他投来异样的眼光。
谈起成长过程中那种巨大的性压抑,钓鱼依然有些不忿,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他所说的“资源”“反而现在的年轻人,性自由了,却好像对性不感兴趣了,宁愿看电脑、看手机”,他现在有点担忧儿子不谈恋爱的问题。
90后凯泽是常年出现在不同团体里的学员,在心理探索领域不断精进。他主动提及自己曾经去参加课程被骗的经历。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员们讲述了对家人的愧疚,所有人哭得稀里哗啦,他感觉到氛围不对,当天下午就跑了。
他也参加过性别学者方刚教授的课,当我问及是不是今年出圈的著名的“男德班”,他说“我是很尊重女性的,不需要上这个课”。谈及他最近的情感状态,他表达了自己对于多元性探索的兴趣,随后便飞到其他话题。
二、“只做不谈”的性
刚从业的几年里,月月积极迎合市场需求,教一些更偏向技能的“术”——如何性感,如何前戏。当时课堂上最受欢迎的便是“爬床”,许多上过她的课程的学生对此念念不忘。
3年前,我采访过月月,选题以猎奇视角切入:一个“性教练”如何炼成?当时她刚拍摄了一组在丛林里的身体写真,光影穿过树叶,她自然伸展的身体上留下树叶的阴影。那是她重新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
早些年,她曾经险些遭遇性侵,那也是她走进两性领域的契机。
那段经历与许多性侵故事如出一辙:职场饭局,酒后,她被“赏识”她的老板带到酒店,无须询问同意、不顾反抗,推倒女性被对方当成一种值得吹嘘的男性气质。
在挣扎到几乎绝望的时候,她突然严肃地看着对方,“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你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我也有男朋友”。对方被吓住,放开了手,她逃过了一劫。
多年后谈起这件事,她原谅了对方。
让她最难受的,是从那之后她的自我批判以及随之而来无法言说的羞耻感。这也是不少受害者的创伤历程:是我的问题,所以他才找上我?遭到这样的对待,我是不是很脏?
这种羞耻来自性别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它将一套身体的规范植入女性的意识里,包括一系列的污名化,它让女性受到侵犯时无法启齿,它也让一些女性,在性生活里很难真正放开。
在她真正接触两性行业之后,她才发现,因为无法正视性、谈论性,很多女性从来没有过良好的性体验,甚至感觉性体验都是痛苦的。对于性,人们“只做不谈”,反而成了最隐秘而重要的问题。
在团体课中,月月设计了一些环节,让所有人参与、体验、分享,让性在这个空间得以敞开地被谈论。
几乎在每个环节,她都极其认真地观察着空间里发生的事情,每个人发言环节时,她总是给予关注和倾听。她认为“性这个事情不是专家说了算,我没有资格去评估你的生活”,她强调人本主义的关怀。
也有学员慕名前来,想来看看这位性教练、性导师的庐山真面目。但月月不是那种有克里斯玛情结的导师,后者有极强的领袖魅力和感召力。月月在课程里的存在感并不强,或者说,她在尽量压低自己的存在感。她经常是静静听着,让其他人表达自己。
她的魅力也正在此,她给人一种感觉:你可以放心说话,不用担心遭到审视和评判。
月月自我定义为一个促进者,她认为“每个人本自具足”,她要做的,是为他人腾出一些空间,“看看他们能发现什么,创造什么”。
三、僵住的身体
2018年前后,几乎快被痛苦溺死的婧秋走进了月月的课堂,她身体僵硬,处在巨大的冲突当中。她和丈夫的摩擦不断,害怕丈夫使用暴力,尽管对方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5年后,她重新出现在月月的团体课上。
婧秋出生于1989年,扎着高高的马尾,素面朝天,皮肤黝黑,有点瘦,举动里带着疏离和执拗。多年来,她一直辗转于各种流派的心理疗愈实践,以寻求自我疗愈。
在第二天晚上的“前戏共创”环节,她抽签抽到和现场年龄最大的钓鱼一组,人们两两一组进行前戏的编排。对方身材轻微发福,圆圆的脑袋上,发际线几乎已经退守到头顶,留下了一撮灰白的头发。
婧秋“心里咯噔了一下”,从前,她从事中医调理的工作,只要遇到相似的身体,她就感觉浑身紧张、汗毛倒立,“好像一只随时准备发起攻击的斗鸡”。
那是无数次梦魇中继父的身体。
那时候她才上小学,只记得夜晚窗外的光照在了天花板上,早上醒来的时候,身上光溜溜的,什么也没穿。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消化了这件事,“人都很恐怖,鬼比人还可爱点”。在往后的日子里,恐惧具体地住在她身体的某个地方,不时会出现,冻僵她的身体。
2017年,在她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她遇到了丈夫。之所以同意谈恋爱,是因为对方听说了她小时候的经历,表现出了真切的理解和关心。
但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仍旧无法和丈夫共处一室,丈夫在家的时候,她经常要出门独自待几个小时。有时候发生争执,她便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身体呈现应激状态,总觉得丈夫要骂她打她,像生命里的两个父亲一样,尽管现实中丈夫从未家暴。
这种感觉几乎从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在和人接触的过程中,脑子时不时会短路,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什么都不知道了,像个傻子一样”。更严重的是突然惊恐发作,全身紧绷,“紧张到神经开始痛”,陷入密不透风的绝望当中。
也就是那时候,在亲姐姐的建议下,婧秋开始尝试各种身心灵的疗愈方式。自救的过程是漫长而反复的,直到最近几年,她才搞明白了自己“脑子的问题”可能是性创伤对脑神经的影响。
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领域,她的状况称为“解离”——当生命中出现重大创伤,创伤情绪没有被及时疏解,直到个体无法承担,出于自我保护,这种极端情绪会被分离出去,个体会将自己剥离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她每次感到恐惧、遇到冲突,便会全身僵硬。
心理学让她得以命名自己的痛苦。如今说起这些概念,她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晰。这些年,她就像一棵被蹂躏到奄奄一息的枯草,又慢慢活了过来。
在修行的时候,她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当时的上师说她命中缺水、缺金,“婧秋”两个字有水,秋天属金,寓意女子有才、收获满满。如今她习惯了这个新的名字。
课室里时而闷热起来,团体课的第二天,先前铺在地板上的地毯有点起球,变得不整齐,就像这十几个人经过一两天密切的摩擦,边界在慢慢松解。有人趴在地上,有人半躺着,大家边看着其他人表演,边讨论之后的前戏情节如何设计。

▲前戏共创环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婧秋又出了神,她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她和妈妈一起去买菜,一个老男人突然挤进人流靠近她,紧接着,他的一只手贴近她的臀部摸了一下。她在原地愣了快5分钟,才反应过来她被性骚扰了。巨大的愤恨出现,她诅咒这个人出门被车撞死。
这种无助的愤怒经常出现。十几岁的时候,在深圳姐姐的家,婧秋从厨房拿着菜刀冲向了继父……最后菜刀被抢了下来,全家人为此责怪她,这位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和她断绝了所有联系。
婧秋涌起孤立无援的愤怒。她怨恨母亲没有保护她,但她内心里最怨恨的,是她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小时候的自己。站在菜市场,她心里又涌出了无助的感觉,混乱的状态让她头痛欲裂。
但那一次她感觉到,她似乎有了别的力量,多年来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中,她逐渐意识到妈妈的沉默给她带来巨大的伤害,她渴望母亲的表态,她需要感觉自己是被爱着的。但此刻她已为人母,察觉到很多无奈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想到这些,她不再像十几岁那时,任由自责将自己吞没。她想起一位儿童性教育老师说,一大把年纪了也会遭到性骚扰,人不管多少岁,也没办法总能自我保护。她原谅了自己。
眼前,这个形似她继父的男性,正在跟她商量接下来前戏情节的设计。他们走到了这个空间的正中央。
“我现在要把你捆起来。”
钓鱼手上拿着一捆绳子,婧秋配合着躺在地上,她的眼睛被蒙住,脸正对着天花板,四肢张开。钓鱼看起来很紧张,他蹲在地上一一把捆绑的皮带放在婧秋身上,场面一度有些滑稽,不少人忍不住大笑。
瞬间,婧秋从地板上站起来,绳子和皮带散落一地,她一声令下,“给我躺下”。
钓鱼被推倒在地上,他的眼睛首先被蒙住,失去了视觉后,他浑身瑟缩起来。
婧秋抓起地上的绳子,先是把钓鱼的脚捆住,捆得很紧,一切反应似乎没有表演的痕迹,捆好了脚,她把绳子在钓鱼的身上绕了一圈,再从后背捆住他的双手。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钓鱼配合地大喊。
婧秋站起来,把一只脚踩在钓鱼身上,虽然她拿捏着表演的分寸,但在她把鞭子挥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似乎能感觉到某种 “投入”。我似乎看见当年在黑暗中无助的女孩,重新把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上,她好像在宣泄“没人有权力伤害我”。
事后,婧秋告诉我,表演中的反转不是他们商量好的,完全只是即刻的反应,“30岁以后,自己的力量好像起来了”。
疗愈的道路仍旧漫长。她给了自己一个积极的方向,她说自己的身体在慢慢记住好的体验,在电话里,她向我讲述了丈夫许多令她感动的地方,他总是默默支持她的决定,她学会感受丈夫安全的爱了。
四、激情的非必要
说话的时候,恩希的双臂像舞者一样伸展,她的身体随着呼吸起伏,双臂自由地张开、合上,像一个呼风唤雨的现代“女巫”。
在关了灯的舞蹈室里,她动用手指、手臂、身体的力量包裹住趴在前面的身体,这样的抚触,强调“全然的接纳”以及“全情地给予”,所有人吃惊地看着,像在欣赏一场即兴艺术演出。
恩希出生于1970年代,是一名抚触疗愈师,在团体课的第二天,她现场示范如何做抚触。
它涉及到人们对身体的感知。恩希所示范的抚触疗愈,通过拥抱、肢体抚触,作用于身体,让人们释放出被压抑的情绪以及欲望,再通过体验“植入或更新”一些信念,让身体熟悉这种感觉,形成身体记忆,从而达到疗愈。
一个礼拜之后,我在恩希的家里又见到她。这一次,我特地观察了她的手,她的手指修长,骨关节突出,灵活又有力量。
这是一双摸过各种各样身体的手,脂肪堆积的、皮肤松弛的、骨瘦如柴的、健壮结实的、白皙的、黝黑的……她疗愈了各种处在困扰中的男人和女人,但对于自己的婚姻,她早已接受了激情的非必要。
她十几年的婚姻,经历过漫长的拉扯。那原本是一段看起来匹配的中产婚姻——双方事业有成,家庭收入蒸蒸日上。
盘腿坐在地垫上,恩希泡着茶,笑着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好像一直要证明自己给人看”,因为“从小被熏陶得个性特别好强,追求完美”,她拼命工作,在房地产、外企干了十四五年,业绩一直都很好。
人生转折在生完孩子那年到来。一个新生命颠覆了她原来的生活。
那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产后抑郁,只是挣扎于一个女强人竟然处理不好孩子的问题。哺乳期间出差,飞机晚点,涨奶让她胸部发疼,她跑到洗手间,边挤奶边流泪,这时电话打来,对面是孩子的哭声、家人的催促,她几近崩溃。
那时候她的事业也面临着动荡。她在乱七八糟的状况之中,发现老公在外面有了女朋友。她无法接受,当她犹豫不决是否要离开这段自我消耗的情感关系时,孩子还小,她生怕旁人的目光,于是,她把关系冷藏进冰箱,“你别碰我,我也不想碰你”,全心投注到孩子以及新的事业中。
那时候,婚恋网站百合网到沈阳开拓市场,寻觅线下合作商,她感觉到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
无法面对自己的关系,她转向“天天搞这些男男女女处对象”的事情。很快,恩希便把团队做到了30个人。打电话邀约、核实资料、签约会员、匹配对象、线下约见、辅导恋爱。
几年下来,她发现这种按照“条件匹配”的方式去牵线恋爱的方法,成功率非常低,很多问题显现出来。人们为何无法寻找到合适的爱人,为何找不到幸福?为了促进会员牵手成功,她带着团队成员去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参与到婚姻家庭咨询里。
此时她的婚姻已经持续冷战了六七年,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婚恋故事,因为介入心理咨询领域,她想清楚了——亲密关系核心的问题来源于自己的课题。
那几乎也是心理学开始在中国流行的年代,2012年左右,许多国外的身心灵疗法涌了进来。教练技术(LP)、催眠疗法、舞动治疗、绘画疗愈、家庭系统排列……各种各样的心理应用流派涌进她的世界。
其间三四年,她频繁飞到各地参加课程,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婚恋事业上,给会员办各种心理沙龙。“按照条条框框找人还是没有感觉,就必须看到底层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遇到合适的伴侣、拥有幸福。
直到2017年,恩希在广州第一次接触到亲密形式的课,老师用某种特别的方式带出人们身体里长期积压的负面及阴暗的情绪,“当你感到极度的愤怒的时候,要允许在肢体有保护的情况下发生一些冲撞”。
在那个课堂上,她多年的盔甲被突然打开。“你就装”,听到老师的这句话,她又惊诧又愤怒,在那个氛围下,她把愤怒用肢体表达了出来,怒吼、放声大哭、打架。
回去以后,她突然感觉到“一些很沉重的东西好像开始剥落和松掉了”。
几年持续冷战的亲密关系里,她无法面对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女性有欲望好像是羞耻的”,长期以来,身体发福,她用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来回避压抑身体的欲望。
她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个“很装、很不真实”的人,“因为我受到的教育,包括以前在大公司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我必须是一个很端庄、很有范的体面人”。当这个壳破掉之后,她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了变化,她开始不再苛刻要求自己成为 “好女人”。
宣泄愤怒的体验让她意识到,愤怒是没法通过压抑它而消失。
它潜藏在身体里,以另外的更具破坏力的形式呈现,直到有一天,你真正能允许这些情绪流动——她说起女性被压抑的愤怒,“当它排山倒海地表达出来的时候,这种能量就转为内在的力量,最后转化为慈悲”。
2018年,她开始跟随世界各地不同流派的老师,学习灵性按摩和手触疗愈。她成了一名抚触疗愈师,走进了疗愈叙事里的一环,以身体作为方法。与人接触,她觉得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有爱的流动,反而那些不得不绑定在一起的关系里,爱早已消失。
这些年,她和丈夫各自经营着自己的事情,一切都没有改变,生活照旧,不同的是,她“不再试图努力去改变他、改变婚姻和改变生活,如实如是地接纳了所有”。
她学会了精进自己,不再对他人有控制,对关系也没有执着。丈夫从前喜欢叫她喝酒应酬,她如今学会拒绝、树立规则。
随着她内心的“放下”,漫长的冷战似乎随着时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她不再试图从婚姻里寻找依赖、索取和证明,她似乎找到了新的脚本——他们走进了一种默契的开放关系中。
她如此淡然自如地感叹着“这两三年是婚姻最舒服的时候”,她感觉到丈夫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稳定支持,她也感受到她建立的边界和秩序带来的自由。
五、亲密关系不再是唯一选择
海星是现场年纪最小的学员,她出生于2000年,目前居住在伦敦,算命师是她的身份之一。
与现场其他人相比,她更积极地袒露自己的欲望,她强调自己对男色的狂热,她对自己的性魅力有充分的觉知,并热衷展示。在电梯里我遇见了她和另一位男性,她便开心地分享:你知道吗?他说我很性感。
我愣住了,报以幽默:这还用得着说吗?
她反而说,觉得好看当然要不吝啬赞美了。
那天,她穿着一件低胸泡泡领上衣,进这个空间不久,她便提到了自己今天没有穿内衣,因为发现不穿也没人会在意你。
她身上拥有前辈女性们鲜少有的自由气息,性别枷锁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痕迹。
既然是这样,我更好奇她为什么来参加这门团体课了。
今年三四月份,她在网易云评论区认识了一位歌手。最近,她回国,在成都进修,见了歌手一面之后,两人便在一起了,歌手家里成了她的停靠之地。自从大学毕业,海星便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不同恋爱决定她在国内时会在哪个城市,她总是随着男友的居所而迁居。
她出生在四川一个十八线小县城,18岁的时候,爸爸意外离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海星把玄学的爱好发展成职业。20岁的时候,因为事业刚艰难起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她想过“要不要早点结婚”。
但很快,她发现婚姻并不是必要的归宿。
当时男朋友对她控制欲很强,她要花很多精力去维持这段关系,拉扯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突然觉得不想再谈,就分手了。一直以来,她对关系的态度都是“能处就行,不能处拉倒”。
在成都的日子里,歌手很细心,每天工作晚回,会给她准备各种爱吃的早餐和食物。但他们也产生了摩擦。她在课间分享自己的困惑,“一个大美女躺在他旁边,他什么也不想做,还给我盖好了被子”。
性欲的不对等,让她有了“对方是否不爱我”“我是不是个备胎”的疑惑。
短暂摩擦后,歌手主动拉着她进行沟通。歌手说自己生活压力很大,爱情对他来说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一对一的男女关系对他来说太多了。这样坦诚的交流,让海星突然解脱,事实上她也觉得“传统的恋爱关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消耗”。
释然似乎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她觉得,脱离了一对一关系的捆绑之后,人们反而可以自由地给予爱,重新获得自由。
“能谈就谈,不谈就拉倒”,是海星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她的想法与吉登斯提到的“纯粹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情爱有共通之处,他们赞颂平等、自由、互利的关系。
但这依然会带来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焦虑由此产生。海星用一种向内审视、修行的方法得到了处理,“如果你别有所求,你希望别人夸你、爱你,那实际上是你自己的问题”。
于是,她来到了月月的团体课,更加认定对关系的控制和焦虑,是“自己的课题”。
在成都待了一阵子之后,海星决定重新回伦敦生活,就在采访那天早上,她收到了歌手发来的消息。
歌手说从她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以自己为中心,不需要为关系隐忍、牺牲。海星告诉我,“当你真的照顾好自己的需求,其实就是自我圆满的时候,你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绝对无私的状态” 。在电话那头说着说着,她说自己有点想哭,因为彼此对关系的不企图。
团体课结束后,海星心里一个念头深化了,那就是爱和性只是一个人的事。她和歌手依然保持着友达以上的联系,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成都,像恋人,又没有约束,生活随时有新的可能。
后记
一开始带着想要学习性技巧,期待解决问题的人们,几乎都走上了探索自我的道路,这条道路包括追溯自己过往的生活直到童年、原生家庭,这也近乎是网络上、以自我为主体的“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的叙事。
研究亲密关系的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在《冷亲密》里提到,临床心理学的许多不同分支在20世纪的美国流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疗愈情感风格,到了今天,这文化景观也在中国发展起来,大量心理学自剖书籍出现,人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了解自己,“人们正在学习自我关照、自我照顾”。
这样的心理疗愈技术,获得了大量女性受众。它确实是女性所需之知识:它的内容反思要求女性进行自我牺牲、自我舍弃的传统性别伦理,它强调女性自我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女性的伦理压力,甚至重新定义女性力量。
月月的工作室叫作“她语”,似乎印证了性从以男性性经验为主导的情况中解脱出来,女性逐渐追求在两性关系中获得平等与自主,就像月月说的,当看见自己,也会看见他人。当人们被看见,便是传统关系变化的契机。
但月月也时常思考两性行业里的一个问题。一些“提升女性魅力”的课程迎来了许多痛苦的女性,最终这些课程让人们修炼成一个一个更好、更具有魅力的“完美自我”,这样的道路永无止境,但是,这似乎离与另一个人的连接越来越远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再次感谢他们的坦诚与勇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小姐MissF(ID:newMissF),作者:刘车仔,编辑:Felic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