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接连塌房,感慨内娱不争气的同时,很多人直接把自己的偶像改成动物界“网红”,从玲娜贝儿到熊猫花花,它们的社交账号每天有上万人围观。
明星为什么老是塌房?我们尝试去书里找答案。在被奉为流行文化研究开山之作的《幻象》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丹尼尔·布尔斯廷曾对名人和造星运动做过深度分析。
名人是人为制造的产品
我们的时代制造了一种新的卓异,它反映出文化和国家的特色,就如公元前6世纪希腊诸神的神性或中世纪骑士精神与典雅爱情。这种新的卓异尚未将英雄主义、圣徒、殉道者完全逐出我们的意识,但每过去一个年代,它便越发夺走它们的风头。所有旧形式的伟大都只能在新形态的阴影中存活。这种新形态的卓异就是“名人”。
Celebrity(名人)这个词一开始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状态——如《牛津英语词典》所说,“一种常常被人谈论的状态;著名,臭名昭著”。这种意义的用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即使在那时,它的含义也比fame(声誉)或renoun(名望)要弱。比如,19世纪时,马修·阿诺德曾说虽然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追随者有名声(celebrity),斯宾诺莎本人却有声誉(fame)。
对我们来说,celebrity指的却主要是人——“一个有名气的人”。该词这种用法明显始于图像革命早期,第一例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爱默生提到了“富有而新潮的名人”(1848)。现在,美国词典把celebrity这个词定义成“一个著名或广为人知的人”。
这种特殊现代意义下的名人不可能在此前任何时代出现,也不可能在图像革命前的美国出现。名人是一个因其名气而出名的人。
他的特质——或他的缺乏特质——为我们的奇特问题给出了例证。他不好也不坏,不伟大也不卑微。他就是人形的伪事件,他是被故意捏造出来满足我们对人类之伟大的过度期待的。他在道德上持中立态度。他不是阴谋产物,背后也没有意图推广恶习或虚无的群体,制造他的是一群诚挚、认真工作的人,兢兢业业,极有职业道德,努力对我们“告知”,对我们宣教。他是我们所有人制造的产品,我们自愿阅读他的资料,喜欢看他上电视,购买灌注了他声音的唱片,和我们的朋友聊起他。
广告业证实了名人的市场影响力,名人在行话里被称作“大人物”(big names)。代言广告不仅用到名人,它还帮助塑造名人;让已然成名的人更加知名,这自然提升了其作为名人的地位。19世纪前,声明产品地位的方法是称其为“国王特选”,这种做法自然也是一种代言推荐。但国王确实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家世,实权和名义上的权力都十分可观。国王不是收受了金钱而做推荐的,他多半也只会使用质量超群的产品。他不单单是个名人,因为成为名人的关键仅仅是有名气罢了。
对大众杂志上传记的研究显示出这些杂志的编辑——恐怕还有读者,在不久前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老派英雄身上挪开了。他们创作传记的热情不再放在因实际功绩而闻名的人身上,而是转向了新潮的名人。
分析《星期六晚邮报》和现已停刊的《科利尔》在1901至1914年间一共五年的传记文章,结果74%是政治、商界和专业人物。但在1922年前后,超过一半文章都在关注娱乐界人士。即使在娱乐界,越来越少有文章关注严肃艺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和喜剧。越来越多的文章(近年来,几乎所有文章)涉及轻娱乐领域、体育界和出没于夜店的人群。

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制造信息的机器制造了一种新的英雄替代品,那就是名人,其主要特征就是有名气。在伪事件的民主特点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名人,只要他能上新闻、不过气。娱乐圈和体育圈的人最容易积攒名气。如果他们够成功,就可以盖过他们所扮演的对象。乔治·亚利斯的风头盖过迪斯雷利,费雯·丽盖过郝思嘉,菲斯·帕克盖过戴维·克罗克特。由于他们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名气,他们也就最能让积极的媒体不断把他们留在公众的视野中。
杂志和报纸读者不再认为能从他们的英雄的生活中学到什么,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通俗传记提供不了多少可靠的信息,因为传主本身也只是媒体的虚构。如果他们生活中没有任何戏剧性事件或成就,那也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他们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戏剧性事件或成就。他们是名人,他们获得名气的主要方法就是依靠名气本身。他们因为自己的昭著恶名而臭名昭著。如果这让人一头雾水、不可思议,如果这不过是同义反复,那也不会比我们的其他经验更让人一头雾水、更不可思议、更同义反复。
我们的经验越发沦为同义反复——毫无必要地用不同措辞和图像表达相同内容。或许让我们苦恼的并不主要是名为“虚无”的缺憾。实际上,因为我们急切地使用机械方式人为制造充实,我们经验的空白变得更加空虚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我们不只用这么多空虚填满了经验,还把这些空虚弄得如此缤纷多彩。
我们能听见自己的声嘶力竭。“他最棒了!”我们描述名人时,满嘴都是“最”。我们读着通俗杂志传记,读到某个演员是“现在电影圈最幸运的人”;某将军是“爱因斯坦之下最好的数学家”;某专栏作家的“求爱最为奇异”;某政治家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刺激的工作”;某运动员“嗓门最大,肯定也是最悍勇的”;某新闻人是“国内最始终如一充满怨恨的人”。然而,虽然标签上有这么多“超级之最”,内容却很平庸。我们所爱读的名人生活故事,如利奥·洛文塔尔所说,不过是一系列的“难关”和“喘息期”。这些男男女女“是坐实了的平凡人物样本”。
这些新模板铸造的“英雄”再也不是赋予我们目标的外部源泉,而是一些容器,我们将自己的漫无目的倾注其间。他们不过是放大镜下的我们。因此,这些表演者——名人无法扩展我们的视野,占据我们视野的都是些我们熟悉的男男女女。正如《名人纪事》广告那令人信服的说法,名人是“过去被新闻造就,如今自己制造新闻的‘人物’”。要制造名人,只需让他们被人熟知,以公关手段引入并强化。因此,名人承载了完美的同义反复: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人们最熟悉的。
名气是速朽的
从前,公众人物需要私人秘书来将自身与公众隔开。现在,他则有媒体秘书,以让他在公众眼中保持良好形象。在图像革命前(也在尚未经历图像革命的国家里),如果某人或某家族置身于新闻之外,那么这就标志着他们拥有坚实的非凡之处。怀有贵族式虚荣的女士只应上三次报纸:出生、结婚、离世。如今,上流社会家庭的定义就是常常上新闻。曾经,真正的英雄人物对公共宣传弃如敝屣,默默依靠自身人格或成就的力量。
英雄是时代造就的:要孕育英雄,至少需要一个世代。俗话说,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创造传统,也被传统塑造。他的成长历经数代,每一代人都从他身上发现新的美德,将新的成就归于他。当他所处的过去变得愈加虚幻,他的英雄气概则有增无减。他的面容和身形不需要有刀削般清晰的线条,他的人生也不需要注脚。
与此相反,名人永远是当代人。英雄是由民间传说、神圣文本和历史著作造就的,但名人是由小道传闻、公众舆论、报纸杂志和转瞬即逝的电影电视画面打造的。时间的流逝,可以创造并成就英雄,但却毁灭了名人。一方由重复所创造,另一方由重复所破坏。名人诞生于日报之中,永远像其起源那样稍纵即逝。
先前制造名人的手段,日后也必定摧毁他。他成于公共宣传,也毁于公共宣传。新闻让他生,也让他死——不是通过谋杀,而是通过窒息和饥饿。没有谁比上一代名人更加彻底地被人遗忘。正因如此,新闻栏目“现在他们怎么样了?”描述的过气名人默默无闻的现状,才让我们忍俊不禁。故意提起一度大红大紫、在过去几十年间名气尽失的人,总能让人发笑:梅·布什、威廉·S.哈特、克拉拉·鲍。
明星的坠落甚至算不上悲剧,因为他只是恢复原形,重归本来的无名状态罢了。根据亚里士多德广为人知的定义,悲剧英雄是从高位坠落的人,是身有悲剧性缺陷的伟人。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伟大害了。然而,昔日的名人不过是普通人,若是他回到该在的平庸位置,这不是因为他本人做错了什么,而只是时间的必然。
公众关注的炽热光芒在一开始给了他徒有其表的辉煌,然后很快让他融化消失。即使在公众关注的载体仅有杂志报纸时,事情就已然如此。如今我们有了全年不休的媒体、有了广播和电视,情况就越发变本加厉。现在,名人的声音和画面尽可能地侵入我们的客厅,制造名人比以前更快,名人也消失得比以前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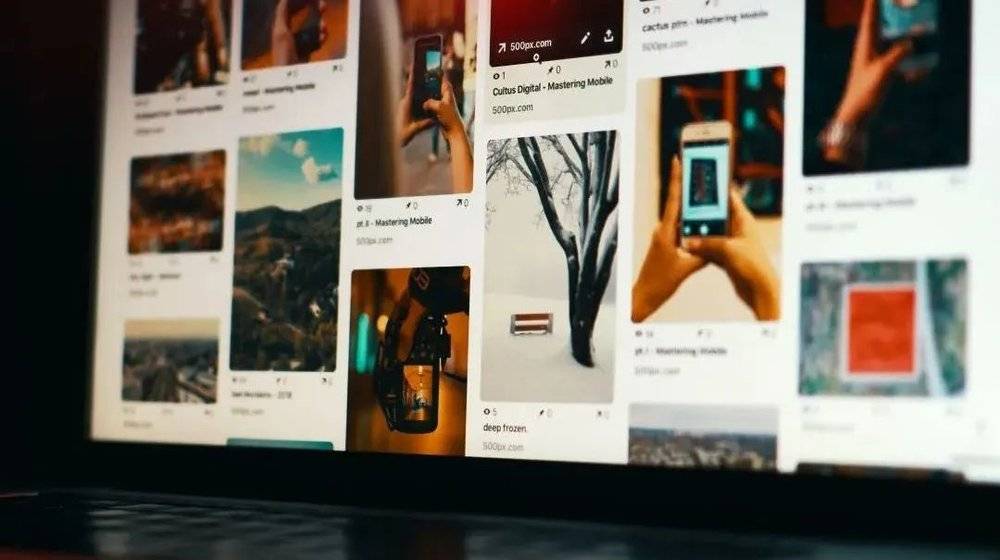
英雄和名人的个性还有更加微妙的差异。这两类人日渐相似,但方式又很不一样。在传统模板下代表伟大的英雄倾向于变得无趣且迂腐。最伟大的英雄有着最没有辨识度的面容或身材。乔治·华盛顿的个性不突出,反而有助于他扮演国父的英雄形象。爱默生说所有伟大英雄最后都会变得超级无趣,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要成为伟大的英雄,实际上就意味着变得毫无生气;变成硬币或邮票上的面孔。这意味着成为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笔下的华盛顿。然而,当代人,以及他们中的名人,却受困于个性。他们太鲜活、太独特,无法打磨成对称的希腊雕像。图像革命的聚光灯照射在脸上、身上,突出了不同人的形象差异。
当各英雄因人格中相似的伟大美德变得越来越相像时,名人的辨识度主要来自他们个性中微不足道的差异。因个性而出名,实际上意味着你是个名人。于是,“一位名人”的同义词就成了“一种个性”。于是,娱乐圈的人便最有能力成为名人,因为他们十分擅长区分个性中的小小差异。他们把自己和一群本质上完全一样的人区分开来,并因此而成功。他依靠的是鬼脸、手势、语言和嗓音中的细枝末节。我们认出(“大鼻子”)吉米·杜兰特是靠他的鼻子,认出鲍勃·霍普是靠他的招牌微笑,认出杰克·本尼是靠他的吝啬。
名人是我们的投影
就如同我们时代的伪事件倾向于盖过真实事件的风头,名人紧跟潮流,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常常雇用媒体经纪人。而且,他们的数量要多得多。名人很快消亡,但更新速度更快。每年,我们眼前的名人都比前一年多。
就像真实事件常常被塞入伪事件的模板中,在我们的社会里,英雄要存活,就得发展出名人的特征。得到最好宣传的,似乎就是最真实的经验。如果有人在我们的时代成就了英雄的功绩,所有公共信息的机器——媒体、讲坛、广播、电视——就会迅速把他变成名人。如果他们做不到,那这位准英雄就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在图像革命后,名人的光彩盖过了英雄,这种现象背后的法则也为其他伪事件带来掩盖一切的光华。当一个人有了英雄和名人的样子,他作为名人的角色就模糊了他作为英雄的角色,并很容易破坏他的英雄身份。在创造名人时,总牵扯到人的利益——新闻人需要新闻,媒体经纪人受雇打造名人,而名人本身也获益。但死去的英雄不会关心热度所带来的利益,也无法雇用专员来保证自己停留在公众视野中。由于名人是量身打造的,可以用来取悦、安慰、迷倒并恭维我们,可以迅速制造、迅速替换。
人民曾经感觉自己是由他们的英雄造就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说:“偶像是信徒的尺度。”而名人是由人民制造的。英雄代表着外部榜样。名人是同义反复。我们还在试着让名人代替我们不再拥有的英雄、代替那些被推出我们视野的英雄。我们忘了,名人之所以出名,只是因为他们有名气。我们模仿他们,仿佛他们脱胎于伟大的模板。然而,名人不过是推广得更好的我们罢了。模仿他,模仿他的穿着、谈吐、外貌、思维,我们不过是在模仿自己罢了。
用赞美诗作者的话说:“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通过模仿一个同义反复,我们自己也成了同义反复;我们代表我们所代表的,努力更好地成为我们已经成了的。当我们称赞知名人士时,我们装作透过历史之窗观看他们。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看着的其实是镜子。我们找的是榜样,但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倒影。
我们揭秘名人(无论是通过新闻传记还是粗俗的“私密”杂志),证明他们不值得我们崇拜,这种种努力就像是讲述制造其他伪事件的“幕后故事”。自己拆自己的台让我们愈加对编造过程感兴趣。这种手段就像普通手段一样,能够创造同样的名人效应。
当然,大部分真正的名人都有媒体经纪人。这些经纪人本人有时也会成为名人。魔术师的帽子、兔子和他本人都是新闻。一个骗子大获成功,那他的新闻价值就翻倍了。他是个骗子,这让他更有个性。名人的私人新闻制造手段并不会让我们对他失望,而只会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名人并且完全能够胜任。我们就此放下心来,因为自己没有错将无名之辈奉为大人物。
今日在美国,英雄就像童话一样,受众已不是成熟的大人了。但我们翻倍制造奥斯卡和艾美奖帝后、给年度最佳老爸发奖、为美国小姐和闪光灯小姐戴上冠冕。我们刚开始不情不愿、而后又心醉神迷,看着每个奖项背后的政治运作,目睹每次为名人披上荣光或选出一日女王而动用的诡计。虽然我们都心怀好意,但制造英雄替代品的计谋最后只是造出了名人。
我们时代这些讽刺的失望之处,其中最挑动人心的是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对人类之伟大的过度期望所做的努力。在自然只允许一位英雄诞生之地,我们徒劳地栽培出几十个人造名人来。
在这个充满幻觉与准幻觉的生活中,身上可供崇拜的素质不仅限于其名气的人、拥有实实在在美德的人,总是不为人所知的英雄:老师,护士,母亲,好警察,干着孤独、低薪、没什么光彩、不为人知的工作的认真员工。但吊诡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还能是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不为人知。他们的美德不是我们努力填补自身空虚的产物。他们的默默无闻保护他们不被闪耀而短暂的名人生涯所害。唯独他们具有神秘的力量,来克制我们对超现实的伟大的狂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经典(ID:Thinkingdom),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图片: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