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法典有言:“如果有人来杀你,你就先杀了他。”这种采取一切措施甚至最极端手段来保护犹太人民的本能,深植于以色列的基因中。建国后,这更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和武装部队的责任。
以色列的多项武器技术是毫无争议的全球领先。还有一种用来对付最严重威胁的手段亦令世人侧目,那就是定点清除。全球追捕纳粹分子,解决频发的劫机事件,诛杀认定的恐怖分子,刺杀敌方的核物理和生化学家等危险人员……迄今以色列已针对大小敌人使用了无数次定点清除。

阿拉法特离开贝鲁特。这张照片是总参侦察营的一名狙击手拍摄的,并由梅纳赫姆·贝京转交给美国调解人菲利普·哈比卜,以证明只要以色列愿意就能杀掉阿拉法特(首次发表于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时)
定点清除需要跨部门协调、精密的策划和安排,行动人员也必须十八般武艺在身。即便如此,面对面的刺杀也会出现客观意外,亦可能因行动人员的瞬间迟疑而功亏一篑。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定点清除行动的执行者变成了无人机,操作人员可以像普通上班族一样走进写字楼,面无表情地按下按键,了结人命……
总之,这种以杀止杀的做法让以色列陷入了与各武装势力旷日持久的冤冤相报,人员伤亡越来越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始终剑拔弩张。
真的可以一杀了之吗?如果不使用定点清除,还有其他手段能够有效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吗?
《先发制人》作者伯格曼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数百次采访过历任国家领导人,以色列国防军、摩萨德、辛贝特、凯撒利亚等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还接触了无数一线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这些人的叙述,加上公开的档案、其他新闻报道和一线人员悄悄藏匿的总计数千份文件,作者深入了以色列最隐秘活动的核心,在书中再现了一次次重大定点杀戮行动的规划、实施过程,以及最终的成败得失。
今天,跟大家分享《先发制人》译者高礼杰撰写的译后记。
真的可以一杀了之吗?——定点清除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之问
如果阿拉法特没能在以色列一次次暗杀中奇迹般地安然脱身,巴以冲突能否走向另一种局面?
如果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公众、议员以及政府能够像阿米特一样看到稍纵即逝的和平窗口并积极推进和平谈判,此后占领区的诸多冲突摩擦是否根本就不会产生?
如果在80年代已经改持温和立场的法塔赫创始人之一阿布·吉哈德没有死于定点清除,一个更为稳定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会不会更有益于和平进程?

曼德拉和阿拉法特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像科学,可以把每一个“如果”视为在实验过程中可控的变量,通过重复实验,检验事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没办法再来一遍,自然也没有办法检验历史中的如果。
不过,历史虽没有如果,却不意味着对历史提出如果假设毫无意义。相反,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恰恰离不开不断设问,才能让历史叙事摆脱事件情节的堆砌,让作品不限于满足猎奇心的单一功能,而是以对事件的理解为纽带,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以色列记者、作家罗南·伯格曼所撰写的《先发制人》就是一部好的历史纪实著作。
在本书中,伯格曼不仅用大量翔实可信的访谈、文字资料,还原了以色列三大情报机构比文学影视作品更加诡谲奇异的定点清除行动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两个贯穿始终的“如果”设问隐藏在了事件陈述的背后。

摩萨德团队:拉菲·艾坦(右二)和茨维·阿哈罗尼(左二)在圣保罗,就在他们看到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之前不久(Zvi Aharoni收藏)
第一个问题关乎定点清除的必要性,它可以表述为:“如果不使用定点清除,还有其他手段能够有效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吗?”
早期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基本是确定的。伯格曼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以色列建国前便已经存在的秘密军事机构,在追捕纳粹分子、刺杀敌方危险人员等行动中体现出了“低成本、高收益”的特性,这使得大卫·本-古里安,沙米尔等人沉湎于“通过定点清除改变历史进程的诱惑”,认为通过定点清除能够有效地把犹太人在种族灭绝期间承受的恐惧,转嫁到以色列的敌人身上。
事实上,摩萨德、辛贝特、阿曼正是由以色列第一位总理,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被尊为以色列“国父”的大卫·本-古里安一力促成。对于定点清除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此时在以色列人中应不存在争议。

摩萨德指挥官约西·科恩(2016—2021)(左)和塔米尔·帕尔多(2011—2016)。他们俩都继续将定点清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二个问题关乎定点清除的合法性,它可以表述为:“如果在法庭上站不住脚,那么还要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作为定点清除行动执行者的特种部队成员及情报部门特工,他们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对这一假设同样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哪怕在废除了死刑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对敌方目标的惩罚不论从程序上看还是从实质上看都无法在法律上站住脚,哪怕本-古里安因此对于情报机构的行动内容三缄其口,但执行人员几乎都不会过分在意自己的行动缺乏法律授权。
在他们看来,定点清除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实在法,而是来自犹太法典:“如果有人来杀你,你就先杀了他”。
不论从共享信念来看,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两个假设在以色列建国之初都大致能获得肯定的回答。
这其实是由彼时的大环境决定的。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凌晨,第一次中东战争或者以色列所称的“护国战争”打响。以色列在军力处于弱势、武器装备全面落后的情况下,艰难获得胜利。但强敌仍然环伺,大屠杀阴影尚未远离,以色列人的处境俨然是霍布斯式的。
身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道出了这一代犹太人的共识:人最为重要的权利就是人权,而人权当中的第一人权就是“获得权利的权利”,即由国家背书的公民权。
因此,以色列的安全显然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家准则。而在这个国力羸弱,几乎没有外交和政治话语权的新生国家,暗杀基本成了唯一可行的手段。

名为“活寡妇”的做法是把携带武装的巴勒斯坦人拉到一块空地上,让躲藏起来的狙击手向他们开枪(Ronen Bergman)
用暗杀敌人来维护国家安全,这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是成本最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收益最高(使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的手段,由此获得了必要性。
与此同时,以色列如履薄冰的处境还为定点清除提供了一种道德论证:如果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摩萨德掌门人、传奇间谍梅厄·达甘的话就没有错——“采取暗杀行动比发动全面的战争要‘道德得多’”。
即便只从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算起,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大半个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境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为标志,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获得了战略优势,在经济、军事力量等各方面都超越了周遭的阿拉伯邻国。
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以色列人恐怕再也无法对上文的两个假设做出大体一致的回答了。定点清除具体行动中由各种意外及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国际丑闻和人道主义灾难,让已作为重要区域性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以色列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这也成为定点清除在这一时期所必须支付的额外成本。

“樱桃”在进行逮捕或杀掉通缉犯的演习(Uri Bar Lev供图)
另一方面,定点清除的大量使用,又使得目标的政治军事组织有所防备,其组织架构更为扁平化,人员替代性增强。其结果是定点清除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定点清除的必要性丧失了。
更大的危机源于合法性的缺失。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此事激起以色列民众“暴风骤雨般的反政府抗议”;8200部队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反法律原则的定点清除命令;拒绝在非法占领区为以色列占领军效力的空军预备役兵变……定点清除的合法性危机愈演愈烈。
与此前仅靠宗教诫命或道德直觉便能提供的定点清除行为动机不同,现在士兵和情报人员更倾向于执行被法律证成过的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法律顾问团的国际法部(ILD)不得不广泛地就一系列可能根本无法有答案的问题给出法律意见:什么样的人算“战斗人员”,什么样的人算平民?为恐怖分子做饭的厨师算不算“战斗人员”或“恐怖分子”?
如果“战争一开始,法律就沉默”,也就是说,如果战争可以降低行为所需的合法性标准,那么什么算战争?是以历次中东战争、大起义等为代表的大规模冲突,还是持续不断的游击活动、恐怖袭击?

“阿曼”指挥官尤里·萨吉(左)和总理伊扎克·沙米尔(Nati Herniki,政府新闻办)
虽然法务部门为了让定点清除具备合法性而总结、甚至“发明”了许多新概念和新原则,但总体上,定点清除的前置条件越来越多。合法性成为了定点清除的阻碍。
大环境的变化同样也决定了定点清除的当代命运。在巴勒斯坦大起义这般百万人自发的运动的背景下,企图用定点清除来威慑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难民,不啻于寄望以蜻蜓点水来抚平大海的怒涛。
巴勒斯坦大起义让以色列本土出生的伊扎克·拉宾走进了以色列权力中心,象征着和平在以色列人的价值排序中得到极大擢升。军旅出身、擅长以暴制暴的鹰派代表沙龙,在晚年时也向着和平进路靠拢。在处理空军预备役兵变事件时,他感觉到定点清除似乎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感觉到“一把火,已经在雪松林中燃烧起来”,这把火将会荡涤旧物,带来新貌,感觉到这把火将决定定点清除未来的命运。
对此,罗南·伯格曼在全书的结尾总结说,定点清除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在战术上取得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在战略上灾难性失败的以色列情报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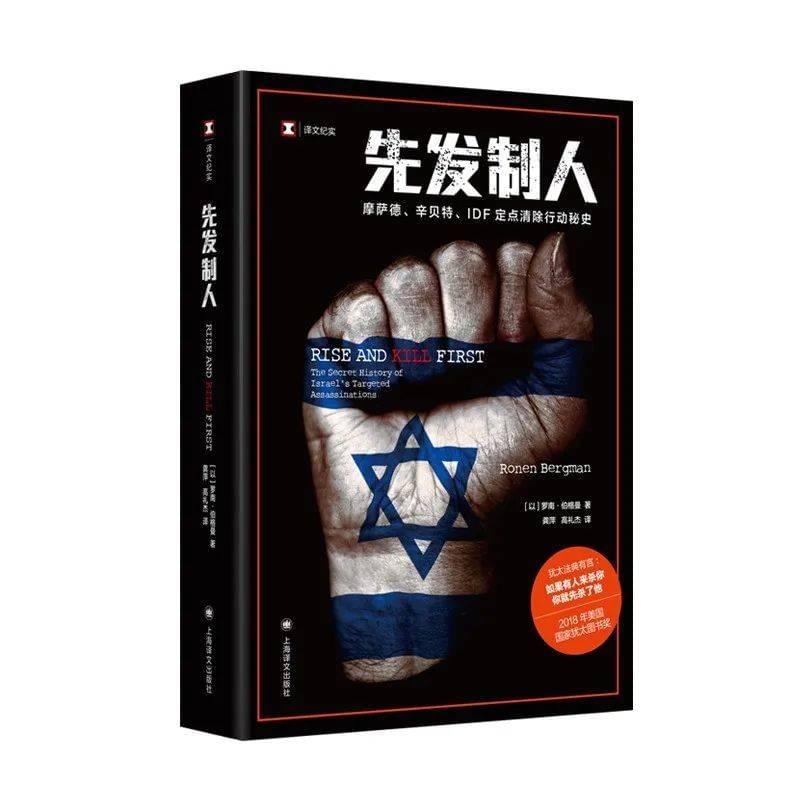
(以)罗南·伯格曼 著,龚萍 高礼杰 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ID:non-fiction702),作者:高礼杰(《先发制人》译者),内文图片来自:《先发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