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是凌晨1点,Vera看着电脑上未完成的project,叹了口气。
现在是凌晨1点,Vera看着电脑上未完成的project,叹了口气。她看了看窗外,灯火通明的曼哈顿倒映着自己额头熬夜的痘疤。中城公寓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下城,高楼大厦平地而起,密密麻麻的小方块里,有和Vera一样不眠不休的人。

室友已经睡了,Vera画完最后一张图,看着熄灭的屏幕,心想:
“来美国上学,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这座被金钱绑架的城市,或许只有在租金4000美金的高层公寓,才不会闻到流浪汉与大麻的臭气。

来到纽约后,Vera明白一个道理:这是一座雄雌双卷的城市。
每次Vera上课,总是穿着随意宽松的衣服、背着沉重的画板,再看看隔壁中国同学,总是背着一只LVMH包,最差也是YSL西装,就连装面料的袋子,都是印着自己名儿缩写的Dior手提袋。
老美同学则在花里胡哨的头发中,化着不重样的亚逼妆。
Vera不明白,在这个男女比例1比9、直男还寥寥无几的地方,似乎穿彩色衣服都犯法。大家的衣服要多黑有多黑,头发要多彩有多彩。

Vera唯一一件MiuMiu的水钻衬衣,也因某次上课沾上炭笔而彻底报废。她看了眼银行卡余额,发现已经买不起一双MiuMiu拖鞋,每月房租也耗尽了2/3的生活费。
她突然有点怀念国内,可以肆无忌惮地订外卖,骑着共享单车去南昌路小桌,在路边大声唱无人听懂的苏联小调。
不用在乎房租,不用在乎project和没做完的衣服,只在乎是否快乐。
上海的晚风那么温柔,梧桐瑟瑟,月光温柔地洒满年轻人的身体。可大洋彼岸的风终究吹不到纽约,林立的高楼大厦让人感觉整个曼哈顿是一座城市监狱。
凝土丛林中,人与人之间都戴着假面。

走在纽约的街上,站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身边每个女生都化着精致的淡妆,戴着浅色美瞳,有着口罩也挡不住的美貌,就连H-Mart里买菜的小姐姐都背着Chanel。
原来郭敬明的小时代,写的也不完全是假的。

Vera也曾下载过dating app。第一次见面,就遇到中英混杂、侃侃而谈的金融男,嘴上说在华尔街负责上亿的并购案,饭后却还要A饭钱,人均30美金。
也遇到过不善言辞的藤校理工男,刚拿到大厂offer,黑框眼镜里写满了自信,上来直接问”今晚你家我家”。
这座城市目的性太强,每个人都被一条叫“欲望”的线缠住,纽约的恋爱更像是一种商业模式,寻找的是满足某种需求的合作伙伴,而非爱情。

Vera的朋友告诉她,在纽约,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住址判断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住在皇后区的人,大多是岁月静好、享受田园生活的已婚女人;住在布鲁克林的,则是耐得住寂寞的、不追求时尚与精致的女生;住在曼岛的,要么是爱玩的年轻留学生,要么是有些家底已经工作的社会人。
“但最可怕的人,都住在新泽西。”朋友说。
Vera问:为什么?
为了便宜的房租,Vera还挺想搬去新泽西的,她笑了笑:纽约人真可怕,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衡量对方的性格了。

欲望大于拥有是常态,只是大部分人不愿承认罢了。而曼岛更像是一座囹圄,到处都是资本化城的粉色幻想。
Vera自诩是一个纯粹搞艺术、不是赚钱的人,艺术是无法被金钱衡量的,但在资本主义的洗脑下,Vera也有些动摇:
或许应该为生存妥协?或许应该把所学的东西变现?而不是创作出一堆所谓的废品?
台上的模特变换了新的姿势,Vera翻开了一页新的速写纸,拿着炭笔却神游起来:
她幻想自己是高原上的牧羊人,皮肤被晒得红肿刺痛。远处,她成群的羊如云朵一般散落在山坡。
呼啸的风声划过耳朵,世间一切与她无关,只有雪白的羊和碧蓝的天空。

即便如此,Vera也会想:这样的城市真的会有爱情吗?
她也会和某个在村里学CS的前任聊天,听他畅想未来进大厂当码农,说不上多喜欢,只是觉得是同一类人。
Vera对恋爱的理解很单纯,牵牵小手亲亲小嘴,就算是一对了。所以Vera的朋友圈也很简单:做点饭、画点画,和除了纽约以外的留学生大差不离。
只是,这样在纽约根本没有行情。
于是潜心研究小红书拍照姿势,并照葫芦画瓢发朋友圈。果然,消息列表多了很多小红点。
只是,这样得来的爱情未免过于快餐,始于欲望,止于厌倦。
渴望的越多,抓住的就越少,爱情如此,世界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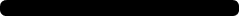
Vera看了看窗外,热闹的灯光映照着天生孤独的星星。
灯光固然美丽,又热闹又有人烟气,但灯火易灭,星光难移。

老罗说,所有的光芒,都需要时间才能被看到。
只是那个时间要多久,Vera自己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