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张医生与王医生》(由新经典·文汇出版社授权),原章节标题:《废墟与沈阳的去工业化》,作者:伊险峰、杨樱,配图:新经典·文汇出版社,题图来自:《钢的琴》剧照
少年昕仔,乘火车到大连,坐轮船,到上海,再上夜班火车,早上到了杭州。
出了火车站,左顾右盼,发现这崭新世界与他的经验世界之间有大不同:杭州火车站边上为什么没有卖轴承的?
昕仔当年 12 岁,心思细密,目光锐利,跟着他做采购的父亲走南闯北,江湖事已尽在掌握。其中一样秘而不宣:走在街上看到上上下下都是卖轴承的门市部,没错,到火车站了。以他在盘锦、大连、沈阳等火车站的经验看,这世界就该如此。

这次他跟着父亲从盘锦出发,计划为工厂买喷涂设备上的一个零件,似乎叫弹吐器。在沈阳没买到,辗转到了杭州,最后终于在杭州偏远的秋涛路上找到了。如何找零件不重要,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是已知世界的背叛。
那个早上,疑问萦绕于少年心头,纵使敏锐而缜密,也还是难以理解:杭州火车站怎么可能不卖轴承?
这城市,有意思。
那天中午,我们叫上李海鹏和昕仔在北京通州小潞邑吃羊蝎子火锅。昕仔,王昕,现在是九州梦圆文化有限公司的老板,还是一个野生民俗学家,这公司的名字听起来不大托底,但办的是正经咨询业务:为想评级的景区做评级咨询,比如说,如何包装一个 5A 级景区。
对于火车站周边要卖轴承,我们有共识,但是对于此中缘由,解释起来各有侧重。昕仔强调市场概念:“所有工业品都在东三省卖,这儿发达。跟杭州火车站边上卖纱巾是一个道理,那纱巾也未必都是他们那儿生产的。”海鹏强调物的流通:“车皮紧张,轴承是找车皮去了。轴承厂送货到那儿,他即使不是工厂的,是个二道贩子,也得在那儿弄个点。谁买轴承谁拿走。”我说可能还是人的流通,坐火车到东北大部分都是来买轴承的,谁到这儿旅游来啊,都是采购的,单位的采购员,采购科长什么的。
那天,从中午一直到西晒满满地灌进来,那锅羊蝎子咕嘟了五个小时,纵然加了几次水,也还是渐渐变得浓稠粘腻,有如火山熔岩。店里反复放着董宝石那首《野狼 Disco》,李海鹏对这首歌的走红心领神会毫不意外,对“老舅”和“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骨轴”传递的丰富信息有深刻感受,话题就此开始,从“东北文艺复兴”一直讲到东北的所有。
“你们学过没?有一个课本,讲家乡地理。讲辽宁和沈阳,那本书看完之后再看别的地方都没法看啊。就是工业总产值,重工业,城市化,啥啥都是辽宁第一,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就二十二个,辽宁占了四个。”
“对对,沈阳,大连,鞍山,抚顺。”
“当时没这感觉,铁西区都是大工厂,往哪边看都是大工厂,机械设备啊高炉啊,铁道啊。现在早没了。鞍山更多,就是规模小。”
“2001 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沈阳有什么玩的。那时候没感觉,想不起来有啥玩的。如果现在问,我会说去铁西区看看吧。那东西现在看能玩半个月。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场景了。”
01
铁西区怎么没了?
官方历史中,2002 年铁西区已经是“一潭死水”,其标志性事件是当时的大型国有企业沈阳拖拉机厂因企业严重亏损,外债高达十亿, 宣布破产。沈阳市政府提出“救活铁西”,于当年 6 月 18 日做出决定,将铁西区老工业基地与沈阳的国家级开发区——张士开发区合在一起, 进行合署办公,并得出一个结论:铁西区的唯一出路就是搬迁。此后两年,铁西区有一百三十多家大中型企业迁出。
铁西区是日本在沈阳规划的工业区,在 1949 年后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现在的铁西区很大,包括了一个甩在市区外面的巨大的开发区,过去的铁西区大部分已经改造成为新的住宅区、洗浴城、包括宜家在内的各种服务和商贸设施,还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以沈阳铸造厂旧厂房为基础建设的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它的前身是沈阳铸造博物馆,后来升级为整个铁西工业的象征。
现在在铁西感受不到它曾经作为机械制造业中心的样子。李海鹏说铁西能玩半个月的时候,已经是它消失十几年之后了。这种回答更接近于情怀,更接近于参观破坏水土环境的梯田、大坝,这情怀需要一点门槛。沈阳人为铁西整个工业的破产付出的代价,主要是一代或者两代产业工人的职业生涯和生计,由此诞生了“东北伤痕文学”或者“东北文艺复兴”,但在大多数沈阳人的感受里,铁西工业区的拆除并没有产生太多波澜。至于未来会否成为新的“伤痛”,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之所以如此,缘由很简单:人们对过去的人文景观采取的态度总是很势利。凯文 · 林奇在《此地何时:城市与变化的时代》中说:“如果过去很遥远,那么保护就是件好事;如果仅仅是昨天,那么就要当垃圾抛弃。”这可能是排在最前面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很粗暴:工业化本身就是丑的。看过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的人会有对铁西的直观感受,但如果细究起来,是纪录片中的人——出现在旧厂区里的人和偶尔笨重的、喷着蒸汽的机车车头共同组成了动静、新旧之间的冲突,它的破败与没有前景的产业工人一道共同完成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虽说喜欢北京七九八艺术园区的人也会对工厂旧厂房表现出热爱,但与其说是喜欢旧厂房,不如说是喜欢粗犷风格的建筑与艺术之间产生的奇妙的中和作用,而且前提显然是对艺术的热爱。

乔治 · 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说他“不相信工业化天生就不可避免地丑陋”,“这全部取决于那个时期的建筑传统。北方的工业城镇丑陋,是因为它们碰巧建于一个现代的钢铁建设和烟雾减排方法尚未发明的时代,一个人人都忙着赚钱无暇他顾的时代”——我们也同样不能指责铁西区和它过去辉煌的历代建设者还要负担起提供审美标的的职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污染、大烟囱、怪味、飘散于城市间的粉尘,是铁西为沈阳创造财富付出的成本。
张岐不希望他的大儿子张晓翔去学化学工业,是以他的经验看,在那种地方生活是要给生命打一个折扣的。奥威尔引用另一位反乌托邦作家阿道司· 赫胥黎的真知灼见:“一座黑暗的恶魔的工厂就该像一座黑暗的恶魔的工厂,而不是像神秘而辉煌的神庙。……喷着浓烟的烟囱和臭气熏天的贫民窟之所以可恶,主要是因为它暗示着扭曲的生活和多病的孩子。”
第三个原因重要但有一点隐晦:拆除一个庞大的铁西区有助于盘活主政者的资产。那些旧厂房、铸造厂也罢,拖拉机厂也罢,如果一百三十家工厂继续留在那里,就意味着:这些通常是全民所有的国有大厂继续奄奄一息地等待死亡,它那动辄上万的工人并没有什么重新上岗的机会和可能,自然意味着它不会产生新的价值;它值钱的那部分可能只剩下厂房和地皮。这些唯一值钱的东西掌握在工厂经营者手里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丁点价值,但如果把它置换出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于级别不高的区级政府来说,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狼狈不堪的庞然大物,现在可能是唯一的机会。通过卖地,把央企所有的地变为沈阳市有,这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当然,说是“救活”也可以, 只是它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再生。产业工人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机会。
工业主导型城市化的完成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产业工人的聚集, 第二步是产业遇到问题——它总是会遇到瓶颈和问题的——之后,如何转变为一个消费推动的城市。
公众可以把铁西区的转变当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下岗”。在“人”之外,在劳动力之外,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沈阳试图完成的是建筑、景观和城市记忆去工业化的过程。
02
“去工业化”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个审美品位的问题,这个审美品位与人性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建筑审美的变化与时尚变迁有关, 一个建筑在它的生命历史中有一段考验期,一般在三十年到五十年。
“建筑品味已经改变,最初的设计不再具有新鲜感的时候,提出拆除或大规模改建,最有可能受到重视。”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嬗变的大都市:关于城市的一些观念》里提到,美国很多有名的地标性建筑也没有逃过这个规律,费城火车站生存了五十四年,拉金大厦四十七年,马歇尔场商店四十三年,麦迪逊广场花园仅有二十五年——这些都是知名设计师的代表性产品。
之所以说与人性有关系,是因为如果过了这段严酷的考验期,人们就会再度认可这些建筑具有的美感,对它产生热爱,并保护它。
凯文 · 林奇也在《此地何时》中说,伦敦的大多数建筑,除少数被认定“有历史意义”的以外,“平均过三十年会进行一次修复,六十年后就废弃不用了”。
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是“有历史意义”。二〇四的赫鲁晓夫楼和铁西大量的工厂,理论上大都毁在它们的审美疲劳期,而现在试图保留它们的人们,会不断强化它“历史意义”的那一面。
不过即便不考虑历史意义这个层面,相对于三十年到五十年的考验期来说,沈阳的许多建筑也过于年轻了。比较多被说起的是沈阳“金廊”沿线的五里河体育场、夏宫和辽宁体育馆。金廊是沈阳市政府推出的从桃仙机场到青年大街到长江街到北陵的一条南北中轴线,集聚了大量建筑景观,辅以金光闪闪的照明,白天黑夜都展现出现代都市忙碌富足的样子。
那三个建筑中,沈阳人最常去的是夏宫,据说是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夏宫是个水上游乐中心,后来不知为什么就经营不善了,土地收回,盖了高楼。五里河体育场时常为球迷所记挂,辽宁队 1990 年获得亚俱杯冠军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体育场,当时场外还搭着脚手架,现代派看了会觉得这是蓬皮杜风格,实际上就是没盖完, 来不及了。
那场比赛辽宁队夺冠,现场扔彩带扔得太起劲,造成电线短路,直播到一半就看不见了。五里河体育场出名是因为中国队在这里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大家认为其历史意义多半也在此。它在2007年被拆除,存在时间不超过十九年,给人的感觉像刚刚竣工就拆掉了。
三十年到五十年?沈阳人等不及。沈阳在拆房子这一点上,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这无关审美,如果善意揣测,主要还是让政府手里有一点钱。
去工业化,虽然于很多城市来说都是必经之路,但去工业化的核心可不是把工厂拆掉了事,干掉人们曾经工作的场所很简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才是目的。
沈阳市有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90 年代末期的下岗职工高达一百万,满足这些人的工作需求,是一件艰难的、基本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工业化在沈阳是个迫不得已的结果,计划经济的终结、国营制度的弊端、传统制造业的衰退与转型,三者结合在一起,直接结果是工人与管理者的素质和技能都不够支撑职业尊严和城市尊严。
沈阳的去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整体财富下行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让城市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里,艰难;实现宜居目标,更难。
2008 年,沈阳铁西区声称获得了一个“联合国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这到底是真是假,还是一个谜。
有人说这就是“联合国人居奖”,但似乎并没有人去查证,除了几个媒体发了通稿,联合国的官网和住建部的官网上都没有——至少“联合国人居奖”的名单在住建部官方网站是能查得到的,而那一年并没有看到铁西区。
很多国家部委都会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联合开发一些奖励,听起来名头甚大,很讨政府或者企业之类的喜欢。“联合国人居奖”诞生于 1989 年,从诞生第二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中国城市或者个人上榜得奖。有两年正是东北下岗最厉害,也是这些城市最不宜居的时候,我猜不出究竟是以什么标准让他们获得如此荣耀。
“宜居”这个词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打造宜居城市”—— 我们看到的所有与它相关的,不管是广告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宣言,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而城市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持续不断地生产出大量的中产阶级,让这个城市在去工业化的道路上产生更多的服务业、更多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服务对象产生更多的需求、制造更多的服务业岗位,这是一个想起来就美滋滋的循环。
铁西区的 2008 年不是一个为“宜居”盖棺论定的好时候。那时节,去工业化肯定完成了,老铁西区腾得已经差不多,地也基本上卖完了,城市进入疯狂盖房子的阶段。如果把目光从铁西移开,全沈阳和全中国也大都是如此。但是,在沈阳,对于传统产业工人来说,没有新的就业机会。
03
一个转型后的新城市,是由消费而不是生产来决定的——生产出足够的消费者,诞生足够多的消费,从而运转起来。听起来没错,工业革命之后相当多的城市转型是以这个路径完成的。
造就一个消费城市,是中产阶级化的根本。产业工人是可牺牲的, 或者说是某一个阶段的阵痛——对于工人阶级本身来说当然不是阵痛, 而是阵亡。但城市则期待着一个中产阶级现代服务业的崛起。
这其中当然有不可见的那部分人的失落。尼尔 · 史密斯是左派的城市研究者。他在《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中说:“士绅化及士绅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重建改造,是晚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系统事件。就像资本主义努力用时间消灭空间一样,士绅化也越来越努力地制造出差异化的空间以作为自身生存的手段。”“打造宜居城市,”他说,“是中产阶级的宜居。”
事实上,并且也是必须的,城市对工人阶级始终也是“宜居” 的。所谓的复兴能够给各阶级人民造福,不过是广告和销售的噱头,因为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年度住房调查结果显示,每年约有 50 万个美国家庭无家可归,这可能造成多达 200 万人流离失所。这些家庭中,86% 是因为自由市场活动导致流离失所,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工人阶级。
每一个中国市长头脑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士绅化的范本,上海的新天地是最合适的那一个:有一个可以持续带来游客的旅游纪念地,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吸引力;本地风格——民国或者清朝风貌的老建筑;大型的商业设施。本地的原住民要被置换出去,反正他们已经厌倦了逼仄的居住环境,在郊区为他们建大房子;开发商拿出一半的空间来做古董街,拿另一半不那么重要的盖高楼;如果魄力够大,再加上足够大的休闲区,成就新景观。招商,传说中的“ABC”是要有的,但要更丰富一点,接地气一点,电影院和餐饮必不可少,本地的年轻人要来,这是关键。
“ABC”指的是艺术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és),全世界都把这视为成功士绅化的核心面貌。(注:莎伦 · 佐金《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

市长们在拆的时候已经勾画好了这样的蓝图,如果实现,就业机会自然也随之而来。
这里往往会变成一个死结,跟铁西区那个死结一样:有着象征意义的厂房这么多,但是有多少个七九八可以装在里面?一个城市,体量远远没有上海那么大,中央商务区也不像上海那么分散,它能创造出几个新天地?
但这并不妨碍每个城市的每个地块的拆迁都把新天地当成目标。到最后,关于城市,要探讨的并不是什么审美或者文化积累的问题, 而是“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招商——吸引地产开发商”的问题。只要能吸引,就要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最快速的吸引资金的办法是卖地。市长们困惑的往往是:这地方能拆吗?能拆,那就拆;不能拆,那是不是可以绕开文物部门的规定呢?修旧如旧呢?异地修旧如旧呢?
从卖地的角度看,问题倒是简单:只有进入市场,它才有价值。这是一个必须要拆的问题。每个开发商都像一根救命稻草,都要抓牢, 只要能说会道,就会得到自己的机会。拆完之后往往听天由命,受制于开发商。没有足够的后续资金,拆一半撂在那里,盖一半撂在那里,盖好了招商一半撂在那里,经营几年没有前景无以为继之后荒一半撂在那里。
所以,在沈阳你会看到最成熟的中街商业区,巴洛克风格的东风商店为了给嘉阳广场这个购物中心让路,拆掉了,嘉阳广场后来牵扯进黑社会的官司,转手给了香港地产商恒隆,现在被命名为“皇城恒隆”,生意堪忧;曾经以银座为模版的另一个商业区太原街——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它以“春日町”为名的时候就已经是商业中心了,现在被几个大型购物中心切割,原始的业态消耗殆尽。
当大型购物中心发展不利的时候,沈阳人发现已经没有什么能支撑起一条商业街的活力,继而又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去太原街了;曾经最有特色的东北电影院,在街区改造中拆掉了,被赶到附近大商场的十楼,据说现代化了很多, 但那个独具风格的电影院也就不见了——在沈阳,从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到 80年代有大量电影院,风格各异,如今大部分都已经不见。
与其他城市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沈阳大拆十几年之后,因为那个死结,那个恶性循环,没有后续的资本去让这个城市建设新的高楼大厦,所以到处都是空地,在市中心,老城区……我们会指着这些空地说,这里以前是亚洲电影院,这里是天光,这里是群众,这里是新闻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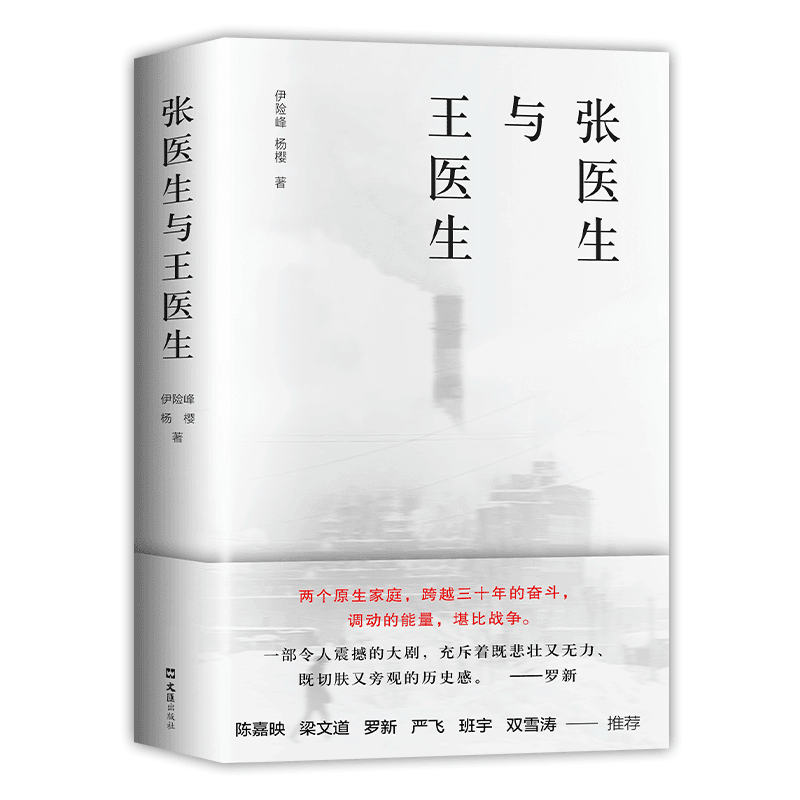
著者:伊险峰 杨樱
出品: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0
定价:68.00
本文摘自《张医生与王医生》(由新经典·文汇出版社授权),作者:伊险峰、杨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