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跳海大院(ID:meerjump),作者:院办gonegirl,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以下内容为作者真实经历)
我上初中的时候,成了“杀人犯”。
还是身上背负着“五条人命”的那种。
这突如其来的人设,是由一位“黄仙”赋予的。
而在之后的数年中,我的人生宛如都市仙侠小说,只不过人设一换再换,从前世将军,神兵天降,出逃仙女,到草木之人,痴傻呆嗫。
你的人生你做主,我的人生则都是被“大仙儿”们轮流做主的。

1
我生长在东北。从出生便被一位算命先生由“生辰八字”断定,此生归宿不是神仙就是恶魔。这句预言在我14岁时,出现了征兆。
为了规避令我头痛的考试,我逃了学。我妈得知情况后,火速通过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三姨约了一位“大仙”,课也不用上了,直接送到“大仙”工作室。
这很寻常,我当时同桌也供奉保家仙,没事就伸出左手“掐一掐”,算上一卦,能知道今天数学老师抽不抽查作业。在东北,谁还不认识一个半个仙家?科学上来讲,此地多山林旷野,野生动物多而杂。不科学一点儿,这些动物都想修仙,身处汇集天地精华之地,还都能修成功了。
林林种种的动物仙出没,狐狸,黄鼠狼,蛇即使修炼成仙,没个万年修为也难过物种进化论,想和凡人沟通必须配备“翻译通”(人肉版),一种叫第马的职业从而产生。他们心甘情愿接受神仙附体,立堂口,治病了事,普渡人类。
我的三姨的第三个女儿的三舅妈,真有这么绕,是“黄仙”的第马。也就是出马弟子。“黄仙”在山海关以北,最为常见,走街串巷的黄鼠狼仙家怪谈,至今仍能在网上搜到一箩筐的目击证人。

14岁的我对看大仙这事有点抵触,但猎好奇心作祟,我还是在市中心一家不起眼的三星级酒店会见了黄仙。黄仙的堂口是楼里的一单间。
本以为会看见黄鼠狼立地幻化成人,仙术满屋乱撞,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只有一个中年阿姨端坐在厅堂里, 还没等我坐稳,她开门见山,问我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梦。我琢磨着,确实有,梦里外面的银行大楼塌了。
阿姨听后,面露狂喜,就差给我跪下,她说,年末了,等了一年的人终于还是来了。随后手脚麻利的从抽屉里掏出一包老汉烟,点上,猛烈入肺。
怪事,抽上烟的阿姨,不再是阿姨了。她清清嗓子,声音低沉,像男性。又好似从未见过我一样,阴狠狠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目瞪口呆的我,别怪,谁见到原地性转不目瞪口呆呢?
没等我反应过来,身上“附”了黄仙的阿姨便一个箭步,窜到身后,伸出手抓了抓我的脑袋,在头顶摸了半天。

“恁这天眼半开,恁不凡呐!”阿姨不仅声线变了,连腔调,都直接从哈尔滨市下调成了郊县口音,“我看你半天,你没什么毛病,就是跟俺一样,天外面来的。”
“来,恁跟我对话!恁一定能听懂俺在说什么!”
黄仙回到桌前端坐,张口就来一串嘀哩咕噜嘀哩咕噜乌鲁巴土,我没法接招,听得云里雾里。她还在不停“乌鲁乌鲁”个没完,用满眼阴鸷催促着我。我实在害怕,急中生智,要不就——“咕噜咕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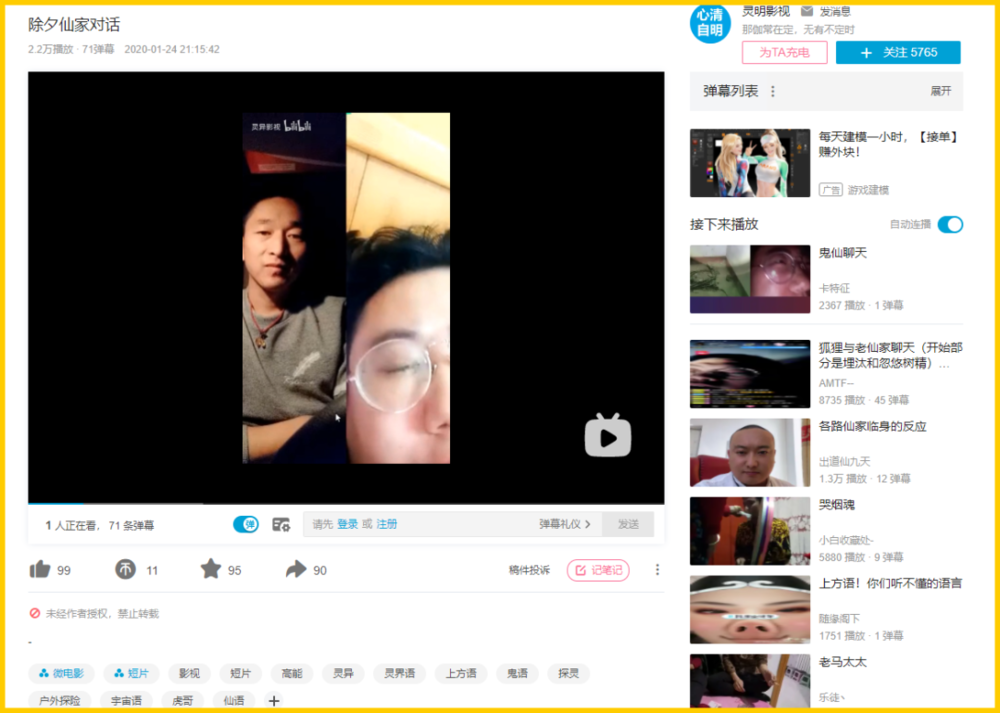
“恁不会?.....无妨,这是宇宙语,恁离以前的生活相去甚远,不怪恁。”黄仙直接拆了我的台,继续自说自话,“宇宙语是天上使用的语言,恁也是神兵天降.......咋能忘了!”
我想笑却得憋,没到十分钟,已经是天外来客了,这变化有点过快,要消化。黄仙并不想给我这个时间,急于坐实身份,又忙从抽屉里掏出一沓黄纸,用黑色0.5中性笔画了三道符,写了一串波浪号。“恁给我说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摊牌了,这题超纲。
黄仙眼看求证无果,只好悻悻收掉桌上摆设,闭了会眼,掌心合十,嘟囔了几句咒,没过多久,又是我三姨的第三个女儿的三舅妈来了。她把我的妈妈从门外叫了进来,放我逃离了算命第一线。
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
年后,我妈花了不少钱,请来了寺庙里的和尚,做法事。用黄仙的说法,我虽然是天眼半开,但前世中杀人无数,现在被一家五口的冤魂,连老带少撞上了,才会出现叛逆厌学等反常情况,必须请他们吃饭,办个焰口法事,好好商议这命债如何抵。清晨五点,我被摁在寺庙大殿上磕头,满地散的都是白花花的碎馒头,和尚木鱼敲的咚咚响。
这还没完。法事过后没多久,我和妈妈,赶赴了五台山。据说,我要面朝东西南北各磕500个头,每磕一个,还得念一遍往生咒,这是黄仙和冤魂们良好沟通后换来的究极解法。
于是,一场大雪过后,天蒙亮,我被连根拔起,完全清醒过来,人已经在爬往黛螺顶的石阶上了。最后到了山顶小庙,看到佛前的软垫,我腿一软“扑通”就跪了。

“磕吧。”我妈掏出一本往生咒,塞我手里,”磕一遍念一遍。“
“南 无 阿 弥 多 婆 夜, 哆 他 伽 多 夜”我刚弯下第一个腰,就觉得难顶了,羽绒服太厚。我妈心急火燎地问:“感没感受到气场,他们都说念往生咒的时候,你每生每世的冤亲债主,都得闻着信来听呢......”
我懒得搭理她跟我讲故事,只觉得今天这劫是必须得过了。磕完东边的200多个,刚想起来歇歇,眼睛已经花的看不清东西了,一想,还有1800个等着我呢,怎么着,要不装晕吧。
我妈识破,提议一起磕,我连忙拒绝,又扑通跪下了。磕到意识涣散的时候,我开始在脑内写故事,入定。仿佛真看到了那一家五口,拿着砍刀,跟我说,“你不还这债,你就别想吃饭了!”。
从早上7点到晚点6点,庙里只有我和我妈两个香客,无人打扰。我不管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地狱还是天堂,总之那天的黛螺顶绝对是磕头地狱没跑了。
管他债抵不抵,我也是明白透透的,这2000个头磕完回去,逃学,不能再发生了。
2
厌学被磕头化解,可天灵盖还开着呢。
我家里心心念念全想着这事。我自五台山归来,决不逃课,但在课上学会了看小说,尤其是仙侠的。家里无奈,眼看中考要来,这可是命运转折点,补课和看大仙还得同时进行。我在短短一个月,就见了各种居士,和尚,得道高人,数学老师,化学老师,物理大讲师,以及那位黄仙。家里只求考好,从此以后,就当凡人,不能瞎琢磨,好好学习,走上正途。
关于开着的天灵盖,我又被领去了黄仙的堂口。这回效率挺快,刚一坐定,我的后脑勺被喷了一大口白酒,那些唾液酒精的混合物,均匀的被抹平了。
“给你糊上了。”黄仙说,全程不超过30秒。
我很想马上洗头,脑壳上还有洞也不怕。糊没糊上不重要,当人还是神仙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是诈骗,侮辱智商的诈骗。我的家人跟atm机也没什么区别了。
只能考好,务必考好。我以差不离的分数上了重点中学,家人都欢喜,但,我也明白,这是把双刃剑,我只要再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看大仙是永远不会停的。
可,真正面对选择的时候,还是得听自己的,即使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十六七岁,对未来想入非非,自己是谁。也太多种可能。我看了太多姜文,决定以后当个导演,文化课什么就别弄了,还是要整艺术,我妈得知,立马跳出来,喊停停停,别。
没什么沟通的机会,我就被送去了见下一个大仙,这“大仙”不是什么动物变的,也没什么堂口,是个住在坟山的老和尚。夏天,我被送到了坟山上,清修。吃斋,念佛,种菜,耕地,看坟,想明前路。

家里的理解是这样的,仙家救不了你,你还一意孤行,不走康庄大道,那就只有佛门渡了。之前看大仙,还能硬着头皮走个流程,没成想,来坟山上和孤魂野鬼作伴了,年纪轻轻,搁谁谁不怕呢,到此,我恨不得跟家里决裂,比起这些,我宁愿被送去让杨永信电个痛快。
幸好,老和尚虽然看着面露凶煞,脸乌黑乌黑的,但好在人还不错,没对我做什么法。
在山上时,他只是带着我在种种菜,学习农业常识,没事给无人看管的荒坟烧个纸,抚慰孤魂野鬼。庙里有尊大佛,但老和尚化缘还没成功,大殿连房顶都没有。他对我也和善,起码把破庙里仅有的风扇和凉席给了我。
一日,师徒二人坐在老和尚办公室吃饺子,老和尚开口: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像凡人。”
又来,我看着他一个和尚,吃素馅饺子还得就大蒜,算什么谨遵戒律的皈依弟子,果然也是个老骗子,我克制了下反感情绪,想套套话,忙问:”为啥?“

老和尚让我烧壶热水,泡点廉价茶叶喝喝,说道,”你聪明,看事情有眼力,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热水咕噜咕噜烧开,我想哭,但觉得丢脸。我去取水壶,背过身,眼泪流了满脸。
茶泡好,老和尚不知从哪翻出了一个佛像挂坠,递给我,让我当护身符,“男配菩萨,女配佛......”
“收钱不?”我时刻保持清醒,不能因一言两语就破防。
“不收,你就是以后发达了,还得记得师傅,给俺这庙,换个冬天保温房顶。“

没过几天,老和尚就让我回家了。他本就是个穷和尚,我在山上差点吃光他所有余粮,他打了个滴滴,顺路送我去高铁站,还得赶着去村里去瞅瞅坟地风水。气氛挺忧伤,下了大暴雨,老和尚送我到了入站口,隔着栅栏,他举着雨伞,冲我喊:“平安平安,平安就好,但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闯啊!”
我想着,估计这庙的房顶一时半会可能是从我这化不到了,但,我自由了。
3
几年后,我休学去了北京务工。没能考上理想的学校,和家里也闹得不怎么愉快,我找了北京一家公司,没事写写稿,闲下来就和大把朋友聊创作,拍东西,算是自己闯了路。
眼瞅过年,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让我马上赶到秦皇岛山海关,要不她就要一命呜呼了。
年末的家中不能接,我很懂,可是这一通电话,彻底让我乱了节奏。14岁的我,不知道怎么不去害怕那杀人偿命“万一”,但,事关老妈性命,“万一”是马克思解决不了的。
即使有99.9999999%的可能妈还在,但是就怕00.000000001%。
我跳上了春运列车,挤在火车过道间,去救我妈。
结果到了才知道,要呜呼的不是我妈,是我。家里人又不知道从何处认识了一名精通万事万物的“大仙儿”,通过寻脉掐指,算出了我魂魄不知何时被换到了阴曹地府,得做一个换魂的法事,才能真正成为“草木之人”而后三年”有血有肉“,如若这个法事不做,年关一过,我就会丧命。

都市仙侠小说可以这么写,但是我的命不行。
我能自己赚钱,有了自己刚刚闯出一点名堂的新生活,而且我已经年满18岁,再也不能任人,任”大仙“摆布。在我眼里,自己的命绝与否,不存在那0.0000001%。
可是在我妈妈那,救女儿,即使就是0.000000001%,再荒谬,也得信。我再三表示,要赶回去工作,看新年里好多好多的live,我妈并不管什么live,她只关心女儿能不能一直live。我听后笑了,想不通,我妈都懂洋文,眼界也够开阔,怎么就不能从封建迷信的裂缝里稍微,往外稍一稍呢。
“可是我不能让我女儿没命。”我妈哭了。
我也哭了,我哭着被摁在新的堂口里,食指扎针,入血化药,混着白酒喝下,这便是换魂药了。仙家还从我被糊死的天灵盖上揪了三根头发,掺了鸡血,包成红符, 这是要随身佩戴的护身符,以防在换魂百天内,被脏东西侵害身体。

法事做的昏天黑地,忙活了一整晚,我回到了北京,躺在我租的10平米小屋里,望着天花板,我从不害怕神还是鬼,我只觉得自己的命从来不在手里,从来没有过。
年后,正是春天,公司发生一些变动,我主动离开,买了张车票,回到老家,复学,更多的时候是躺在床上,流眼泪,流眼泪。
在妈妈眼里,我是换魂之后,正常的躯体反应,一切都可以从仙家那讨来说法。可是我心里,只想着在北京能看到的乐队,和同事们在一起聊过的天,还有那些还未成型的创作,奇奇怪怪有待完成的想法。
我也觉得自己有毛病,身上浑身都是病,我时常怕死怕到不敢睡觉,又想一死了之。这一切都贴和了仙家的描述,像是一场精准预言。无奈之下,妈妈带我去了好几次仙家法会,我这次似乎是心甘情愿喝了符化水,吞生鸡蛋预防病毒,以及很多第马的口水,是的,在他们的说辞中,只有被第马用白酒喷过的食物,才能称之为仙人度过的食物。我甚至一度陷入秃顶危机,护身符每隔几个月就得换一次,每一次都要拔三根头发......
我不是不怀疑,只是没力气怀疑。没什么比丧失了主动权,再也不想争取,更令人难过。我的归宿不是神仙就是恶魔,你们这些跪在地上求仙问药的人,也早就走火入魔了。
是的,你肯定不会猜错。我的痛苦完全没得到任何缓解。几个月之后,我仍在恐慌,流泪,怕死,想死,直到我摔在雪地里失去意识,送去医院,又转入精神科,病历上写——抑郁焦虑。
我妈依然焦急地向大仙求救,但这下仙家居然也没辙了,说我三年后才能完全康复,并建议我赶紧去住院,去北京,住精神专科医院。
4
我在半开放的病房里呆了将近两个月,就被医生确定情况稳定,放了出来。期间,和病友打成一片,在精神病院里玩出了不少名堂,画画,捏陶土,写东西,还结交到了院办碳酸狗此等挚友......
“你就是你自己,我信任你。”我的心理咨询师在诊疗过程中,这么来了一句,“你的妈妈好像更相信你被附身,撞邪,也不愿意相信你是你?”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同一病区的病友表示妈比妈,她妈更离谱,已婚的她,因生病被家中请的大师算出“中邪”,需要和他打炮才能化解。她妈不禁一次鼓动病友,“睡一觉就能解决的事,吃这么多药干嘛呢?”
“有时候,我真觉得我在这住院,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是正常人,而我是他们中唯一的正常人,你说对吧,小陆。”
5
那位仙家说的第三年,正是今年。我大学眼瞅着毕业,也和家人好好道了别,来到南方。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给人家背书。
是的,把树苗扔地里,我也能指着树苗说,他三年之后,会长出来,但是枣子树还是苹果树,可不太好说。长达十几年的算命生涯,我接受了太多因果逻辑,似乎在那套逻辑里,只要有因有果,甭管是否是恰当,合适,妥贴的,安在我身上,它就是成立的。

《叫魂》那书里讲过一段,农庄闹了蝗虫灾,他们造了个蝗娘娘出来,祈祷风调雨顺,结果有了杀虫剂,蝗娘娘退役了。
在无路可走,没有办法承认的巨大失败面前,将信念寄托在形象高大的事物上,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不知道我妈妈的蝗娘娘什么时候能退役,我只知道,在整个漫长的青春期,我和她一次又一次沟通解决问题的大好机会,碍于“蝗娘娘”的存在,再也抓不到了。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我到底是天外来客还是杀人魔头的虚无,只是一种更扭曲的诅咒,叫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跳海大院(ID:meerjump),作者:院办gonegi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