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将被终身监禁在自我的地牢中。
——西里尔·康诺利(《不平静的坟墓》,1995年)
想象下面的场景: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一辆公共汽车来了,却没有停下。开始,我只是因累有些辛苦,但当公共汽车快速驶过甚至没有减速时,我感到一种无助感。我想,“他(司机)故意不搭理我”,我感到很生气。不过,随后我就注意到公交车是满员的,然后我的怒火平息了。引发我愤怒反应的关键是我把司机的行为理解为故意忽视。实际的疲累感和我假定的冒犯行为相比不值一提。一旦我重新思考这个情况后,“冒犯感”就烟消云散了,而我只会认为这个事只是有些不便而已。然后,我会关注去确定下一班公共汽车何时到或是考虑其他到达我的目的地的方式。
延误和沮丧本身不一定会导致愤怒。真正的导火索是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解释,以及这个解释能否让我们接受该行为。如果不能,我们就会恼羞成怒并且想责罚对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将冒犯我们的行为视为故意而非偶然的、恶毒而非善意的举动。不方便和沮丧感来去匆匆,可蒙冤之感会经久不散。
一、是批评还是冒犯?
我们与他人的交往都遵循着一套行为规则和标准,这套范式让我们得以以一种相对顺畅和谐的方式交流。社会压力会促使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尽可能公平、合理和公正。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冒犯他人。如果自尊受到伤害,我们就会动用相关的规则来对事情做出判断。如果我们认为肇事者武断专横、蛮不讲理或不公正,我们就会认为对方不对或不好,然后会感到愤怒。自尊心低的人会试图以一堆错综复杂的规则来保护自己,但恰恰是这些规则注定了会被触犯而导致更多苦恼。人们的敏感度和过敏反应各自不同,某人眼中无法接受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人眼中是完全允许的。
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批评而变得如此烦恼,即使批评是想要帮助我们的也会忠言逆耳?我们应该如何区分那些意图让我们做得更好的有效纠正反馈和那些故意贬低的批评指责?
很多人对建设性批评的反应就好像是受到人身攻击一样。显而易见,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可能包含贬低的成分,有时能反映出批评者(父母、老师、上级)的失望。此外,即使纠正或批评是客观的(例如,可能是在试卷中圈出错误答案),也会影响我们的自尊心(“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或者“她不看好我”)。而当我们的自尊受到伤害时,我们会倾向于得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评判,而后可能会变得愤怒以维护我们的自尊。
先天因素与生活经验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反应,让我们倾向于将他人的评论过度解释为对我们的羞辱贬低,这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我们会困惑:“她是想帮我呢,还是向我炫耀她的聪明呢?”或者,“他是在暗示我很蠢吗?”。抑郁的人则经常将不公正的批评当成是合理正确的,这是因为这些评判与他们对自身的负面评价是一致的,因而不公正的评判就变成合理的了。
二、自尊:自身价值评价的量化表
一个人的自尊代表了他在特定时期对自己的重视程度——“我有多喜欢自己”。我们的自尊是一个压力表,它可以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实现我们的个人目标,并成功地应对他人的要求和制约,它会自动量化我们每时每刻对自身价值的评价。
个人的整体自我评价——或者更为重要的是,自我评价或自尊的改变——通常能触发人的情绪反应:快乐或痛苦,愤怒或焦虑。人们会根据他们当前认为的自己的样子和自己“应该”的样子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评价自己的价值。抑郁症患者通常会认为“现在的我”和“应该的我”有着巨大差距,所以他们经常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而易怒的人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别人更多的价值推崇。
事件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会因所涉及的人格特质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对我们“重要”的人格特质的贬低显然要比贬低一项次要特质对我们的自尊造成的影响更大,造成的伤害和愤怒也会更多。如果负性事件(例如拒绝或失败)的影响很大,我们的自我评价可能会变得更加绝对化和确定(例如我们太软弱、不可爱、没有用),我们的自尊心会随之坠入低谷。
当然,我们也及时掌握了一些通过淡化事件重要性来缓和诸多负性事件影响的技巧:正确地看待它们,寻找“保住面子”的解释,让批评无效,或者贬低那些轻视我们的人。类似地,自我激励事件能激发我们的积极自我意象,从而提高自尊心水平和带来积极预期,这又会反过来鼓励我们参加更多扩展活动。
我们的自尊不仅受到个人经历影响,还受到我们内在社交圈(家人和朋友)振奋或受冲击的士气影响。当喜欢的球队或政治党派获胜或失败时,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一种类似于“集体自尊”随之起伏的现象。人们对自己国家战争胜利或失败的反应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一群体(胜者或败者)中的个人在自尊方面经历着类似的波动,但其自尊变化的程度则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他对这个群体及其愿景的认同程度。
我们以前的评价或与他人比较造成的自尊变化特别能影响我们的情绪。例如,特德因为加薪感觉很好,但当他听说他的朋友埃文也加薪后就感觉不好了。虽然他与埃文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但他觉得很沮丧。对特德来说,埃文的加薪意味着:“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被看重。如果老板也给埃文加薪,就说明他并不认为我有什么特别。”
在特德的心中,他之前所有的成功都付之东流了,他整体自尊的跌落就反映了这一点。自尊与我们对他人评价的关系就像一个跷跷板。我们对别人的价值评价升高,我们自己的价值感就会下降。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认同他人的好运,我们的自尊心就会增强,也会因此感觉良好。
在利兹的案例中,利兹惹恼了别人,因为无论话题是什么,她都会把话题变成她自己的经历和观点的独白。有一次,她最好的朋友告诉她,很多人都不喜欢她,因为她只谈论自己。利兹被告知的这种负面社会形象让她感到很糟糕,她想:“我已经被这个圈子抛弃了。”她的自尊开始降低。她的第二反应是对自己“不被欣赏”愤怒。
不过,在她痛苦过后,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可改正的行为表现结果,而不是攻击性的、无可救药的人格缺陷。她下决心与他人交谈时减少自我中心的言论。因此,这件事以及引起的自尊受挫结果让利兹经历了一次有效的学习成长。如果利兹只是生气,把朋友想象成敌人伺机报复,她的自尊虽然可能会暂时有所改善,但她将会失去将不愉快经历转化为建设性学习经历的机会。
人们在受到排挤或指责而产生的如利兹体验到的心理痛苦或烦恼和物理攻击造成的身体疼痛一样有着类似的功能。而身体疼痛能调动人们通过自我矫正去解决问题,而且能作为一种学习经验用于应对未来类似的情况。
同样,推定的被贬低所造成的心理痛苦也会刺激人们去直面应对问题。人们在暴怒下可能会攻击导致痛苦的源头,也就是他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尝试澄清对方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心理上的痛苦通常是由个人内心投射的社会形象,即假定的他人对他的看法的贬低而引起的。虽然攻击他人可能会让投射形象有所改善、让自尊心有所恢复,但这却不一定能解决他的人际关系问题。
假设一位妻子认为丈夫骗她做了她不愿意做的事情。她一开始先是自尊水平急挫,随即就会痛苦。她会认为自己无能、脆弱。当她注意到丈夫的不当行为时,她开始变得愤怒并想要对丈夫做出反抗。情况的发生顺序可能是这样的。她想到,“他利用了我。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看起来简直像个白痴”。她感到痛苦,然后是愤怒。她下定决心,“我必须要惩罚他”。她投射出的自我形象——“看起来简直像个白痴”——降低了她的个人尊严并制造了痛苦。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妻子认为丈夫做得不对,并且形成丈夫的负面形象时,她才会感到愤怒。
对丈夫的还击可以抵消对她投射的社会意象和自尊的伤害,可以暂时减轻痛苦。这种反击可能对她与丈夫之间的权力均衡起平衡作用(例如,让丈夫“学习学习,长点经验”)。但这也可能会成为新一轮的敌意互动,这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夫妻关系的质量和丈夫对批评的接受程度。
实际上许多“急性子”或容易“发飙者”的自尊并不稳固。他们的高度敏感通常是建立在他们自己无能、脆弱和容易被影响的核心意象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他们发展出许多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侵害的代偿方式,他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核心利益的人保持警惕,他们随时准备把对手当作作恶者或坏人。他们的心理“防御”力量可能已强大到足以阻止对自我的任何损害。
偶尔可能会有侮辱或谴责能击穿他们的防御,会伤害到他们的自尊。但他们会调动防御策略,把对手解释成“敌人”并给予还击,这样他们就可以快速地把自我意象从无助的受害者转变为强大成功的复仇者。自我意象的改变可以暂时修补自尊受到的伤害,但那些脆弱无助的记忆却被封存下来,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无能和脆弱的基本形象。出于对负性自我形象的部分代偿,受害者可能会把“施害者”的负性意象具体化为迫害者和共谋者。这种压迫者或敌人的负性意象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奇幻妄想中有生动戏剧化的体现。
一个人各种自我意象的系列组合不会随时间推移轻易变化,而是会趋向于保持稳定,每个意象都会对应(或被激发)于某一类情形。自我意象这种对特殊事件的稳定选择性提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自我意象是更全局性的心理结构(自我)持续的外部呈现。自我概念整合了各种自我意象,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整体结构,无论何时都不可能窥其全貌。自我概念就像一个档案柜,收纳合并了各种自我意象,它包含对个人主要特点、次要特点、内部资源以及条件、各种责任的表征。
三、社会意象的投射
我们的自我意象对我们生活的控制远比我们了解的多得多。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够强大、能胜任和有能力,就有动力解决难题。我们如果有一个无助、无能的自我意象,如处于抑郁中,我们就会感到伤心。我们认为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即我们的社会(人际)意象投射,也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和动机。我们的优势社会形象会影响我们对其他人的反应。如果我们认为对方不友好或者挑剔,我们就会采取策略保护自己。
回避型人格者为了保护自尊只会尽量减少社交。无论是幻想的还是真实的毁谤,敌对型人格者会高度警惕他人的毁谤,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他都随时准备做出攻击。上述两者都把不友好的形象投射到了其他人身上,并试图保护自己脆弱的自我意象。当然,这种投影或幻想的意象是可以自我应验的。人们对回避型人格者的态度可能变得挑剔和忽略,对敌对型人格者可能变得愤怒。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鲍勃邀请阿尔一起去看演出,却遭到了拒绝。鲍勃的反应是:“他认为我不够好。”他感觉很糟糕,他的负性社会意象被激活了。鲍勃反应的背后是他的范式在运作:“人们觉得我不配跟他们在一起。”这种伤害来自鲍勃被贬低的社会意象,而不是阿尔的不陪伴。例如,如果鲍勃知道阿尔是因生病了而不能去剧院,那他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去,除了有点轻微失落,他不会觉得自己被贬低。
我们关于他人的意象通常都有固定的范式,我们能看到他人的那些只与这个范式意象相一致的特征,所以是我们过滤掉了他们的其他特征。对一个既复杂多变又不稳定的现象进行简化和同质化处理是一种很省事的做法,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他人的解读可能会被我们建构的范式扭曲。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勾画自我,这样的方式最好也就是我们的认知不完整,但最坏则是歪曲认识。
我们通常如何看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们占据优势的自我意象控制的。鲍勃想到阿尔认为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难过是因为阿尔的否定推断被分解纳入他的自尊。但如果鲍勃认为“没有人喜欢我”并接受“我肯定不讨人喜欢”的解释,那么他的负性自我意象就会被激活,他的自尊心就会显著下降。
另外,如果鲍勃有一个稳定的正性自我意象,阿尔的否定就不会影响到他的自尊。实际上,鲍勃也有可能会将阿尔的拒绝解释为阿尔的自私表现而生他的气。鲍勃从负面角度看阿尔,这样可以保护他的自尊。或者,如果鲍勃的自尊不受阿尔拒绝的打击,他可以无视它,他也就无须为自己辩护了。简而言之,个性化的意义解读及其与自尊主题的关联决定了人们的反应。
显然,任何的人际交往都至少涉及六种意象:我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我的意象投射(我想象中的你对我的印象)、你眼中的我、你的社会意象投射(你想象中的我对你的印象)和你眼中的你自己。这些意象相互作用并呈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中。如果我认为自己弱小而你很强大,并且你也认为我弱小而觉得自己很强大,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你会支配我,或者至少意图这样做。这些不同的意象有很多种可能的组合,至少能部分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对方做出友好或不友好的行为和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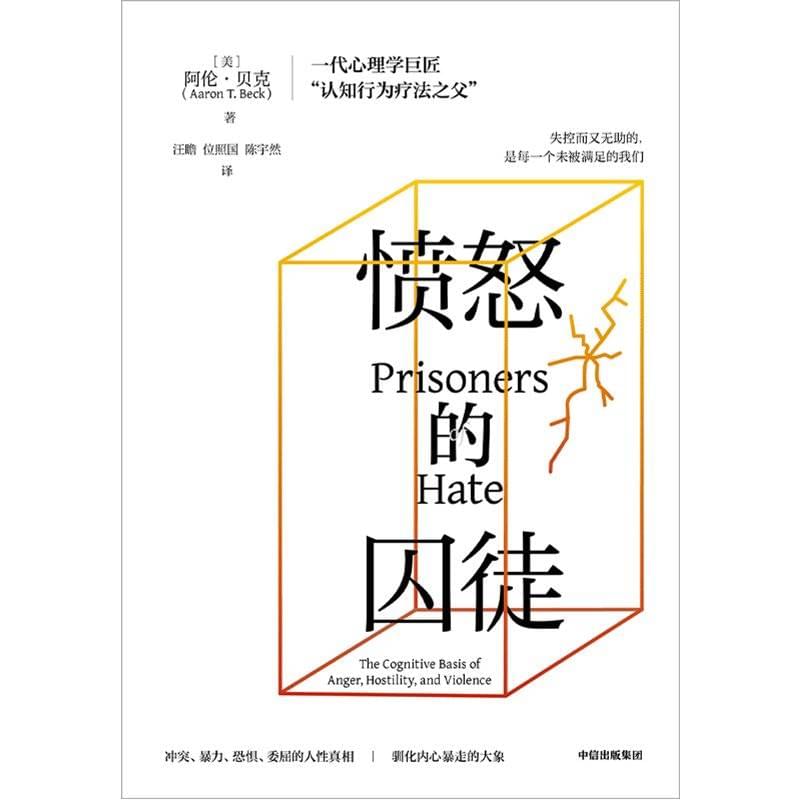
本文整理摘编自《愤怒的囚徒》,作者:阿伦·贝克,出版社:中信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