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总觉得自己这一代人是非常独特而幸运的,我们亲历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巨大而迅急的文明跃迁,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速率空前的巨大发展,物质生活面貌更是直接从中世纪飞到后现代。我从乡村走来,感受尤其强烈,因此常说:“最近50年许多方面的变化超过了以往5000年。”
故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毫无疑问、也自然而然是我的关注重点。自17岁离家外出学习和工作,如今年过花甲,鬓须皆白,但对故乡风物景致、民情习俗,对故乡语言调韵与泥土芬芳,始终魂牵梦萦、无法忘怀。不论先前研究农业史还是现在研究环境史,它们一直都是我叙事、说理的重要“参照系”。可以说,儿时故乡的生活体验对于我的课题选择和问题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宿松有一条二郎河,河畔是家
我的家在安徽省宿松县城西北一个名叫元湾柏树塝的普通村庄。村后是相对高度200-300米的狮子山,山势东西耸立,两头的岩石极像一对雄踞蹲坐的狮子;村前是一片开阔的田畈,一条宽约百米的河流从畈中穿过,形成自然地理分割,东西两岸的村落房舍大抵都是靠山面河而建。
元湾与湖北黄梅一山相隔而又一沟相连。记得当年生产队的灌溉用水并非由宿松水库供给,而是通过几十里蜿蜒曲折的小渠从一座黄梅县的水库绕山过岭引来,因此我们与黄梅老乡有着同饮一沟水的特殊情谊。那边的人来这边拣粪从来不遭嫌弃、驱赶,这边的人去那边购物、看戏、看电影也被视作理所当然。分属两省两县的人民风俗习惯高度相似,通婚联姻非常普遍,血缘亲戚关系十分紧密,言语声调却是差别显著,彼此交流毫无障碍,但开口便知是宿松佬还是黄梅佬。
宿松、黄梅都在长江北岸,与江西省九江市一江相隔。这个三省毗邻交接的地方很是神奇,社会经济、文化风尚乃至血脉基因水乳交融,三地人民有许多同宗共祖的本家和亲戚,共同拥有和分享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层累,语言声调却判然有别。
我讲宿松腔,故是宿松人。这里早在西汉时期即有行政建制,隶属古松兹(滋)侯国。魏晋南朝时期,盖因移民侨置之故,松滋西迁去了今湖北省松滋市一带。以“宿松”之名置县始于隋朝(或意指此即宿昔之松兹)并一直保留至今,隶属关系则屡经变化。
这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带,降水丰沛,四季分明;地势北高南低,地貌景观多样;自然环境优越,水陆物产丰饶。北部是千里大别山之余脉绵延,南侧有万里长江之水滚滚流过,兼擅山地、丘陵和江湖、平原之美。既有山之巍峨,更显水之灵秀,自古即是山货聚辏之地,更是鱼米充牣之乡,经济结构和生活风尚富有地方特色。这里古称“吴楚咽喉”,兼受吴、楚两大地域文化影响,而楚风更显强劲,民俗淳厚古朴,生活勤劳节俭。
由于地处皖、鄂、赣三省交界之区,历史上多有异乡人民移居于兹,因此多种方言交流混合,一县境内即能听到多种不同乡音语调,吐字发音犹带古韵。最难忘却的,是故乡的每一缕气息之中都飘荡着的那些婉转、悠扬的黄梅曲调。
如果说,峰峦叠嶂的北部山地矗立了宿松的峻拔风姿,倚江抱湖的南部水域展现了宿松的宽阔胸襟,那么自北而南贯穿全境的二郎河,则飘逸着宿松的灵秀气韵。她湍激山谷,洄绕丘陵,承接大小泓溪、沟渠,串连众多田畈、村镇,最终汇流龙湖,接浪长江,慷慨地惠赠予丰饶的物资,不停地絮说着绵长的历史。
二郎河是宿松最大的一条河流,干长66.3公里,年均径流38万多立方米,流域面积约597平方公里,仅有32平方公里在湖北黄梅县境内,基本上是一条宿松境内河流。她起源于哪个地质年代?未及考证。但我知道她一如祖国大地上的其他众多大小河流,在漫长历史进程之中塑造了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民。
古往今来,人们逐河而居,与河共生。水的流淌与人的活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持续书写着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彼此因应的悠久历史,共同描绘着环境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生态—社会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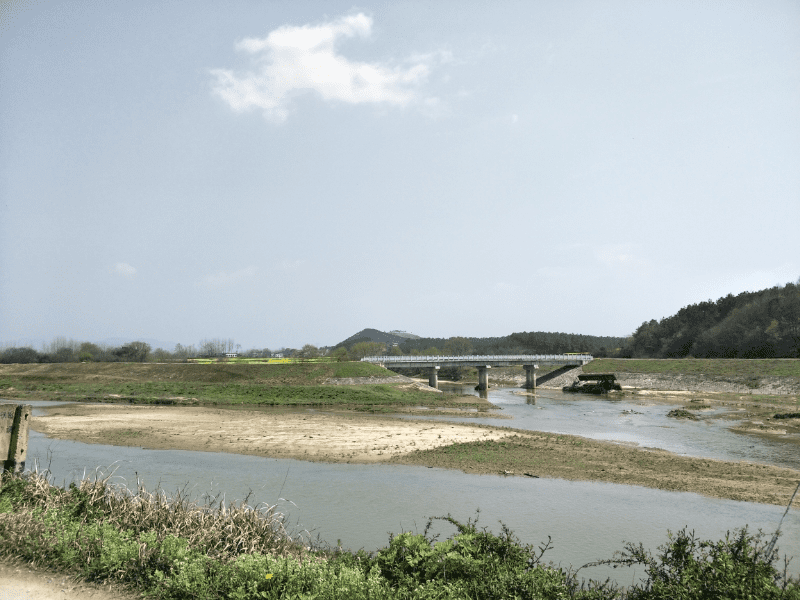
▲二郎河畔的景色。
因为向往外面的世界,幼年之时,我或因打柴、或因放牛,有时只是单纯地想要登高望远,经常爬到狮子山顶向远处眺望。向西望,是湖北黄梅绵延起伏的山峦,恰如江河波浪奔涌,让我领略到毛主席那句“五岭逶迤腾细浪”诗词的妙意;向东南,循着锦带一般飘逸远去的二郎河,极目所见,除了断续布列的一个个山丘,便是一片片田畈,一座座村落,以及镜片一般光亮闪耀的大小池塘。
在天高气爽的日子,目光追逐二郎河水流淌的尽头,天际一线茫白,听说那便是同万里长江连成一体、相互吞吐的龙感湖。惜因少小离家,我至今没有去过龙感湖。或许退休后可以找个机会循河而下,前往一览那江湖云天浑然一色的壮阔美景。
二郎河的慷慨馈赠与儿时生计
大约在1977年冬天,为解决二郎河汛期决溢、泛滥之患,当地政府组织成千上万民工对河道进行重大改造,拓宽河道,高固堤坝,裁弯取直。那年我在上初中三年级,快有15岁,作为半个劳力参加了“挑河”工作。从此二郎河旧貌换新颜,水道通直,堤岸高筑,生态系统随之发生了诸多意想不到和值得反思的重要变化。我家附近河段最显著的变化是沿岸竹、树大多消失,不再有大群鸟类聚集栖息,河里原本很是丰富的鱼类更是骤然减少。
存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是那条弯弯曲曲的二郎河。河中沙滩随着水流的季节涨落时隐时见,极不规则的堤岸水际杂乱地长满水杨、垂柳、芦苇、霸地草和更多不知名的杂木、野草种类,大片水竹林错落散布在河湾隩曲之地——那是无数飞鸟、昆虫、蠕虫和小型哺乳动物的家园。我还记得两三里外的青圩那边,在二郎河与车马河的交汇处曾经有片很大的竹林,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每到黄昏落日时分,就传来无数归鸟的吵嚷、嬉闹之声。最让我追怀的,还是二郎河里的鱼、虾和螃蛴,有数十种之多,但许多鱼儿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
二郎河的馈赠慷慨而丰厚,是我儿时生计的主要来源。她给我们敞开了草肥水美的牧场,生殖了种类繁多的野菜,其中不少种类可做菜蔬,更有大量鲜美的鱼类水产。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贫困时代,二郎河给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食物营养。二郎河畔更是我们野性成长的乐园——天然清洁的泳池、拾贝寻珠的宝藏、写字涂鸦的沙盘以及排兵布阵的战场。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个时代的孩子,打小就懂得并且亲身体验到生活的不易,很早就能做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同长辈们共谋生计。我从五六岁就开始承担多项有实际经济意义的事务,除了上学、做饭和照看妹妹,放牛、打猪草、挑野菜、拣粪和捡柴是主要的几项。
放牛伢的生活大抵是开心、快乐的。应该是六岁的时候,我尚未上学读书,生产队分给我家一头牛,由我负责放养,一年能挣几十个工分。记得第一次放牛是两位哥哥带着:一位是同姓的笑平,另一位是诨名唤作“岳西佬”(岳西是安徽大别山区的一个县)的吴姓亲戚。那次放牛是在山上而不是河边。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村庄是背山而建,屋后是山,门前是田,田畈之外就是二郎河。这样的格局规定了我们上学、放牛和其他诸项活动的空间模式。在小学阶段,我们的白天划分为早晨、上午和下午三个时段,除星期日外,早晨我们都把牛儿牵到狮子山上野放,这样不必担心它们闯入田地毁坏庄稼。那时下午不上学,因此大多是在水草更加丰美的河堤草滩上放牛。
比较而言,我们更喜欢后者,因为可以划水、摸鱼、寻找酸甜的野草果实和茎根,渴了就趴在河里喝水。在河滩开阔地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疯牛顶角,牛牯儿们——不论水牛、黄牛都猝然怒起的顽命搏击,总让我们全体情绪炸裂,撕心裂肺地喝彩、嚎叫,双方的小主人们更是面红耳赤,血管偾张!
更激动人心的是“沙场练兵”。那个年代,个个孩子都有“战士梦”,打仗不分昼夜,用杨柳树枝编扎的帽子是标配军装,杨子荣、少剑波、郭剑光是争相竞夺的角色,而充当座山雕、栾平、胡传魁、刁德一之类则是不情不愿的强制安排。
不过,在对战河东放牛伢时,我们的“沙场练兵”是有组织分工而无偶像角色的实战,擅长投掷就做尖刀班的战士,臂力弱小就负责搬运武器。战斗通常以羞辱性对骂起衅,然后互相投掷“手榴弹”——河里的鹅卵石或从附近窑场搬来的碎砖、瓦片。两岸“战争”持续了多年,我们都知道对方投掷又远又准的悍将,彼此视为劲敌。直到上了初中,“宿敌”变成了同班甚至同桌的同学,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不少还成了终生守望的亲密兄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食物相当匮乏,饥饿难捱让我至今感到心悸。所幸那时乡村还有一些野生资源能够发挥补苴作用,采集野果野菜以弥补粮蔬不足,捕鱼、捞虾、捉泥鳅获得少许动物蛋白,便成为非常重要的食物营养补充。
大约四五岁时,我便加入了“采集者”行列,挑野菜,拣柴禾。隐约记得最早的一次采集活动是堂伯母陈嬷嬷带我去的。那年春天,二郎河上东风依然有些料峭,嬷嬷带我到河沙滩上寻找早生的野菜,一一告诉我哪种人能吃,哪种猪能吃,哪种有毒,由此我获得了最早的野生植物知识。
那个时代的乡村,人人都是植物学家,都知道几十种乃至更多野生植物的名称、性状和用途。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们,上中学前的日常任务除了放牛、拾柴、拣粪,就是挑野菜了。起源于二郎一带的黄梅调《打猪草》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吟唱。只是,打猪草的不只有小女子,还有少儿郎。
在差不多的年龄,我还成为一名“捕捞者”。记忆中的最早捕捞活动是春耕时节跟在赶牛耕田的父亲身后抓泥鳅,在四岁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还清晰记得的捕鱼活动始于1970至1971年间。当时,一支医疗队进驻宿松农村。为了杀灭钉螺(血吸虫的宿主),医生们在田间、沟渠、池塘等有水的地方投放药物,大量被毒死的鱼、虾、泥鳅和黄鳝浮上水面,我们捞起掐头、挤肠,煮煮便吃,顾不上、也不知道可能中毒。
打那以后,乡民竟然学会了用农药毒鱼(亦因农药开始推广使用),每年都有人在二郎河畔的废河汊、野池塘里多次投放农药,包括1605(乙基对硫磷)、滴滴涕(DDT)和666粉(六氯环己烷)等高毒性、高残留农药(现已禁止使用),直到1980年离开家乡之时,我还看到有人用这种方法捕黄鳝。后来学农学、做环境史,我才意识到自己居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直吃着用高残留、甚至剧毒农药杀死的鱼类,怕是有些毒素仍然残留在我的体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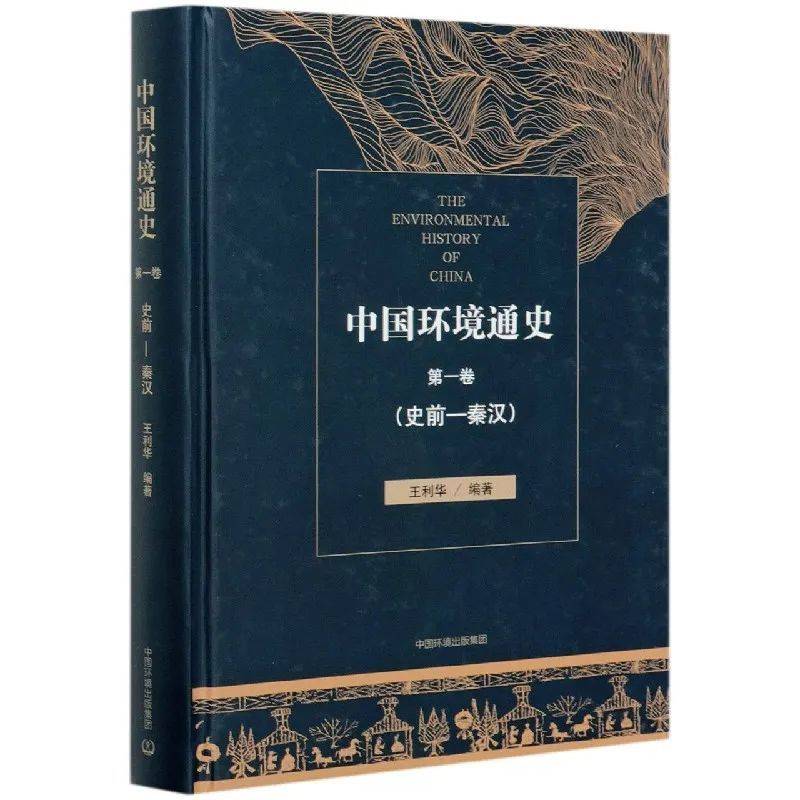
当然,捕鱼并不都靠投药,笼截、罩扑、竿钓、网捕和徒手摸鱼都是当地常见的方式。记得梅雨季节河水上涨之时,有一种名叫“窜条”的小鱼非常繁多,每天傍晚二郎河里都站满了持网截捕的人群,如果位置选择得好,一个晚上就可能捕到数十、上百斤!
不论钓鱼、捞鱼,我都很早就成了一把好手,原因有点滑稽:因父亲不像其他大人那样对此上心(梅雨天下河捕鱼除外)。父亲上过初小,稍能断文识字,一直担任队长、指导员之类干部,思想正统,小时候总是批评我不务正业,“捕鱼捞虾,耽误庄稼”。但是对我捕、钓得来的鱼,每次他也吃得津津有味——毕竟那是难得的美食啊!那时我家五、六口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斤猪肉、几个鸡蛋,二郎河里的野生鱼类便成为我们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
儿时的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吃食:下水采摘菱角、茭白、鸡头米,抓捕野鱼、泥鳅、黄鳝、青蛙,上山采集毛栗子、橡树子、野山楂、野蘑菇和地衣,打野兔、野鸡和掏鸟蛋……一切能够想到的方法全都试过,由此我掌握了数十、上百种水陆野生动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生境和生长、活动季节。
后来研究农业史和环境史,翻阅古籍中的相关资料,我常常与少时的经验知识对应,愈来愈感到这些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必要生产生活知识,成千上万年来不知帮助过多少饥饿的人们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下来。除了寻找吃食,还有不少防治意外创伤、毒虫叮咬和常见疾病的经验知识,许多草药在二郎河沿岸的沙滩、堤坝、田埂、地头和附近山林中都能找到。
对于这从小习得民间经验和乡土知识,我一直自鸣得意,曾跟同学们开玩笑说:“如果搞一次野外生存冒险,不准携带任何食物、药品,我一定能比你们多坚持几天。”这些亲身生活经历,对我理解古代中国的环境、经济、社会特别是食物的历史具有很大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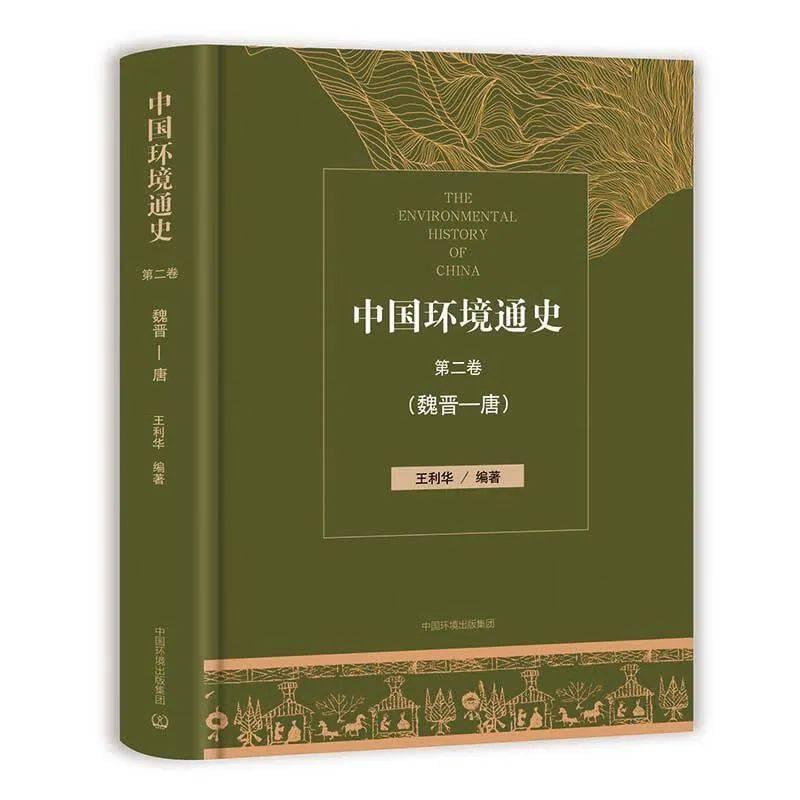
或许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能产生特殊的美,如今我的记忆淡化了曾经的苦涩,留下了儿时的美好,但我们这代人是在大自然中“寓乐于劳”地成长起来的。
如今中国人民早已丰衣足食,数代忘饥,物质之富庶、生活之便利远超前人梦想。只是不知二郎河水是否依然清澈如故?春天的杜鹃花是否依然红遍山坡?青翠的马尾松树是否已是粗大如拱?家乡的后辈少年郎君们,是否依然在山水田园中赤脚奔跑、恣肆放歌,享受着那份人与自然交融的惬意?
二郎河畔的儿歌、学堂和老师
二郎河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也是一条文化的河流。在人类的生活世界里,自然与文化从来不是互相隔离,而是彼此交融:自然是文化的根基,文化是自然的灵魂。二郎河畔,我的故乡,那个拥有浓郁民俗特色的地方,人心敦厚,尊师重教,文化发达,在那里出生长大,实为吾生大幸!

▲二郎河畔的景色。
我从懵懂不识的年龄开始就沐浴在各种儿歌、童谣和民间传说的文化氛围之中。当然,还有那些令人腿软的鬼故事和一度被禁止演出的黄梅戏。我的启蒙教育是听长辈讲故事、听同伴唱儿歌。这些流传久远却经常被忽视的民间文化,以看似简单甚或不合乎逻辑的方式教导人类的萌宠学语、识物和知理,传授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初始知识。故乡的儿歌,往往是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互相结合。记得有一首歌中唱道:
萤火虫,低低飞。飞到外婆家菜园里吃乌龟。
乌龟乌龟冇长毛,爹爹叫我摘葡萄。
葡萄葡萄冇开花,爹爹叫我摘王瓜(黄瓜)。
王瓜王瓜冇长蒂,爹爹带我去看戏。
看戏看戏冇搭台,爹爹叫我去割柴。
割柴割柴冇带刀,爹爹打我一头的疱!
流传颇广的《撤炮(撒谎)歌》很有特色,讲了一连串反话却是为了传授物理、生物和农业方面的常识:
唱歌不唱撤炮(撒谎)歌,风吹石磙过江河。
山坡头上鱼生子(产卵),急水头上鸟做窠。
烂泥田里打大麦,青石板上插秧棵。
山羊跟到(跟着)老虎跑,猫鼠共舞享乐多。
更家喻户晓的《打铁歌》,不仅涉及二郎河畔人家的娱乐节俗、劳作时令、饮食结构,还包括女性角色、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理想等。这首儿歌版本颇多,且不只在宿松流行,但只有宿松话的音调能够唱出它的独特情韵。歌中唱道:
张打铁,李打铁,打一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去家打夜铁。夜铁打到正月正,我要去家玩花灯。花灯玩到清明后,我要去家点黄豆。黄豆开花绿豆芽,哥薅草,妹送茶。妹呀妹,你莫哭,来日帮你搭个好花屋……
作为一名教师,我一直在观察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变迁,思考如何促进人的全面成长与发展。对曾经上过的学堂和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始终心存一份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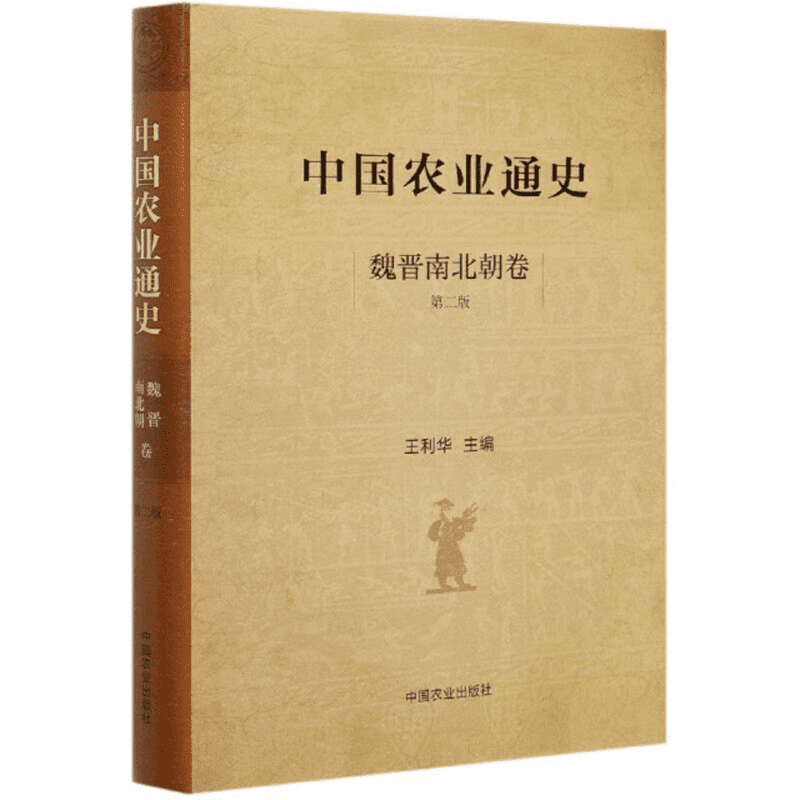
按照今天的标准,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艰苦而不正规。小学只有半天上学,差不多全部由民办教师代课,两、三个年级合用一间教室,老师讲课的方式是给这个年级讲一段就转到另一个年级。最大的问题是除课本之外没有任何带字的册子可读。我很幸运有二伯父在堂屋供奉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那是我的主要知识来源,不知翻过了多少遍。
我的初中在韩文中学,入学报到时每名学生必须交纳一块木板,因为没有桌椅。即便都交过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用的还是水泥或石灰台子。学校在二郎河的东岸,离家约有两公里,又没有食宿条件,所以我们每天需往返三次、奔跑十八里地。
河上的小木桥经常被冲断,摆渡的竹排时有时无,因此寒冬经常赤足涉水。雨季更加麻烦,河水一涨就无法到校,或者到了学校就不能回家,因故旷课和空腹上课是常事,真急了就孤注一掷、涉险凫渡过河。
小学阶段课外要煮饭、放牛、拣粪、打柴,初中则要支农学农——插田、摘茶、搬煤、挖树坑……值得一提的是,初中三年半,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在搞建校劳动。多年前就听说母校被撤销了,不知我们磨破手脚建造的校舍今属何人?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学习也渐渐正规起来。我的高中——花凉中学是一所老校,建在高山脚下一个名叫鹅颈湾的地方,周围山景峻秀,但离家三十多里,只能住校。每周回家一次,驮米、装咸菜罐头和向父母讨要炊火费。学校缺少供给,我又没钱,所以一周6天只能以咸菜、萝卜干、腐乳、豆豉和辣椒酱下饭。只有周六晚餐和周日早、午餐才能在家吃些青菜,肉、鱼、蛋就别指望了。
但生活困苦的并不只有我们,我的老师们同样清贫甚至更加艰辛。几十年来,虽然逐渐失了联络,有的老师已经过世,但我的内心深处始终雕刻着一组慈祥而清癯的乡村教师群像:赵旺德、吴行素、郑谦一(小学),石铁稳、徐崇森、郭铁汉(初中),沈明开、周治野、孙皖樵(花凉高中),吴一、刘泽川、张留火、蒋在文、汪御寇(程集文科集中班)……还有更多老师,他们谆谆教我,谔谔训我,关键时刻指引我破除迷障,克服胆怯,勇敢前行。我知道,我们是他们文化生命的延续,最好的报恩方式是恪尽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把老师的神圣功德持续光大,让他们的伟大精神恒久不坠。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农业古国,辽阔大地上蕴藏着亿万卷乡村历史,我的故乡只是祖国版图上的一个珠点,但那里是我的根,有我的魂。我的记忆,只是关于乡村故事的一个微末碎片,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习惯于将中国乡村变迁放置于一个纵深的时空场景进行观察和思考。
毫无疑问,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许多挑战,在各种现代性因素如大潮巨浪一般急速涌现之际,如何处理好建设与保护、革新与继承等等关系,我的家乡也有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等待破解。每念及此,我有千言万语,难以尽道。我未曾学过拼音,平仄音韵、诗词格律更是不懂,为了表达此刻心情,斗胆呈献一首打油诗,为故乡加油并且表达诚挚的感恩和祝福:
不要问我哪里来,二郎河畔是故乡。屋后狮子山顶卧,堤外鱼虾水中翔。
杜鹃马尾争红绿,垂柳修竹自俯仰。曾为古楚渔樵客,拣粪打草放牛郎。
逆旅人生换甲子,读书论史话沧桑。常念双亲劬劳苦,犹忆诸师在学堂。
儿时伴侣今何在?走南闯北可安详?二郎精进志高远,一梦圆碎又何妨!
罗汉尖峰抬望眼,天高水阔是长江。士农工商齐努力,五位一体绣华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 (ID:farmercomcn),作者:王利华(安徽省宿松县人,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农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受聘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岗位,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环境史、生态文明基础理论、中国农业史和社会生活史),图片:宿松县韩岭村委会副主任王鹏提供,编辑:桑妍,总策划:何兰生,总监制:王一民,监制:施维、冯克、张凤云,统筹:梅隆,美编:刘念,出品:农民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