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这个概念有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古代社会,劳动是天经地义的,很少有人赋予劳动以神圣的意义。从17世纪开始,英国哲学家洛克开始思考劳动的概念,他把劳动看成是人类通过开垦大地、索取资源和材料来制造和加工物品的一个过程。
劳动是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差别,动物也寻找食物以维生,但是只有人的劳动——人从大地上寻找资源来加工的这个过程——才被称为劳动。简单来说,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都被看作上述过程,都属于17世纪的主流劳动。
到了20世纪上半期,随着现代社会科层化的发展,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工作类型也越来越多。韦伯重新解释了劳动的概念。从他开始,不生产具体可见的商品的工作,比如计划、分析、管理、组织、教育等事务也被归于劳动。社会分工的每个层面的活动都可以被归入劳动的范畴,劳动主体不再仅限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农民或工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女性的家务活动都被排除在劳动概念之外。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觉醒,家政工作,尤其是妇女在家的私人活动(包括家务和抚育孩子)也被视为劳动。
在今天,随着各种服务行业的兴起,尤其是媒介和互联网的扩张,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和劳动类型。意大利理论家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这样的劳动甚至不会产生任何物质产品,它们与沟通和交流相关,生产的是信息、情感和话语。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所谓的情感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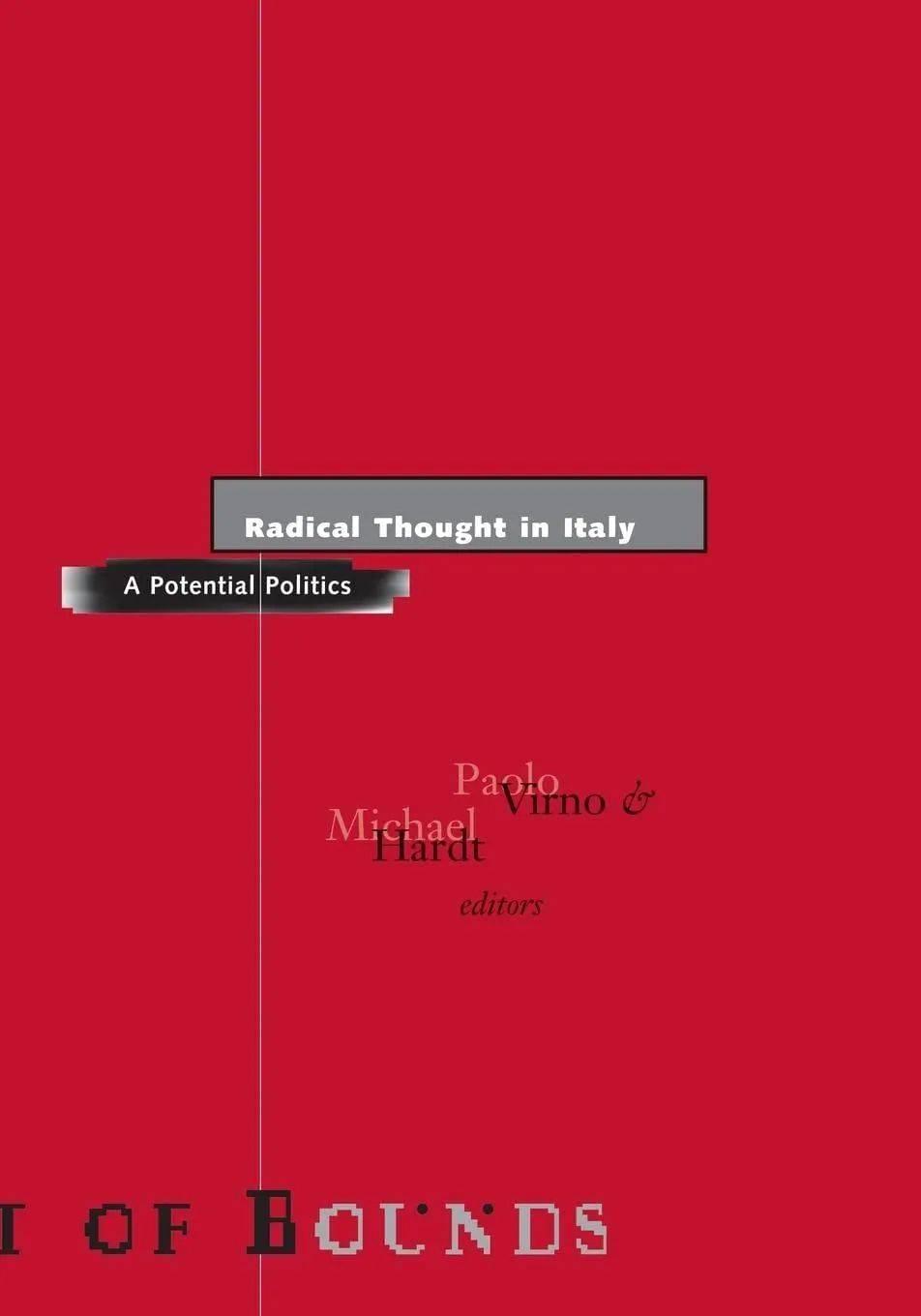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拉扎拉托的论文《非物质劳动》收录在这本当代意大利政治理论文集中。
“躺平”是一个现代现象。要理解“躺平”,我们也许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论劳动。劳动可分为两种类型:自主劳动和雇佣劳动,或者说主动劳动和被动劳动。自主劳动是为自己劳动,即劳动是劳动者自己主动选择的,劳动所得也归属自己,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到了快乐——比如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这样的劳动会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一种主动性的创造,是人的自由的表达,它不会让人感到厌倦,反而会激起人们的兴奋感。
与之相反,被动劳动是一种机械的、重复的、消耗性的劳动。它是一种雇佣劳动,这意味着你是为别人劳动的,虽然有所得,但更主要的是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对此有精辟深入的分析,且在今天仍都不过时。
你在这样的劳动中不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被雇用的劳动者总是被动的,在这种工作当中很难找到快乐、自由,它很容易变成持久的消耗,会让人产生厌倦。人们之所以不断地换工作,就是为了尽可能找到一种能让他快乐、感到有创造性的工作。所谓的“躺平”,只会出现在被雇用的、被动的劳动者身上,他们确实厌倦了这样的劳动。
但我们也不要因此简单地把“躺平”视作一劳永逸的。它总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一份既有的工作——停止这份工作并不意味着永不工作。也就是说,“躺平”是拒绝既有的、乏味的、无聊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拒绝被剥削的雇佣工作。只有拒绝了这样的工作,劳动者才有可能获得有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躺平”一方面是消极的,是对既有工作的否定;它也可能是积极的,是积极工作的开端。
严格来说,雇佣劳动中的“躺平”不独见于今天。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就出现了一个工人运动组织,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就叫“永不工作”,著名的情境主义运动的口号也是“永不工作”。“永不工作”,是要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雇佣关系当中解放出来。
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对资本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拒绝。通过停止和中断工作来质疑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体制,从而打开新的可能性。对他们而言,拒绝工作,既不是像以前的工人阶级那样去砸毁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去造反,也不是采用工会斗争模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和雇主谈判或协商,而是直接从不合理的关系中退出。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暴力砸毁机器的方式——来制造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危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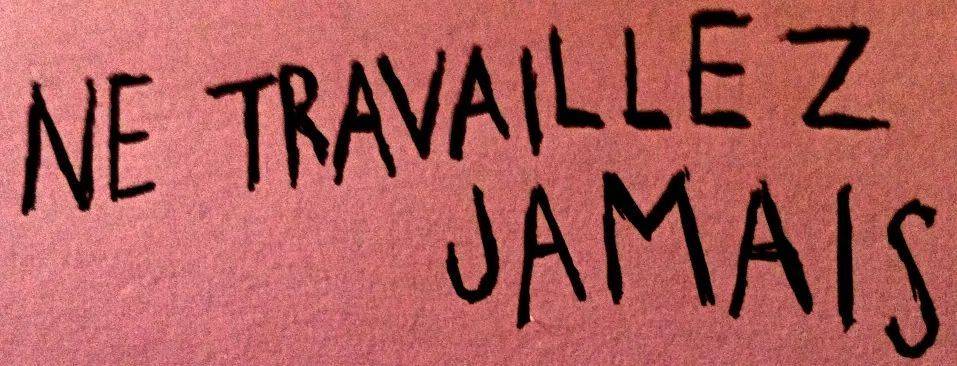
Ne travaillez jamais (“永不工作”)是著名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情景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1953年写在巴黎塞纳街墙上的一句口号。
跟“永不工作”这样充满理论思考的实践不同,“躺平”是由当下年轻人的劳动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以及复杂的现实因素引发的。实际上,古代人并不怎么思考劳动的意义。劳动对他们而言是什么?从大自然中采集食物让自己生存下来就是劳动,劳动是一种很本能的、为满足生活所需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行为。
但在17世纪,劳动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基督教肯定了劳动的其他意义:劳动可以克服懒惰、欲望,可以禁欲,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成为人们最终进入天堂从而获得拯救的手段;劳动具有神圣维度,是对上帝圣训的回应,劳动所得是上帝的恩赐。基督教认为,人类应该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去工作,而且人类生而有罪,必须用工作来向上帝赎罪——勤勉劳动的意识就这样被刻在新教徒的骨子里,并将其成功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勤勉工人。
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宗教意识衰退了,劳动不再跟神圣性相关,对劳动的赞美以其他方式出现,比如劳动能够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提高社会的效率,改善人类的状态,最终让人类获得自由等。劳动总是有超越自身之外的意义和目标。
但在今天,劳动根除了它的超越性意义,它既不是遵循上帝训令从而修筑的一条通往天堂之道,也不试图让人类在此世获得解放。劳动重拾了它的内在性,它仅仅是个人挣钱谋生的手段而已。它已经从过去对宏大精神价值的探究退化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形式:如果这份工作不能挣钱而且让我倍感痛苦,我为什么还要去完成它呢?再也没有超验的意义神话来帮助克服劳动本身带来的负面效果。
每个劳动者都会感觉到巨大的体力消耗,这是其所面临的最直接的痛苦。但是,远不止如此。马克思提到工人劳动的残酷性,即工人超额的、高强度的劳动所得大多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的所得仅仅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即能够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从而使自己能够继续从事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批判传统,即无论是卢卡奇(György Lukács)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深入地批判过资本主义的劳动体制: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制度将人变成了单面人,人成为机器的配件,人像机器一样运转,人成为不会思考的人,这样的劳动让人变得毫无情感和个性,变得麻木和物化——劳动让人成为现代奴隶。
信息化的劳动更是如此,比如斯蒂格勒就认为人对技术的依赖会让人变得全盘性的愚蠢。信息劳动让人仿佛失去了大脑和意识,使人的劳动变得完全是被动性和适应性的。大体上来说,左翼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批评资本主义劳动剥夺了人性,剥夺了人的能力,剥夺了人之所能。
但是,阿甘本认为资本主义剥夺了人的不能。阿甘本提出的“潜能”概念——这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习得的——包含两种意义:一种是可以去实施、可以现实化的潜能,另一种是不去实施、不去现实化的潜能。也就是说,潜能有不做的维度,不做就表示我们有能力不去做。
阿甘本特别看重后一种潜能,他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实践不去做的潜能——不仅要在技术方面施展不去做的潜能,而且应该在政治生活中也实践这种潜能,一个人应该保留自己有所不为的能力。而“我能”正是资本主义的律令,即我必须能,因为一切都在鼓励“我能”,“我能”成了对人的价值的评判取向。每个人都觉得“无能”是一种羞耻。我不能“不能”,我不能说“我不能”,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资本主义将人的“不能”体验彻底剥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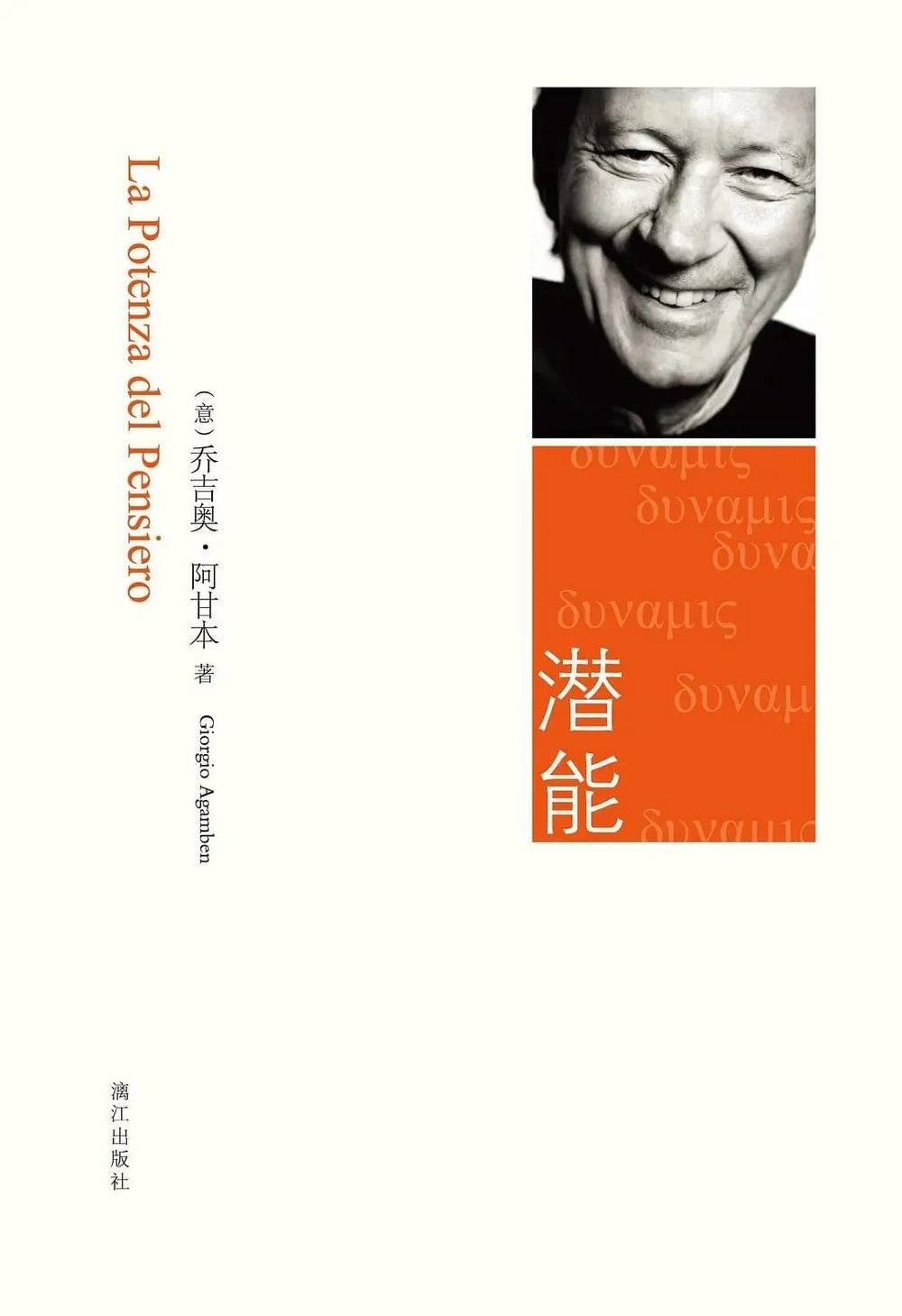
潜能阿甘本,漓江出版社 2014
实际上,在此之前,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就提出过懒惰的权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也说过类似的话,即人们要敢于懒惰。这实际上都是在维护人们“不能”的权利。
但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剥夺了人的“能”,机器将人的能力损毁,将人变成了物,即所谓的物化;另一方面也剥夺了人的“不能”,它要求你必须去做,必须不停地做,必须什么都能做,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它要求人们永不知疲倦地工作和劳动。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变成了一个劳动机器,一个永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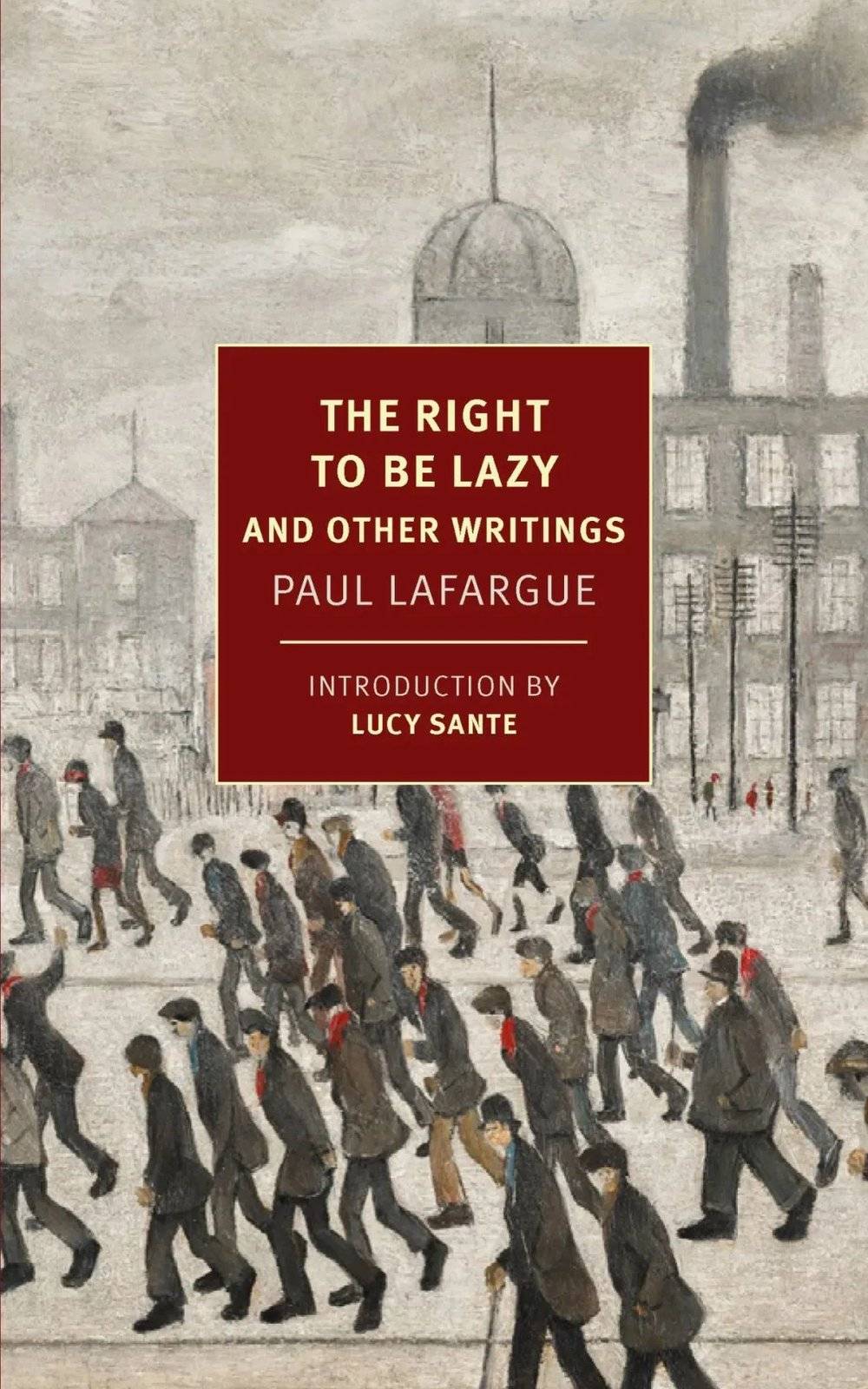
The Right to Be Lazy: And Other Writings,Paul Lafargue,New York Review Book Classics 2022
我们也可以从效用上来区分劳动或者工作类型。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写道:现代社会有大量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在这种工作中,人毫无快乐可言,也看不到自己对社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益处,但又不得不做,因为这些毫无创造性、毫无意义的工作毕竟能给他提供一份薪水来谋生。
同时,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工作,因为如果很多人不工作,就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就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低效、无意义的工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格雷伯列举了很多他认为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前台接待员、保安、公关、人事专员,乃至华尔街的金融家等。在他看来,这些工作对社会来说是无意义的,无论在这些岗位上能挣多少钱。格雷伯认为,真正有意义、能让人获得成就感的工作是清洁工、护工、志愿者、幼儿教师等,他们对社会的作用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社会就很难运转,但事实上,他们拿到的工资却非常少。
格雷伯认为,这正是劳动的不合理之处: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通常回报甚少,而那些金融、法律、咨询等他认为无意义的工作的回报过多。劳动的价值和回馈并不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毫无意义的工作,大卫·格雷伯,中信出版集团 2022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的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但这种满足并不等于自由。我们看到了太多努力工作挣钱的人,也确实有很多人通过劳动挣到了很多钱,但这种劳动本身并不使人快乐,是通过劳动取得的报酬让他们感到快乐。
但如果你是通过自己并不喜欢的劳动挣了很多钱,又通过获得金钱满足了自身的欲望,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反而会让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痛苦地劳动。只要这种劳动本身并没有给你带来快乐,你就很难体会到自由。
相反,如果你从事的是一种主动性的、创造性的劳动,你就会充满快乐,就会体验到劳动带给你的自由和意义。这样的快乐不是金钱带给你的,而是创造带给你的,这是一种劳动创造的快乐。这也是人的一种自由实践,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能够快乐地劳动,从劳动中获得快乐。在我看来,这样的劳动也是有尊严的劳动——因此也可以说,一切违背自己意愿的劳动,都是没有尊严的劳动。
至于技术能否将人从这种没有尊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不确定。至今为止,我看到的新技术都让人卷入到更深的束缚和被动中去了。但也许会有一天,技术能够发展到完全取代人的劳动,从而将人类从所有烦琐而痛苦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人类不再从事痛苦劳动的那一天,人类还会存在吗?或者说,人类还有自主性吗?也许,由于一种新型智能的出现,人类确实不用再劳动了,但是,他也可能因此成为新的奴隶,不是劳动的奴隶,而是一种新型智能的奴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汪民安,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