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斯(Jon Bernardes)认为,传统的“家庭”概念是保守的,存在种族和阶层色彩,也是物种主义的。长期以来,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二元对立掩盖了传统家庭观点中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使学者们忽略了构成家庭的物种间依赖性。[2]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家庭的构成是,而且一直是“超越人类的”(more-than-human)。多物种家庭(Multispecies Family),也被称为“超越人类家庭”和“后人类家庭”,是指伴侣动物在关爱的、亲子的关系中或作为家庭成员融入家庭,与人类组成并维持家庭。在这里,“多物种”、“超越人类”和“后人类”等术语交替使用,以承认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互联系以及动物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参与。
在多物种家庭的视角下,家庭不再被看作一个预先构成的实体,而是采用“成为家庭”的概念。能否成为家庭除了取决于传统意义上家庭的一系列事务和关系,还取决于一系列非人类角色,包括伴侣动物,也包括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的“水稻、蜜蜂、郁金香和肠道菌群等有机生命——所有这些都造就了人类的生活,反之亦然”[3]。家庭是在与这些生物共生的过程中产生的。
将家庭视为“多物种的”,揭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相互交织,同时,人类承担着责任,制定规则,并照顾其他生物。多物种家庭代表了一种混合体,包含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社会与自然的多重关系。
本文以多物种家庭的视角分析了猫狗作为伴侣动物的驯化起源,及其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的情感体验和互动,以期重新理解人类和非人类伴侣动物如何彼此积极塑造家庭和家庭的生活方式。

When Species Meet, Donna Haraway
Universt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猫狗的驯化和自我驯化
狗是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4]狗能关注和理解人类的沟通线索,包括人的面部表情、声音语调和手势,尤其是能理解人类的指向手势。狗的这种能力一直令科学家着迷,因为很少有其他种类的动物能够理解人类的手势,这与黑猩猩等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动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狗很容易利用人类的社交线索找到隐藏的食物,但黑猩猩运用这种社交暗示的技巧却较差[5]:虽然黑猩猩在接受训练以后可以学会关注指向手势,但是不会自发地跟随人类的手势。[6]
狗对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表情的理解能力也许是其能够与人类一起生活、成为人类家庭成员的核心原因之一。为了解释这种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如何进化、为什么会进化,科学家提出了许多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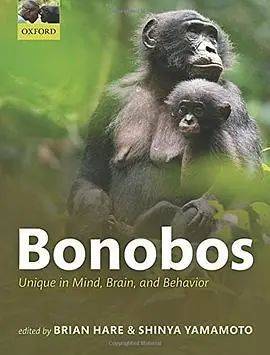
Bonobos, Brian Hare / Shinya Yamamo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黑尔(Brian Hare)等人[5]提出的“驯化假说”(Domestication Hypothesis)是这一领域最具创造性的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在驯化过程中,人类特别选择和保留了使犬类能够完成与人类交流的那些特征,这使其进化出了在以目标为导向的情境(例如觅食)中理解人类的指向手势并做出反应的能力,没被驯化的犬科动物则不具备这种特点。
此外,还有学者[7]提出“两阶段假说”(Two Stage Hypothesis),提供了一种补充观点,认为狗理解人类社交暗示的能力取决于两种个体发育的经验:狗在发展敏感期与人类的互动,以及不局限于其特定发育阶段的学习能力。
在人类有意识地参与狗的驯化之前,犬类很可能是为了利用人类创造的新生态位而进行了自我驯化,这也增添了狗能够进入人类家庭并成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自我驯化假说(Self Domestication Hypothesis)是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狗作为自然选择的产物或副产物而驯化多代的过程。
黑尔等人[8]提出狗自我驯化的两步模型(Two-Step Model)。第一步是在没有人类有意让犬类进行繁殖的情况下,犬类进行了自我驯化。与攻击性较强的犬类相比,攻击性较弱的犬类可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活动,吃人类提供的食物,并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和安全感。这一步使第二步——包括人类有针对性地、有意识地培育攻击性较弱、亲社会性较强的狗——成为可能。
与狗相似,猫进入人类家庭也包括人为的驯化和自我驯化。考古研究表明,大约5300年前,猫被啮齿类等小动物吸引到中国泉护村,这些小动物在农民种植、食用和储存的谷物中觅食。[9]尽管这些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但有证据表明其与农民之间存在亲密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互利性质。在中国传统农村,猫狗最初主要发挥工具性的功能,比如狗看家护院、猫捕鼠。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城市中的猫狗数量开始增多,并逐渐发挥情绪性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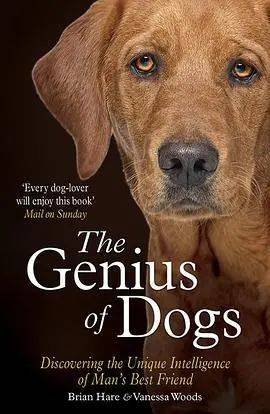
The Genius of Dogs, Brian Hare / Vanessa Woods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5
猫狗与家人的依恋和互动
大多数伴侣动物的主人都认为他们与伴侣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关爱的、亲密的或如家人一般,这种人与动物的联结(human-animal bond)建立在实践和情感上的彼此关怀、保护和安全感上。鲍尔比(John Bowlby)将“依恋”(attachment)描述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联结倾向,婴儿最初的依恋对象通常是其主要照料者,表现为婴儿强烈希望与照料者保持身体上的亲近,与照料者分离时表现出痛苦的行为。
研究者发现,依恋存在于所有年龄段的人之中,也包括人与伴侣动物的关系。人与伴侣动物的依恋符合人与人的依恋的四项标准[10]:
(1)希望接近依恋对象,
(2)从依恋对象那里获得情感支持和慰藉,
(3)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
(4)在分离时经历痛苦。
猫狗可以成为人类的依恋对象,人类也可以成为猫狗的依恋对象。一些猫狗离开主人时也会产生与小孩离开父母一样的分离焦虑,与主人再次相聚时则表现出积极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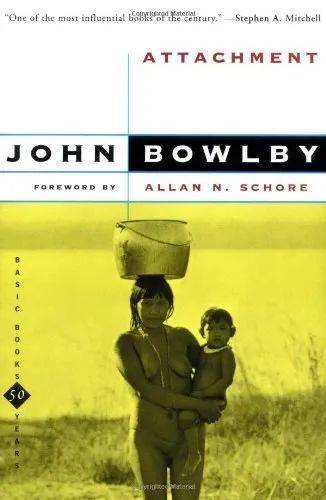
Attachment, John Bowlby
Basic Books 1983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爬行动物被作为伴侣动物饲养,但是由于各国普遍缺少针对作为伴侣动物的爬行动物的医疗和照护资源,爬行动物也缺少前文提到的驯化和自我驯化的长期过程,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公众对“爬宠”的健康和福利状况表示担忧。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主人对爬行动物的情感依恋程度与对传统伴侣动物的情感依恋程度相当。[11]此外,主人对蜥蜴的依恋程度高于蛇或乌龟,对蛇的依恋程度高于乌龟。这项研究揭示了人类与爬行动物之间也存在强烈的依恋关系,爬行动物不佳的健康和福利状况可能不是因为主人依恋的缺乏,而是因为缺乏相关的饲养和照顾知识。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动物都有可能成为伴侣动物,但是从动物福利的角度出发,人应该为伴侣动物提供必要的生存和幸福保障,才能保证人与伴侣动物都能在这段关系中形成安全的依恋,获得积极的“宠物效应”(Pet Effect)。
“宠物效应”这一观点认为拥有伴侣动物可以改善人类健康,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流行,当时有报告称,拥有伴侣动物可以改善心肌梗死的存活率。从那时起,学者就伴侣动物对其主人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12]
大量研究表明伴侣动物对人的情感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可以缓解主人的孤独感,提高自尊,降低抑郁程度,提高生活满意度和意义感。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拥有伴侣动物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为零,甚至是负面的。[13]一些研究者还关注到伴侣动物可能为主人带来对自我的消极感受和对自己作为主人的能力的质疑。[14]
曾经有人认为,一个人养伴侣动物是为了弥补其在子女、兄妹、朋友或者夫妻等人际关系中存在的缺陷,一些社会偏见也这样看待养伴侣动物的无儿无女的夫妇、未婚个体和丧亲的老年人。当一个人处于变化、混乱和失去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伴侣动物可能是可用的、可靠的、稳定的依恋对象。
然而,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缺陷补偿”的观点,是否拥有伴侣动物的最佳预测因素并不是孤独感或不安全感等个人特征。有研究表明,童年时期是否拥有伴侣动物是预测一个人成年后是否养伴侣动物的有力因素。[15]
童年时期也是一个人对他人和其他动物发展同理心的关键时期,这种同理心是亲社会行为的心理基础。[16]伴侣动物出现在课堂还能够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伴侣动物也能在学校和家庭中提高儿童的社会情感技能。[17-18]
从超越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长期接触和照顾伴侣动物有可能扩大人们对其他动物的关注,与伴侣动物的积极关系有时会促使人们对其他动物做出更积极的判断。[19]
伴侣动物作为其他物种的友善大使,帮助我们超越人类至上的物种主义偏见,达至“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在全球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锐减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这种超越对人类单一物种的福祉的关注,将更多的物种视为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有助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Animal是一本致力于探讨动物世界各种现象、行为及保护问题的专业刊物
结语
如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猫狗与人的跨物种关系并非坚不可摧。伴侣动物可能因为生病或衰老而离开一个家庭,伴侣动物的去世会让其主人感受到与亲人去世相同的哀伤。伴侣动物可能因为一些小的意外(如过年的鞭炮声)受到惊吓而走失,可能因为主人搬家、离婚等变故而遭到抛弃[20],也可能仅仅因为主人觉得“不再喜欢”“太麻烦”等原因而沦为流浪动物。
繁荣的伴侣动物产业背后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流浪动物。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1年,我国流浪猫的数量高达5300万只,流浪狗的数量高达4000万只,流浪猫狗的数量合计接近1亿。
这些流浪动物在城市生态中的角色和作用,及其应该如何被对待和管理,正逐渐成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的话题,连同城市伴侣动物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管理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例如,在生态学上,野生动物保护范式将流浪猫视为入侵物种,城市生态范式则考虑城市生态下流浪猫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丰富互动。[21]
超越人类的视角也为理解家庭以外的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它在人文学科中受到欢迎,被称为“动物转向”,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向动物中心主义(承认动物是完全或部分主体)转变。这种视角模糊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开辟了探索当代世界如何存在和成为的新视角。
例如,传统的社会工作是围绕人开展的,在后人类中心社会工作(Post-Anthropocentric Social Work)或后人类社会工作的框架下,伴侣动物、伴侣动物与人的关系、多物种家庭以及流浪动物也会被纳入社会工作的关注范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一些学者更喜欢用 "伴侣动物" 一词, 而不是 "宠物" , 并将这种关系中的人类成员称为 "监护人" 或 "共同居住者" , 而不是 "主人" 。"宠物" 这一称呼轻视了其他动物在关系中的作用, 而 "主人" 这一称呼则加深了其他动物作为 "物品、财产或可支配财产" 的地位。新术语反映出人与其他动物界限更模糊的趋势, 但也有学者对这一称呼提出批评。
[2] CHARLES N. "Animals Just Love You as You Are" : Experiencing Kinship Across the Species Barrier[J]. Sociology, 2014, 48(4): 715-730.
[3] HARAWAY J D. When Species Meet[M]. Minneapolis: Universt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4] FREEDMAN H A, WAYNE K R. Deciphering the Origin of Dogs: From Fossils to Genomes[J]. Annual Review of Animal Biosciences, 2017(5): 281-307.
[5] HARE B, BROWN M, WILLIAMSON C, TOMASELLO M. The Domestication of Social Cognition in Dogs[J]. Science, 2002, 298(5598): 1634-1636.
[6] BRAY E E, GNANADESIKAN E G, HORSCHLER J D, LEVY M K, KENNEDY S B, FAMULA R T, MACLEAN L E. Early-Emerging and Highly Heritable Sensitivity to Human Communication in Dogs[J]. Current Biology, 2021, 31(14): 3132-3136. e5.
[7] UDELL A M, DOREY R N, WYNNE D C. What Did Domestication Do to Dogs? A New Account of Dogs'Sensitivity to Human Actions[J]. Biological Reviews, 2010, 85(2): 327-345.
[8] HARE B, WOBBER V, WRANGHAM R. The Self-Domestication Hypothesis: Evolution of Bonobo Psychology is Due to Selection Against Aggression[J]. Animal Behaviour, 2012, 83(3): 573-585.
[9] HU Y, HU S, WANG W, WU X, MARSHALL B F, CHEN X, HOU L, WANG C. Earliest Evidence for Commensal Processes of Cat Domestic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1): 116-120.
[10] ZILCHA-MANO S,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Pets as Safe Havens and Secure Ba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12, 46(5): 571-580.
[11] HADDON C, BURMAN H O, ASSHETON P, WILKINSON A. Love in Cold Blood: Are Reptile Owners Emotionally Attached to Their Pets?[J]. Anthrozoös, 2021, 34(5): 739-749.
[12] AMIOT C, BASTIAN B, Martens P. People and Companion Animals: It Takes Two to Tango[J]. BioScience, 2016, 66(7): 552-560.
[13] SCORESBY J K, STRAND B E, NG Z, BROWN C K, STILZ R C, STROBEL K, BARROSO S C, SOUZA M. Pet Ownership and Quality of Lif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Veterinary Sciences, 2021, 8(12): 332.
[14] HAWKINS D R, HAWKINS L E, TIP L. "I Can't Give Up When I Have Them to Care For" : People's Experiences of Pet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J]. Anthrozoös, 2021, 34(4): 543-562.
[15] IRVINE L, CILIA L. More Than Human Families: Pets, People, and Practices in Multispecies Households[J]. Sociology Compass, 2017, 11(2): e12455.
[16] GU X, XIE L, BEXELL M S. The Link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 Animals and Empathy with Humans in China: Mediation of Empathy with Animals[J]. Anthrozoös, 2024, 37(1): 75-88.
[17] CHAN H M C, SCHONERT-REICHL A K, BINFET J-T. Human–Animal Interac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A Scoping Review[J]. Anthrozoös, 2022, 35(5): 647-692.
[18] WAGNER C, GROB C, HEDIGER K. Specific and Non-Specific Factors of Animal-Assisted Interventions Considered in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931347.
[19] POSSIDÓNIO C, PIAZZA J, GRAÇA J, PRADA M. From Pets to Pests: Testing the Scope of the “Pets as Ambassadors” Hypothesis[J]. Anthrozoös, 2021, 34(5): 707-722.
[20] GU X, BEXELL M S, WANG B. Attitudes Toward Nonhuman Animal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J]. Anthrozoös, 2022, 35(2): 219-235.
[21] GU X, ZHANG Z, GUO P, NI A, WANG B, XIONG X, LIU Y, WANG L. A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on Community Cats'General Health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with Residents in Urban China[J]. Animals, 2024, 14(3): 52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0期,作者:顾璇(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