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际社会对于基辛格逝世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反应:中国民众表示深切哀悼,但巴勒斯坦民众及声援者却在欢呼。王逸舟认为,作为当代最有名的外交家之一,基辛格身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复杂性,以及身上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正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谓“极端的年代”所具有的两极冲突的体现。
2. 王逸舟认为,基辛格为世界留下了三种宝贵遗产。第一种是外交遗产,基辛格将外交视为一种艺术,发掘了外交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张力:既可以不择手段,也可以巧妙迎合;第二种是均势遗产,他同样善于在铁腕与和平的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第三种遗产是基辛格创造的历史本身,当下我们面对现实冲突时仍能引起共鸣。
3. 王逸舟指出,基辛格的盲区和毛病是忽略了国际制度、多边主义或小国利益。但是他也让人看到了外交的塑造作用,启发了更加全面的外交观点。作为一种巧实力、智慧、想象力,和在不可能中发现可能性的艺术,外交其实还有很大余地,只不过当下被强权式的简单粗暴的外交方式所遮蔽,如美国蓬佩奥式的霸凌式外交,这让外交沦为一种工具,我们要重新发掘大外交的潜力。
对话丨侯逸超
编辑丨刘锦恩

极端年代的体现:基辛格身上的张力
《凤凰大参考》: 我们今天想请您谈谈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基辛格式“秘密外交”在今天有怎样的价值?
王逸舟: 英国有一位已过世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极端的年代》),他说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有最好的人类科技进步,也有最糟糕的两次世界大战,还列举了很多这种极端的现象。基辛格作为一个当代最有名的外交家和外交史家,他身上确实给我们体现出这种张力。他留下的外交遗产,不管是思想遗产,还是“秘密外交”的这种行动方式,都是过去这个极端的世纪在他身上的体现。在他过世短短的一天中看到的两极反应,就能够作为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点。
中国一直将基辛格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首先是由于他是中美关系破冰的一个使者。毛泽东当年用谐音称他为“寄信鸽”,意为“寄信的鸽子”,实际上表明他是中美关系破冰的一个重要使者,打开了交往的大门。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普通的干部和公众心目中,基辛格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比较好的:他使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了,特别是中美关系使中国的发展环境、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

▎ 1973年2月22日,北京,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亲切交谈。

▎ 1975年10月30日,北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邓小平。
但中国一般的公众可能并不知道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被“深恶痛绝”的,也做了很多中国民众不知道的,但是可能在道义上很可耻的、很可怕的事情。比如我看到今天巴勒斯坦民众,包括纽约的巴勒斯坦声援者为他作为一个美国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的去世而欢呼雀跃,这是多么大的仇恨。其实,未必是基辛格个人直接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他更多地是一种象征,为巴勒斯坦人对当下美国政策的不满的提供了一个宣泄出口。
再比如今年是智利领导人阿连德被暗杀50年。今年在智利从官方到民间举行了很多抗议活动,声讨50年前美国中情局指使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及对很受民众爱戴的智利民选领导人的暗杀。虽然基辛格对暗杀阿连德一事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但各种信息披露,正是基辛格直接授意中情局对许多不满美国的中美洲政权实施政变。其中,阿连德当然是最突出的一个。

▎1975年12月,基辛格、福特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和外长马利克会面,商讨入侵东帝汶的计划 。
此外,除了特别痛恨基辛格的阴谋权术之外,我看到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曾经是美国盟友的一些国家的有趣回忆:伊朗的前国王巴列维,他说他当时特别没有尊严的请求基辛格帮帮他,而70年代后期伊斯兰革命的时候,基辛格觉得他大势已去,就完全把他踢开让他流亡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辛格也对当时的南越政权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世界对基辛格去世两极化的反应,其实也正让人感到基辛格的复杂性。他的这种复杂性使我感受到他身上的张力:既让人爱,也让人恨。 这在全世界的外交官中并不多见。比如蓬佩奥、特朗普,很难看到他们还有什么让人觉得喜欢的地方。而基辛格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他们。这个百岁老人的过世,包括他一辈子大量的著述与外交成就,将持续使人兴趣盎然。

▎ 2021年4月24日,北京,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图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通过视频致辞。

基辛格留下了三种遗产
王逸舟: 我个人觉得,基辛格留下了三种重要的遗产。 第一个遗产是外交的。他身上体现出外交作为一种权术——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种“艺术”——所具有的极大的潜力和张力。 不管是外交方式上的不择手段,还是他通过巧妙迎合对手最终实现的外交目标,都达到了任何国家任何外交官在这方面的极致。所以,当人们提到外交是一种艺术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基辛格的名言,想到他在这方面的实践。 外交作为一个重大的手段,作为当代的一种突出的国际交往的方式,是他身上留下的重要的遗产。
另一个遗产是均势的。 基辛格确实在当代均势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为各国的外交史所铭记,提供了政治家、战略家们奉行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可以说是当代在这方面的一个鼻祖,他身上有着德国的基因。而早年他对于欧洲著名政客,如奥地利的梅特涅、德国的俾斯麦等在18、19世纪纵横捭阖的人物有非常精深的解读,所以他身上也留下了丰富的均势遗产。我们每现在讲到他一个重大成就,仔细想想都是在两极之间找回了一种特殊平衡。比如他曾因推动美国撤出越南获得诺贝尔奖,但其实也是他当时帮助尼克松在越南实行最大规模的轰炸,并造成了很多人死亡。

▎ 1975年,基辛格与福特总统秘密批准让美国支持的印尼军队入侵东帝汶。超过10万东帝汶人口被饿死。
他让当时的越南人在接 受他的和平提案或者撤军提案之前,先让他们感受到了最可怕的轰炸、最残酷的来自美军B-52的打击。 他把这两种手段都做到了极致。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与北越外交官黎德寿会面。他们的谈判达成了美国在越南停火的协议。两人共同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但黎德寿拒绝领奖。
包括他在中东的外交,比方说他对埃及的萨达特或者是叙利亚的阿萨德这些领导人,心里其实非常厌恶的。基辛格尤其是非常不喜欢阿萨德,但是他又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朋友,让他们觉得美国是在为他们着想。他用欺骗的手段,最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使美国在中东实现了某种平衡。他不是单纯的去说好话、办好事,他一定是让对方感受到恐惧,再实施他的手段。
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往往觉得他是中国的老朋友。其实基辛格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讲,他有时对中国人的这种真诚好客、对友谊的执着感到很困惑。因为他并不真的是中国人民心目中那种两肋插刀、始终如一的友好使者,不是。他只是从利益的角度看,当时美国需要跟中国拉近关系,需要在与苏联的博弈对抗中间来分裂削弱苏联的力量。
而且,关于他在当代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他曾一再表明他并不是所谓“亲大陆”,而只是因为台湾太小了,美国人必须要顾及重大的中国崛起,将此作为美国最大挑战的大的视角,而不要因小失大。他始终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复杂的一种挑战。他也非常清晰的辨识出俄罗斯的位置,虽然他对于普京也很感兴趣,但是他很清楚地看到,普京的俄罗斯实际上处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衰败的轨道上,对美国来说它仅仅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能构成一个全方位的未来式的综合性挑战,而中国在他看来是这种全方位的综合式挑战。所以说到底他并不是拜登、奥巴马。奥巴马、拜登这些人很不喜欢他,但是他跟特朗普又有某种心灵相通之处,就是让美国重新伟大,或者让美国在这种看上去很糟糕的、衰败的轨道中间,不要犯更大的错误。

▎2017年5月,基辛格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特朗普曾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拜访过基辛格。
他的这种为了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而避免被其他的大国、其他大的事件、其他大的冲突地区所误导的“走钢丝”式的努力,常常被人们后来简单的概括为“均势”,其实可以说是过于简单化了。均势背后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国力的对冲与平衡,它包含了特别多的因素,是另一种我们需要看到的他留下的外交遗产。
基辛格的伟大的遗产还包括了他所创造的历史。像中美对话和解、越战、美国巨大创伤难题的消弭,包括中东当下看到的巴以冲突中人们的束手无策,看到这样一些人们眼下的焦虑、眼下的无奈、眼下的愈演愈烈的对抗式冲突,人们不禁想起基辛格这位智者。他的外交遗产中的可以挖掘的价值,仍然值得回味和思考。

今天我们还需要外交吗?
王逸舟: 还有一个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个人很不喜欢他“秘密外交”,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杀人如麻,很多完全是很暗黑的东西,甚至暗黑都不足以形容那种可怕。但是他有一种逻辑跟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他觉得国家的这种所谓的道德——如果说有道德的话——跟普通人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他所说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政权,国家的法存在的意义,一切都以他所追求的根本的力量为宗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坏事情在国家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开展:暗杀、牺牲盟友或欺骗对手。但是背后又有一种让人很着迷的点,他确实是个新旧时代的一种复合体。他的身上又体现出某种新时代的、让人觉得很有趣的、就我个人而言很喜欢的东西。
我记得在20多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时小布什的战争内阁提出了很委婉的批评,书名是“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 当时的布什内阁就被认为是战争内阁,铁三角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当时几乎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上的霸凌式的美国强权——山姆大叔挥舞大棒子在中东各地打。
他提出了一个疑问,提出了一个批评,虽然很委婉,他说美国还需要外交吗?换句话说,他把外交看成是一种远比军事手段,比单纯的强权霸凌要复杂得多的一种东西,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是很有意思的。

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民粹主义高涨的环境下,在全球化停滞时期普遍的排他、以大欺小的霸凌行为。军事上使用蛮力的风气上升,使得外交在现在越来越多地沦为一种简单的工具,甚至是陪嫁或者是奴仆。
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可以重复基辛格的这个问题——外交还有用吗?我们还需要外交吗?在大国博弈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在力量,特别是军事的、经贸的、器物的力量看上去很流行的同时,作为一种巧实力,作为一种智慧,作为一种想象力,就是在不可能中发现可能性的这种艺术——我们叫外交——它还有多大的余地?

▎1971年访问中国期间,基辛格与助手在起草公报途中打乒乓球消遣。
我觉得基辛格的遗产给人们一个巨大的想象的空间,我们还应当继续发掘外交。 外交实际上有巨大的空间,只不过当下被迷雾、被阴影,被某些这种霸凌式的或者强权式的,或者是崇尚单纯力量型的,简单粗暴的方式所掩盖、压倒、遮蔽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基辛格的思想中间,其实还有一种对未来世纪有启发的观点,虽然他自己对于制度不屑一顾,对于全球主义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很少使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多边机制。 但是我个人认为, 也许他很不喜欢外交的另外一面,但是他无形中启动了它们。
就是外交在新世纪的塑造作用和主导力 ,随着技术进步、人类知识的提升、教育水平的发展,外交的价值未来实际上有更大的空间。 人类的进步,哪怕有曲折,哪怕有短时间的回转、逆转,但是包括像道义、像制度、像外交,在人类进步长河中间,类似于康德主义,或者我们古人所说的“大道”,孙中山所说的这种“潮流”,实际上还是会激励着外交积极的一面。
《凤凰大参考》: 我感觉到其实和您上次讲的外交金字塔概念有点像(王逸舟曾在5月的专访中提出,外交决策层属于塔尖,而地方外交、民间外交属于塔身。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外交体制是多层级的。塔尖要特别高,塔基要宽大,塔身要非常厚,各个层级要衔接好——编者注),其实在现在越来越民主化的一个时代,外交的维度会变得更多,或者说它发挥作用的方面会变得更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逸舟: 是的,而且我自己平时看基辛格的作品,发现其实他有盲区的。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均势论的推动者、实践者,他确实忽略了国际制度、多边主义或全球化所包含的某些新的动能、新的要素,这很复杂。
对于全球的进化过程,全球制度的巨大潜力,包括进化——从传统的尚武到后来外交的复杂转型,再到未来人们的道义、人们的教育和新的时代意识进化,这个过程基辛格他是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觉得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历史的循环,看到大人物的纵横捭阖,看到秘史里的心机,但是实际上他给人看到了外交了不起的塑造作用,看到外交在新的时代转型的价值,这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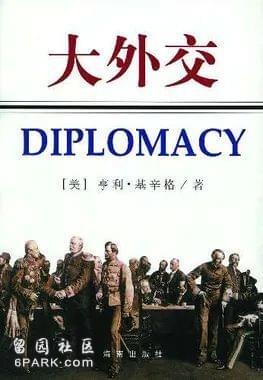
《凤凰大参考》: 我感觉到他的书虽然叫《大外交》,但是从这个维度来看其实还不够大。
王逸舟: 对,我们不能犯类似像特朗普这种错误,就是追求片面的蛮力、实力,或者是外在的器物力,如军舰、GDP等的狠劲。其实从基辛格身上你能读到非常睿智、非常复杂、潜力无限的想象力。这对大国的领袖,大国的外交思想,大国的公民很有启发。这方面我们不要学美国的那种蛮力,以及蓬佩奥之流的这种霸凌。

基辛格实际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他对全世界的小国、弱势群体、平常看不见的阶层,都是不屑一顾的。 他看到的都是那些大的力量。但是你又觉得他所创造出来的神话,创造出来的巨大外交奇迹之中本身包含了跟初衷可能相反的效果,包含了巨大的潜力。相比时下很多很简单化的结构、策略或者手法,我觉得让人感觉到有趣并值得回味地方还很多。
《凤凰大参考》: 谢谢王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