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18世纪的清代普通女性,可能会经历什么?在清穿剧里,常见的叙事是庶女逆袭成为帝后。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她恐怕很难活到成年。
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普通女性的生活,仍然了解不多。更多时候,我们能了解到的,除了明清时期那些跻身1%的精英阶级女性留下的诗词记录,就是男性精英阶级对于当时女性生活的讲述。在性别史研究领域,性别化文本一直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制约因素。
而历史学家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找到了进入清代下层百姓生活的入口。在博士求学期间,他经由导师介绍接触到了一批清代司法档案,这些案例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物画像:乞讨者、苦力、鳏寡、小偷、妓女……占据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有女性,也有边缘化的男性,他们因为“性”的越界而在历史中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此后的三十年里,苏成捷将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泡在了帝制晚期的司法档案里,出版了两本在清代法律史、社会史与性别史领域影响深远的书。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通过厘清18世纪围绕“性”问题的法律变化,呈现了下层人在性行为、社会性别角色与家庭生活方面的丰富历史。第二本《清代中国的一妻多夫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则进一步聚焦那些为了生存而违反儒家性别伦理与官方斡旋的清代司法案例。
今年5月,《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首次引进出版。我们和他做了一次对谈,聊的主题是他这几十年来对于清代“性”问题的研究,以及从历史到当下的性别问题。在谈及清代女性的生存选择时,他打了一个比方:
“有一句英语谚语,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if all you have is lemons, make lemonade(如果生活只给了你酸柠檬,那就做一杯柠檬汁吧)。对于生活在当时的女性而言,她们的选择不像是藤校学生选择想学什么专业的情况,而是说在你面前,有三个选择,它们都是坏的,你只能从中选了那个相对不那么坏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现实。”
以下是青年志对苏成捷的专访。
18世纪、背德者与他们的“性”
青年志:从早期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到2015年《清代中国的一妻多夫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再到即将出版的帝制晚期的跨性别研究,你一直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社会史,尤其是“性”(sexuality)问题。最早是什么促使你进入这一课题的研究?
苏成捷:在博士第一年的研讨会上,我当时的导师黄宗智向我们介绍了一批司法档案,这些资料从前很少有人注意过,包括一部分巴县档案、一套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清代中央政府档案集,里面囊括了很多《刑科题本》的资料。看完之后,我被档案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几乎所有案例都是关于普通人的,有一般的农民、穷人、乞丐、苦力、鳏寡……占据了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有关他们的历史研究比较少,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文盲,没有留下日记、笔记,当然也不会写小说什么的。而这些司法档案中有他们的口供,也有卖身契之类的民间文献,这让我终于有机会去接近18世纪普通人的具体生活经验,听到他们的“声音”。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也是这些资料中最有趣的部分,都是关于“性” (sexuality)问题、社会性别和家庭生活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在中国性别史方面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关于精英阶级的。仅有的例外是由人类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台湾地区和香港新界完成的田野。但毕竟这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们有可能借助这批资料来做一项全新的社会史研究,将“性”(sexuality)问题放在故事的中心,让女性、也包括边缘化的男性成为故事主角。
青年志:这也是我读完你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的感受,你对清代社会“性”问题的关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下层男性的,尤其是“光棍”。
苏成捷:当我第一次对中国的性别史感兴趣的时候,也是在我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作品的时候。她在关于农民起义的书《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就谈到了“光棍”现象:没有妻子,也没有土地的边缘化男性农民。
因此,你也可以说,我最早对性别史的兴趣来自于那些在当时社会等级制度中最为贫穷、最受侮辱、也最被剥削的男人,比如“光棍”。尤其是在阅读司法档案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忽视他们,因为他们不断地在案件中出现。
青年志:关于“光棍”问题,我们之后细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是你的第一本书,脱胎自博士论文。你在这本书中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有关“性”问题的法律从身份地位展演转变为社会性别展演。关于这点,能否展开聊一聊?
苏成捷:这本书的核心目标,就是去理解18世纪清代有关“性”(sexuality)问题的法律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结论是你提到的这个公式。
我们知道,帝制中国的法律框架是由身份等级来构建的。瞿同祖在《清代法律中的等级制度》中就指出:官吏、平民(=良民)和贱民这三大身份等级构成了法律的框架。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受到不同的性道德标准与家庭道德规范的约束。“性”(sex)是展示身份等级差别的一种关键性标识,而对性行为的规制是为了确保人们依照不同的社会地位相应行事。
那么在清代之前,贱民意味着不自由的身份,因为他们负有服劳役的义务。对于贱民中的女性(包括水户、娼户、乐户等,也包括婢女——无论她们结婚与否)而言,这还意味着她们需要提供娱乐服务和性服务。因此所谓的贞节观和婚姻规范并不适用于他们,更多是良民和官吏需要恪守的规制。与此同时,相对于良民,对官吏的性道德要求也会更高。比如一般的良民男性可以宿娼,但官吏宿娼是犯罪。再比如,良民寡妇可以在丈夫去世三年后合法改嫁,但官吏的寡妇就不行。
但到了18世纪,大部分民众已经是自由良民了。野心勃勃的雍正帝登基之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将原本已经占据少数的贱民提升为良民。与此相应的,他将此前针对良民和官吏的性道德标准和刑责标准扩展适用于所有人。于是,我们就看到,官方对“性”的规制不再是根据此前的身份等级,而是无差别地对于社会性别角色展演的规制。
什么是社会性别角色展演呢?——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是妻子和母亲,所有的男性都应该是丈夫和父亲,正所谓“良家妻女”、“良民子弟”。
具体到法律层面,一方面体现为对女性贞节的强调,包括妓女入罪化,也包括官方提高了强奸罪的惩罚力度——如果一名男性调戏了一名女性,这名女性因为见不得人而自杀,那么法律就认为这名男性对这名女性的死负责,他触犯的不再是犯奸罪,而是杀人罪,将被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则是“光棍”成为清政府忧惧的人物形象——他们是游离于家庭秩序之外的无赖汉。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僵化的儒家道德秩序理想。后来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些举措不切实际,也并没有奏效。
贞节崇拜与“光棍”威胁
青年志:具体而言,清代的贞节观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苏成捷:在强奸法这一章,我谈到强奸法是如何变化的。毫无疑问,从明朝开始,女性的贞节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新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新的士绅阶层崛起的一部分。士绅阶层与新儒家性别制度有关,即“男女有别”,女性处于内室,性别隔离,缠足盛行。这与唐代或更早期的态度不同,唐代没有缠足,在唐朝宫廷里,妇女会骑马、做运动,而当时的美人是胖子。
到了18世纪,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围绕这些问题的法律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一方面是为了更新法律以适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对新的社会性别展演原则的强调。
清代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因素。明代的贞节崇拜,主要是地方精英的现象,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豪门大户和地方郡县会在他们的家族、宗族或是郡县,旌表这些贞节女英雄。因此,在明代方志中你会看到有关烈女的记录,她们的地位不低。但在那个时候,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并没有那么多的参与。
清代的一个新变化是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亲自参与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把这种精英价值观移植到了权力中心,与皇帝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看到,是皇帝发出诏书来旌表烈女,是皇帝向这些家庭颁发奖金,也是通过皇帝,地方官和县令才可以下达相关的举措。
青年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苏成捷:我认为部分原因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关。当清征服明帝国,他们拥有庞大的帝国,但统治者满洲人是非常少的少数。
那么他们如何统治自己的帝国?基本上是吸收了不同民族的政治精英。
他们又是怎么拉拢这些精英的?清政府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制度、价值观,通过保留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给了那些精英们在帝国的某种投资。所以蒙古人一开始是有自己的法律的。蒙古贵族与清朝皇室联姻,使得早期他们在蒙古享有很大的自治权。
清政府保留了郡县制度,也保留了科举制度。官员队伍里的大多数由汉人组成,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然后为清政府服务。他们没有试图把汉人变成满族人,唯一的改变是剃头、留辫子。除此之外,汉人完全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社会制度等,特别是早期,清政府对每个地区的统治都极为轻微,而各地区的地方精英则是代表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
也就是说,虽然清政府是在满洲人的统治,但他们基本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保存了它,加强了它,使它变得更好。通过这样做,他们赢得了大多数汉人精英的效忠。
这和贞节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清政府和汉人精英阶层的联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联盟,他们信奉儒家价值观、制度和道德观。通过将旌表制度、女性贞节与帝国的皇权中心联系在一起,某种意义上,他们再次捍卫了这些汉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汉人精英与清代统治者的关系也更为紧密。这是清代真正的变化,也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其他学者也可以提出他们的看法。
青年志:在这本书里,你提到“光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威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苏成捷:这个问题涉及儒家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在儒家的道德和社会秩序观中,每个人都应该归属于规范性的家庭关系网络之中,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被社会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一个男性可能是父亲的儿子、兄长的弟弟、妻子的丈夫、子女的父亲,等等。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男性在这样的家庭中得到了适当的教育,那么他最终就会被卷入或“困”在各种关系网中,而每种关系网都有自身的期望和责任。身处其中的人必然也会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中表现得恰如其分,成为忠于皇帝、遵纪守法的臣民,就像《论语》说——“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但“光棍”是对儒家道德理想的背离。光棍意味着游离于家庭之外,没有社会化,没有纪律,与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毫无关系。从正统的儒教观点来看,这样的人本质上就是危险的。
在 18 世纪人口过剩、农村贫困、性别比例恶化以及单身男性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光棍”这一幽灵般的存在就成为了国家和精英阶层偏执幻想和恐惧的焦点。
法律的阳具中心主义
青年志: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有一条贯穿的线索,就是被你称之为彻底的阳具中心主义。为什么选用了这个概念?从明清时期对“性”的规制方面,如何理解你说的这种阳具中心主义?
苏成捷:几乎所有父权法律体系都有阳具中心主义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相似。
我认为,18世纪发生的从身份地位展演到性别身份展演的变化以及清政府对“光棍”的恐惧,让阳具中心主义变得更极端。“光棍”被塑造成绝对的男性掠食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光棍”这个词也是生殖器的象征,尤其是“棍”。如果你读过明代小说,“棍”是阴茎的俚语。
但如果从历史长程来看,情况一直是这样,中国强奸法的历史,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强奸法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美国或印度等地,也都极为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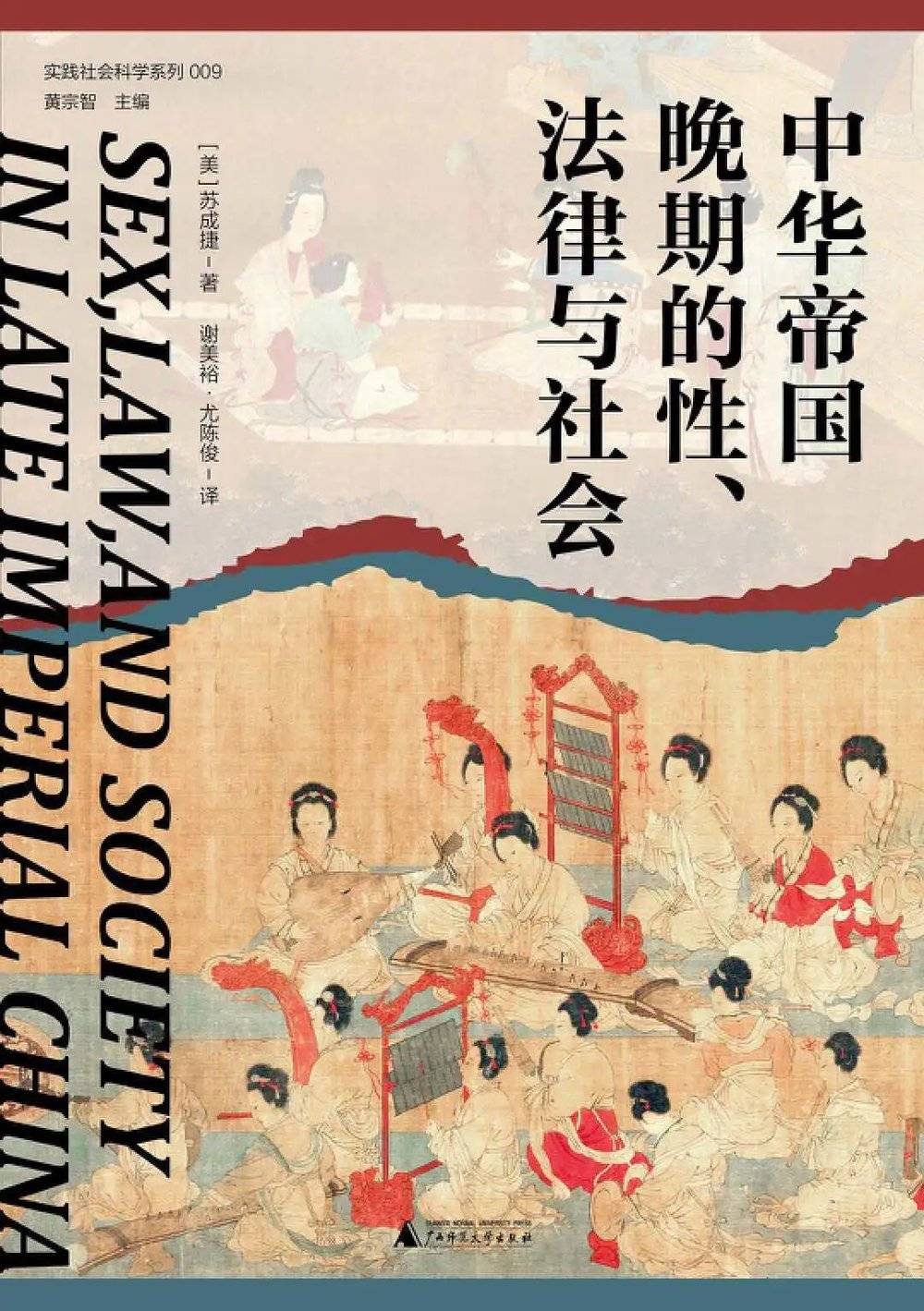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作者:(美)苏成捷
译者:谢美裕/尤陈俊
大学问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
青年志:这种极端体现在比如说在强奸的案子里面,与其说判官认为男性强奸是犯罪,不如说是对女性贞节的审查。
苏成捷: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强奸是对一个人的完整性和身体主权的攻击,侵犯了个体的权利和独立人格。但这不是传统社会对强奸的看法。
强奸在当时主要被定义为侵犯丈夫或父亲的特权和权利。甚至于在某些传统社会(不仅限于中国),如果一名男子实施了强奸,他只需向父亲、丈夫支付一笔赔偿或者答应娶被强奸女性为妻就可以了。
因此,我认为,理解清代强奸法的部分挑战在于如何抛开我们现代人对权利的看法,试图从当时社会的司法角度来理解这些官员是如何理解这一罪行的,它和前代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的一点是,当一个女人说她被强奸了,她的贞节首先会受到审判。
正如前面提到的,明清时期强奸罪的真正变化,在于刑罚提高了,变成了死刑。这项法律始于明朝,到了清朝则更加极端。死刑是重大罪行,这意味着施加在妇女身上的压力大大增加了,她必须证明自己足够贞节,才值得让加害者被处死。如果她不够贞节,就没有理由将他处死。因此女性要证明贞节的成本变得更高。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时,就能理解,这些清代的司法官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贞节,但同时因为要判处死刑,所以对贞节的审查就变得更为严苛。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非常奇怪,相当于是将处死强奸犯视为对女性贞节的一种奖励。
青年志:你在书里还讲到有一些女性可能也会利用贞节的话语来谋取生存空间。
苏成捷:对于拥有财产的寡妇,是这样的。因为根据法律,寡妇不能被迫再婚。因此,如果一个寡妇有足够的财产,她相对可以独立自主,通常也不会想要再嫁,除非是爱上了别人。在许多案例中,寡妇会用贞节话语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但夫家也会用贞节话语来攻击她们好不容易拥有的独立性。
青年志: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个寡妇出轨了,还怀了对方的孩子,但她依旧可以利用贞节话语去讲这个孩子是从天而降,甚至赢了这个官司。
苏成捷: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些案件中的女性知道,如果她们能保持贞节的名声,她们就能说服地方法官,就是安全的。但如果做不到,那就完蛋了。这么做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追问,这些女性用贞节话语制定战略,最终真的是为了贞节吗?贞节只是一种谈论利害关系的方式。而那些官员其实也心知肚明。
我曾在中国多次遇到一些本应更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但当我谈到招夫养夫(注:贫困家庭为了生存外找男人到家同居帮衬,用性换取外来男性的劳动力,组成一妻多夫关系)时,他们会说那只是一群罪犯,人数非常少,因为中国女性都非常重视贞节。他们真的相信这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我也想问问他们,这些观察究竟是基于什么事实?电视剧吗?即使他们读过明清小说,大概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
清代同性性关系——污名与抹除
青年志:在《关于被鸡奸男性的问题》这章中,你对鸡奸者和被鸡奸者在司法档案中的描画,尤其是被鸡奸者的污名化,让我想起赛吉维克(Sedgwick)提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和同性恋憎恶。我很好奇这种被鸡奸者的污名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苏成捷:我认为,被鸡奸者的污名化是厌女症的一种表现。因为它的范式是,在父权社会中,男性主导女性,女性为男性服务,繁衍家庭。而成人的性别角色是由婚姻和生育来定义的。因此当男性被插入时,就被视为一种耻辱——这是将他女性化。
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性性行为的性规则是非常严格的:一方插入,一方被插入。有行奸者,有被奸者,非常死板,而且几乎总是年长的男性插入年轻的男性。但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性行为不一定会那么简单。但它在当时被描绘的方式,总是遵循着这样一种僵化的等级制度。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性角色的性别化表演。年轻的男性伴侣是欲望的对象。年长的男性会彼此争夺年轻的男孩,就像他们会争夺一个女人一样。伴随而来的便是对被鸡奸者污名化。被鸡奸者通常被等同于女性的性别角色,而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性欲望,同样是将被欲望的男性与女性、或者阴柔的性别气质联系在一起。这都是厌女症的表现。
青年志:你在书中谈到了很多男性同性关系的案例,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同性关系的记录。
苏成捷:在帝制时期的任何法律文本中,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女性同性性行为的内容。
青年志:很多传统小说里提到过。
苏成捷:但它们服务的多半是男性读者,而且作者大多数也是男性。我们看到的可能更接近男性的幻想,而不是现实。这是在中国做女同性恋历史研究的挑战。关于女同性恋的历史资料往往比关于男同性恋历史的资料少得多。
青年志:为什么会这样?
苏成捷:从根本上讲,对于传统的父权社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控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接触,因为这才关系到父权社会的存续,血统、财产之类。刚才我们也谈到法律的阳具中心主义——真正重要的是男性性器官,也就是阴茎,因为它是规范性社会性别角色和父系家族延续的来源。它也是强奸和社会威胁的根源。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女性同性性行为的忽视是阳具中心主义的体现,也是厌女——女人做什么并不重要。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关心女人的性行为,不然也不会有贞节观。但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来自男人(光棍)的威胁。贞节宣传的一部分就是让女性挺身保护家庭,免受外来男性的侵害,无论是通奸还是强奸。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人们当然知道女性同性性行为的存在,但它在当时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性行为,因为不涉及阴茎。当然,这是我的假设,在事实层面上,我们很难证明为什么有些东西不存在。
有趣的是,如果你看文学作品——小说或戏剧,描写女性之间爱和性的经典方式是在一夫多妻制的大家庭中,通常包括正妻和妾或婢女。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是嫁给同一个丈夫的女性之间的爱情,就不会威胁到丈夫的性特权,也不会威胁到他的生育特权。对他来说,这可能还是一种性刺激。在小说中,尤其是在黄色小说中,女性之间的性与爱经常被描绘成丈夫和妻妾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副产品,是丈夫和妻妾发生性关系的组成部分。
在崇祯版《金瓶梅》里有一张插图,讲述的是在西门庆死后,陈经济和潘金莲、春梅有染。画面是他们三个在一起做爱,春梅和潘金莲在接吻和拥抱,陈经济在和其中一个做爱——原谅我的语言,但我的意思是,在这幅插画中,主要的画面是男人和这些女人的做爱,这些女人属于他。这同样是一种对女性性行为的淡化和抹除。
一妻多夫——边缘人的生存策略
青年志:你在第二本书《清代中国的一妻多夫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中(编者注:还未引进出版),着重探讨了清代中期的下层百姓在面临人口压力、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扩大等多重压力下,为了生存而违反儒家性别伦理的与司法斡旋的案件。你的核心观点是,一妻多夫、卖妻等行为在当时的普遍流行,反映儒家正统思想和法律中关于家庭结构和性行为规制对下层社会的穿透十分有限。从清代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理解当时下层民众这种“被统治的艺术”?
苏成捷:我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清政府非常脆弱,就像任何一个前现代国家一样,它对社会基层的渗透非常小。19 世纪的县里很可能有超过一百万人,而最多只有一个县令和几千胥吏来管理。
清代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微观管理百姓的生活。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很多事情政府实际上并不知情,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与现代国家非常不同。但即使是现代国家,也无法真正微观管理大多数人的生活。
其次,精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些招夫养夫的家庭基本都是穷人,要解决生存问题。
因此,对清代而言,你有法律制度,你有成文法,你有地方法院,但同时也有很多从未进入法院的事情。有很多事情,虽然官方认为是违法的,但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就去做了,然后在社区范围内组织管理起来,既不用上法庭,也不用让政府介入。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之外存在着巨大的行为空间。
青年志:在这本书中,你也提到不同类型的非主流家庭模式。能否展开谈谈这些非主流家庭模式?它们是否创造出了另类的性别气质?
苏成捷:例如招夫养夫有两种基本的组织方式,一种是与双方利用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达成协议,第二种,也是更常见的,是两个男人结拜兄弟,缔结同声同气的兄弟情谊。这种做法源远流长,在这些案例中,两个男人结拜之后,分享一切——资源、食物、劳动,也分享妻子。
与兄弟共享妻子的丈夫必须放弃丈夫的特权,放弃对孩子和血统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再是丈夫了。他首先是兄弟,而女人依旧是从属者,就像 “先有兄弟后有女人”。这不是儒家思想中的规范性男子气概,而是另类的男子气概,但它同样是建立在厌女症基础上的。
其实有很多说法都表达了这种价值体系。类似“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真的好兄弟不会重色轻友”等。这种另类的男性气质,可以说是“光棍”男性的理想,帮助他们缓解这种三角关系的紧张感。
婚姻、人口买卖和性工作——模糊的界限
青年志:你在第二本书中还谈到人口贩卖的问题。去年任思梅的《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也在中国出版了。她在书中认为,如果只将人口贩卖视作家庭危机时刻的生存策略,依然无法解释为何普通人会持续参与人口贩卖。使得买卖人口在中国曾如此猖獗的特殊力量是中国家族的“交易性质”。你如何理解中国家族的这种“交易性质”?
苏成捷:我一直认为,如果从穷人的角度出发,你无法清晰区分婚姻和人口买卖的界限、婚姻和性工作的界限。
为什么这么说?通常,我们会从精英价值观和法律的视角出发来看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从社会下层的边缘视角出发,首先,很多普通人的婚姻是父母嫁女儿,并收到一份财礼钱。当然他们不一定会直接将它称之为“买卖”,但下层百姓对于财礼钱的认知就是,这是对他们养育女儿的成本的补偿。这难道还不够直接吗?
再来看精英阶层的婚姻,妾和婢女从何而来?也是从穷人父母那里买来的。因此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也依赖于人口买卖。当然,丈夫是不能合法卖妻的,除非她犯过奸。而父亲为什么可以合法地卖自己的女儿?因为精英阶层对此有需求,他们需要从穷人那里买女儿,成为妾和婢女。这很讽刺。
因此,在社会尺度的两端,两类婚姻都涉及买卖。从这一角度来看,卖妻不是例外,应该被理解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婚姻和性工作。从穷人的角度来看,招夫养夫、婚内卖淫和典卖妻子等做法,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持婚姻而买卖妇女的性劳动和生殖劳动。招夫养夫是引入另一个男人来维系家庭和婚姻。婚内卖淫也是如此,是为了让夫妻双方能继续生活在一起。
所以在我看来,假装这两者没有关系是虚伪的。在当时,大多数妓女都是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要么允许她们这样做,要么强迫她们这样做。你能说性工作和婚姻之间有清楚的区别吗?这些行为都是维系婚姻的一种手段。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承认两者是彼此重叠的、彼此联系的。如果她们不这么做,丈夫可能就得把她卖了。
在思考婚姻和性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历史学家路易斯·怀特(Luise White)的《家的慰藉》(The Comforts of Home)对我影响很大。
这本书讲的是殖民时期内罗毕的劳工与性工作者组成的特殊家庭方式。从农村进城务工的男性通过劳动力获得钱物,用钱物购买女性的亲密关系。女性在获得钱物后,或奉献于家庭,或购置房产。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因为以前大多数关于性工作的学术研究都将性工作者视为简单的受害者。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考方式,有些性工作者是绝对的受害者,没有任何话语权,但在很多情况下,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路易斯·怀特的这本书就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它展示了在这种情况中下层女性能动性的复杂性。
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当我提出这两个论点时,我是在故意挑战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惯常假设。
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例如费孝通和武雅士(Arthur Wolf),他们更关注事物的分类学(taxonomy)。因此,他们想要确定什么是亲属关系,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这就要求他们在什么是婚姻,什么不是婚姻之间划定清楚的界限。
我和武雅士谈到过我的研究,他非常鼓励我,但当我谈到一妻多夫,他承认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但他希望在婚姻和非婚姻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就是故意想要模糊这两者的边界。我认为,为了反映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现实而划定婚姻的边界,是高度意识形态导向(ideological)的,反映的恰恰是规范性的精英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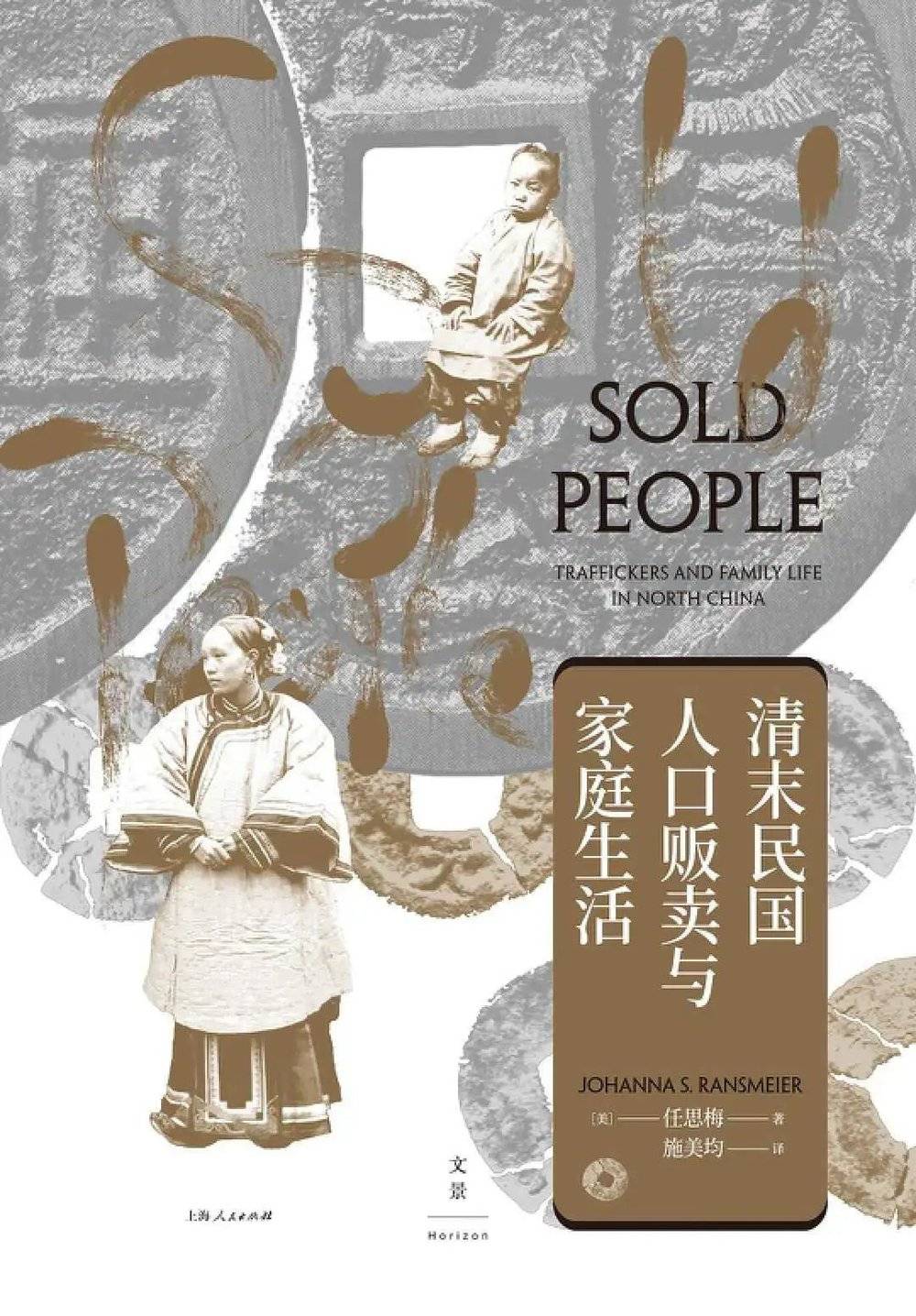
《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
作者:(美)任思梅
译者:施美均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
青年志:你参与了“中国历史上的性别、法律和妇女买卖问题”圆桌研讨会。从历史的角度,你认为人口贩卖在中国屡禁不止的原因有哪些?
苏成捷:我认为这当中有深层的连续性。首先,买卖人口与性别失衡的问题相关。尽管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别失衡和重男轻女一直存在。尤其是在饥荒时期,性别比例失衡变得更为极端。
我基本上应该算是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所以我认为人口买卖既与意识形态有关,也与物质因素有关,比如小农经济制度、诸子均分继承制度等。在传统社会的农民家庭中,通常是女儿出嫁,儿子留在父母身边,娶媳妇、传宗接代、耕种田地、供养父母、敬拜祖先……都是为了延续香火。女儿通常会嫁出去,因此对一个家庭来说,她相对是可有可无的。这是性别失衡的深层故事。
哪怕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都还是农业劳动力。所以我认为,性别失衡和人口买卖和小农经济塑造下的生活模式相关。当然,随着这种生活模式的逐渐消失,这个问题可能正在好转。
但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只是人口买卖的背景。在清代也是一样,穷人处在一种矛盾的情况下,扭曲的性别比意味着到了结婚年龄,很多男性娶不到妻子,但他们需要儿子来延续香火。小农经济的基础是一块土地和一个妻子。这就产生了需求与市场。同时还有社会深层的厌女基础,于是就有了罪犯从城市将女性贩卖到农村。而当地的警察基本都是本地男性,很多时候他们同情这些没有妻子的男性,不会严格执法。而很穷的大山里没有网络,被拐女性如何求救和逃走呢?
“五四”妇女史观与90年代性别史浪潮
青年志:九十年代美国中国史领域经历了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转向,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在当时提出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问题。她认为,今天人们对于明清妇女作为儒家礼教的受害者以及无声边缘群体的集体想象,源自五四新文化思想出于现代化目的制造的历史建构,而非明清妇女的真实写照。你对此有不太一样的视点,能否展开说一说 ?
苏成捷: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高彦颐开创了中国性别史的新浪潮。除了她之外,还有曼素恩(Susan L. Mann)、白馥兰(Francesca Bray)等重要学者。高彦颐的第一本书《闺塾师》出版于1994年,那时我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我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在2000年出版了。在那6、7年里,学者们还出版了一系列类似的性别史著作。
她们在美国开启了中国性别史领域的一场运动,真正地改变了英语学术界的中国性别史研究。从那以后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建立在这些洞察之上,某种程度上,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波浪潮的尾端。
高彦颐批评了“五四”妇女史观把传统社会的妇女塑造成了僵化的“受害者”的刻板形象。如果你读过巴金的《家》或者鲁迅的《祝福》之类的文学,就会发现里面充斥着类似的形象。她认为,问题不在于这样的形象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这不是唯一的真相。
她还指出,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时期,这种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成为旧社会落后的缩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感情,又被当时的不同政党利用和强化,因为没有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之中的传统妇女,妇女解放运动就无从说起,没有解放运动,就无法建构现代的新中国的蓝图。于是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变成了真实的历史经验。
我认为她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想了解革命前女性的生活,特别是明清时期,就必须抛开那种刻板印象,因为那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女性是如何经历她们的生活、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的。
与此同时,她们更关注一夫多妻制,纳妾,缠足,贞节意识形态这类的话题,尤其是这些女性为何愿意缠足、接受一夫多妻制,她们如何理解贞节,为什么投身于这些压迫她们的事情,甚至帮助延续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彦颐她们感兴趣的是在儒家性别体系中,女性如何理解和落实自身的自主权/能动性?
另一方面,她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明清时期江南大城市的精英妇女。这些妇女识字,写了诗、信和其他东西,其中一些还留存了下来,我们因此能看到这些女性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但高彦颐和曼素恩也承认,她们研究的这些精英女性是少数中的少数,曼素恩就在书中写过,这些女性的数量大概不超过当代中国女性的0.1%。
我曾经指出过高彦颐的一个问题——她研究的精英女性群体与典型的受害女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也完全不同,因此也就很容易说,受害女性只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经验,在我教的本科生之中,他们在读完高彦颐的作品之后往往有这样两种反应:一种是,他们以为中国所有的妇女都是识字的,都在写诗。另一种是,也许0.1%的女性过着美好的生活,那是因为她们很富有,但是,99.9%的女性大概还是刻板的受害者形象。因此,我觉得高不一定成功地挑战了这种刻板印象。
当然,我不是想批评高。我认为她的作品是伟大的,但关键是什么才是更大的图景?一部分因为我的政治立场,一部分因为我的兴趣——老实说,我对这些精英诗词作家不怎么感兴趣,我对普通人的生活更感兴趣。
青年志:那么你觉得清代这些下层妇女有能动性吗?
苏成捷:这很难一概而论。更大的背景是:父权社会的系统性厌女对女性来说是致命的。这是性别失衡的原因,是女性被商品化的原因,也是在人口贩卖的案件里,女性通常是被卖一方的原因。
具体来说,性别失衡的原因不一定是杀婴。更常见的做法大概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男孩优先吃,女孩吃剩下的。孩子生病了,男孩就去看医生,女孩就会先等待。此外,通常给男童的母乳喂养时间会比给女童的长。在儿童虐待案件里,女孩的情况往往比男孩更严重。所有这些因素相加,到了适婚年龄,女性的数量就会比男性少。
我不想理想化女性的能动性,但在特定情况下,比如卖妻,实际上或许是女性想要被卖。因为卖妻的动机大多数是极端的贫穷,这样一来,妻子就摆脱了困境,甚至有机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婚姻、比较安全的经济状况。而她原本的丈夫把财礼钱花光之后(包括还债、赎回典当的冬衣、买粮食,等等)就会成为光棍,一无所有。在招夫养夫的案件里,也存在女性的能动性,有些情况是女性主动出去找男朋友,招他进来,招夫养夫的人不一定是丈夫。
如果我们将卖妻与招夫养夫对比看,它们都是解决贫困的策略。但为为什么有人选择卖妻,有人却选择招夫养夫呢?如果丈夫和妻子相处融洽,他们想要在一起,大概会倾向于招夫养夫;如果妻子本就讨厌丈夫,不想和他在一起,大概会倾向卖妻。在这些情况中,妻子的感受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她的选择里包含着是否必须抛弃孩子。
当然,我不想把这样的情况理想化,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这样受限的情况下,人们依旧还是有一些能动性的。
有一句英语谚语,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if all you have is lemons, make lemonade(如果生活只给了你酸柠檬,那就做一杯柠檬汁吧)。对于生活在当时的女性而言,她们的选择不像是藤校学生选择想学什么专业的情况,而是说在你面前,有三个选择,它们都是坏的,你只能从中选了那个相对不那么坏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现实。
女性主义、历史的当下与未来
青年志:之前邮件里你提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很好奇你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对你而言,女性主义意味着什么?
苏成捷:我的女权主义出发点很朴素。我认为,不论性别、性取向、种族、国籍,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对我来说,这就是女权主义的本质。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就是做个好人,尽管它听上去很简单。
从个人经历出发,我之所以会成为女权主义者,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哥哥。他是同性恋,十多年前死于癌症。我们一直非常亲密。我记得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向我出柜了。我是他第一个出柜的人。而我当时大概十五六岁,还是个高中生。在那个时期,大多数高中男生都非常恐同。其实大家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但是非常恐同。对于同性恋来说,他们也不敢出柜。在我的哥哥向我出柜后,我的内心感到一种尖锐的拉扯:我的哥哥是同性恋,他也是个好人。
与此同时,当时在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刚刚起步,天主教和基督教保守派与新右翼的反扑就已经开始了。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非常热门的政治话题,也是争议性话题,有非常多杀害同性恋的声音,对我来说,这就不是抽象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实的危险——我的哥哥会不会被人伤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开始对性别问题产生兴趣的原因。
那么,我是从同性恋权利问题进入女权主义的。事实上,恐同本身就是厌女的体现,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被鸡奸者的污名化一样。在我求学阶段,我读到了更多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我也开始对性别史产生兴趣。
这些经历让我逐渐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当然我不会说自己是个行动派,但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学术中,我努力践行我所了解的女权主义。
青年志:说起反扑,去年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也被推翻了。
苏成捷:这是另一个反弹。但现在也有很多人反对,大家都很愤怒。事实证明,即使是许多右翼或者共和党女性也堕过胎,或者她们的女儿堕过胎,或者她们的姐妹堕过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确实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跨越了不同的政治光谱。
当你不需要堕胎时,很容易会想要反对它,堕胎对他们来说是抽象的,但直到你也需要堕胎,这件事就变得真实了。这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情。而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极端了,以至于跨越派别的很多人都表示不满。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会影响他们在选举中的利益。当然,最高法院已经完全疯了,我感到非常沮丧。
青年志: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采访中也聊到历史和当下的关系,在你眼里,历史研究如何和现实发生关联?学习历史如何可以帮我们更好理解当下?
苏成捷:从根本上说,要想了解现在,就必须了解现在是如何产生的,这就与过去有关。其实也不需要过多解释,每个人类社会、每种人类文化都想了解自己的过去,想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许多神话与宗教的起源,也是现代历史的起源。
因此,对我来说,研究历史、理解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身就有价值。当然,我很难说,你读了我的书就能解决实际问题,但你可能会更好地理解某些问题,比如性别失衡问题,至少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存在已久,而且不容易解决。中国社会的文化有非常深层的连续性,尽管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然能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18世纪的影子。
还有一点,政治家总是热衷谈论历史,通过讲述一些历史故事来证明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你就能分辨出什么时候他们是在胡说八道,历史就像是废话检测器(crap detector)。而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可能就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青青子,编辑: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