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城中,谁没有过痛苦的通勤经历呢?每天往返,让工作之余的社交时间岌岌可危。
有研究表明:
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离婚可能性会高40%;
邻居中开车上班的人越多,彼此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越低;
郊区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和情绪问题……
通勤时间越长,婚姻、生活和子女越不幸福,这是著名记者查尔斯·蒙哥马利在《幸福的都市栖居》一书中重点论述的城市困境之一。蒙哥马利指出很多城市扩张过程中会形成“社交孤岛”,无处不孤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
下文选自查尔斯·蒙哥马利《幸福的都市栖居》。
一、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离婚可能性会高40%
2004年,每晚一起吃饭的美国家庭不到30%,近1/4的人每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次数不到4次。问题也在像城市扩张那样不断扩大:每周和家人一起吃饭的加拿大人少于半数,2010年的研究则发现,英国2/3的孩子希望能恢复一家人一起吃饭的传统(1/10的英国家庭从不一起吃饭)。在韩国,社交孤立与自杀率都在急剧攀升。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因为城市的分散发展继续加剧,我随后会解释这一点。但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这些会引发幸福灾难。
和对他人的抱怨一样,社交匮乏也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对瑞士各城市的一项研究发现,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各种精神障碍最常见于社交网络薄弱的社区。社交孤岛大概是城市生活中最大的环境危害,比噪声、污染甚至拥挤更糟。我们与家庭和社群的联系越多,患感冒、心疾、中风、癌症和抑郁的概率就越低。与社区里其他人保持简单轻松的友谊是经济困难时的一剂减压良方。
事实上,社会学家发现,如果大人们能保持这种关系,孩子们也更不易受父母压力的影响。社交广泛的人晚间睡眠质量更好,应对困难的能力更强,也更长寿。在自评中,他们的幸福感也更高。
美国人的社会支持网逐渐缩小有很多原因:婚姻维系的不如以往持久,工作时间变得更长,搬迁也更频繁(次贷危机期间银行的强制驱离可不是什么有利影响)。但社交匮乏与城市形态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的人离婚可能性会高40%。
住在功能单一、依赖汽车出行的市中心外社区的人,比起住在步行尺度社区、周围有各类商店、服务和工作场所的人,对他人的信任感更低,认识邻居、参与社会团体的可能性也更低,更不太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不会响应请愿,不会参加集会,不会加入政党或倡议团体。实际上,这些生活在城市扩张区的公民,比住在联系更为紧密的区域的人,也不太认识他们所选代表的姓名。
这一现象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参与政治是一项公民义务,也不是因为这只是可以增进社会福祉的一项额外因素(不过顺便一说,它确实是这样的因素:我们如果感到参与进了那些影响我们自身的决策,是会感到更幸福的)。它的意义在于,城市比以往都更需要我们彼此接触。在世界承认了社交资本的价值几年后,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证实了,大城市越发由其族群区隔框定,而这又与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关联,这是一个让人难过且危险的事态。
信任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基石,现代大都市的存在,依托于我们超出家庭和部落想问题的能力,依托于我们去相信与自己在外表、穿着和行动上完全不同的人,也能公平对待我们、履行承诺与契约、能在自身利益之外也虑及我们的福祉、最重要的是能为共同利益做出牺牲。污染和气候变化等群体性问题,需要整个群体的回应。文明发展是一个共享项目。
二、邻居中开车上班的人越多,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越低
不可否认,城市的分散发展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产生交集的方式和速度。分散社区推远了日常目的地,使步行无法企及,这就挤压了我们与他人不经意间偶遇的机会。这一点,山屋和威斯顿牧场很像。若是你需要的不只是一杯冰沙那么简单,你就必须开车到其他的城镇,人人都在这么做。
兰迪·斯特劳塞可能有这个汽油钱,但过远的出行距离改变了他的社交格局。那个在街边给自家草坪浇水的人只是个飞快掠过的模糊影像,兰迪要驾车8英里去特雷西那边的麦克斯食品超市。在空旷的杂货店里,兰迪可能会对几个人点点头,但很可能再也遇不上他们。他的社交网络就像盆栽的根,生长受阻,紧紧缠绕着唯一一个社交核心。
严格来说,社交资本的干涸不是城市扩张导致的。但仔细研究这些调查就能发现分散型城市在凭借怎样隐秘的系统性力量改变着人们的关系。使社交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是城市的社区环境,和居民的日常出行距离。在任何一个社区,人们的通勤时间越长,与朋友闲坐、观看游行、参与社会团体或团队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远途出行的生活影响巨大,2001年有一项对波士顿和亚特兰大各社区的研究,研究表明,邻里关系情况单凭依赖汽车出行的人数即可预测。邻居中开车上班的人越多,彼此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越低。
等一下,你可能会说:这年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朋友遍布某城。汽车解除了地理距离对我们的束缚,城市高速路让我们能穿越60英里的都市圈去上班。你只说对了一部分。距离也提高了朋友间的日常会面成本。假设你我想在一日工作结束时见面吃个甜筒,然后再回家吃晚饭。我们首先必须画出两人当时各自能达到的区域,然后看有无交集,还必须想清楚去那里见面再离开,花的时间是否值得。我们每个人的时空连续性都有一个封闭范围,两个范围交集越大,我们才越容易在实际生活中见到对方。
利用这一模型,犹他州大学地理学家史蒂文·法伯(Steven Farber)与同事开始了一项研究,计算在美国特大城市生活的人下班后在1.5小时的时间窗口内与他人见面的难易度。他们用一台超级计算机处理关于城市规模、人口、地理、形态和土地利用的数字,进而获得了数亿个可能会面的时空范围,结果就是法伯所说的每个城市的“社交互动潜力”。
意料之内,法伯的社交互动潜力所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分散化。城市扩张得越分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途径就越少。法伯对我说:“城市不断扩张,我们越发难以进行社交互动。你如果住在一个大城市,除非就在市中心生活工作,不然就得付出巨大的社交代价。”
城市距离不仅限制了见面时间,实际上也改变了社交网络的形状和质量。这获得了一项研究的证实。2009年有一项对瑞士通勤者的研究,在瑞士,许多人都要开车前往日内瓦和苏黎世等国际中心。
果然,研究发现,长时间通勤对人们的社交网络产生了分散效应:通勤时间越长,朋友间就住得越远,像一张向四面八方延伸的网(确切说是,某人通勤距离每多6英里,其朋友就会住得离他再远出1.39英里,而每两个朋友彼此的距离则增加1.46英里)。社交网络拉伸的结果是,长途通勤者的朋友彼此更难成为朋友,当事人要和每个朋友单独见面,交通方面更加困难。长途通勤者可能有很多朋友,但从朋友那儿获得的支持却会更少。
社交时间有多重要?2008年,盖洛普组织与健康之路公司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幸福与闲暇时间存在直接关系。与亲朋的休闲交往越多,无论何种形式,人都会汇报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享受度,更低的压力和担忧。与喜欢的人进行休闲交往是有益的,这一点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应对的社交体量。在达到每天六七个小时的社交时间后,幸福曲线会由升转降。和兰迪·斯特劳塞一样,逾3/4的美国通勤者是独自开车上班的。经过半个世纪的主干道及城市路网的大量投建,美国人的通勤用时竟比休假时间还要多。
三、孩子们为距离付出代价
2010年,我回圣华金县去看远郊地区的恢复情况。我途经斯托克顿的威斯顿牧场,这里的变化很明显。草地和灌木丛被杂草淹没,缺乏打理和浇灌,围栏也褪色、损坏。一群青少年在人行道当中开酒会,我停下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的父母10年前从奥克兰搬来远郊,希望远离城里帮派的影响。少年们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帮派色——皮带、头巾、连帽衫都是北墨西哥式的血红——然后做了郊区孩子一代代都在做的事:抱怨居住环境。
他们说自己被困在了这里,去哪儿都要好几英里。此类抱怨并不稀奇,但形容这座没有城市的城市却异常贴切。行将成年的他们不仅很难获得工作和受教育机会,周围也鲜有商店,更不要说去派对、电影院、餐厅什么的了。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研究城市与幸福。一个女孩掀掉帽兜,露出一头“脏辫儿”,对我说:“你知道什么会让我幸福吗?一个商店,买什么都行,开在这个拐角就好。”
“别做梦了,”一个朋友朝她喊道,“我们需要的是一辆汽车和一箱汽油。”
这些孩子担心的事情可远不止去哪儿买更多啤酒这么简单。我走之前,他们提醒我一定要在天黑前离开威斯顿牧场,不然会遇上拿枪的人。我以为是他们大惊小怪,但扫了一眼斯托克顿当地报纸《记录报》(The Record)的一些标题后,我发现我错了。上面报道了一系列在威斯顿牧场发生的枪杀和袭击事件,2009年一个孩子只因趴在窗口往外看就头部中弹身亡,2012年一名说唱歌手在附近的亨利长条公园(Henry Long Park)的长凳上遭枪击身亡。
斯托克顿发展出了全加州最严重的青年帮派问题,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贫困和移民困扰,但亲子疏远、社会关系淡漠则是导致帮派问题的关键原因。“如果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付出爱和情感,我们该能消除多少帮派活动?”斯托克顿市长埃德·查韦斯(Ed Cha-vez)反问,尽管外围县域仍觉自己相比内城贫困区是更好的选择。
斯托克登青少年帮派危机干预项目负责人拉尔夫·沃麦克(Ralph Womack)表示,在中产阶级眼中,威斯顿牧场的帮派招募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如果孩子没有父母的看管,便可能转而在帮派里寻求替代品。一项调查发现,1/4的人会到其他县区上班,其余则在圣华金各地之间奔波。圣华金县的孩子不得不暂时与亲人分开,同时也无法得到社区服务。
五年级和七年级的孩子中,有近一半放学后完全不受成年人的监管。威斯顿农场的大谷(Great Valley)小学被逼无奈把家长会安排在深夜,以照顾长途通勤的父母。沃麦克说,“空巢”儿童因身边没有父母指导,于是其中许多人最终投向了帮派寻找替代。
许多人搬去边缘郊区,忍受通勤煎熬,似乎是在为孩子们做出牺牲。但事与愿违,这些地方对培养孩子而言更不是什么好地方,此类办法默默地走进了死胡同。孩子们不单单是被困在了这里。有证据显示,来自郊区甚至富裕郊区的青少年比城里的孩子更易出现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萨尼亚·卢瑟(Suniya Luthar)在研究美国东北部富裕郊区的青少年问题时发现,他们尽管拥有资源、医疗服务和优秀的父母,但比内城的青少年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即便内城的孩子要面对各种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条件较好的郊区,青少年吸烟、喝酒、吸硬毒品的人数更多,特别是在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卢瑟解释道:“这表明他们在进行心理上的自我治疗。”
在这些研究中,不幸福的青少年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因缺少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而情绪不稳。能和父母中至少一方吃晚餐的孩子都会有更好的学业表现,情感问题也更少。这年头父母有很多事要忙,马拉松似的通勤、长途购物及远距离见面,这些分散型城市特有的现象让孩子们极度缺乏宝贵的与父母共处的时间。当然缺少父母陪伴的现象不只发生在远郊区,但这些社区的设计无疑造成了居民的时间赤字。
对所有这些,兰迪·斯特劳塞皆不感到惊奇,虽然他承认家人因他的作息表抻长付出了代价。兰迪的女儿金和儿子斯科特还在蹒跚学步时,他就开始了超距通勤生活。科技浪潮席卷硅谷,房地产价格也一路上涨。和其他有子女家庭一样,兰迪开车上了新建的高速主路,越过代阿布洛岭去圣华金的特雷西打拼。两个孩子在工作日基本见不到他。兰迪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金和斯科特十几岁时便搬去和兰迪的前妻生活,但她也是一个住在远郊的超距通勤者。
那几年的多数夜里,孩子们只得自己照顾自己。金常常加热冷冻食品,喂弟弟吃晚饭,但谁能指望她一个孩子挑起养育弟弟的重担?斯科特的生活偏离了正轨,他先是被重点关照,继而逃学,扒窃商店,惹的麻烦越来越大。
我们终于到了去往山屋的岔口,兰迪脸色凝重地说:“他成了盐湖城县的客人。”他这话的意思是斯科特蹲了监狱。我也该换个话题了。
......
过去10年里,城市扩张分散的趋势已经减缓。从曼哈顿到温哥华再到墨西哥城,许多大城市迎来了新的居民流,他们愿意为了距离优势再试一次,但逃离城市扩散的影响并非你想的那么容易。作息表变长的城市系统涵盖建筑、公共空间、基建预算、法律、交通网络等等,影响着大都市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不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不断增加。
如果想逃离城市扩散的影响,我们就要把这看作是集建设、规划和思考为一体的系统。我们要思考城市为什么会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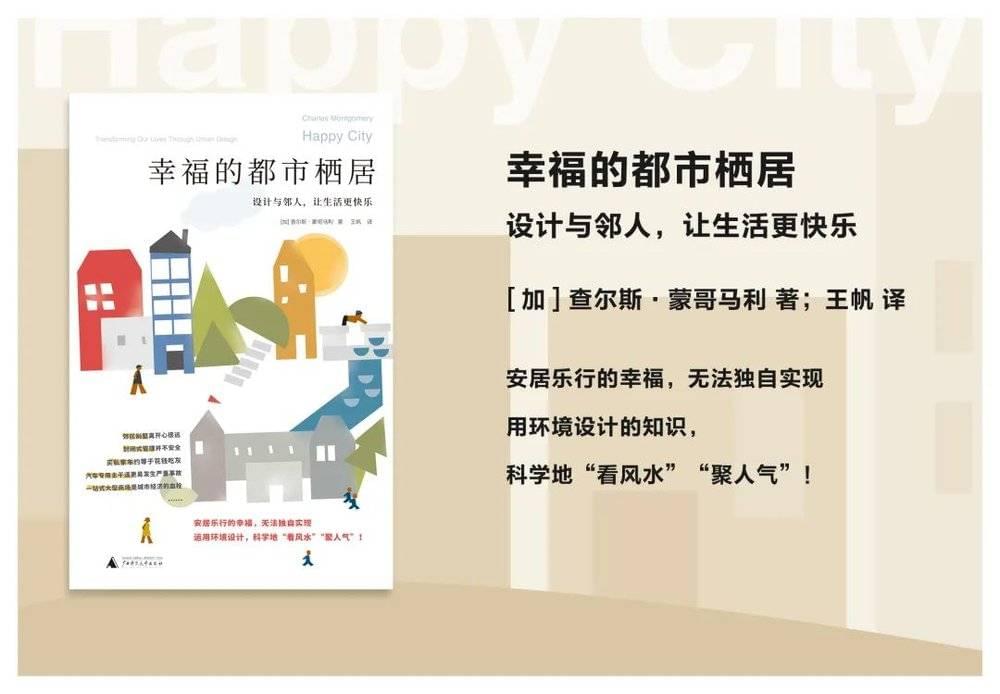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查尔斯·蒙哥马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