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规则的悖论》,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作者:大卫·格雷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以一个与官僚制有关的故事开始说起
2006年,我母亲多次中风。很快,她便明显不具备在家中自主生活的能力。由于她的保险没有涵盖家庭护理,前后有不少社会工作者建议我们申请医疗补助。然而,要符合医疗补助资格,个人总资产只能最多6000美元。我们着手转移了她的积蓄——严格来说,这应该算诈骗了,尽管这种诈骗很不寻常,因为受雇于政府的数千名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似乎就包括告诉公民如何令这种骗局长期存在。
但此后不久,又一次严重的中风发作将她送进了疗养院,以便接受长期的康复治疗。等出院后,她肯定还需要家庭护理,但问题来了:她的社保支票是直接存入账户的,而她几乎无法签名,所以除非我获得她账户的授权,以此帮她支付每个月的租,否则账户余额将迅速累加,令她失去医疗补助资格,即便我已经填写并提交了海量的医疗补助申请文件,替她暂时保留了资格。
我去了她的开户行,领了必填的表格,然后把它们带回疗养院。文件需要公证。病房护士告诉我有一名内部公证人,但要预约。她替我拨通电话,随后,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帮我转接了公证人。公证人接着告知,我需要先获得社会工作负责人的授权,然后便挂断了。于是我要到了社会工作负责人的名字和办公地点,老老实实乘电梯下楼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结果发现该负责人其实就是一开始把我的来电转给公证人的那个不明声音。社会工作负责人拿起电话说道:“玛乔丽,刚刚就是我,你一通瞎扯都把这人搞疯了,我也被你搞疯了。”然后,他微微比了个道歉手势,为我敲定了下周的预约。
次周,公证人尽责地出现,陪我上楼,确保我填完了该我填的那部分表格(在这一点上我已被反复提醒),随后,她当着我母亲的面填完了自己该填的部分。我有点纳闷,因为她没有让我母亲签任何东西,只有我签了,但我想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次日,我带着文件去银行,柜台后的女士扫了一眼,问为什么没有我母亲的签名,随后她把文件拿给经理看,经理让我拿回去改好。看来公证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我得到了一套新表格,老老实实填写了每张上面该我填的地方,然后重新约了一次公证人。到了约定的那天,公证人现身,我们尬聊了几句这些银行有多爱刁难人(为什么每家银行都得自己弄一套完全不同的授权书?),随后她领我上楼。我签了字,我母亲也签了—费了一些劲,当时她连撑起身子都难。次日我又去了银行。另一个柜台的另一个女士检查了表格,问我为什么会在注明需要工整书写名字的那栏写了手写签名,又在注明要手写签名的那栏用印刷体写了名字。
“我有这样吗?好吧,我完全是按公证人说的去填的。”
“可这里清清楚楚写着‘手写签名’。”
“哦,对,确实,不是吗?我猜是她说错了。又来。好吧……可所有信息都在这儿呢,不是吗?只是这两小处弄反了而已。这真的算个问题吗?情况有点急,我真的不想再等下一次预约。”“呃,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全部签字人在场,我们连这些表格都不收的。”
“我母亲中风了,卧病在床。所以我才要申请授权啊。”
她说她去跟经理核实一下。10分钟后她回来了,经理就站在听得见我们说话的不远处。她宣布银行不能接受目前这样的表格——除此之外,即使表格填好了,我还要让母亲的医生出具一封信,证明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允许她签署这样的文件。
我提出,先前可没人说过需要这样的信。
“什么?”经理突然插了进来,“是谁给了你表格又没告诉你信的事的?”
鉴于肇事者在众多银行员工中算是比较有同理心的,我躲掉了这个问题,转而指出存折上分明印着“由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代管”。不出所料,他回复,那个要等她死了才能作数。
一语成谶,整个问题很快成了一纸空谈:我母亲真的在几周后去世了。
令人愚蠢的官僚制
当时,这段经历搅得我心神不宁。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里过着一种不羁的学生生活,与这种事情相对隔绝。我开始询问身边的友人:这真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平常生活吗?整天东奔西走,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不知怎的被摆到了某个位置,结果真的做事像个白痴?大多数友人倾向于认为,生活大抵就是如此。
诚然,那名公证人异常不称职。可在那之后不久,我又被迫耗了一个月的时间处理纽约机动车管理局某工作人员把我的名字录成“Daid”造成的严重后果,更别提威瑞森通信公司职员把我的姓记成“Grueber”的事儿了。
无论出于何种历史原因,公共和私人官僚制的组织方式仿佛旨在确保相当一部分成员无法按预期完成任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官僚制完全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式的组织形式。毕竟,我们常说的乌托邦不就是这样吗?天真地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拒不面对人类本来的模样。
我们不也知道,正因如此,它们才会设置不可能的标准,然后又责怪个体无法达成吗?但事实上,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因为总有很多人无法达到预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从个人层面看,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跟这些表格打交道好像让我变蠢了。我怎么没注意到自己把印刷体的名字写到了手写签名栏?表上明明提示得很清楚啊!我自认通常情况下并不算蠢。事实上,做我这行的立身之本就是让别人相信我是聪明的。可我显然犯了蠢,而且不是因为不注意;事实上,我在整件事上倾注了大量心力。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于花了多少精力,而在于大部分精力都被用于随时试图理解和影响任何可能具备某种凌驾于我之上的官僚权力的人——事实上,他们只需精准解释一两个拉丁文词语,并正确执行某些完全机械的功能。
我花了太多时间担心,生怕自己表现得好像在质疑公证人的专业能力,或者想象自己该怎样才能显得更体谅银行员工,因而没怎么留意他们让我做的蠢事。这显然是个错误策略,因为我能说上话的人通常无权在规则上通融;而就算我真的碰上有这种权力的人,他们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告知我,如果我要投诉,哪怕单纯针对结构性的荒谬,那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令某些基层职员陷入麻烦。
身为人类学家,这一切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人类学家的专长就是研究出生、结婚、死亡及类似场合下的通过仪式。我们格外关注有社会效用的仪式化动作:单凭某句话或某个行为就能造就社会事实。
人是社会动物,出生和死亡绝非单纯的生物事件。通常要借助大量工作才能将一个新生儿变成一个人——有名字、社会关系(母亲、父亲等)和一个家,有别人对他负责,并期待他有朝一日也会对这些人负责。通常,大部分此类工作都经由仪式完成。正如人类学家指出的,此类仪式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可能涉及洗礼,坚振,熏香,剃胎发,隔离,报喜,制作、挥舞、焚烧和掩埋仪式用具,还有念咒语。死亡更复杂,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获得的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又要逐步被切断和重整。一个人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死去,其间轮番经过下葬(甚至重新下葬),焚化、清洁和重整骸骨,宴请,还有仪典。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大多数社会中,上述仪式进不进行都有可能,但恰恰是文书工作而非任何其他形式的仪式承担起了这份社会效用,令这些改变实际生效。
例如,我母亲希望不办葬礼,直接火化。我对殡仪馆的主要记忆就是那个胖胖的和善文员,他带我过了一遍获得死亡证明前必须入档的14页文件,文件要用圆珠笔在复写纸上填写,如此得到一式三份。“你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填这样的表格?”我问道。他叹了口气:“我干的全是这个。”说着抬起一只因为某种早期腕管综合征而缠了绷带的手。他没得选。要是没有这些表格,我母亲或任何在其机构火化的人都将无法在法律意义上——从而在社会意义上——死亡。
对官僚制批判的缺席
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研究美国或英国通过仪式的民族志著作(内含大篇幅介绍表格和文书工作的章节)?
有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文书工作很无聊。你可以描述与之相关的仪式。你可以观察人们如何谈论它或应对它。可一旦涉及文书工作本身,你就没多少有趣的东西可说了。表格是怎么设计的?配色呢?为什么它们选择问某些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为什么问出生地而不是,比方说,你上小学的地方?签名为什么那么重要?但即便如此,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评论员,很快也就提不出什么问题了。
事实上,研究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文书就该这么无聊。而且其无聊程度与时俱进。中世纪的凭照往往相当美观,通篇是书法字和纹章装饰。其中一些元素甚至直到19世纪还保留着:我有一份我祖父出生证明的副本,1858年签发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它色彩斑斓,有着哥特体字母、卷轴和小天使(还是全德语写就)。
相较之下,1914年于堪萨斯州的劳伦斯签发的我父亲的出生证明是黑白的,毫无装饰,只有线条和方框,但好歹由一手漂亮的花体字填写。而我自己的,1961年出具于纽约的那份,连这一点都没有:它是打印后盖章的,平平无奇。当然了,如今大量以计算机界面呈现的表格,其乏味程度还要略胜一筹。仿佛文件的创造者们一步步地尝试剥夺文件中的任何一丁点儿深意或象征性。无怪乎这一切可能会令人类学家绝望。人类学家为密度所吸引。
我们手头的解释性工具最适于在复杂的意义之网中穿行——我们寻求理解纷杂的仪式象征、社会戏剧、诗歌形式或亲属关系网络。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既无限丰富,同时又无限延展。单单一个罗马尼亚的丰收仪式、阿赞德人的巫术指控或墨西哥的家族传奇,如果想把其中包含的所有意义、动机或关联都研究透彻,都得穷尽一辈子时间——其实应该是好几辈子时间,如果还要在更广的社会或象征场域内追索它们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这样的工作一贯是开放性的。
文书工作恰恰相反,其设计初衷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简单和自足。表格再怎么复杂,哪怕复杂到令人傻眼,它也是由非常简单但明显对立的元素无限叠加而成的,就像一个完全由两三个简单几何图案无限并置而构成的迷宫。而就像迷宫一样,文书工作并不真的向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开放。结果就是没什么可供阐释的。
克利福德·格尔茨因提供了一种对巴厘岛斗鸡的“深描”而成名。他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能剖析一场特定斗鸡比赛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理解巴厘岛社会的一切:那些概念关乎人类境遇、社会、阶序、自然,以及人之存在的所有根本激情与困境。从一份抵押贷款申请中不可能得出这些,无论文件本身的信息量有多大;即便有哪个不信邪的只为证明其可行性而着手写了这样一篇分析,也很难想象有谁真的愿意去读。
有人要反对了:可伟大的小说家不是经常围绕官僚制创作出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吗?这当然不错。但他们的成就恰恰在于直面官僚制的循环和空洞,更别提愚蠢了,而由此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具备了某种同样迷宫般的麻木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这个主题下的伟大文学作品都采用了恐怖喜剧的形式。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小说作品都不仅强调了官僚生活滑稽的无意义感,而且掺入暴力元素,至少是作为弦外之音而存在的。这在某些作者(如卡夫卡和海勒)那里更明显,但暴力似乎总是潜伏在表面之下。更重要的是,明确以暴力为主题的当代故事也有涉及官僚制的倾向,因为毕竟大多数极端暴力行为要么发生在官僚化环境中(军队、监狱等),要么直接充斥着官僚式流程(犯罪)。
伟大的作家懂得如何处理真空。他们向它敞开怀抱。他们凝视深渊,直到深渊也凝视他们。相形之下,社会理论厌恶真空;或者说,如果它还继续像先前那样思考官僚制的话,这个判断就完全成立。愚蠢和暴力正是它最不愿谈论的元素。
批判的缺席显得格外奇怪,因为从表面上看,高校学者个人所处的位置使他们理应去探讨官僚式生活的荒谬。部分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自己就是官僚——情况越发如此。“行政职责”、出席委员会会议、填表、阅读和撰写推荐信、配合院系领导的心血来潮……所有这些占用了普通高校学者越来越多的时间。
不过,学者们也是逼不得已的官僚,因为即便当所谓的“行政”最终成为教授实际工作的大头时,它也总是被视为附加之物,显然并非他们真正的职责所在,也不能真正定义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学者,是研究、分析和阐释事物的人,即便他们的学术灵魂越来越为官僚躯壳所禁锢。
你可能会觉得,一名高校学者该有的反应是研究、分析和阐释这一现象:我们怎么就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到文书工作上了?文书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其背后的社会动力是什么?然而出于某些原因,相关探讨付之阙如。根据我的经验,当高校学者围着饮水机(或学院里更常见的咖啡机)休息闲谈时,他们鲜少谈论自己“真正的”工作,而几乎时刻都在抱怨那些行政职责。但在日益缩水的可供他们深度思考的时间里,这似乎又是他们最不愿去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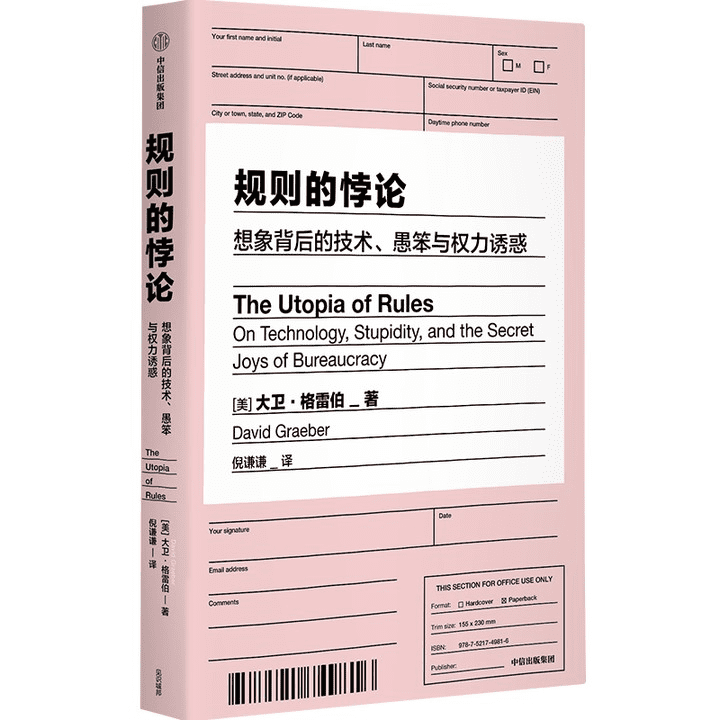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 2023.4
本文整理自《规则的悖论》,作者:大卫·格雷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