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摘编自《未来大历史》,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出版社:中信出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可是,小鼠呀!并非只有你,才能证明,
深谋远虑有时也会枉费心机。
不管是人是鼠,即使最如意的安排设计,
结局也往往会出其不意。
于是剩给我们的,只有悲哀和痛苦,
而不是指望的欣喜。
你还算幸运的呢,要是与我相比!
我只是现在才伤害了你。
可是我呢?唉,往后看,
惨惨凄凄,一片黑漆!
往前看,虽然我还无法看见,
可只要一猜,就会不寒而栗!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致田鼠,犁田时将她从窝里翻出》
对于人类而言,很多决策层面的未来思维都是有意识的。很可能许多其他聪明的物种也是如此,包括彭斯诗中“微小、狡猾、胆怯、怕羞的小兽”。但是和其他聪明的物种相比,人类未来思维所发挥的能力与其重要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都拜两个相互关联的变化所赐。在人类数百万年的演化中,神经系统和生物构造上所产生的变化让每个人在思考、想象、计划、模拟可能的未来时都可以做到炉火纯青。
然而,这些技能所带来的冲击可以被放大很多倍则有赖于第二个变化——人类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让人类得以分享见解并作为一个集体积累信息。在不同个体间分享信息意味着人类对未来的思考和管理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人类技术与文化的演进也大体如此。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这些能力一代比一代强。在这些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人类与未来以及地球家园的关系焕然一新。为此,迪迪埃·索内特用过一个很好的比喻。用他的话说,我们都变成了“龙王”。众所周知,如今“龙王”是指突然有惊人的新表现的已知生物。
一、生物结构上的不同
我们属于用双足行走的高智慧灵长动物,这个族群也被称作人族。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间,人族一直在演化,而最近200万年人族大脑的体积急速扩大。现代黑猩猩大脑的体积为300立方厘米到近480立方厘米。直立人/匠人生活在200万年前,它们大脑的体积为900到1000立方厘米。现代人类大脑的体积大约是1300到1400立方厘米,而我们的亲戚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更大,体积可达1500立方厘米。
当然,大脑的体积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已知的生物界当中,抹香鲸拥有最大的大脑,它的体积大约是8000立方厘米。大脑尺寸与身体大小的比例才是关键。这是因为大型生物体的神经系统里会有更多不动产需要管理。这也是在演化过程中为何大脑的体积会随着生物体形的增加而变大。然而,人族大脑的增长速度比这一规律所能预料的还要快。与人体大小相比,人类的大脑尤其大。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的,在人脑专门负责计算与规划的额叶皮质区中,神经元数量也是不一般地多。
是什么驱使这些变化发生的呢?这是研究生物演化的学者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数十亿个神经元不断通过动作电位进行点火的过程中,它们会消耗非常多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这让拥有较大脑部成了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生物演化中这样的大脑并不多见。(从生物演化时间尺度上来看,)变化的速度表明有正反馈环在起作用。
其中一个可能的反馈环表明了大脑尺寸和社交之间的关系。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恒定,它们平均每克体重所需的食物量会比爬行动物多10倍。想要得到如此之多的食物,一种办法是变得更狡猾,而另一种办法则是合作。因此,哺乳动物都倾向于拥有大大的脑。为了将本领和体能都集中到一起,它们喜欢成群结队地生活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群居对智力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你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未来。你还需要为其他个体的未来着想。无论出于情义还是职责,你都得关注他人的动向。你得揣测女性首领在想什么,还得盘算你的敌人又在打什么主意。所以,社交很可能会让脑部变大,而更大的大脑则又助社交一臂之力,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馈环。
无论我们对人族大脑的快速增长做出怎样的解释,它终究让人类的未来思维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额叶皮质通常被认为是工作记忆的大本营,而其中增长最快的区域主要负责控制我们的时间观念、情绪以及行为的目的性与计划性。这个区域还会帮着整合视觉以及其他的感官信息,以此建构我们所处环境的模型,并把想象中的事件按照设想中的时间顺序来排列,这正是你在模拟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时所需的技能。如同帕特里夏·丘奇兰德曾经写到的那样,更大的额叶皮质意味着“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身体层面上都拥有更为强大的预测能力”。
要说模拟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的序列,人类的确技高一筹。比如制作复杂的石质工具或者成功生火。人类格外擅长在宏大的时间范围内想象未来的样子——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就将以恢宏的结构来探索某一个未来的形态。更多思考的空间也意味着认真思考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所谓“认真思考”是指考虑某事时集中注意力再三斟酌,从而由“快思考”转向“慢思考”。信息如潮水般涌过大脑,不着急的时候,大脑可以选择把注意力集中于信息洪流的某些部分上。人类似乎很善于集中注意力,哪怕有让人分心的东西在也没关系。这是一项冥想者会去练习的技能。注意力集中的有意识思考让我们更好地厘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也让我们更有能力去比较不同的未来可能性。
简而言之,人类的大脑似乎已经扫清了不少障碍。它让我们得以更好地对许多不同的未来形态进行想象、揣摩与比较。
二、社会与文化差异:语言与集体学习
带着这些加强技能,我们的祖祖辈辈在演化过程中还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更大的大脑让另一个更具变革意义的转变成为可能——集体学习(或者称之为文化演进)。
很多物种都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因为它们有语言,也能分享信息与想法。但唯有人类在分享信息时可以如此高度精确。集体的知识储备随之增长并代代演进,直到它们重塑了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我所说的“集体学习”的意思。集体学习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这个物种会有历史一说。这正是因为随着集体知识的不断累积,我们的技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起初很慢,但接着就加快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储备让我们驾驭周围环境与生物的能力越来越强。
集体学习让变化越来越快。板块运动、太阳与月球的运行,还有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它们是地球历史的几大推动力。而它们都差不多得在成千上万年乃至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中才能看到作用的效果。但随着人们将观念口耳相传,集体学习的成效几乎立竿见影。
诚然,自然选择仍然在人类历史中拥有一席之地,它解释了游牧族群的后代为什么成年以后喝奶也通常可以消化。但正是集体学习才让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如此迥异,而它的时间进度比自然选择要快得多。亚历克斯·梅苏迪是研究文化演进的专家。他将跨越多代人的知识积累描述为“定义了人类文化的特征”。
集体学习和文化演进之所以成为可能,有赖于人类语言的演进。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把语言的演进称为“拥有令人生畏的集体力量的信息分享网络”。虽然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演进的过程完全搞清楚,但不少假说都很合理。
将大脑发育与社交联系在一起的协同作用可能同样驱使着人类语言的演进。社交属性的增加促进了个体间更好的沟通,而这些个体都很想知道别人在思考些什么、计划些什么。难怪所有的社会性物种都拥有某种形式的语言,包括鸟类、鲸类以及灵长类。狒狒会用简单的信息向彼此发出警告,比如,“小心!老鹰来了!”然而,人类的语言独树一帜。人类的额叶皮质区空间更大,所以神经系统也有地方来储存大量的名字、词语和观念,还可以用语法这样的车床把词语和观念变成故事。有些故事讲的是现实世界,有些则是假想出来的。
无论语言的起源在哪儿,它终究让我们人类跨越了一道重要门槛,不管“人”是作为个体还是一个种群而言皆是如此。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认为,正因为词语浓缩了太多的信息,它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为周围事物建构模型的新方法。想象一下,要是有人喊了声“粉色大象”,那能在你的头脑里引发怎样的一番轰鸣。这四个字所传递的信号在神经元网络中弹来弹去,也在你的脑海中把一个生动而复杂的概念点亮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是你从来没见过的,至少在现实世界中从未见过。
字词打包成了一个个概念,而语法再把概念安进复杂的故事当中。在故事中,我们可以颠来倒去地重新进行布局,并模拟出未来的不同形态。我们脑海中的假想工作室安全无虞,在那里,我们可以把上面说的这些统统实现,大可不必在现实世界中碰运气。对于婴儿来说,学会说话有助于他们在玩耍中建构起可能的未来的模型,而他们的未来思维能力也会因此大大加强。
但是,语言对我们个人的思考过程的影响还不是最大的。它最显著的影响一直都体现在集体学习与思维的层面。经过所有社群的代代积累,人类拥有了巨大的知识库,而这个知识库还在不断扩充。语言让我们每个人都得以从中略窥一二,也可以为之添砖加瓦。
历经检验的知识成为人类共同的故事,也让人类有了驾驭环境与其他动植物的超凡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群都很珍视传统知识,也会对之呵护有加。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当中,知识都是通过丰富的口述材料、故事歌谣,或是历史遗迹,乃至自然地貌存储下来的。人们精心地将传统知识教授并传承下去,通常还要经过一番仪式,而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可能需要数十年。
如同自然选择会对可能产生的新物种进行检验,集体学习也会对观念进行检验。不成功的、无效的观念很可能迟早会被“证伪”。这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用的一个术语。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朋友亚当·弗格森就意识到这些变化具有多大的革新意义:“对于其他纲的动物来说,个体从婴幼儿长大成年或成熟······但是,对人类而言,除了个体的成长之外,整个物种也在进步:人类的每个时代都建立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
集体学习所释放的迅猛势头把人类历史带入了新的方向。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趋势作用缓慢,几乎无法察觉。有一个规律很突出——不管是单个家庭的起起落落,还是族群与帝国的兴衰沉浮,都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但今天的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过去的知识要多得多,于此回望便更容易发现集体学习所带来的趋势实则左右了全部的人类史。
有三大趋势尤为突出。第一,集体学习让人类愈发强大。新观念与新技术的涓涓细流永不停歇,它们也让人类左右自身所处环境、经营自身未来的能力与日俱增。第二,随着人类的圈子越来越大,在集体学习中观念分享的维度也越来越广。这种分享终于得以跨越大洲,而今天的我们得以在一个全球互联且能力超强的网络中交流思想、交换货物。人类圈子的扩大也让人们得以将自己置于不断扩张的“关注圈”当中。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社群观念所包含的人会越来越多,比如自己的部族,乃至自己的国家。
第三,集体学习使得变化越来越快,这是因为它触发了许许多多的反馈环——各种创新又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变化都是很慢的,也很难注意到。只是在最近的几千年间,特别是过去的几个世纪,变化才如此迅猛以至于人们似乎无可逃脱。哲学家怀特海曾经写道:“在过去,重大变化的时间跨度比个人的一生要长许多。因此,人类的培养目标是要去适应不变的条件。今天,这种变化的时间跨度比人的一生要短许多。相应地,我们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必须让个体准备好面对新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时间观念多了几分“时间的A序列”中的喧嚣而非“时间的B序列”中的沉静。
增长的技术力量、扩大的交互网络以及不断变快的变化——这三大趋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对时间与未来的理解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三、关于时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为何时间的体验会有差异
人类从首次出现至今已经有几十万年,而其中大多数时间里人的想法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所以,很难追溯我们人类的未来思维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变化的。如果可以派一队人类学家回到过去,让他们带着录音设备、相机以及全能翻译(没准儿要找一条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里可以插进你耳朵里的巴别鱼)去采访我们的祖先,那可就太棒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文字证据也很不错,比如说5000年前的手写日志或者哲理短文。不幸的是,最早的文献也没有超过5000年。
证据的缺乏迫使我们回到纳斯列丁·霍加寻找光源时所采取的策略。在这里,它意味着要对当代的狩猎-采集者进行研究或者去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人类学家试图对这些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加以描述,并期待那些关于时间与未来的古老观念在这些社会中还留有一些踪迹。但是,对于卡拉哈迪沙漠中的现代民族或者澳大利亚原住民,又或者今天生活在北极地区的民族而言,他们仍然秉持的观念又有多大的可能性真的与最为古老的未来思维形态有共同之处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而很多人类学家也对此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当代人类学研究还是揭示出人们对于时间的态度可谓五花八门,这也使得关于古人对未来态度的假设性推测层出不穷。
四、关于时间的人类学
20世纪4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曾表示,有的社会没有时间观念。在霍皮族的语言当中,没有发现词语、语法形式、句子结构,或者表达方式会直接指向我们所称的时间。大约在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宗教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将考古学和关于传统社会的现代证据加以结合。他认为,在过去的小规模社会中,人们对于时间的想法会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不会把时间看作动态的、线性的,这与当今世界用钟表体现的时间不同。
相反,伊利亚德声称他们对时间的体验有两种相关联的方式:“凡俗时间”与“神圣时间”。凡俗时间是对变化的浅层体验。处于这个区域的时间有点像是“时间的A序列”,除了一点:在凡俗时间中,大多数的变化都被视作循环往复,比如太阳落山、冬天来临或者从生到死的生命循环。神圣时间有点像是“时间的B序列”:时间是永恒的、稳定的。通过仪典、梦境、通灵和恍惚状态便可以抵达神圣时间。在伊利亚德看来,只要对神圣时间略窥一二,便会让人确信变化皆为幻象。从更大的维度来看,变化的东西其实很少。
到了20世纪,人类学家意识到我们当今的时间观念——钟表上的那种单线的、动态的、持续向前的时间其实是很晚近才产生的。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何包括沃夫在内的部分学者不再认为时间观是一大人类基本思想。
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接受这样的观点:虽然对待时间的态度五花八门,但在其表象之下存在某些重要的共性。沃夫所声称的霍皮族语言没有时间一说不再被人们认可,因为后续的研究表明:即便是语法中没有时态的语言也有处理过去与未来的办法。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渚里查德曾写过,在尼日利亚北部的提夫族人的语言中似乎并不存在明显可以与现代时间概念相对应的一类词,但“时间却内化为提夫人思想和谈吐的一部分”。
与之相仿,很多当今的人类学家会认为米尔恰·伊利亚德夸大了凡俗时间与神圣时间作为古老时间体验的独特性。即便在今天的时间观念中,动态与恒定的感觉也都包括其中。循环往复的变化形态对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来说也并不陌生。在变化的表象下潜藏着深深的永恒感。在当代物理学和研究时间的哲学理论中,这种永恒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1992年,阿尔弗雷德·盖尔曾对关于时间的人类学著作做过一番终结。他如是写道:
设想一个这样的仙境,那里的人们对时间的体验与(今天)我们自己的体验有着显著的不同。那里没有过去,没有当下,也没有未来。那里的时间是静止的,或者首尾相接,又或者像钟摆那样左右摇晃……但这样的仙境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另一种形态的时钟或者能让人了解最新情况的日程表。令人沮丧的延误、令人欣喜的期待、事件的意外转折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乏味单调,它们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人类学家杰克·古迪认为所有人都会体验到时间的先后(有的事情跟在另一些事情后面)和时间的长短(有的事情花费很长的时间,而有的事情发生得很快)。
那么,就不同社群对时间以及过去和未来的体验与描述方式而言,它们为何在人类学家的眼中会如此多样呢?
五、自然时间、心理时间与社会时间
看看人类在体验时间时是如何把三种不同的节奏混为一谈的,你便可以对这种多样化有所解释。这三种节奏分别是自然时间、心理时间和社会时间。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活动跟上它们的节拍。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和技术的变迁,这几种节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社会对时间和未来的体验与理解方式也由此发生了转变。
昼夜的流转、旱季雨季的交替、太阳以及各大行星的运行都有节奏,自然时间与这些节奏步调一致。这些节奏,特别是昼夜交替的节奏左右着所有生物的起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时间中重复的一面显得尤为突出。从日到夜、从夏到冬、潮起潮落皆为周而复始。只是到了最近的几百年间我们才学会在更长的跨度中追踪线性的自然时间。这一时间跨度可以是几千年,乃至几百万年。比如,我们可以追踪长期的气候变化以及海陆板块的移动。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自然时间似乎就是由无尽的周而复始组成的,这正如同伊利亚德所说的凡俗时间。
心理时间就比较多变了。它所跟随的是我们身体的节奏:激素的消长、呼吸、心跳、饥或饱、清醒或酣睡、激动或者沉闷、惊慌失措或是心满意足。这些节奏都会被即时体验左右。它们可以有节律地跳动,比如心跳。但我们惊恐时它们一眨眼就变了。它们或快或慢。我们感到无聊时,时间慢得像是在爬。(你可以检验一下这种说法,盯着手表的秒针看5分钟就可以了。)当我们岁数越来越大时,时间变快了,所以每年的生日和缴税日似乎都来得越来越快。
这可能是因为在对内心体验的总体时间进行测算时,我们是以自己的一生来作为标尺的。对于一岁大的婴儿来说,一年就是一辈子;而对于百岁老人来说,那不过是百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对心理时间有几分掌控力。醉酒、悠长的舞会、半梦半醒、兴奋与沉静都会改变心理时间的作用。冥想者有时会表示,在过于沉静的状态下,时间流动之感会消失。这种心理时间中易变的节奏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可见一斑,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内心独白。
社会时间基于他人的节奏而存在,而这些人是我们必须与之保持步调一致的。对于所有的社会性动物而言,社会时间都存在。然而,对于人类而言,曾经相互独立的社群发现自身已经被裹挟进了齿轮当中。这套齿轮驱动着愈发扩张的交流网络,而人类也在其历史进程中因此变得越来越强。
今天,社会时间通常比我们所感知到的自然时间与心理时间更为重要。从悉尼飞到伦敦,早上8点落地(我就这么飞过几次),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但如果你日程很赶的话,社会时间会告诉你这一天才刚刚开始,而你很可能只能强迫自己跟着社会时间行动。在当今世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裹挟在了一起。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行动步调跟其他几百万人保持一致。教堂祷告的钟声、缴税日、上课铃、日历都培养了我们有关社会时间的认知。从会谈到时刻表、从仪式到日程安排、从许许多多的社会职责到法律义务,它们都让我们深陷于这种认知当中。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曾有一部关于时间体验变化的先锋著作。他认为,正因为规模不断扩大的人类交流网络让社会时间愈发强势,所以它成了塑造当代时间观念的首要因素。巨大的网络把你锁定在拥有共同节奏的网格之中,而这些网格是由数百万人组成的。随着这些网格的增大,它们也左右了我们对过去与未来的认知。
在前国家社会的案例当中,相互依存的人际链条相对较短。所以,在其社会成员的经验当中,过去与未来较当下而言并没有太多不同。人们对于此时此地,也就是此刻、当下的体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管是与过去还是与未来相比都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在更为晚近的社会中,这种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区隔会更为突出。拿此刻要在此地进行的所有活动来说,对预知的需求、实现预知的能力以及对较为遥远的未来的考量都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们对于时间的体验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塑造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首先说服众多学者相信了这一点。和康德一样,涂尔干没有把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视作宇宙中的固有存在,而是将其看成一种世界的投影。但是,涂尔干所说的这种投影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它是社会层面而非心理层面的。我们在社群中成长,而社群所特有的节奏会赋予我们这样的投影。时至今日,不管是自然还是我们自身心理的节奏,其重要性都无法与这样的社会节奏同日而语。
六、关于奠基时代未来思维的推想模型
对于究竟是什么左右着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我们有了些简单的概念。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试着建构这样一个推想模型——最早的人类社会中的未来思维是什么样的。
从数十万年以前智人的演化到大约一万年前的末次冰期为止,这是人类历史最初的阶段,属于“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但在这里我要把这段时期描述为奠基时代,因为人类余下历史中的社会、文化、技术和道德标准正是在这段时期打下了基础。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奠基时代的大多数社会是由比家族规模稍大的小型团体组成的。人们在最为了解的自家领地中四处流浪。为了维持生活,他们狩猎、采集,所用的技术代代相传,但也会很好地与环境相适应。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压力驱使这些小团体进入新的环境中。他们进入了热带丛林,也踏上了北极苔原。结果,在几十万年之后,人类慢慢地扩张到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地球各个大陆上。
一万年前,奠基时代终结了。那时候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还不到600万。然而,从非洲南部到西伯利亚,从美洲大陆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已经到处都有人类的身影。今天的世界已经城市化,80亿人分散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奠基时代则与之不同。那时的世界由几万个小的社群组成,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领地,都有各自的传统与技术,也都只和少数几个邻近的社群有接触。和当代的狩猎-采集者一样,这些上古的社群很可能在一年之中会跟邻居们见上一两回。他们会互赠礼品、交流思想、切磋仪典的操办、分享故事与知识,这也是人口和基因的交流。这就像是古代的奥运会。这样的会面也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几百个人,会碰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礼仪、技术和语言传统。但是,只有在物资富足的时候,大型聚会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小小的区域才能喂饱许多人,比如北美洲西北部原住民的鲤鱼洞游季或者末次冰期法国南部的鹿群大迁徙。
尽管邻近的群体间会互通信息,但最关键的还是本地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奠基时代的社会会极度多元化。本地知识是许多代人累积下来的,历经检验。故事、歌谣与仪典的不断重复让这些知识得以延续,偶尔还会向邻近的社群输出。本地知识立足经验,注重实用,详细而精确,而且不管怎么说也很“科学”。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黛博拉·伯德·罗斯曾经写道,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澳大利亚,“赖以为生的基本要素既非技术又非劳动,而是知识”。这样的知识包括“资源的位置、水源地、生态进程、地形地貌、季节变化、动物的行为、动植物生长周期以及哪些动植物适合被驯化、食物来源、药品以及‘烟草’。不少知识都被编成了歌谣与故事”。
在奠基时代,知识很可能是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在小型社会中,各成员的财富权力与强制权力大同小异,但某些晦涩难懂的知识仅由特定的个人掌握,而这一点放大了各成员之间威信与权力的差距。关于未来的特殊知识也同样仅限于某些人掌握。
七、奠基时代关于时间与未来的观念
我们基于推测对奠基时代人们关于时间与未来的思维方式进行重建。我们的推测主要关注四个主要的特征。
(1)社群规模很小。社群之间的联系也是个人之间的,所以,未来也是个人层面的。
(2)我们的祖先认为他们属于自己所居住世界的一部分,而居住地的法则必须得到尊重。有一种现代观点认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理应驾驭未来。然而,这样的狂妄在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中难寻其踪。
(3)大多数人很可能认为世界在变化的表象之下其实基本上是静止的。
(4)在大多数人的经验当中,整个世界都被精神、实体存在以及可以左右当下与未来的力量充满。对于所有带有目的性的生物体而言,它们都可以与这世间万物进行沟通,也可以与之斗上一番。未来思维与计划的很多方面都由其间的种种关系决定。
首先,在小型社群当中,与你相关的未来关乎你的家人、你家园里的动植物。本地的天气很重要,它决定了海豹狩猎或是薯类采集的成败。你与邻居关系的好坏、你健康与否、打猎能否满载而归、可食用的植物是否丰收以及你周围的生命轮转也都为天气所左右。这样的未来是个人层面的,它与全球性的未来不同。
其次,奠基时代技术的局限让人们肯定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中并与世界共存。人们不会想着去主宰世界、改造世界。所有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社会都有一个有力的共同认识:生态和道德法则的存在要求人类去保护与关心土地。人类有能力影响本地动植物的多样性,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么干的。人类烧掉了土地,而过度捕猎则让一些物种到了灭绝的境地。的确如此,大多数奠基时代的景观已经被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人类活动的边界在哪儿。因忽视“法则”和对“法则”不敬而遭受惩罚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事物运转皆有法度,对之视而不见实在愚蠢。因为对某种猎物有偏好就将其幼崽也杀个干净,或者在土地上放火的时候心无半点波澜,这些也是愚蠢的行为。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拜访了昆人部落,并同他们一起居住。这群人生活在卡拉哈迪沙漠中,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和大多数农耕民族不同,昆人对于操控世界兴趣不大:“人们不会试图强迫自然世界去完成什么。比方说,他们不会求雨,不会给动物催产,不会种植。他们会时不时烧掉枯草,这样才能让青草更好地生长。但除了这个例外,他们不会试图促使任何事发生”。
今天的人们广泛认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有别,人类驾驭着自然世界。但在这些狩猎者与采集者的神话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想法。与之相反,这些人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分子,所以他们会让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以及心理时间的节奏相协调,而不会把自己的节奏强加于周围的环境。
社会时间当然很重要。有时候它会凌驾于自然时间以及心理时间之上。对于所有的社群而言,他们很可能都会运用天文学或者周围环境的变化来为社会活动与仪典建立历法。美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也确实认为一些3万年前的文物可能是早期形式的历法。但是,社会节奏从未如今天这般主宰着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人类学家理査德·李曾对卡拉哈迪沙漠社会中日常生活的节奏有所研究。他对此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一个女人一天采集的食物可以喂饱全家三天。在剩下的时间里,她就在营地休息、绣绣花、去别家串串门或者招呼访客。每天,诸如做饭、开坚果、拾柴火、打水这样的厨房工作会占用1到3个小时……狩猎者的工作会比采集者的更频繁,但他们的日程分配很不平均。集中力量打猎一星期,再彻底歇上两三周,这对男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打猎是个难以预料的活计,而且还得听从巫术的摆布,所以猎人们有时候会接二连三遇上不顺。他们一歇就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男人的主要活动就是走亲访友、招呼客人,更常见的是跳舞。
在古老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中,人们周围的世界中有着许多不同的节奏:梦境与身体的节奏、狩猎与采集的节奏、日月潮汐的节奏、动物迁徙的节奏、部族仪典的节奏等等。但人们似乎都能与这么多不同的节奏和谐相处。这与今天的世界非常不同。对于今天我们周围大多数事物的节奏来说,统一的钟表时间为其规定了单一的坐标网。
第三,很多线索都暗示了一点:尽管我们都生活在“时间的A序列”当中,但人们曾经认为时间基本上是静止不动的一更像是“时间的B序列”。在日常生活与个人经历变化的表征之下,人们想象出一个静止的、大体上一成不变的世界,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眼中的世界。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小型社会对于精准的历史时间轴没有什么兴趣。澳大利亚学者琳恩·凯利主要从事口头文化的研究。关于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地的雍古人的时间观念,她曾经写道:“时间是不分先后顺序的。神话传说里的事件被认为发生在很久以前,但它也是持续不断的当下的一部分。”
人类学的证据表明,过去往往没有被想象成向前移动并由当下继续前行的单条时间辄,相反,过去很快就会变得模糊并融入一片混沌的创世期。澳大利亚原住民对于生活着祖先的过去存在一种信仰,现在多被称为“梦创”。我们这里谈论创世期也不妨借用这个比喻。梦创其实翻译自一个阿兰达人使用的词汇。阿兰达人生活在艾丽斯斯普林斯附近。但这样的解释有些误导人。正如人类学家罗斯琳·海恩斯所说,这个词本来指的是“一种永远存在于当下的现实。它所存在的维度会比物质世界来得更为真切,也更为根本,因为物质世界仅仅存于一时一刻且为外界所左右”。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施坦纳将这个区间描述为“每时每刻”。被译作“梦创”的阿兰达词汇也有“法则”的意思,它指的是事物现在的形态,也是其必须且永远不变的形态。这与很多印度传统中所说的一个基本概念很接近,也就是法。历史学家安·麦格拉斯曾写道:
“在很多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中,关于,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概念都有其特别的表达方式。表达创世的‘梦创’也在其中,但它实际上说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时间,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看作一个连续体,它被当作关于当下知识与真相的集合。
在巴门尼德式的宇宙中,过去与未来不再有区分,也无足轻重。当下才是关键。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思想中,你真正该弄明白的是自己身处何地而非现在是何时。你的国是哪个国?你的忠诚、你的故事、你的知识、你的一切一切都源自地点而非时间。在这样的世界中,地图比时间轴更为重要。杰克·古迪写道:
在没有文字的文化中,关于过去的观点与态度倾向于反映当下的关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社会皆会如此,而在依赖记忆的情形中尤甚。然而,在文化的传播完全依靠口头交流的社会中……过去难以避免地会被当下呑噬……在书写工具大规模传开之前(在这之后也部分如此),过去成为当下的反向投射。回溯到神话时代,我们便能从中一窥人性以及当下人类生活方式的发韧。
这种对于时间的敏感是巴门尼德式的,而其中有些部分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中也得以存续。就像《圣经·传道书》中的优美章节所描绘的那样: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在巴门尼德式的宇宙中,人们不必觉得未来有什么神秘莫测,也不会感到未来的咄咄逼人,这是因为在其表面的涟漪之下几乎毫无变化。困扰20世纪末人类学家的一个问题也可能因此有了解释:为何当代的狩猎-采集者似乎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担心未来上?某些观察家视这种习惯为懒惰或者不负责任。但整整一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其实来源于一种经验。在这些狩猎-采集者的经验中,世间万物皆在已知和熟悉的范围内,未来所给予的都是过去已有的。卡拉哈迪沙漠中的科伊桑人对人类学家理查德·李提问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蒙贡果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种粮食?”
话虽这么说,几周后、几个月后或者几年后的短期未来从来都很重要。为了基本的生存,人们需要具体预测婴儿的降生、鹿群和袋鼠的迁徙,或者什么时候去采摘蒙贡果的能力。从这个层面来说,预测是实用主义的,是以实验为依据的,是大势所趋的,在所有社会中皆是如此。不管在什么地方,参照天文学都能可靠地知晓一年年的周而复始。对于航行的人来说,天文学也能提供重要的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已知的所有社会中天文学都有很重的分量。19世纪时,有一个欧洲人抵达了澳大利亚。据其记载,当地人掌握的关于天空的知识“远远胜过大多数白人。关于星辰的知识对于原住民的夜行来说很重要。想要清楚地识别出自己身处一年中的哪个节令也少不了这些知识。因此,天文学被当作最重要的教育门类之一”。对于奠基时代的所有社会来说,天文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天文学也教给人们:在表象之下并不会有什么变化。
第四,在奠基时代人们的假想中,世间充满了游走于感知边缘的灵魂与玄力,而他们很多的未来思维也都为其所左右。我们已知的大多数宗教传统会假定灵魂与众神的存在。2000年前,西塞罗曾写道:“多数思想家确信众神的存在。而此种看法拥有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皆由自然指引。”
这些信仰诠释了一种独特的未来思维。这种未来思维在多数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于人们确信自己可以向存在于灵界中的主体问询自己的未来并进行讨价还价,就如同你也可以对其他人这么干一样。
这样的信仰之所以会无处不在,可能还有一些神经学上的原因。所有的人类以及很多其他的智慧生物都可以区分活物与非活物,也能区分某个客体是不是有能动性。它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两者的区别会影响很多事情。黄昏时分,我们往芦苇荡里瞥了一眼,看见的物体究竟是根原木还是条鳄鱼,这差别可就大了。有的东西虽然移动得快,但人类的婴儿也能区分它的死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物体的运动方式以及发出的声音中找到线索(狗和汽车的运动方式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而且物体与之互动的方式也能给出答案。
然而,负责做出区分的神经系统远远谈不上完美无瑕,所以区分我们今天所称的自然现象和超自然现象并非一直都很简单。一有动静,我们的大脑就会四下打探是哪里发出的,而当夜里听到背后有人窃窃私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搞错。为什么铁屑会慢慢向磁铁靠近?为什么发洪水时的河流似乎那样愤怒?梦境与幻觉鼓励我们相信世上有多种多样有目的性的生物。
语言也是如此,语法规则告诉我们凡是动作都要有施动者。英语语法强迫你去说风吹、太阳闪耀着、世界在旋转、传染病扩散了。我们的思维有了偏差。在寻找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事物时,它会过度解读,因为比起熟视无睹,过度解读就算搞错了也不至于那么危险。把木头当成鳄鱼可能只是让人一笑了之,但把鳄鱼当成木头可能就会没命了。
简而言之,这种观点相信具有目的性的主体与力量几乎无处不在。它可能源自我们思维的运作原理。19世纪的人类学家称之为万物有灵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把灵魂的存在当作显而易见的事情。即便在西塞罗那充满狐疑的头脑中,灵界也是有经验支撑的。所以,为西塞罗撰写传记的伊丽莎白,罗森就曾认为,占卜可以被视作“‘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作为对自然世界研究的一个分支”。
在奠基时代,人类未来思维和未来管理的诸多方面都可能为精神信仰所左右,而伊丽莎白·马歇尔20世纪50年代对于昆人精神世界的描述让我们得以略窥一二。昆人认识很多神,甚至还包括了创世大神。但昆人把这些神也视作狩猎-采集者。尽管昆人的神威力十足,但它们少了几分在更为晚近的王朝时代诸神身上所见的伟岸与至尊。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正常体型的人类。它们跟人一样要打猎,会娶妻生子。和人一样,它们的营地也会生起篝火,它们也要住草搭的棚子”。神既不会为人类指点迷津,也不会对人类指手画脚。尽管它们危险起来可能会难以预料,但它们也可能会呆头呆脑。
对昆人以及很多其他小型社会而言,在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时,通过仪式与灵界取得联系便成了一种很重要的方法,而且在事关健康时尤其如此。太阳西沉、满月东升之际,伊丽莎白·马歇尔也曾目睹迷幻状态下于黄昏时分开始的舞蹈。女人们会在主营地附近生起火堆。然后,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跪坐在火堆边。当星辰显现时,有的女人开始一边歌唱,一边拍手,其他人也纷纷加入。相同的韵律与唱腔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不断重复,呈现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丽”。有些男人的大腿上套着拨浪鼓,他们这时候在女人们的外侧围成一圈,然后开始起舞。最后,有些男人会陷入迷幻的状态。他们开始在火焰中“洗涤自己”。接着,他们会靠近一个女人,把手放在女人的胸前和背上。然后他们突然尖叫着站起来,好像把女人体内的什么东西给拽了出来。是疾病,他们把疾病扔给了逝者的亡灵。
舞蹈一般会持续到拂晓,在太阳升起时达到高潮,之后就戛然而止。“筋疲力尽的女人们全身僵硬地站起来。她们已经跪坐了差不多12个小时……她们说笑着伸伸懒腰,然后四下看看有没有剩下的柴火。”卡拉哈迪沙漠中有着古老的岩画,有的岩画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这些岩画也表明类似的传统与世界观可能深深根植于奠基时代之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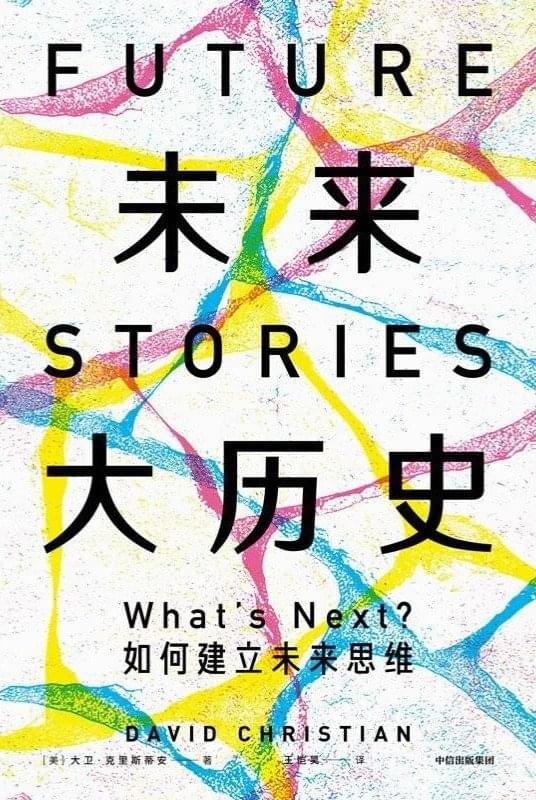
本文整理摘编自《未来大历史》,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出版社:中信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