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颜,什么样的女生找不到?为什么非要嫖娼?”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现在这个社会,发生一次非金钱交易的性关系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大多数人都在谴责嫖娼行为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试图为嫖娼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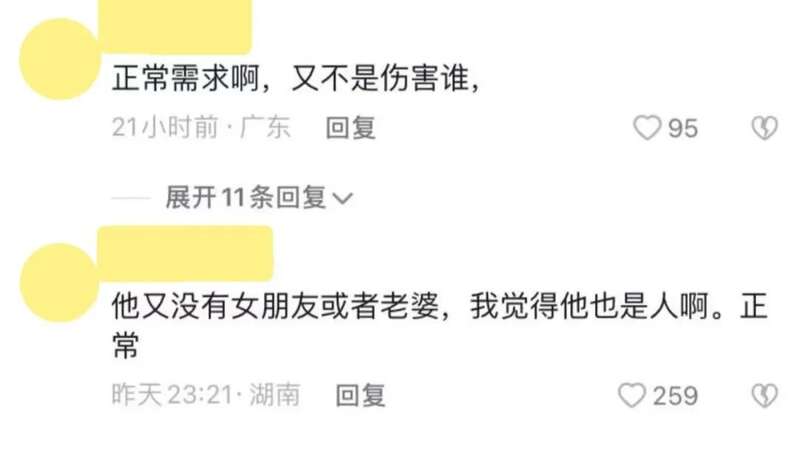
关于该不该嫖娼, 我国法律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
今天,我主要是想深究一下:嫖娼的底层逻辑。
“嫖娼,只和男人的下半身有关吗?”
我们采访了 8 位有过嫖娼经历的男性。
从他们的身上,我找到了一些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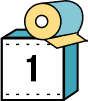
男性社交场
是嫖娼高发区
国内“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 2015 年调查显示:
“ 18-61 岁的男性 13.6% 曾经找过小姐。”
“其中 25-39 岁嫖娼的主力年龄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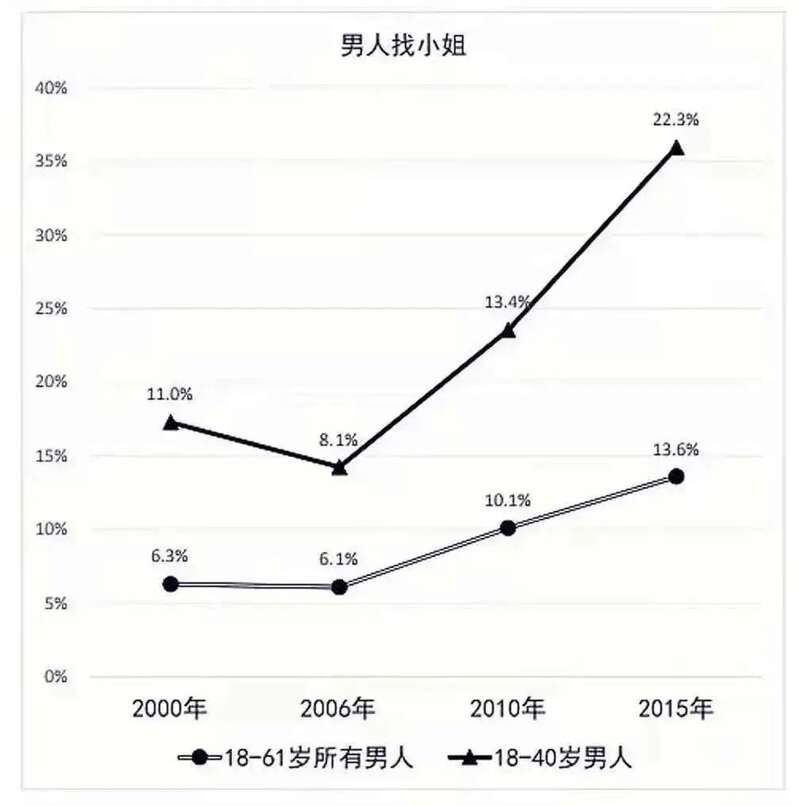
关于男性选择嫖娼的因素,排在第一类的是:
男性的社会交往。
做土木工作的@可乐平时很难接触到异性,嫖娼对他来说是“刚需”。
“再加上我自己条件也不行,家里给相亲也相不上,我工地上的同事都干过这事,我就去了。”
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东门吹雪,在嫖娼之前还没有过性经历。
为了摆脱处男身份,他选择用 500 块钱,来交换自己的人生第一次性体验和“准男人证书。”
“嫖娼不丢人,被人说是小处男才丢人。”

大多数人嫖娼的原因都是从众心理作崇主要为了应酬别人。
甚至是“陪绑”
@大鱼做练习生的时候公司规定不能谈恋爱,正好队长有这种资源,两个人一拍即合,成了“按摩店”的常客。
“主要是觉得跟着队长干坏事,比较有安全感。没有队长,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
当两个女人坐过来和他们聊天,用手摸他们身体时候,朋友驾轻就熟的跟着一个女人进了里间。
开始他是拒绝的,但在对方的不断地挑逗和劝说下,他选择了和朋友“同流合污”。
“干坏事就怕成群结队,我朋友说他经常来,我就想他没事那我肯定不会那么倒霉。”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描述过“男性共同嫖娼”的另一层心理动因:
和战争时期的轮奸行为类似,男性共同嫖娼,是通过“把女人视作共同祭品”来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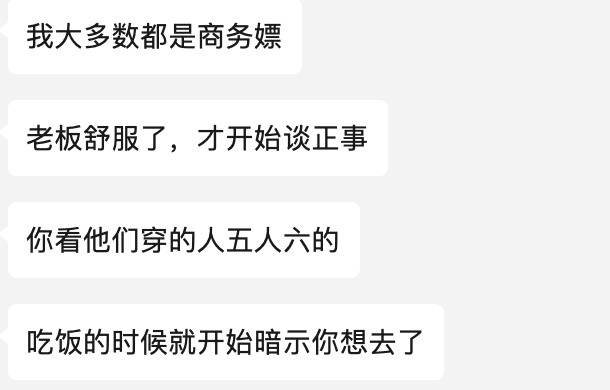
嫖娼不仅仅能性”也能买到一种“社会关系”
摆脱了处男身份的@东门吹雪,把嫖过娼当作一种谈资。
面对同伴们的好奇追问,他隐隐感觉曾经性经验滞后的自己,终于走在了同龄人的前面。
@大鱼靠着陪队长嫖娼成功和队长打好关系,成了队长的亲信。
@唐没门甚至被朋友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全是有过嫖娼经验的人,在群里他发现了不少身边的熟人。

嫖娼,只有
0 次和无数次吗?
梳理了一下几位明星的嫖娼史,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惯犯。
我们的 8 个受访者里,有两个人只嫖过一次。
“我就想增加人生体验,最主要的是怕得病,就算有安全套,她们也不干净。”
剩下的 6 人把嫖娼当作生活的常态,甚至每次有欲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解决,而是嫖娼。
第一次是尝新,第二次才是享受。
在潘教授的报告里,另外一组数据指出:
「嫖」是一种阶级行为,越有钱,消费次数越多。

这 6 位受访者也坦言,能影响他们嫖娼次数的原因主要是:没钱。
做了两年练习生的@大鱼没什么出道希望退出了团队,但嫖娼的习惯已经养成,每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会去一次。
“可能是开了荤了,有钱的情况下,我一有欲望就想嫖,没钱了就先忍忍。”
在现实生活中难找女友的@可乐,把嫖娼当作一种向上的自我驱动。
只要肯花钱,他就能挑选自己平日里幻想的类型。
也只有这样,那些在现实生活上看不上他的女人,才能一排排站在他面前等他翻牌。

“有钱了才能搞好的,倒不是有慢慢向上的探索欲,就是单纯地想搞好的,觉得自己的‘档次’也变高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可乐认为自己在性服务者身上,获得了两性关系中才会拥有的关爱。
他们一致认为,
嫖娼既可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又可以低成本的享受到更多性资源。
@大熊不认为嫖娼是没有自我道德约束,也不是无法战胜欲望的表现。
“我觉得我付钱了就是交易,买卖。就像天冷了要买件衣服一样。”
但只要是违法交易就存在风险,大熊就曾被抓过一次。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我家人知道以后差点和我断绝关系,我戒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想了。”
为了降低被抓到的风险,大熊把“作案”地点选在熟人开的民宿,交易方式基本也都是用现金支付。
既满足了寻找刺激的需求,又省去了谈恋爱的麻烦,还可以通过“征服女性”实现了更高的自我认同。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他们选择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

嫖娼半宿
归来仍是好男人?
在潘教授对 7288 名买春男子的调查发现中,有一项数据引起了我的兴趣。
“婚姻并不会约束这部分男性,反而让他们的嫖娼可能性提高 62%。”
某发达省份公示的 13 万条嫖娼行政处罚记录也证实了潘教授的数据结果:
已婚男性,比单身人生更喜欢嫖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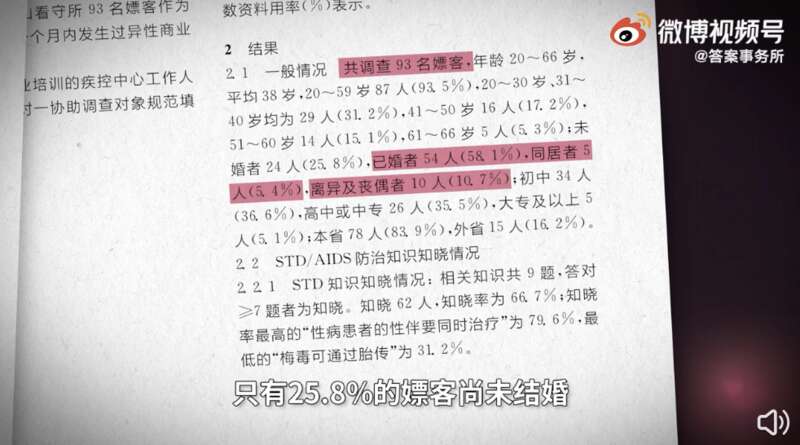
在我们的 8 位受访者中,有一半的受访者在有固定伴侣的情况下,也发生过嫖娼行为。
每嫖娼一次,他们都会对伴侣产生深深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让他们在平时生活中表现得更爱对方。
这让我想到《婚前试爱》里有一句台词:“你爱她,就要伤害她,因为内疚,是维系爱情最好的办法。”
@唐没门对“嫖”的定义仅限于发生实质的性行为,其余的都是“代餐(平替)”,并不会为此产生任何心理负担。
“没有到最后一步就是图一乐,体验下不一样的。”
“我只爱我对象,那种都是生理需求,对象不在身边的时候发生的,我心理上是干净的!”

在社会发展和流动的背景下,婚姻和家庭的约束机制已明显弱化。
@琪琪对有伴侣还去嫖娼的行为嗤之以鼻,但身边人的案例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我有一个老大哥,他老婆生完孩子以后三四年都不愿意让他碰,后来他就去嫖了,我挺理解他的,假如我是他,我也会去。”
已经步入婚姻阶段的老王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小爱好”,对于伴侣的不配合,他只能通过嫖娼来追求自己的“性福”。

“我要不嫖娼,可能和我老婆过不到现在,在她身上我找不到作为一个男人的成就感。”
《妓院谈话(Conversations In A Brothel:Men Tell Why They Do It)》一书中记录了某位买春男子的内心想法:
“这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男人的地方。”
因为他觉得“男人就应该是这样。不会内疚,也不会感到与社会格格不入。”

嫖客眼里的她们
只是工具
对于性工作者,这些嫖客们的态度也很微妙。
在采访中,我发现这些嫖娼的男性对性工作者的“痴迷”,并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在工作中的性技巧。
只有在嫖娼的时候,作为顾客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上帝。
那种绝对服从的掌控感,在其他地方即使花钱也买不到。
“像个大老爷一样被人伺候能不快乐吗?”
@可乐会在心里先构建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然后按图索骥,找一个符合他要求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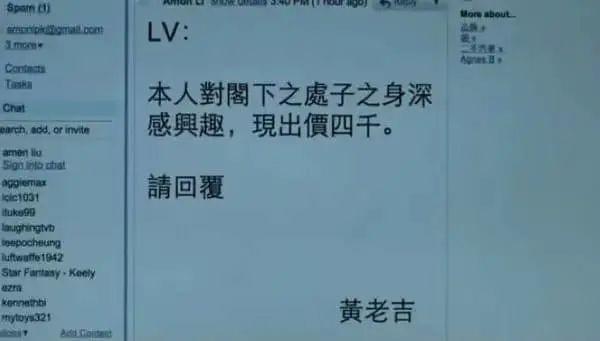
可乐希望有一天这类群体会被AI机器人取代,这样他就会在道德上没有任何顾虑。
“我会选择一个商品,但我不想取悦一个商品。”
性工作者对@唐没门来说只是一种泄欲的工具,他觉得和那些女人们太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他曾经遇到一个单亲妈妈,在结束以后对方试图和他说一说心里话,在他眼里,这只是一种销售手段。
“谁知道她说的真假,也许这套话她和每一个客人都说过,就是为了让我同情她。”
“没有一个嫖客,愿意在一个妓女身上浪费时间。”
正如《金赛性学报告》中所说:“各阶层的男性中都有人觉得,嫖妓比追求一个非妓女姑娘更省事。”

虽然在采访的过程中,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笑贫不笑娼”,“笑偷不笑嫖”。
但依然无法接受自己的女性伴侣和亲戚,从事性交易行为和以此为生。
——
文章到了这里,“男人”为什么要去嫖?已经有了明显的答案。
嫖娼表面上是性,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
潘教授指出:“男人的性交易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是一个钱够不够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地位高低的问题。”
在正常的男女关系中,性关系通常是双方互相取悦的过程。
而嫖娼过程中,则是完全取决于买方的需求。
在这样不平等的状态下,嫖客处于一种“上位者”的状态。
女性被当作一件商品,这些女性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同时,也“可以被蔑视”。

性的目的,往往在性外。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明星嫖娼事件发生后,一些鼓吹“嫖娼合法”的论调也会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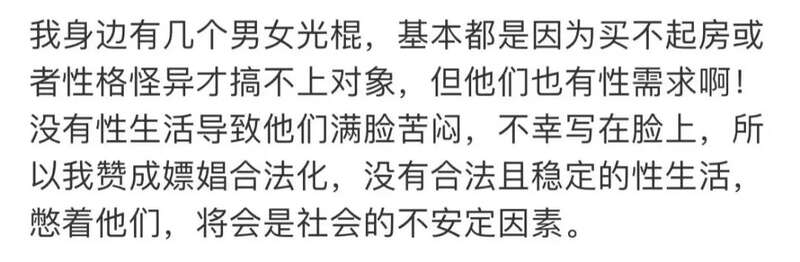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联合国发布的《人口贩卖特别小组报告》,在被调查的 1.3 万名女性中,有超过 80% 的人都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从事性服务。

纪录片《日本未成年人色情交易》
在合法嫖娼的荷兰,有学者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在 788 位性工作者中, 60% 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人身攻击,40% 经历过性暴力,28% 被强奸。
嫖娼,不仅是违法行为,更是对弱势群体的性剥削。
当“性需求”可以通过买卖而获得满足,每一个女性都会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
罗翔老师说过:“没有底线的自由,势必会造成强者对弱者的压迫”。
当女性被认定为可以解决性欲的“资源”,“吃人”二字必将重新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