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9期,作者:林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原文标题:《平台研究的迷思:关系性视角与治理困境》,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某种意义上,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那群20世纪80年代的汾阳文工团演员们对火车与站台的想象,或许暗合了今天有关互联网平台的隐喻(“站台”与“平台”的英文都是platform)。资本与国家建构下有关现代与技术的美妙叙事联结着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对意义与美好的追寻,而其中的大多数人却又在积极参与和被边缘化之间徘徊往复,回归庸常。
就像站台与火车象征着看似美好又遥不可及的远方,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也在不断地生产关于连接、提升与改造的迷思,它们既是技术、资本与国家权力反复博弈的结果,也是普通人的日常参与和微观实践的产物。因此,平台研究就是要直面一系列平台迷思,解剖平台权力,拆解所谓“平台化”背后的历史、现实语境与技术变迁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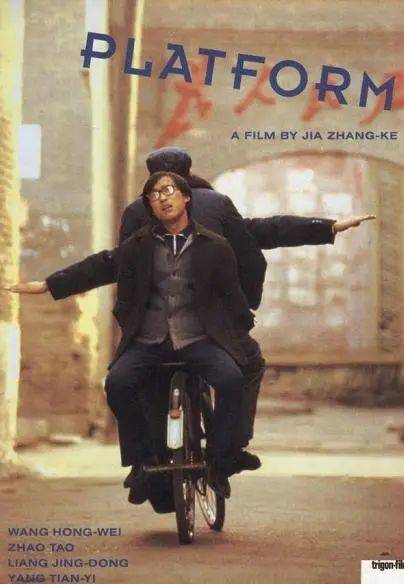
平台逻辑
平台研究者的首要关注对象是由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架构与商业模式衍生出的对平台用户与文化的治理逻辑——平台逻辑。其基础是支撑平台商业活动与用户实践的交互设计与底层技术架构,它们不断地形塑并适应平台生态中多样化的用户实践,进而深刻影响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
首先,不同平台交互界面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平台的可供性。点赞的呈现方式、原创及分享内容的可见范围、聊天框的背景设置与表情包的设计,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互选项与设置安排无不体现了平台的设计语言,及其或迎合或培育的用户文化。
按照环境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 Gibson)的解释,可供性指的是物体及其所处环境给生物提供的或好或坏的可能性,其实现依赖于生物本身的感知。这一概念在被引入设计研究与人机交互等领域后得到了广泛运用,学者们将可供性划分为物体的固有属性与可感知属性,并认为设计师的角色便是去发现、组织和引导用户建立对事物特定属性的感知。
同时,物体的可供性与主体的行动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行为与社会文化可以导向对物体属性的不同感知,进而构成差异化的可供性。因此,可供性概念的内核在于对物质性与行为主体能动性的双重强调,正如布彻(Taina Bucher)与赫尔蒙德(Anne Helmond)所指出的,当我们谈论媒体或平台的可供性时,必须以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去解读媒介技术的可供性。[1]
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对内容可见的设置是微信用户广泛介怀并经常使用的功能,这种设计或许契合了中国独特的关系文化与人际交往(尤其是公共交往)中信任的稀缺,但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有用或有效的,更毋论那些于中国社会文化少有浸淫的跨国用户群体。
其次,应用编程接口(API)与推荐算法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以数据化、网络化、个性化为特征的平台底层技术架构。API接口的广泛运用将平台打造成为一种看似开放、共享、可编程的计算网络,方便其他程序开发者调用、接入平台数据库,编辑和完善第三方程序,实现数据共享与流通。
用美国学者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的话说,平台之所以为平台,不在于其本身的代码与程序,而在于其提供的交流、互动与交易的可能性。[2] 回看互联网业界在世纪之交的讨论,就会发现平台的技术逻辑其实是对协作参与式网络(即所谓Web 2.0)理念的延伸和发展。平台话语之下的程序不再是静态的服务提供者,而是一套可协作可编程的平台网络。
例如,新榜作为一家中文社交数据分析平台,其搭建完全依赖于通过API调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的庞大数据库,进而开发出提供社交数据分析与排名的应用程序。诚如赫尔蒙德所言,在这种协作编程的逻辑之下,主流平台借助API实现了其在互联网空间的基础设施化。
无论是谷歌、脸书,还是微信、淘宝,尽管牵涉API的管理规则迥异,但它们都在与大量第三方程序进行数据流通的过程中实现了去中心化的生成性,并凭借其在数据格式标准化上的宰制性权力完成了对互联网世界的再中心化。
此外,推荐算法帮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对现实世界方方面面的数据化,以及平台消费的个性化与广告的精准化。简单来说,推荐算法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运算规则对数据进行分析、分类,进而生成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平台内容产品过滤与分发的自动化。
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自动化的背后是一套不透明的“黑箱”:一方面,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对数据的处理过程高度自动化,即使是专业的算法工程师,也无法真正理解机器决策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对于公共社会而言,平台企业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往往对各自推荐算法的设计规则与反馈机制严格保密,普通公众亦缺乏理解编程语言的专业知识。这种高度不透明性也为平台治理带来了潜在的隐患。
吉莱斯皮曾指出,算法机制的核心在于对“相关性”的生产,一种基于机器学习与运算的知识生产逻辑应运而生,而在实践中,这一机制深受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从数据的选择到对“相关性”的判定,算法决策都无法离开参与者和技术掌控者的主观意图而单独存在,企业的商业利益、社会的既有认知、政治意识形态乃至主流文化观念等都会给看似客观中立的算法系统带来事实上的偏差与偏见。
最后,基于上述技术架构的互联网平台在实践中深度嵌入既有的商业活动与产业体系之中,以开放、共享、提升为话语,建构起一套以互利协同参与为特征的多边市场体系与商业生态。[3] 其中,平台扮演着中介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以数据化为基本规则,将形形色色的内容与产品生产者、服务提供方、广告商、终端用户等多元主体统一界定为平台互补者,完成对不同产业部门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平台化。
很显然,平台企业,尤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设施型平台,在这一看似开放多元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天然地占据支配地位,其技术与商业逻辑也逐渐演变为一套平台企业主导的文化与经济治理逻辑。
平台劳动
就工作与劳动而言,平台与平台化催生了众多新型职业与劳动组织形式。形形色色的打车、外卖与众包平台支撑了庞大的零工经济,在给平台用户提供了日常便利之余,也给众多劳动者创造了灵活的就业机会。然而,在便利、灵活的平台商业话语之下,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也变成了一种临时性的、缺乏保护的服务合同关系,平台企业则以中介者的身份豁免于劳动保险与福利保障。
荷兰学者范·多恩(Niels van Doorn)认为,零工经济下的平台劳动是对新自由主义社会以“后福特制”为特征的不稳定劳动的进一步制度化,性别、种族、阶级等不平等问题不再是偶发性的事件,而是成为平台劳动的普遍性特征。[4]
一方面,平台与零工经济话语将平台企业界定为服务中介而非雇佣者,进而将其从实体经济有关劳动保障的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算法技术的引入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监视与控制,用户评价与实时定位、摄像等机制实现了对新自由化的平台劳动主体的规训与建构。
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了诸多智慧。通过对滴滴的潮汐战略及其城市交通监控系统的分析,陈玉洁与邱林川认为,滴滴一类的打车平台借助算法成功地实现了对出租车与私家车司机的整合与规训,并据此建构了一套基于数据化劳动的 “智慧城市”话语。[5]
潮汐战略的内核在于,通过算法与平台监控实现对司机与乘客出行与驾驶数据进行实时搜集。在此过程中,司机与乘客被规训为出行平台的数据劳动主体,出行产业的平台化进而演变为一种数据劳动密集型经济。
但是算法与平台对劳动的规训与吸纳并非完全单向度的,孙萍在对外卖平台与外卖员的研究中就发现,平台与外卖配送员之间的日常互动构成了对平台算法的生产与再生产。[6] 一方面,平台通过对配送时效与劳动情绪的管理建立规制,并辅以游戏化的评价和奖励机制来实现对外卖配送员的劳动规训;另一方面,在日常劳动过程中,外卖员们也采用转单、借助外部社交软件等方式搭建内部的沟通互助社群,积极地挪用平台算法,降低平台劳动的不确定性。
除了零工经济,平台对劳动的重新组织在由社交媒体平台所构建的新型内容产业上同样体现了深度的矛盾性。以 Instagram、YouTube、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凭借其强大的交互与创意功能吸引了全球广大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催生了一大批创作者达人,并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创作经济。
相较传统媒体文化产业中的创意工作者,这些在互联网空间中异常活跃的社交网红达人至少看起来是草根的、非专业化的,他们的内容呈现出高度的互动性,粉丝经济与社群空前重要。用“劳动”去概括他们的日常工作与身份甚至都不合时宜,无论是国外的influencer还是中国的“网红”,我们习惯于将他们描述为勇敢、新潮、个性化的内容创作者。
然而,正如前述的那些出租车司机、外卖员一样,社交内容的创作达人们同样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应对高度不透明的平台算法机制,他们的内容创作需要在算法可见性、个性表达与商业变现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社交平台高度的交互性使得社群与虚拟关系的建设成为创作者日常劳动的天然需要,在高度拥挤且资本化的社交平台世界,网红创作者似乎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的典型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网红经济与劳动因其所处的独特环境又呈现出更复杂的特性。在短视频等社交内容平台诞生之初,我们确实见证了大批草根社会群体在平台算法的赋权下从原先边缘化的社会身份之中跳脱出来,转变为“网红”,进而构成笔者先前研究所提出的“不可能的创意阶层”[7]。
然而,高度的资本化运作与日趋严格的内容监管也在不断挤压平台算法之下的未知空间。资本所背书的MCN机构逐渐主导中国社交创作者的劳动市场,网红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和有机性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侵蚀。
平台文化
平台逻辑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蔓延也在不断重构当代的文化生产,我们或许正在见证新型流行文化的诞生,算法化的内容分发与个性化消费,也通过新闻、娱乐重新塑造着公共领域与公民身份。
尼博格(David B. Nieborg)与波尔(Thomas Poell) 指出,无论是新闻、音乐还是影视产业,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带来的直接改变在于算法开始取代传统的人工编辑在内容分发上占据支配地位。从BuzzFeed、Spotify到中国的今日头条、网易云音乐,平台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化生产的盈利方式,社交媒体与流媒体平台开始取代传统机构媒体成为内容分发与消费的主要渠道。
然而,在平台生态中,内容生产机构与生产者面对平台企业的协商空间相对有限,文化产品在平台生态之中演变为流量获取的途径之一,其本身区别于一般商品的公共属性与文化价值开始消解,呈现出高度的平台依赖性,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平台化文化生产的高度不确定性。平台作为网络与算法技术的综合体,本身就处于不断的变动、进化中,其商业模式、算法与平台界面等层面的任何轻微变动,可能都会对依赖平台商业模式与平台基础设施的内容生产者造成重大影响。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对平台权力的解剖也需要避免简单化的单一视角。平台所连接的多元市场始终处于动态的权力关系之中,在不同文化行业、不同政治经济语境下,平台化的路径也纷繁多样:一方面,平台逻辑形塑了文化生产;另一方面,文化场域内外的多元主体也在积极地挪用并重新书写平台化。
具体而言,以西方的新闻生产为例,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在内的主流新闻媒体纷纷采用付费门槛机制来应对内容平台所谓的“补偿赞助模式”(以免费内容换取流量广告收益),社交平台的庞大用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助推了公民新闻的成长。重要的是,如果按照生产、编辑、分发、营销到盈利的不同阶段将平台化拆解开来,平台权力,至少在西方的语境下,对新闻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后三个阶段。
这种复杂性在西方的音乐与唱片产业中表现得同样明显。以 Spotify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的崛起看似对传统唱片产业构成了颠覆性冲击,然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证明,在平台化时代经过短暂的萧条之后,主流的唱片公司借助对音乐版权的控制成功实现了持续盈利。对于音乐人而言,流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与算法机制既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他们对唱片公司的依赖,但因未能摆脱版权机制的束缚,赢者通吃的逻辑却也被放大。
流媒体平台之间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平台商业模式与技术逻辑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反过来或许也给小众、多元的独立音乐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等人的研究就表明,与Spotify同一时期诞生的Bandcamp平台恰恰凭借其“准平台”甚至“反平台”的设计语言,成功发展出一套以独立音乐人为中心的可持续盈利模式。[8]
与此同时,以TikTok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内容平台也给音乐产业与音乐人带来了新的危机与可能性。短视频平台的社交属性与极致算法逻辑,一方面给初出茅庐的音乐人提供了绕过既有唱片产业体制直面广阔受众的空间与新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短视频对速率与节奏的快餐式追求也蔓延到音乐生产之上,音乐消费开始呈现从专辑到单曲再到片段的碎片化趋势。
最后,文化生产的平台化也激发了新的内容形式与文化价值,前文提及的社交媒体娱乐与网红文化便是其中代表。与传统的娱乐内容相比,网红文化的内核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本真化展演及在此过程中虚拟社群与社交关系的建构。
坎宁安(StuartCunningham)与克雷格(David Craig)在专著Social Media Entertainment(《社交媒体娱乐》)[9]中明确表达了对全球语境下社交娱乐内容背后所暗含的文化政治潜力的期许,与传统媒体相比,他们坚信社交媒体娱乐代表着更为广阔、直面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
然而,也恰恰是在文化价值与文化政治潜能的议题上,我们必须强调重视不同政治经济结构下的平台文化所体现出的深度差异性,单纯地将平台及其运作逻辑解释为宰制性或解放性的单一权力主体都是不合适的。平台之外,是广阔而多元的个人、组织、公共机构以及政府与国家,平台文化及其政治可能性,也恰恰需要在这些多元主体不平等的相互协商甚至斗争中充分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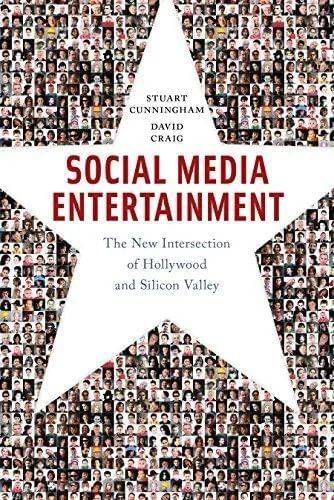
平台治理
平台研究的诸多讨论最终总会落脚于平台治理之上。事实上,平台治理包含两个层面:平台作为主体对平台生态及外部社会的治理,以及外部社会对平台与平台经济的治理。前文提及的平台逻辑、劳动与文化已经囊括了平台作为治理主体的基本内涵,从根本上来说,无论采用何种商业话语,平台已然成为当代全球社会中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行动者。
据此,平台研究的关键便是基于一种关系性的视角理解平台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商业实践中暗含的政治复杂性与矛盾性,这些复杂性与矛盾性也直接指向平台作为治理客体的必要。
多数平台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商业组织,其治理性实践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利益与商业逻辑的驱使,如范戴克(José van Dijck)等学者在The Platform Society(《平台社会》)中剖析的那样,无论是平台垄断、算法黑箱、数据安全,还是虚假信息与极端言论,平台基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大规模数据化商业实践构成了对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价值的挑战。[10]
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立足在地语境,不断反思应以何种形式对平台及其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的治理,进而弥合平台经济与公共价值之间的潜在鸿沟。
按照戈瓦(Robert Gorwa)的总结,西方社会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实践主要发展出三种模式:自我治理、外部治理与共同治理。[11]
其中,自我治理指平台企业依据现行法律,自发、主动地对平台生态中的用户行为、内容与服务进行规制,回应社会有关公共利益的关切。这一模式在欧美的平台经济治理中占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平台企业对相关平台技术细节的调整、对平台内容与用户的监管与审查,以及对平台自我治理透明性的提升。
很显然,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平台自我治理拥有诸多优势,公民社会通过新闻媒体、非营利机构与学术机构对平台企业进行调查与监督,平台企业积极回应并迅速调整相关政策,进而避免了通过立法机构实施外部治理的低效。但自我治理的弊端也很明显,平台企业往往会迫于公共压力出台临时性的治理措施,缺乏对平台生态中系统性弊病的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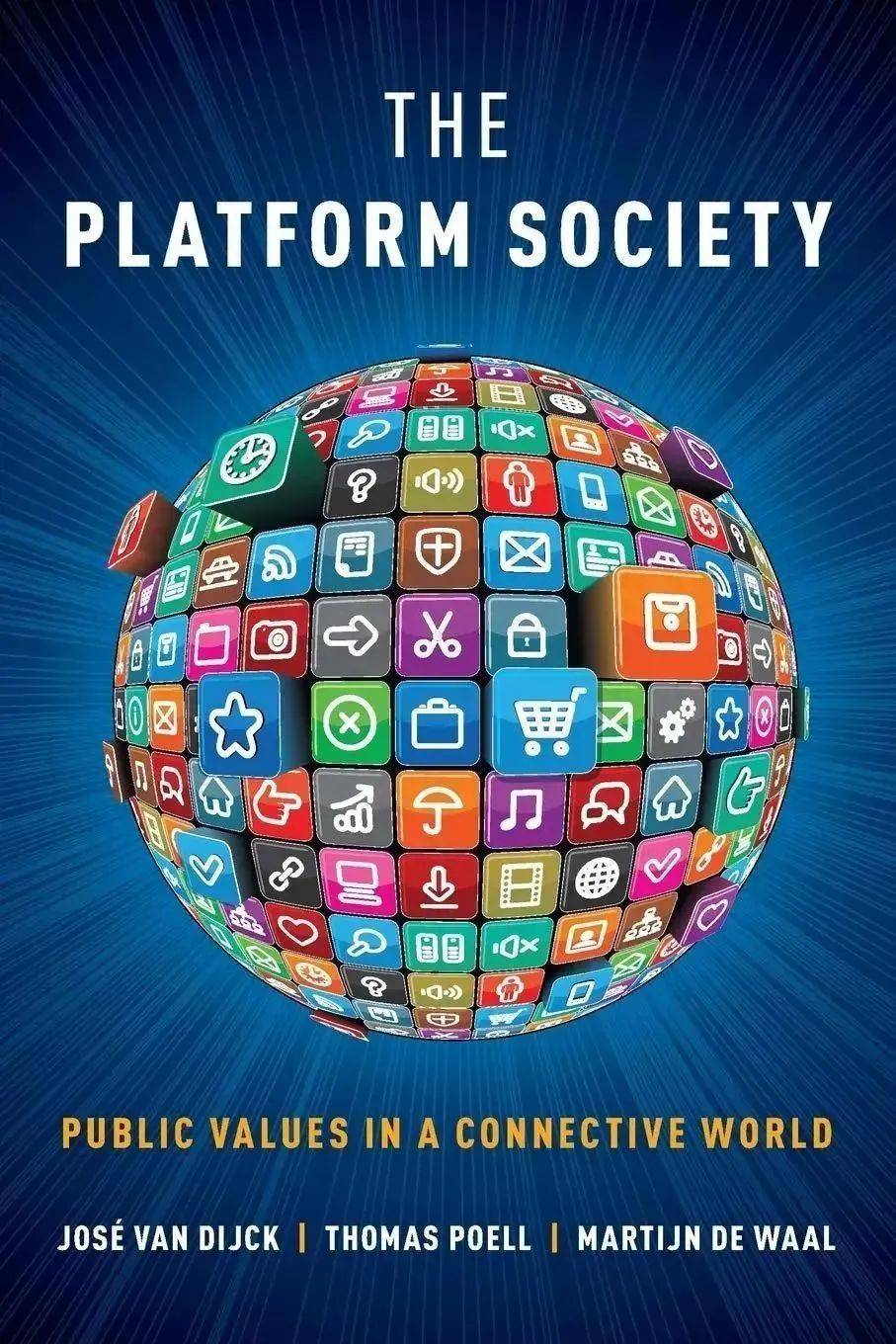
相较自我治理,外部治理主要由政府与立法机构实施,旨在通过法律手段约束平台企业的商业行为,欧盟2016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规范》(GDPR),欧洲议会2022年夏天通过的《数字服务法案》与《数字市场法案》,都是在区域范围内针对数据隐私保护、平台内容监管与市场秩序等进行外部治理的典型实践。不过,尽管外部治理可以凭借其高度的权威性有效地对平台企业及其服务进行系统性监管,但受制于自由民主政体下漫长的立法周期,实际效率往往偏低。
在自我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天然缺陷之外,西方学者与行动人士近年来开始积极倡导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治理模式:共同治理。其基本理念在于将平台治理的主体从企业与政府转移到公民社会,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市民组织、学术机构与公共机构联合平台企业参与对平台监管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这一看似理想化的治理设想并非遥不可及。在欧美社会,以共同治理理念为基础的平台合作主义实践已经展开。
受马斯克收购推特影响,近期突然进入西方主流视野的另类社交平台Mastodon就是平台合作主义的一个典型。该平台是一个自由开源、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微博客社交网络,它的用户界面和操作方式跟推特类似,但平台网络却并非由单一机构运作,而是由不同独立的服务器(实例)以联邦形式组成,不同实例拥有不同的数据监管规则,用户则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相应的实例社群。
Mastodon的运作完全基于不同独立社群的共同治理,其资金来源于网络众筹,社群之间可以合作互通而非依赖,形成一种虚拟的非营利性联邦社交网络。
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平台之隐喻承载着普通人对于便捷生活、自由职业与多元文化的想象,却也是资本与国家共同建构的权力关系在新技术网络中的延伸。你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却也困于其中。
如果将视线拉回当下,我们可能会失望地发现,批判学者们有关另类平台的构想距离此地的现实还很遥远。如果我们以一种关系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分析今天中国的平台经济与平台化,可能会得出与上述西方文献不甚相同的结论。但在一个权力边界相对模糊的社会中,谈论平台有效治理的前提或许应当是法治的健全与对公共利益认知的共识,类似的问题恐怕仍需更多讨论,而非结论。
参考文献
[1] BUCHER T, HELMOND A. The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M]//The SageHandbook of Social Media. London; New York: SAGE, 2016.
[2] GILLESPIE T.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0,12(3) : 347-364.
[3] NIEBORG D B, POELL T.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1) : 4275-4292.
[4] VAN DOORN N. Platform Labor: On the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Exploitationof Low-Income Service Work in the “On-Demand” Economy[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7, 20(6) : 898-914.
[5] CHEN J Y, QIU J L. Digital Utility: Datafication, Regulation, Labor, andDiDi's Platformization of Urban Transport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2019, 12(3) : 274-289.
[6] SUN P. Your Order, Their Labor: An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s and Laboringon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12(3) : 308-323.
[7] LIN J, DE KLOET J.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9, 5(4):2056305119883430.
[8] HESMONDHALGH D, JONES E, RAUH A. SoundCloud and Bandcamp as AlternativeMusic Platforms[J]. Social Media+ Society, 2019, 5(4) : 2056305119883429.
[9] CUNNINGHAM S, CRAIG D. Social Media Entertainment: The New Intersection ofHollywood and Silicon Valley[M]. New York: NYU Press, 2019.
[10] 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Connective Worl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 GORWA R. What is Platform Governance?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 2019, 22(6) : 854-87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9期,作者:林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