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Julia B. Frank,译者:刘凯、张亚楠、张涛,推荐:于欣,原文标题:《将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合而为一?强扭的瓜不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医学专业能用科学化的技术和临床应用来定义的话,那么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应该或终将合并。2010年推出的“研究领域标准”框架,意图豪迈地将精神疾病的原因解释为内表型,即可还原为由基因决定的神经回路和神经化学过程。功能神经成像取得长足进步,广泛涉及构成学习、奖赏寻求、恐惧反应,特别是连接记忆和预测的超凡能力的脑网络。这些都是构成多种精神障碍的“积木块”。对精神疾病更合理的分类及更精准、更有效治疗方法的期待,让人望眼欲穿。
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的知识、历史和临床传统表明,这种神经科学“大一统”的愿景,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神经病学关注神经系统的功能及失能,在实验和临床上都与它们产生的背景相分离。相比之下,精神病学关注的是意义世界本身。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断地体验到内心状态与个人记忆、社会互动以及由语言构建的周遭文化信仰和习俗的交汇。
鉴于此类情况,由于不能将疾病名称准确追溯至特定病灶或神经病理过程,精神病学往往从经验中发现能减缓病情的治疗方法。神经学家就像来自“索证之州”的密苏里人,他们最喜欢诊断那些在幻灯片或扫描片上清晰可见的病症。精神病学家则好似研究火星或月背的天文学家,依靠推理和类比,从月球车传回的分散图像中拼合出整个行星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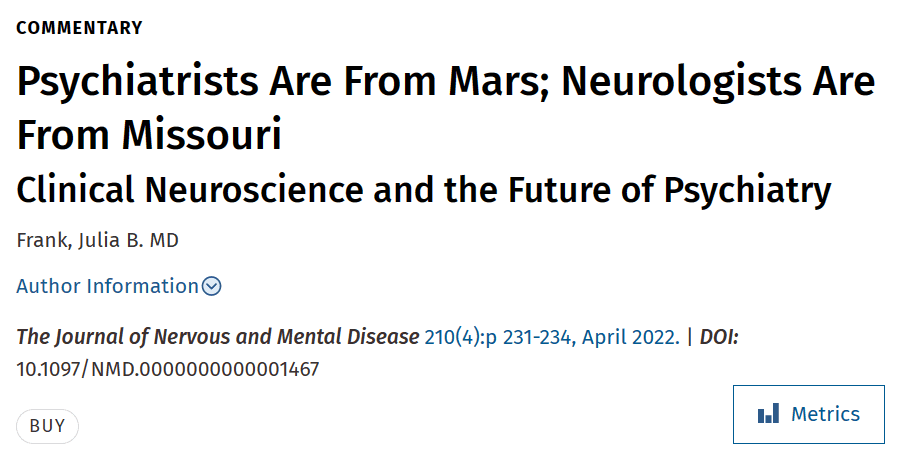
推动将相关专业都合并至应用神经科学的努力从未停止。许多医学院已采用基于器官或系统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将临床前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精简成一个“大脑区块”。全美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对精神病学的能力要求就包含神经科学的教育,并提供大量的在线课程。
然而,这些拥护者不能宣布“大功告成”。神经科学的系统应用似乎只限于最基础(教育)和最高级的(科研机构)领域。精神病学实践仍然需掌握经验性的诊断和药理学,但药理学的病理生理学模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国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委员会(ABPN)的认证核心对神经病学家来说主要是基于诊断(癫痫和神经肌肉疾病),对精神病学家来说是基于群体和实践(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老年精神病学、心身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
在磁共振成像呈阴性后,如果能联系到精神病医生,患有偏头痛的抑郁症患者会转给精神病医生。如果联系不到精神病医生,也会转给初级医师。在群体层面,尽管人们对因恐惧条件反射而产生的神经健康系统的影响的认识越来越多,但呼吁扩大灾后精神卫生健康服务时通常会忽略神经病学家的声音。
精神病学的知识传统允许其从业者对病人疾病的意义及其神经生理学过程一样感兴趣。就此而言,意义绝非重申过时的身心二元论。这个概念意味着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包括从脑网络间的化学交流到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表达的信念。
当然,不只神经病学家,事实上所有的医生都需要培养对人类经验的理解力,这包括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及正常活动和疾病的个人和社会背景。
然而,精神病学家在医学同仁中脱颖而出,他们认真而系统地关注意义的影响,并将广义的意义视作疾病的一个关键因素。意义虽是在大脑中构建的,却需要用远比神经科学更严格的方法进行探索。
例如,对依恋和分离的基本过程的阐释,来自于对动物和人类长期密切的观察。尽管依恋的过程牵涉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化学活动和结构,但是依恋的演化和文化意义,即其目的、影响和决定因素,构成了精神病学调查的应然领域。
同样,对创伤反应的研究,包括致残性疾病的创伤,主要通过与有思想、有感觉、有行为的人的交谈所实现。不过,就连最复杂的神经生理学或神经心理学调查也没能提出或解答如何分类和帮助创伤者等重要问题。
精神疾病的神经科学方法阐述了一些精神病学的重要问题,却也掩盖了其他问题。抑郁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仅与奖赏或恐惧的脑网络失调有关,还在于它们是否作为失败的结果或受挫的依赖而被体验到。即使对有创伤经历或持续压力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也可能忽略构成原因的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像其他抑郁症患者一样被诊断。
但是,对于这种情况的治疗,需要探索先前事件的个人意义和支持性社会干预,才能妥当处理当前与后续的疾病问题。社会心理和行为干预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如减少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自杀行为,匹配或超过非忧郁抑郁症、成瘾症、强迫症、围产期情绪和焦虑症等严格意义上的医疗治疗获益,而这仅是其中的几个。心理社会疗法之益还拓展到许多慢性疾病,例如给透析患者或进展性神经肌肉疾病患者提振心气。
精神病学对意义的兴趣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诚然,心理治疗已经从住院医师培训中心转移到外围,许多关于心理治疗的研究已默认为心理学。而且,即使是精神药理学家或神经精神病学家,当他们像受训时那样给予病人希望、激发信任和共情倾听时,也会在不经意间进行了心理治疗。
尽管存在许多阻力,特别是歧视性报销,让医生不愿进行系统性的心理治疗,但许多精神科医生仍然从事全职或兼职的私人执业,以维持其在这一领域的兴趣。除了美国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委员会的证书项目之外,研究生心理治疗培训项目也吸引了精神病学家及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对文化表达的严肃关切进一步说明了精神病学对意义的特别关注。神经病学家可能会用在加德满都和卡拉马祖的相同的发现来诊断中风,但精神病学家却知道,许多疾病的症状和有效治疗方法因文化背景而异,正如《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文化表述纲要所言。
就好比,神经病学家“看”他们的病人,精神病学家则“听”他们的病人。神经病学家已经投入巨大精力来开发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功能磁共振成像和其他超越结构而捕捉功能的成像技术,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进步。不过,最为复杂的功能图像也只是像无声电影一样,事后才添加了简单的字幕。相比之下,临床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和实践就像看电影,对话和动作同样引人注目。
也许有人会说,研究意义是别的学科而非医学的事。然而,一旦精神病学放弃了它的阐释要点,那么任何其他解释型学科——人类学、哲学、文学,甚至心理学——都无法填补这个空白。虽然精神分析提供了一本早期且有严重缺陷的解释规则词典,其所依据的理论囿于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至于太过僵化和缺乏实证支撑而无法解释当代的问题。但是,由此衍生的方法促进了调查和有效治疗,从精神分析性心理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到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疗法,以多种形式结合二者的元素。
与非治疗性的心理咨询师或严格以器官为主的临床医师不同,精神科医生有一种特殊能力,可以将医学上衍生的意义应用于恼人的临床问题。我们的折衷教育提供了事实知识和医学权威,可从独特的角度解释主观状态或行为障碍。
19世纪的医生把创造力缺乏或慵懒散漫的“肺痨态”变成了结核病——一种传染病*。精神病学家遵循同样的传统,将注意力缺陷障碍儿童的无序行为解释为执行功能的问题,而非懒惰或消极的攻击性。未来的精神病学家将需要熟练掌握神经病学和医学,才能做出这种医学的知情解释,但珍视症状的道德、社会和文化背景仍至关重要。对于那些静坐不能的孩子来说,建议学校提供便利并帮助父母更多的理解,这可能和兴奋剂药物同样重要。
*译者注:19世纪中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尽管人们对汹汹来袭的肺结核束手无策的,欧洲中上阶层却对肺结核出现了反常的喜爱,甚至“以病为美”。详见:《19世纪的欧洲,有些人唯恐不得这种传染病》
从这个角度来看,阐释意义仍是精神病学家在其医学定位中的核心工作,亦是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例如,精神病学家不再接受“冰箱母亲”的自闭症理论假说,也不再接受曾一度被吹捧的无意识冲突与溃疡性结肠炎之间的联系。精神病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关注意义层面,从生活史分析到基因测序,穷尽适合的研究方法,来构建影响个人如何体验和应对他们生活世界的网络。
人类灾难的流行病学进一步支持了精神病学与其他专业的持续分化。将精神病学缩小到应用神经科学的领域,会把它的关注点局限在那些最令人信服的大脑疾病上,如精神分裂症、痴呆、谵妄、双相情感障碍等。而事实上,精神诊疗的报销规则已经迫使许多精神科医生绑上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可这些困难无论多不可抗拒,在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自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就已指出,一般的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是全球范围内精神障碍的主要原因。然而,抑郁症并非一种明确的脑部疾病,而是一种包含生物、心理和行为因素的复合型综合症。
在工业化、人口拥挤、大流行病肆虐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当代世界,严重的精神压力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精神病学问题。例如,对已证实或疑似COVID-19感染者,其长期症状的研究和治疗需要广泛了解症状的免疫决定因素,以及这一可怕且具有社会破坏性的大流行病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对于这些工作,精神病学的加入实为必然。
实际上,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合并并不能让这两门学科摆脱其曲折的过往。神经病学出现在19世纪末,早于神经科学大爆炸的时代。病理解剖学、染色技术和人体成分分析技术将痴呆、癫痫、全身瘫痪和许多其他隐性综合症重新定义为特定疾病过程。根据定义,这些疾病是永久性、不可逆的脑损伤。得益于这些新技术和新理解,神经病学家积累了诊断和预后方面的专业知识。
相比之下,精神病学(至少在美国)起初作为一种起源于精神病院的治疗活动,其核心价值仍是治疗。尽管精神病学家从未忽视神经机能障碍在重性精神疾病中的作用,但直到上世纪中叶精神药理学取得进展,以及人脑实时发育和运转的神经科学脑模型创建后,对大脑机能的强烈关注才开始主导这个领域。因此,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神经病学一直致力于寻找治疗方法的疾病,而精神病学则致力于寻找疾病的治疗方法。
历史让科学变革清晰展现。当神经病学知识最初的爆发尘埃落定,临床神经病学由于缺乏治疗手段而几近没落,精神病学却通过接受文化和流行病学上的重要问题以及持续关注患者的社会和情感需求而壮大和繁荣。这促进了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住房和职业规划的发展,进而能够帮助患者在应对慢性致残性疾病的同时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尽管今天这种治疗大多由非医学人士提供,但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仍在研究、推进和指导这项工作。
新的神经科学远比旧的更有活力,也拥有更加光明的治疗前景。不过,与将神经病学融入精神病学的趋势正好相反,对将精神病学纳入神经病学趋势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对于从多发性硬化、创伤性脑病甚至痴呆等慢性致残性疾病所导致的个人困境更为系统的关注,让当今神经病学家获益匪浅。和精神疾病一样,这些疾病会导致人格的改变,并对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和思维表达等能力产生影响。
对重症患者(包括破坏性神经肌肉疾病患者)心理治疗的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和家庭及社会干预或许在提振患者精神面貌和帮他们过上尽可能有意义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神经病学家所需的精神病学教育只涉及精神药理学和一些简明的心理治疗示例的展示(虽然并不熟练)。然而,这些内容无法满足如今任一确诊致残性脑病患者的需求,无论他是经由精神病学或神经病学的研究和诊断。
无可否认的是,在治疗上,避俗趋新或是放任不管都有风险。每个领域的治疗手段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经验主义和应用科学主义,二者为治疗的热忱和治疗的失误推开新的窗楹。
与精神病学家一样,神经病学家也倡导过极不光彩的疗法。臭名昭著的“休息疗法”由19世纪的神经病学家塞拉斯·韦尔·米切尔提出,他曾叱责精神病学是医学的耻辱。这注定成为一块永久的纪念碑,它证明了以临床实践来评判一个专业是多么危险。
无论精神病学多么真诚致力于神经科学,它终将发现,今天看来科学合理的程序,在多年后的专家眼中也将显得过时甚至荒谬。精神药物的混合给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经病学家同样面临着因其治疗活动而被评断的风险。近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一种价格昂贵但效果一般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药物,这也说明将专业地位建立在现有治疗方法上是非常危险的。
最后,尽管将精神疾病重新定义为大脑疾病,也许会减轻一些患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但它不能消除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和歧视。精神疾病之所以被污名化,是因为精神障碍的患者违背了社会和道德期望,扰乱了他人的生活。尽管人们认识到不少精神疾病是大脑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遗传缺陷和自主神经过程的结果,但这既未能减少精神分裂症或酗酒对患者的损害,也没有减少社会对他们的排斥。
更让人担忧的是,如果精神病学不再研究那些神经科学不认可的病症,许多疾病将从医学中完全除名。基于医学的治疗方法对一般创伤、饮食障碍、物质使用障碍、意识状态改变和隐性躯体症状的局限性表明,我们不能等到对这些疾病有了详尽的神经科学理解之后,才试图帮助这些患者。
事实上,其中许多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束缚症侯群”,生物医学永远无法充分解释它们。虽然将这些疾病描述为精神疾病并不能解决污名化或可靠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偏爱将它们视为软弱、罪恶或邪恶表现的其他解释体系,精神病学和医学则必须与之抗争到底。
总而言之,尽管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无疑会对未来精神疾病的分类和治疗以及从业者的教育产生影响,但精神病学具有的研究传统和临床关注,使其成为一个合理而独立的专业。全世界范围内,对精神病学(不仅仅是神经精神病学)专业知识的需求是巨大的,且仍亟待满足。如果两专业仍保持独立,那些需要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理解的患者都能得到最好的服务,至少密苏里的宇航员登陆火星,并找到方法将他们分析散落岩石而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地球上有意义的问题之前都将如此。
原文:https://journals.lww.com/jonmd/Citation/2022/04000/Psychiatrists_Are_From_Mars__Neurologists_Are_From.1.aspx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Julia B. Frank,译者:刘凯、张亚楠、张涛(渤海大学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所),推荐:于欣(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