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阿莉莎·夸特,节选自《夹缝生存》,原文标题:《从“少爷和我”到“少爷和老奴”》,题图来自:《寄生虫》
从世界杯赛事上格外抢镜的卡塔尔王子到“万柳少爷”的意外走红,许多网友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对特权阶级的渴慕,“王子”与“少爷”评论区中的“老奴”,一度成了浏览过亿的热点话题。
十分有趣的是,除了自我降格为“老奴”,这些评论区中还常见对于少爷们的夸赞,赞赏他们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出来的礼貌、温和等良好品质,并归因于“家教好”。教育水平的背后是随经济与社会资本沿袭而来的文化资本,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我们无法忽视这些现象带来的影响。那些表现特权阶级生活的电视节目、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光鲜亮丽的网红或明星,都可以被视为“1%社会顶层”节目。今日我们讨论的“慕强”倾向,也能从经典英剧《唐顿庄园》中看到:贵族是善良的,底层仆人是丑恶的。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似乎毫不费力就过着普通人渴望的富足生活的明星网红,使我们感到艳羡、羞耻,想要把自己包装得同样光鲜亮丽,却忽视了真实生活的状况。
这些节目或社媒内容看似是“励志”的,将阶层流动表现得触手可及,实际上是将社会上那1%的人变成万众瞩目的存在,以至于大多数人会忘记,自己属于其余那99%。这1%社会顶层节目是如何让我们日渐沉溺幻象,步入深渊的?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中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
(下文节选自《夹缝生存》)
“楼上的人”总是善良,“楼下的人”总是邪恶
我喜欢看这些在我看来很“励志”的节目,或者叫作“1%社会顶层”电视节目(1 percent TV)—关于最顶层的1%(或与之接近的)人群为所欲为的故事。
这类描述顶层生活的电视剧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以极端残暴却又聪明绝顶的企业家为主。这些反派英雄拥有技术专长,并设法将其转化成了犯罪技能。在网飞的电视剧《黑钱胜地》中,财务管理被用来洗黑钱;在《绝命毒师》中,高中化学老师变成了制毒专家。当然,这些主角也经历了一些观众们同样在面临的挑战:他们的生计岌岌可危,或是遭到同事的背叛。这些节目暗示,他们的主角是为了保住其中上阶层的地位,迫于无奈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他们得自力更生,没有富有的祖父母或父母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困境。

还有另一类顶层电视剧,其中的富人与上面那些没有道德准则、一心向上、手段残暴的野心家相比更为超凡脱俗。与过去那些兢兢业业的实业家和大亨不同,这些节目中的主角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是时尚大师、品牌专家、投资人,或者莫名其妙就有个好出身。他们显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身处美国顶层1%最顶端的人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通常并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投资和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政治体制和税收制度。
我决定去探索前面提到的这些剧目,部分原因是在我怀着女儿、想要逃避自己经济不稳定的状况时也曾经选择过它们。我现在仍旧把它们当作生活的“止痛药”。这些梦幻的故事为许多和我一样的观众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在我们中的许多人面临职业危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持续的稳定感。我想要逃入这些节目之中,一面评判这些角色如何道德沦丧,一面代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我是从2010年开始这样做的,当时我那不堪重负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与屏幕上豪爽的虚拟世界相去甚远。当时最流行的是描述社会顶层生活的历史剧《唐顿庄园》,该剧的主要人物是20世纪初的英国贵族克劳利一家。演员们身着长外衣和天鹅绒烧花连衣裙梦幻登场,让我忘却了身体上的不适和对未来的迷茫。经济贫困的刺痛让我沉迷于这些真切反映20世纪初英国贵族生活的华丽景象。我几乎可以闻到他们的丰盛菜肴散发的香气,而在这些父母欢宴之时,未来的继承人们正在育婴室里受着家庭教师的照顾(我不是一个人,《唐顿庄园》的大结局吸引了960万美国观众)。

在《唐顿庄园》中,“楼下的”仆人阶级是不守规矩的,而且经常从头到脚都是邪恶的。我在怀孕时观看了第一季,看到一个男仆和一个贴身女仆合伙谋害他们的仆人同僚,这个贴身女仆还设计让她的女主人踩到一块肥皂上滑倒而流产。与此相反,贵族们都是善良的。《唐顿庄园》反转了前一年的PBS热门剧《楼上楼下》中精心设置的格局。《楼上楼下》从英国引进,曾在70年代播出,相比今天的电视节目,此剧更青睐住在“楼下”的人——坦诚友好的女仆和厨子。
躲进黄金遍地的屏幕世界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渴望。其他人和我一样想要在屏幕上观看这些节目,观看其中的暴力、枝形吊灯、私人直升机旅行,看仆人擦亮主人的银质茶壶、穿着一身皮衣的平民百万富翁举办私人说唱秀。美国劳工统计局2016年的年度调查发现,看电视是美国最普遍的休闲活动。我们每天在看电视上花费大约2小时44分钟,占据我们闲暇时光的一半以上。
我采访过的一些工作不稳定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关于游手好闲的顶层1%人群节目的热爱。“躲在网飞之类的东西后面要轻松得多,”一位不堪重负的家长说,“电视节目很轻松,能够短暂地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我是为了里面的华服和豪宅才看的,然后我会想:为什么我不能拥有这些?”
我喜欢看描绘顶层生活的电视剧,是因为我想看特权阶级的人为所欲为,但我也非常希望看到这些超级富豪受到应有的报应。
那样的报应永远不会到来。
社交媒体上的顶层信息,如何让我们感到羞耻?
这类关于游手好闲的顶层1%人群的电视节目真正火起来,是从2004年唐纳德·特朗普的真人秀《飞黄腾达》开始的。这个节目经历多次迭代,一共播了十几年。在节目中,特朗普把他在电视上的员工当成狂热的支持者。(正如特朗普当时所言:“我的飞机将会出现在每一集。”)这一切让我怀疑,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越是沉闷和不稳定,我们就越会依赖这些表现特权阶级多彩而又阴暗堕落生活的节目。

顶层真人秀让我们看到了极其奢华的婚礼、育儿管家和儿童生日派对策划人、出奇宽敞的豪宅、熠熠生辉的洛杉矶现代主义住宅、私人音乐会、精致的衣橱,以及高级发型设计师。顶层电视节目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部分解释了像我和本书中这些父母一样的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会为陷入困境而自责,却不去指责体制的失败。
正如詹姆斯·沃尔科特在《名利场》中就当今这些关于最富有人群(且看不到他们劳动)的节目写道:“如今,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描绘的巨额财富已经与制造业和那群看不见的辛勤劳动者脱离了关系,它与类似工作的一切都不再相关。它无牵无挂,充满爱意,生生不息。”
美国人现在接触的媒体越来越丰富,他们的信息来源不再仅限于好莱坞的编剧工作室或者暴躁的政治演说家。他们很可能也在消费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创造的媒体产品——像是网友们在YouTube,Twitter,Facebook或者Instagram上发布的反映个人生活方式的视频。虽然我们可能希望这些内容跟属于1%的顶层节目相比会是更为合理的99%,但通常事与愿违。我们在观看了别人的顶层电视节目之后,更倾向于产出自己的顶层社交媒体信息。
我采访过的许多中等危险阶级父母都提到,自己每天登录社交媒体时会感到头晕目眩。尽管这本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体验:像是一个孤独的从事专业工作的母亲在网上找到了组织。但是许多社交媒体信息中那种“快来给我点赞”的语气,可能反而会加剧你的孤独感和对自己社会地位的羞耻感。“谁要看那些存心让你觉得自己又穷又老又不酷的Instagram?”一位女士对我说。“Facebook就是魔鬼。”另一位母亲告诉我。她在Instagram遭遇了一连串阳光灿烂的家庭度假照片的打击,正在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
那些大晒优越地位的人可能会让周围无法享有这一切的人产生羞耻感。曾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研究的作家迈克尔·勒纳在《纽约时报》中写道:“我发现劳动者的压力往往会因为羞耻感而加剧。按照他们所受的教导,美国经济是由精英主导的,他们为自己无法在其中‘获得成功’而感到羞耻。”
根据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传媒学者列夫·马诺维奇的说法,觉得别人的社交媒体信息令人惊奇,而且经常比现实更为光鲜,并不是一种错觉。我们在网上展示自我时,确实是在创造一个关于自己的励志故事。马诺维奇跟一位经济学家一起,研究了从纽约、曼谷、圣保罗和伦敦等地分享的数以百万计的社交媒体图像,并把其结果称为“不平等的Instagram”(Inequaligram)。在五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对分享自曼哈顿的7442454张Instagram公开照片进行分析,他与合作者发现,不管当地拍摄者自身的社会阶级地位如何、家庭住址在哪,他们发布的Instagram照片大部分都集中在当地相对富裕的区域。
如今,很多美国人每天都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向他们的一小群受众展示自己的时间线(timeline)。他们发布的信息往往具有顶层1%的审美特征——在海边或者山里度过的家庭假期、昂贵的青铜耳环、或者家庭手作苹果方块酥。浏览这些图像当然会让我们感到嫉妒,降低我们的价值感。我们深陷于经济条件远比我们优裕的人(或者希望看上去如此)的土地上,为了逃避现实又躲进所谓的朋友们在海滩上把酒言欢的照片里,但又怨恨自己无法获得这些。

“在莫斯科这样的地方,整个城市的分布更为平等。为什么在纽约的人们不去展现自己真实居住的地方呢?”马诺维奇问道。经过进一步研究,他指出在Instagram等平台上,人们更喜欢极简主义的视觉风格,这种审美观念是由iPhone等事物助长的:极简主义曾经是特权的标志。“这些人都不是有钱人,也没上过哈佛。”马诺维奇说,但他们却知道怎样拍出透露着“经济和社会特权”气息的照片。如他所言,这是“被大众占用的精致美学”。
事实上,包括我采访过的人、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在内,任何访问社交媒体平台的人都无法忽略那些看上去可能比他们实际更加富有的人(在滤镜之下,你看不出一条连衣裙是化纤的还是丝绸的)。人们还会晒出他们阶级地位的象征:美貌的伴侣和外出探险的假期。这些呈现着繁荣景象的照片:“富拍”(wealthies)而不是“自拍”,正是我在《品牌阴霾》(Branded)一书中所称的“自我包装”的延伸。这里所展示的往往是充满想象力、志得意满、品位不凡的个人形象,或者是过着“最好的生活”的家庭形象。
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马克·利里表示,我们的社交媒体信息往往会提升和夸大我们的社会地位。“通过发布自拍,”他写道,“通过里面的服饰、表情、物理场景和照片风格,人们可以让别人记住自己,以此树立自己特定的公众形象,而这想必是他们认为能为自己带来社交优势的公众形象。”
如果我们被Facebook上的幸福笑容和关于社会顶层的电视节目包围,又怎么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呢?
根据明德学院电影和媒体文化与美国研究教授贾森·米特尔所言,从历史上看,电视节目一直热衷于表现社会阶级的向上流动。但与我童年时相比,如今网络上流传的特权形象更为刺眼,并且充斥着社会阶级焦虑。过去节目中邪恶的富人形象与现在那些富有的反派英雄截然不同,过去电视上的家庭如同代代相传的王朝,从来没想过会遭遇经济危机。
克里斯蒂娜·韦恩是《绝命毒师》时期AMC电视台的节目总监,她认为这部剧的热播跟2008年的经济衰退大有关系。这部剧于2008年开始播放,但走红是在2009年经济衰退到达低谷的时候。“那时人们看到了金融界对美国的所作所为,看到华尔街的人越来越富有,”韦恩说,“人们想要看到他们的英雄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在此过程中,这些人物可能确实超越了善恶:他们抢劫和欺诈暴徒恶棍,然后开始设法惩罚那些甚至比他们更富有的人——例如毒贩和跟他们竞争的对冲基金经理。韦恩表示,《黑钱胜地》和《绝命毒师》等电视节目也是对复仇的幻想。这些反派英雄可能很富有,但他们依然对超级富豪实施了复仇行动。这样看来,他们依旧属于失去稳定、心怀愤懑的中产阶级一分子——就和他们的观众一样。
正如一位中年求职者告诉我的:“这些电视节目中的每一个人都精心装扮、美丽动人。然而,这不是我的生活!我欠着女儿的学校学费,而且房租也不便宜。”
那些观看《亿万》的人——2016年播放的第一季吸引了630万人每周观看,用《娱乐周刊》的话说,带来了“真实的资本收益”。人们看着一个一头红发、有点邪恶的长岛对冲基金大亨,不禁对他又嫉妒又钦佩,尽管他明显是在犯罪。如果收看《嘻哈帝国》,他们便会拥戴一个富比王侯的嘻哈巨星,而这个人同时百分百是个杀人犯。

目前播出的两季《亿万》塑造了男主角博比·阿克斯罗德,昵称“阿克斯”。他外表英俊,长着一头红发,对妻子忠诚,对朋友也很照顾。他可以让大牌乐队金属乐队为他私下表演,却拒绝了一个乐迷的肉体诱惑。阿克斯的另一个加分项是:他靠自己打下江山,不像保罗·吉亚玛提饰演的查克·罗兹出身富贵世家。
这一正面设定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阿克斯在道德上受到了深刻挑战。“9·11”事件发生时,他没有在位于世贸中心的公司办公室上班,而是去会见律师了——他因为从事灰色交易即将被公司解雇。在许多同事丧生后,阿克斯接管了公司。此外,他谎称自己参与了救援行动,事实上他通过立刻抛售航空公司股票等手段发了一笔灾难财。还有一件令人不齿的事,阿克斯阻挠一位垂死的员工获得治疗癌症的实验性药物,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个人继续活着可能会给他带来法律上的灾难。总而言之,阿克斯和他的工作人员利用内幕消息和精心策划的诡计进行交易,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亿万》等电视节目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观众得以躲进顶层人士的生活之中,而这些顶层人士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不受规则的约束。
不平等娱乐节目:从什么时候起,1%变得比99%更伟大?
我们怎样才能开始创造和消费反映我们真实情况的文化:负债累累、在各种不稳定的工作之间跳来跳去?而这种冷峻的写实主义又会对我们的心态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有一种电视节目类型对贫富差距进行了批判——主题不那么光鲜(例如债务、失败)的电视喜剧。这种节目比顶层电视节目要小众得多,我们称之为“不平等娱乐节目”(inequality entertainment)。
根据我们的经验,不平等娱乐节目听起来不太可能成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但我将它视作其中一味药方。为什么这样说?不平等娱乐节目用我们的自我意识或欠的债来娱乐大众,否则令我们沉迷的屏幕上将全是关于顶层阶级的谄媚故事。不平等娱乐节目挑战了潜藏在一些华丽形象背后的东西。正是成千上万发布在社交媒体和YouTube上关于学生债务的个人故事,撕下了Facebook上幸福形象的面纱。
电视上的不平等娱乐节目包括《黑客军团》和《硅谷》等。《黑客军团》的主创萨姆·伊斯梅尔借鉴了自己因为教育而欠债的经历,他曾经提到自己直到毕业多年以后的2015年才还清贷款。《黑客军团》塑造了一个名叫埃利奥特·奥尔德森的角色来表现“占领华尔街”事件之后的贫富差距。

这个家伙身材瘦弱、睁着一双泛红的大眼睛,在某一季中黑进了朋友安杰拉的学生贷款账户,以期减轻其经济负担。白天,他在网络安全公司Allsafe工作;到了晚上,他的任务是和一个类似匿名黑客游击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一起打倒这些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抹去所有债务。
在《黑客军团》中,奥尔德森有许多冷静而饱含愤怒的旁白。“从什么时候开始,广告感染了我们的家庭相册?”奥尔德森说,“从什么时候开始,1%变得比99%更伟大?”
由HBO播出的《硅谷》也是如此。这部电视剧审视了吃拉面、睡沙发的低端科技工人与1%的科技专家和霸主之间的巨大鸿沟——此剧的戏剧性和笑点主要来源于此。从风险投资的长袍派对到摇滚小子的私人演唱会,《硅谷》中科技巨头的荒唐放纵与下层梯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一个绝望的追梦者只能在他打工的酒铺里向顾客推销他的APP。剧中,我们主人公的大买卖一次又一次落空,把他们不断推回一贫如洗、到处睡沙发、在憋闷的房间里昼夜无休地敲代码的荒诞而残酷的世界。
然而,顶层电视节目相比不平等娱乐节目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些1%社会顶层电视节目和我们总统在电视上的滑稽表现当作指南,那么终极的奢侈不仅意味着可以看到滔天的财富,而且还能看到那些巨富为所欲为,不用考虑后果、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就像众神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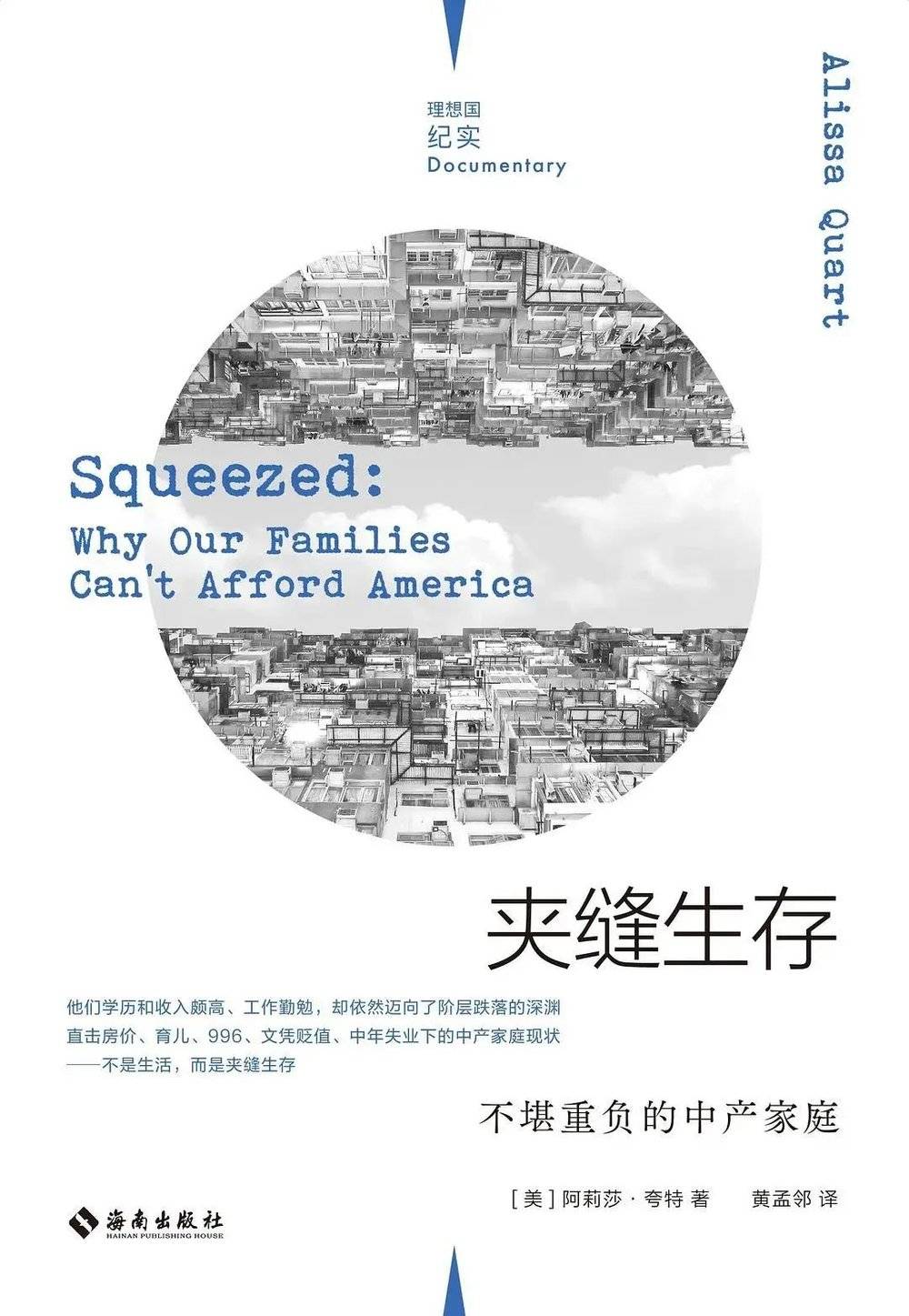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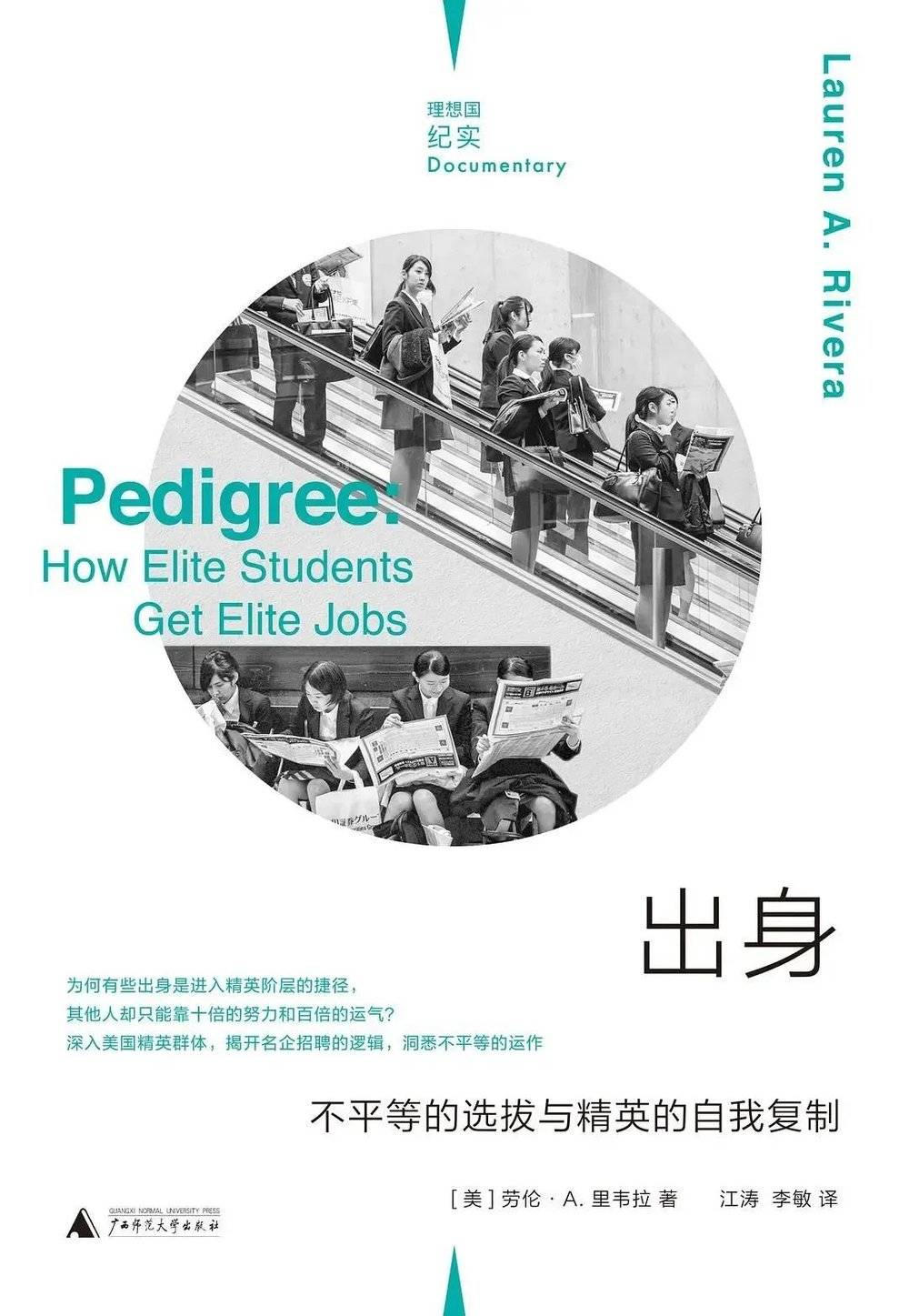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阿莉莎·夸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