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王小伟,原文标题:《王小伟丨接物与待人:囤物癖、断舍离与崇物文化 #“技术向后看”专栏11》,头图来自: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据我观察,我们和父辈对“物”的看法差距非常大。老人爱囤东西是一个普遍现象。“80后”“90后”的父母仍然有囤积癖,善于在本已狭小的空间中生产角落。有一次,我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不少藏匿的塑料袋,这才注意到父母每次买东西用的塑料袋很少扔掉,甚至连外卖的塑料袋都打包装好。但这些东西早就被忘在角落里,永远不会再被翻出来用。为了保持整洁,我只好定期把屋里的东西扔一部分。
然而,近来这种囤积癖似乎逐渐蔓延到年轻人身上,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储物空间不够用。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扔过两次哑铃组、三次跑步机,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我为减肥付出的纠结。收纳变成了一门大学问,很多家庭主妇甚至专门去学习收纳术。
人的一生究竟需要多少东西?2005年,艺术家宋冬在798艺术区做了一个叫“物尽其用”的展览。[1]这个展览占据的空间非常大,硕大的展厅当中摆放着宋冬的母亲赵湘源女士毕生搜罗来的各种物件,有的用过,有的还没用过,包括各式各样的盆、水壶、褥子、鞋子和衣物。“物尽其用”曾在光州双年展、柏林世界文化宫、悉尼艺术节、现代艺术博物馆、温哥华美术馆等亮相,获得了极大成功。据说有人默默地看着满眼的物件,突然就痛哭流涕。

可惜当时我没能去现场,后来看了不少展场图,大概搞清楚了展品的体量。查看图片时,人的视角不具备涉身性,不能走进物品堆里移步换景。不过,我因此获得了另外一种视角:所有的物体透过广角镜头展开,作为一个整体被凝固了下来。盆、衣服、箱包等本来独立存在的个别物品,此时都嵌入到一个整体中,向外展示着一个普通人的一生。
一个人的一生,似乎就是由他/她用过的、正在使用的和从未使用但业已拥有的东西构成的。看到满屋的东西,虽然没有见过赵女士本人,但总觉得她像是个故人。后来看采访,我了解到宋冬是有心把这些琐碎的生活物件都搜集起来的,最后用来打包展示。他回忆说,母亲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就是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比方说:铁线不舍得扔,觉得可以用来做衣架;破衣服更舍不得扔,可以用来做袜子、补丁;饮料瓶舍不得扔,可以用来做杯子、花瓶,更可以做成厨房里的调料瓶。
这让宋冬非常恼怒:他家的阳台总是被母亲堆满各色物件,眼见着屋子成了垃圾堆。后来,宋冬想到了一个狡猾的办法,半带恐吓地告诉母亲,房价一平方米4000块钱,要把这昂贵的空间变成杂物间,实在是得不偿失。这一手段立竿见影,他的母亲最终停止往屋里囤东西。
我对父母的囤积行为一度也非常光火,但看到“物尽其用”之后,又莫名其妙地感动。后来我琢磨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展览和现实不同,真实的生活是无法容忍大量囤积的,而当把囤积的东西分门别类地铺在广阔的空间中时,杂物就不再制造角落,而是有秩序地摆放着。这时,旁观的你获得了另外一个视角,才发现一个人的人生居然可以这么满、这么大、这么博杂,同时又这么琐碎和无关紧要。
或许,在赵女士心中,物品从来没有像艺术品那样被分门别类地归置过:这个盆不应和另外一个盆放在一起,它应该和盆架、毛巾甚至铁丝(作为潜在的晾衣架)摆在一起。各种东西实际上是通过生活目的产生关联的,各不相同的物品被看成一个大系统上的小零件。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物品不按它的属类来分,而是按它的用处来分。
而从用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功能的系统中,和其他的物质广泛地发生着联系。“物尽其用”的艺术感在于将一个人一生所用的物品摆放成一个沉思的对象,这些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在展览中立刻变得陌生了起来。这一令熟悉物陌生化的努力,也使得我们得以端详自己的东西。
为了反抗囤积,日本作家山下英子写了《断舍离》,成了中年人尤其是中年主妇的枕边书。我第一次看到媳妇有这本书时,吓得以为婚姻出现了危机。翻开书才知道,所谓“断舍离”是要抛物,而不是要抛人。作为一项生活主张,“断舍离”指要断绝物的进入,舍弃不需要的物,进而远离物,以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个主张居然是从收纳文化特别发达的日本传过来的,或许可以把它看成是对收纳文化歇斯底里的反抗。相较于收纳,“断舍离”转换了根本视角,认为在一个空间里之所以收不下东西,不是因为箱子不够大,而是因为东西太多。

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一日一处》中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位女士,因为丈夫对她不好,所以日夜想要跟丈夫离婚。一天晚上,她看到结婚时父母给她陪嫁的衣柜。这位女士有很多漂亮的和服,父母特意送来两个柜子,虽然里面的和服她从来没有拿出来穿过。现今父母相继离世,这位愁容满面的女士端详两个柜子良久,曾一度放弃离婚的想法。作者诱导我们去想象: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两个柜子,或许这位女士早就离开那个男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也许,我们的确拥有太多,房子又的确太小,所以需要一些取舍。很多人觉得是物造成了自己的痛苦,只要把物从生活当中尽量减除,少买一些衣服,少买几部手机,就可以获得幸福的人生。还有人认为,物背后的资本才是造成痛苦的原因:资本家开足马力不停生产,不断用新的物来诱惑我们。抖音、快手和小红书这三台“虚假需要”制造机,不断地诱发我们产生不正当的欲望。[3]当这些欲望实现不了的时候,人会陷入痛苦,而当这些欲望得以实现时,又会陷入空虚。
“断舍离”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解决方案。讲“断舍离”的杂志上常出现的一个经典画面是:在一间空空如也的白房子里,一人身披禅衣,枯坐其中。每次看到这样的图片,我都看不到宁静,我看到的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大拒绝。只要是一个有活力的空间,尤其是有孩子存在的空间,就一定会有堆叠,会有不断增加的角落,瓶瓶罐罐,邋邋遢遢,这样的房间才有人味。我甚至觉得,这一画面在今天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粗俗的营销,背后兜售的是一种单身贵族式的消费生活方式:他/她决意要一个人过,买了几件设计师单品,放在一个铺满石灰水泥的大白房子里,自己半跪着,面对一盆池坊花。
“断舍离”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小到仅能放下自己。我不仇物,觉得并不是物,甚至也不是其背后的资本给人带来了痛苦。这种痛苦都是外在环境施加的,要摆脱它并不太困难,不买东西即可。真正的苦是内在的,是一种很摩登的苦,它可能源自一种人、物二分的形而上学,把物看成中立工具,继而可以任意使用它。任性的使用将人和物的本真的关系割断了,我们和物不再交流,只能利用。之所以会囤东西,恰恰说明我们不重视东西。因为东西什么也不是,所以可以随意添置,也能随意丢弃,导致海量物品涌入生活世界。而当东西太多,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压抑。
“断舍离”不大能帮助我们真正摆脱物品带来的困扰。甚至一旦走火入魔,或许还会使人罹患“仇物症”,就像减肥者不幸得了厌食症一样。以为通过对物的排斥,就能纯化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错误。我们都是物品依恋者,物是人们走入精神深处的梯子。我们经常说“待人接物”,接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待人的态度。如果你真的去践行“断舍离”,反倒可能变成一个冰冷的人,没法自然地与人相处。
在当今商品社会中,物的生产被少数人垄断,而物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有人对物能有另外的知识。我们大多只知道一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但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在这个时代,要建立与物的妥当关系,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物的理解和熟悉,这有赖于发生一场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适当的接物方式,或许一旦重视物的介入,我们反而不会随意让大量的物涌入人生,就像一个重视爱情的人,其伴侣数量通常也十分有限一样。
人是非常善于迁怒的动物,有不开心的事,就要怪罪他者:如果不是自己的错,就是别人错;如果不是别人的错,就是资本的错;如果资本也没错,那就是东西的错。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提示我们,人的本质不是智人(Homo Sapien),而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4][5]物不是一个中立的、被动的工具,它实际上具有意向性,能参与构建我们的知觉和心灵。[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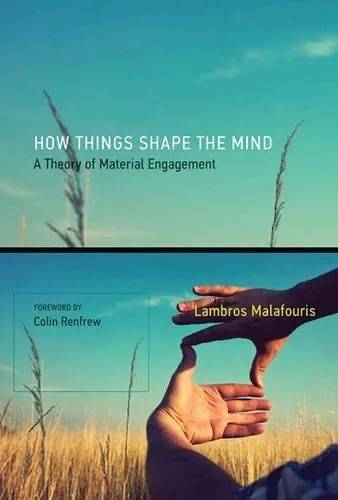
据我观察,人对故人的追忆、对故事的反刍实际上不是在脑中随意完成的,而是通过物的引导来完成的。人的精神常常纷念迭起,千头万绪,像四处乱窜的苍蝇,很难安静下来。而物的呆板能给精神提供一个锚点,扣紧这个锚点,人才能从此岸的世界成功地登陆彼岸的世界,从世俗的生活跨入神圣的领域。
就像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说,人的生活总是在世俗和神圣之间摆动。年轻人用一个东西,可能仅仅把它当作纯粹的工具;当其年龄不断增加,生活经历足够丰富之后,熟悉的物件就变成了一件礼器,承载着大量的生命信号。一言以蔽之,我们并不是简单地用一个东西去实现一个功能,我们是在与物“交往”。
对中年人来说,物事关过去。比如,铁丝不仅能用来绑东西,也可以做成衣架。多年以后,衣架还在,但做衣架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看着这个衣架,就会常常想起他。再比如一个心思细腻的中年女人把母亲去世前做的豆包冷冻起来,一两年舍不得吃,存储在冰箱的角落,仿佛母亲还在人间,自己还能被她在乎。物比人坚挺,它因为缺少灵魂而显得呆滞、倔强,能够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也因此成了一个完美的“时间琥珀”,看着它,就能让人想起围绕它的人间苦乐。
我逐渐理解为什么有的老人有囤积癖。一方面,老一辈人用到的物的生命周期都是短暂的。他们常用草木灰刷碗,皂角洗头,纺线制衣,斫木成车,几经轮转,这些东西逐渐隐入尘烟,不留痕迹。可能因为这样,另一方面,老一辈人特别爱惜物在每次轮转中的停留。老一辈的物质生活曾经非常匮乏,加之当时物质生产力低下,经济又不发达,这也使得他们必须惜物。
但我怀疑更核心的原因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在他们心里,当下用的东西当然是要保留的,而旧的东西也不能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附着自己的心血和重要的生活记忆,丢弃了它们,就像背叛了什么一样;另一方面,每当看到、摸到过去的物件,过去那些重要的生活内容就透过回忆变成了栩栩如生的现在。
最神奇的是,这些满载过去的物件,其实是储存在未来之中的。老人们经常说,这些东西不要扔,以后还能用得到。似乎在提示我们,未来用不到的东西,就真的无处安放了。我把这话看成一句箴言,意思是:面对无常的未来,我们可能要经常从过去调取相应的资源。对老人们来说,旧物能不能在未来用得上,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
每个人在生命意义上都是一位老人,我们真正持有的只有“过去”,当你注意到自己的“当下”时,其实它就已经成了过去。有时候我想,每一次当母亲掏出一个藏好的塑料袋去买菜时,都是一次心灵的治愈活动,它确凿地说明:旧物可以新用,枯木可以逢春。
物于人生如此重要,以至于日本人不仅供奉人,还供奉东西。日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叫“针供养”,即妇女把用断了的针插在豆腐上供奉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说的是钢针一辈子勤劳,其坚硬的刺头刺穿了很多东西,等它用坏了,就要把它插在全世界最柔软的东西上,让它好好享福。头一次听说此事时,我觉得有股荒诞气,后来想起来,心里又有点酸。中国人不吃耕牛,日本人不舍断针。不过最近听说有国人在“放生”矿泉水,如果是真的,也算大败日本对手。

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将东方文化称作“崇物”的文化,而把西方文化叫作“制物”的文化。[8]东方人对天下万物抱有很深的感恩情怀,物与人交往,而不是纯粹地被拿来使用。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也强调格物致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从来没有只是把物当作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把人和物置于两个存在领域,将人和物看成是根本上联系着、彼此亏欠着的关系。为了理解接物的态度,古人的世界或许值得再一次走入。
参考文献:
[1] 巫鸿. 物尽其用: 老百姓的当代艺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 山下英子. 断舍离: 一日一处[M]. 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 2021.
[3] 马尔库塞专门讨论了“虚假需要的问题”, 参见: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4] IHDE D, MALAFOURIS L. Homo Faber Revisited: Postphenomenology and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9, 32(2):195-214.[5] MALAFOURIS L. How Things Shape the Mind[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3.
[6] VERBEEK P P. Cyborg Intentionality: 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Sciences, 2008, 7(3): 387-395.
[7] IHDE D.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钱明, 难波征男. 崇物, 简素, 兼和: 冈田武彦与张岱年的世纪对话[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王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