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道风物 (ID:didaofengwu),作者:鹿鸣谷,图片编辑:何鹏飞,制图:鱼一条,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东北孩子的基因里,一半是雪,一半是辣椒
餐桌正中央,一小碗儿炸鸡蛋酱。蒸腾的热气下面,巧克力色的豆瓣颗粒,罩着薄薄的蛋花“金缕衣”。
旁边的盘子里,刚洗净的青椒,还挂着水珠。小孩子早等不及大人把饭上齐,先抄起一根“辣味长矛”,朝“金缕衣”戳了过去。

“喀嗤”一声,裹着酱香蛋液的青椒断掉,脆爽溢满口腔。随着辣椒籽次第爆开,火辣辣的脉动阵阵冲击着味蕾。小孩子带着逞能的表情一口咽下,胃里仿佛窜进一条调皮的“跳跳龙”,肆意撒欢儿翻腾热浪。
这几乎是每一个东北孩子,印刻在基因里的,童年生吃辣椒的回忆。
辣椒之于东北,是白山黑水的热土乡恋,是延边风物的姹紫“腌”红,是林海雪原的“只此青绿”。
东北与辣椒:“冰火两重天”的邂逅
大航海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百年后,发生了两件事:1591年,明代戏曲家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第一次提到辣椒这种美洲作物;翌年朝鲜爆发了“壬辰倭乱”,辣椒挟带着日本海腥咸的风,经朝鲜半岛传入辽东。
东北这“嘎达线儿”,是继浙江“海上丝绸之路”之后,有史记载的第二条辣椒传入中国的路径。尤其是辽东地区,对于辣椒的记载早而且多,不但和浙江几乎同时,就连后续记载也多。
比如康熙年间的《辽载前集》中说:“秦椒,一名番椒。椒之类不一,而土产止此种,所如马乳,色似珊瑚。”
地处塞外边陲、“古来冰冻皆寂寞”的东北,与南美拉丁风情的辣椒看对了眼儿,主动“壁咚”发起攻势,二者竟出人意料地“冰火两重天”,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东北虽然高冷,却是一位老“湿”。一些地方相对湿度在65%以上,属温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在1120mm以上,特别是东北东部降雨量更丰富,湿度更大。所以客观上促成了一定的食辣环境,给了“辣椒小姐”一副可以倚靠的肩膀。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就下雪。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东北还是被忽视的辣椒产区呢。东北肥沃的黑钙土,非常适宜辣椒“窜个儿”,要知道,辣椒对土壤酸碱度非常敏感,而黑钙土恰恰是中性的,而强烈的光照和干燥的秋风,又加速了辣椒的自然风干。

吉林省的洮南辣椒种植基地,红干椒作为商品已有近百年的生产加工历史了,还曾于2003年被中国特产乡推荐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辣椒之乡”。而辽宁省的北票市辣椒种植基地,出产的红干椒已成为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进击的辣椒君从东北走向全国。
全国人民的春晚欢乐回忆,也有东北对辣椒唱的情歌。不信,请看1997年春晚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面魔性洗脑的主题曲:“火辣辣的心,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唱得多带劲儿呀!

东北对辣椒的感情,也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各种版本“东北话十级听力题”中,“辣椒”都是高频出现的考点。
比如,形容食物非常辣,叫——“猴辣猴辣的!”
形容辣得不能自拔,就说——“辣得薅(hāo)的!”
形容小鸟依人的辣,也有专有名词——“辣姑囡(nān)儿的!”
就连形容人阴阳怪气,也要带上“辣”字——“这个人酸饥辣臭的!”

出了山海关,明太辣鱼鲜。
东北对辣椒的感情,也写进每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散发着绿皮火车气息的味觉记忆里。
“花生瓜子儿烤鱼片,啤酒饮料矿泉水儿”,是各地列车员统一的“喊麦”,可等到火车驶出山海关,进入东北境内,列车员“麻溜儿煞投儿”(mā liū shà tōu:东北方言形容迅速),把普通烤鱼片换成黄色袋装的延边特产——明太辣鱼。与沟帮子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车厢三宝”平起平坐。
看!东北老铁对辣椒的爱,就是这么直白!
朝鲜族的辣菜坛子,装得下一个宇宙
在我的家乡东北,朝鲜族是一个鲜活的文化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四江(图们江、鸭绿江、牡丹江、松花江)及两河(辽河、浑河)流域。小时候,我的左邻右舍近半数都是朝鲜族。我的小学旁边有朝族小学,等上了中学,旁边还有朝族中学。
童年时代身边的朝鲜族文化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一年四季穿白裤子的朝鲜族老爷爷;“头上能顶万物”的朝鲜族老奶奶;班里数学最好的永远是朝鲜族同学;去朝鲜族家庭做客,进屋就能上炕(名为“地炕”,有点类似日式榻榻米)……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朝鲜族邻居们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的辣菜。朝鲜是一个能吃辣的民族,而且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清代《高丽风俗记》《朝鲜风土记》中便有记载。
比如《朝鲜风土记》中说:“国人无分贵贱,皆酷嗜辣椒,极沃之田多种此种,收后或晒于屋上,或凉于田间,远望之如火如荼,颇也骇目,市中堆积如山,或有舂为细末经售人者。”

古代有食辣传统,现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的家乡,人口多的朝鲜族家庭,一年要储备一百多公斤辣椒呢!每到秋冬,空气中便弥漫着辣味,朝鲜族邻居在室外摊晒的干辣椒,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腌菜坛子,提供了干湿两种气息。辣椒里的各种芳香化合物,渗透进童年原初的味觉记忆中。
众所周知,东北大米好,空口吃都香。可是在朝鲜族孩子那里,打小就知道一个进阶吃法——辣白菜汁儿拌白米饭。
冬天的时候,刚盛出来的白米饭冒着热气,先空嘴儿吃一口,支链淀粉的甜顿时溢满口腔。朝鲜族阿妈妮(大娘)会从室外的腌菜坛子里,舀出一瓢带着冰碴儿的辣白菜汁儿,鲜红透亮。
当红如琼脂桂魄的辣白菜汁儿,浇在晶莹如雪的米饭上,强烈的视觉反差极具冲击力,辣白菜汁儿逐渐融化的冰碴儿,在蒸腾的热气中影影绰绰,有着“昙花一现”般的美。
等到辣白菜汁儿与米饭完全交融,但见每一颗白皙嫩弹的米粒儿,都挂上一层红色“包浆”,就像初进贾府的林黛玉,披着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斗篷),化身冰雪聪明的精灵,叩响门牙“贾府”的大门。
闭上眼睛细细咀嚼,你会感觉舌尖舒展成了红毯,丝丝沁凉的辣,就像纤细的高跟鞋一样,在味蕾上跳起“踢踏舞”;接着,辣白菜特有的发酵酸爽接踵而至,与米香交织缠绵,又仿佛在口腔的“维也纳大厅”里跳起华尔兹。
冰碴,白米,红汤。
椒辣,汁酸,饭弹。
如果说辣白菜汁拌白米饭的味觉体验,是“林黛玉进贾府”,轻盈婉转,那么辣腌紫苏叶,就是“鲁智深进野猪林”,泼辣豪放。
朝鲜族对紫苏叶的处理方法,不同于南方的“小清新”,像薄荷一样泡茶、或像罗勒一样作为调料点缀,而是直接整张大片抹上辣酱腌制。
我曾亲眼见识过朝鲜族阿妈妮腌紫苏叶的过程。
那还是小学时候,我们一班小伙伴到朝鲜族朋友家做客,围观阿妈妮腌菜。但见她拿起一张紫苏叶,展开在手心,刷一层辣酱,放到坛子里压实;再拿一张刷一层辣酱,叠在上一张紫苏叶上,像堆积木一样,但是每一片都错开一定角度,整体呈螺旋状排布。
我们看得满脑袋问号,阿妈妮笑着解释道:“这样才能让紫苏叶锯齿状的边边角角,与辣椒酱充分接触呀!”


等到整个腌菜坛子都压填得差不多了,阿妈妮让我们往里面一瞧,只见几座紫苏“巴别塔”矗立在眼前,每一座侧面都缠绕着“锯齿旋梯”。
不同于辣白菜叶片肥厚,需要腌半个月才能开坛,紫苏薄薄的叶片很好入味儿,如果想吃“暴腌菜”的鲜爽,两三天就可以吃了。如果想要乳酸菌充分发酵,则需要等上一个星期,那时候,紫苏叶腌透了,辣椒酱也变成暗红色。
夹起一片,但见薄薄的紫苏叶裹着厚厚的辣酱,仿佛酲红面膛的鲁智深,在野猪林里左冲右突。吃法也很豪迈,要好几片一股脑儿塞进嘴里。
这时,紫苏特有的清凉气息直冲脑门儿,虎虎生风的酱辣在舌尖纵横恣肆,而叶背的绒毛刮刮的、痒痒的,让我感觉像是鲁智深在嘴里挥舞着“月牙禅杖”。
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家中的辣腌菜畅快朵颐,学校里的辣菜炒饭,则另有野趣。
辣牛蹄筋炒饭,是多少东北孩子心中永远的冬日之光!每个小学、中学校门口,几乎都有一个朝鲜族阿巴吉(大爷)开的流动餐车,叫卖辣牛蹄筋炒饭。
阿巴吉在铁板上刷一层油,然后摊开晾凉的米饭,用铲子搅匀,再撕开一袋东北特有的辣牛蹄筋,不同于熟食店的整条柱状牛蹄筋,朝鲜族牛蹄筋是压扁后撕成细细的小条儿。
铁板前,阿巴吉手起铲落,殷红的辣牛蹄筋和白雪一样的米饭上下翻飞,如同白衣剑客和红拂女在镜湖上比武,十分具有观赏性。让周围一这脸蛋通红、拖着鼻涕翘首以盼的小孩,瞪大了眼睛。
只听“咵喳”一声,阿巴吉一铲子填满了饭盒,前面的孩子赶快接过,“提了突噜”吃起来,被辣得“嘶嘶哈哈”,还是停不下来。嘴里,牛蹄筋的韧性,米饭的弹性,加上辣酱的野性,“三管齐下”,收服了孩子放纵的天性。
除了辣白菜、辣腌紫苏叶与辣牛蹄筋炒饭,在遍地山珍的黑龙江南部长白山地区,沙参、桔梗(朝鲜族称“道拉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也是朝鲜族“腌菜坛宇宙”里的明星。
而在不乏海味的吉林沿边地区,辣腌“海虹” (一种贻贝)、明太辣鱼(一种鳕鱼),辣腌“海桔梗”(一种海藻)也是朝鲜族辣酱坛子里的“轮值盟主”。
朝鲜族腌辣菜的明太鱼,是一种鳕鱼,它不同于英国“鱼炸土豆条”里的鳕鱼。英国鳕鱼属于“大西洋鳕”,东北的明太鱼是“黄线狭鳕”,脂肪含量比英国鳕鱼还低呢。所以,朝鲜族用这种鳕鱼做辣菜,口感特别有韧性。
小时候,每到秋冬时节,我家乡的公路两旁,都挂满了晾晒明太鱼干的松木架子,一眼望不到头,鳞次栉比的排列着,就像安徒生笔下“坚定的锡兵”,守望着来来往往的大货车辆。
朝鲜族辣腌明太鱼的成品,除了出口到韩国,或者做成韩餐厅里的明太辣鱼丝,最常见的就是火车上叫卖的黄色袋装的整条明太辣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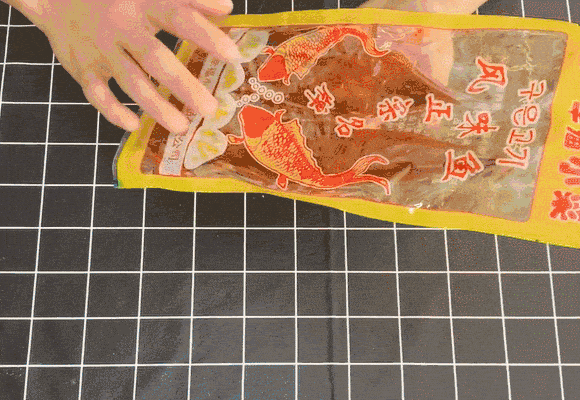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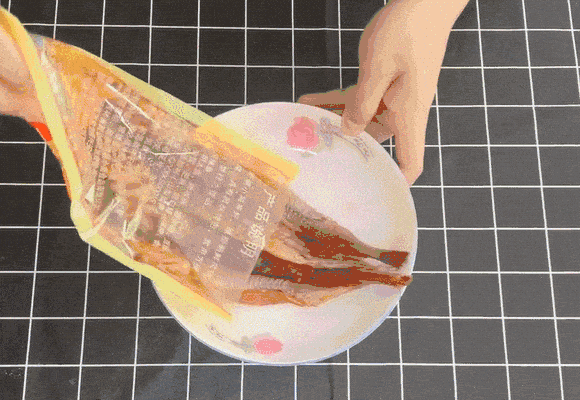
一口明太辣鱼,一口啤酒,是每个东北大地火车上的“寒冬夜行人”,打发漫漫长夜的最惬意的方式了。整张明太辣鱼硬如木板,需要用手撕成一条条的。饱浸辣油的明太鱼肉条在火车昏黄的车灯下,宛若寿山石般莹润。可是放到嘴里,却十分耐嚼,尤其是鱼刺部分,最考验牙齿。
明太辣鱼的小刺不多,而脊骨大刺部分,经过朝鲜族阿妈妮的捶打、塞北凛风的阴干,已经变得柔软可咽,甚至比韧性十足的鱼肉还有嚼头。
能够赋予明太鱼特殊口感的辣椒,也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辣椒。
朝鲜族腌明太鱼的辣椒,属于长角椒的一种,有形正、色红、皮厚的特点;鹰嘴型,口味辛辣、营养丰富。而且椒红色素及辣椒素含量也高。在地的辣椒、在地的鱼、在地的风土,才酝酿出得天独厚、只此一份的明太辣鱼。
朝鲜族吃辣,不同于四川的麻辣、湖南的香辣、贵州的酸辣、云南的糊辣、陕西的咸辣、江西的鲜辣,自成一套味觉体系,迷人而又具有豪爽气息。
谁是东北人餐桌上的“倔强”,让才女和大帅破防?
“买不起豆腐的人对那卖豆腐的,就非常地羡慕,一听了那从街口越招呼越近的声音就特别地感到诱惑,假若能吃一块豆腐可不错,切上一点青辣椒,拌上一点小葱子。
但是天天这样想,天天就没有买成,卖豆腐的一来,就把这等人白白地引诱一场。于是那被诱惑的人,仍然逗不起决心,就多吃几口辣椒,辣得满头是汗。”
这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东北籍女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对青椒拌菜和生吃青椒的描写。
青椒的身型不同于小巧玲珑的子弹头泡椒、纤细苗条的杭椒、肥壮敦实的番茄菜椒,却有自己的修长与宽厚的体格,如同娇憨“大只”的东北姑娘。
如果把子弹头、杭椒、菜椒按辣度从高到低拉成一条线,东北青椒恰恰就在那个“黄金分割点”上,处于人的口腔生吃可接受的范围内。一根大青椒,撅一口酱,“喀哧”一咬,是东北人餐桌上的“倔强”。
若说有一种拌菜能代表东北的话,那么青椒C位的“老虎菜”必定榜上有名。据说这道菜的来历,还和北洋时期的东北“大帅”张作霖有关呢。
张作霖对老虎情有独钟,绰号“东北虎”,就连接待客人的大厅也叫“老虎厅”,缘于里面摆放了两只真老虎标本!美国记者鲍威尔在晚年写回忆录还心有余悸:采访老张的时候,椅背后的虎须直撩他的后脑勺儿!
就是在这座令人胆战心惊的“老虎厅”里,有一次,张作霖与客人发生了不愉快,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家厨两股战战,冥思苦想为大帅“研发”开胃小菜。试验了无数种搭配组合,最后发现,“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把青椒切条,大葱切丝,再撒上一把香菜,佐以酱油、醋盐(有时再来点香油),三样食材简单一拌,竟激发出了不一样的口感。大帅尝后“虎颜”舒展开来,家厨心头悬着的刀终于落了地,从此,这道菜便得名“老虎菜”。
酱焖一切的东北人,也少不了对青椒“下手”。如果说炸鸡蛋酱、酱焖小河鱼、酱茄子,是东北酱焖“三剑客”,那酱焖大青椒便是“达达尼昂”。里面妥妥的C位。
青椒经过酱焖以后,脆爽蜕变成软糯,整个青椒的肚子里,也被辣酱填满,辣椒籽儿与东北大酱中的豆碎颗粒完美融合,辣度也被植物蛋白所稀释,椒的清香与酱的豆香相得益彰。一整条塞进嘴里,可以干一碗饭!
青椒与大酱的缠绵,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如胶似漆;
红椒与腌菜的交织,是萦绕在东北孩子童年记忆里,《道拉吉》(朝鲜族民歌,意为桔梗)的婉转旋律。

从长白山麓到松嫩平原,从图们江畔到延边口岸,连片的东北辣椒产区,像黑土母亲长长的脐带,羁绊着每一位大地上的异乡者,对故园火辣辣的热恋。
涉过漫长的凛冬,那些挂在故乡墙面上、屋檐下的辣椒串儿,是自带大地温度的天然风铃,永远驻望着游子归家的方向,这么近,又辣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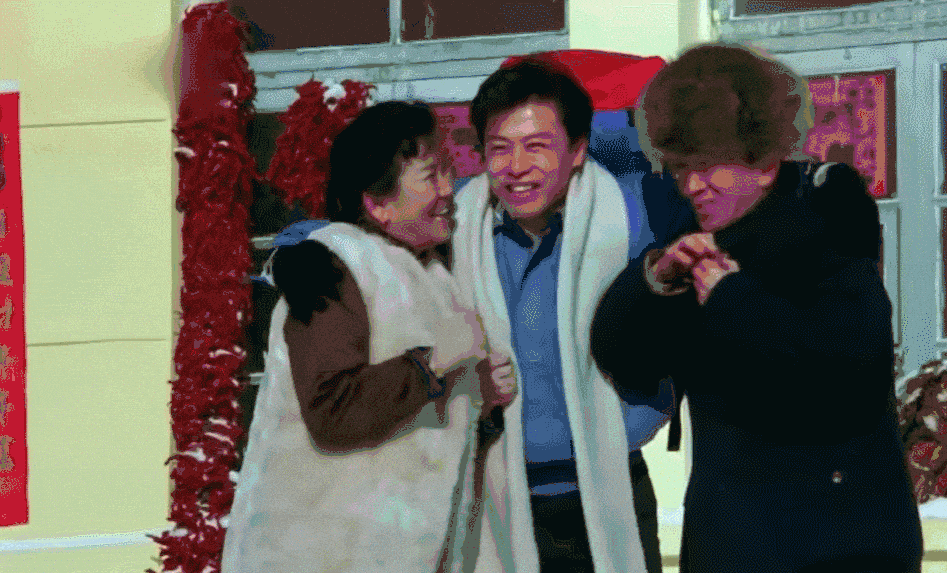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道风物 (ID:didaofengwu),作者:鹿鸣谷,图片编辑:何鹏飞,制图:鱼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