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4期,作者:杨吟竹(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在读),专栏主理机构:神经现实,原文标题:《自由意志、测谎仪与“读心术”#“神经漫谈”专栏10》,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们的颅骨包裹着的果冻状物体,重约1400克,湿润黏稠,脆弱易毁,却隐藏着不可穿透的无限宇宙。人们向来着迷于触碰这片不可触及的宇宙:在科幻作品《X战警》中,拥有读心能力的X教授是最强大的变种人之一;在《三体》中,拥有碾压性科技的外星智慧生命“三体人”唯独不能看穿人类的思想,由此诞生的“面壁计划”[1]让个体的大脑成为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今,读心术已不再是独属于至高者的领域。随着当代神经科学,尤其是脑电图(EEG)、脑磁图(MEG)以及神经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读心术似乎已在地平线上显现,易朽的凡人也能触手可及。
人类的每个心理状态都对应着特定的大脑活动模式,通过EEG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手段测量大脑活动,随后用计算机进行模式识别,就能“解码”出与这一特定大脑活动模式相关联的心理状态,并有可能从大脑活动中直接读取人们的想法——这也就是“读脑术”(brain-reading)或“解码心理状态”(decoding of mental states)。如今,借助相关技术我们已能解码出非常具体的视觉图像、记忆内容,乃至决策与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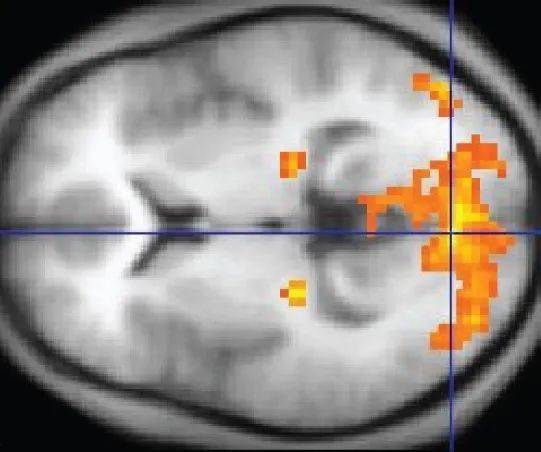
不过,在伦理层面,人们对读心术有着数不清的担忧。譬如在《少数派报告》与《心理测量者》描绘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基于解码大脑活动而设计出的先知系统能够提前侦测有犯罪意图的潜在犯,并在其尚未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进行逮捕乃至处决,但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读心术不仅有可能侵犯人们的隐私与自由,甚至有可能带来一个恐怖的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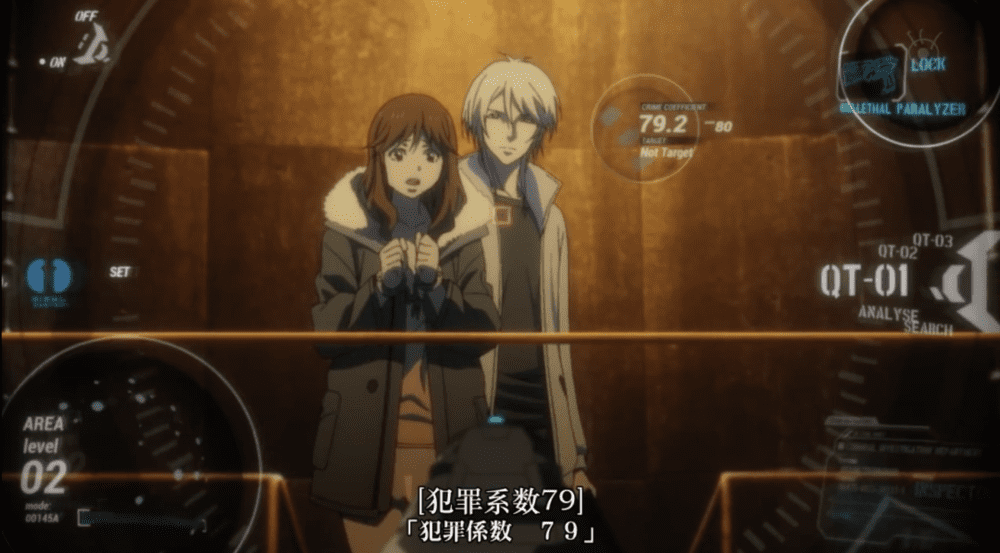
读心术蕴含的力量使人心驰神往,也令人心生畏惧。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前所未见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神经伦理学应运而生。一方面,神经科学领域的进展给传统的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饱受争论却停滞不前的问题也被革新。
比如,在人类是否拥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以往的哲学家只能纸上谈兵,但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却通过实验(Libet's Experiment)发现,能够根据人们做出行动的几秒之前的大脑活动预测出未来的行为,这代表着人们或许并无自由意志。[2]随着更多神经科学实验的开展,这柄利剑能否劈开缠绕已久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另一方面,神经科学这一学科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经技术又派生出崭新的伦理学问题,一些隐蔽却持存的问题也被淬亮。比如,以读脑术为基础的谎言检测若被证实有效,这项技术是否应被大规模使用?在下文中,我们将以解读意图(intention)的读脑术为例,分别对以上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古至今,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一信念也构成了法律与伦理体系的基石。在罗马法中,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包括犯罪行为(actus reus)与犯罪意图(mens rea),后者指的是必须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因此,一个人不用为那些并非自己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且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就意味着此人在当下可以有别的选择,而不是只能做出某一行为。
然而,当代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对上述图景构成了冲击——行为由大脑的生理学过程产生,大脑则依据自然律运作,这些自然律都能被还原为最基础的物理定律。如果行为像被预设的程序一样,不过是一系列被预先决定的因果律过程,那么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力做出规定程序之外的选择,因而我们并不拥有自由。
里贝特实验就是这种常识图景与科学图景撕裂时最戏剧化的体现之一。实验结果表明,在你有意识地决定要移动手指之前,从EEG记录的大脑活动的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中,就已经能够看出你即将移动手指——无意识的大脑信号先于有意识的决定。该实验结果一发表就引发了轩然大波与强烈质疑,尽管如此,它还是经受住了一代又一代可重复性实验的考验,一些继承其精神的改进实验也不断涌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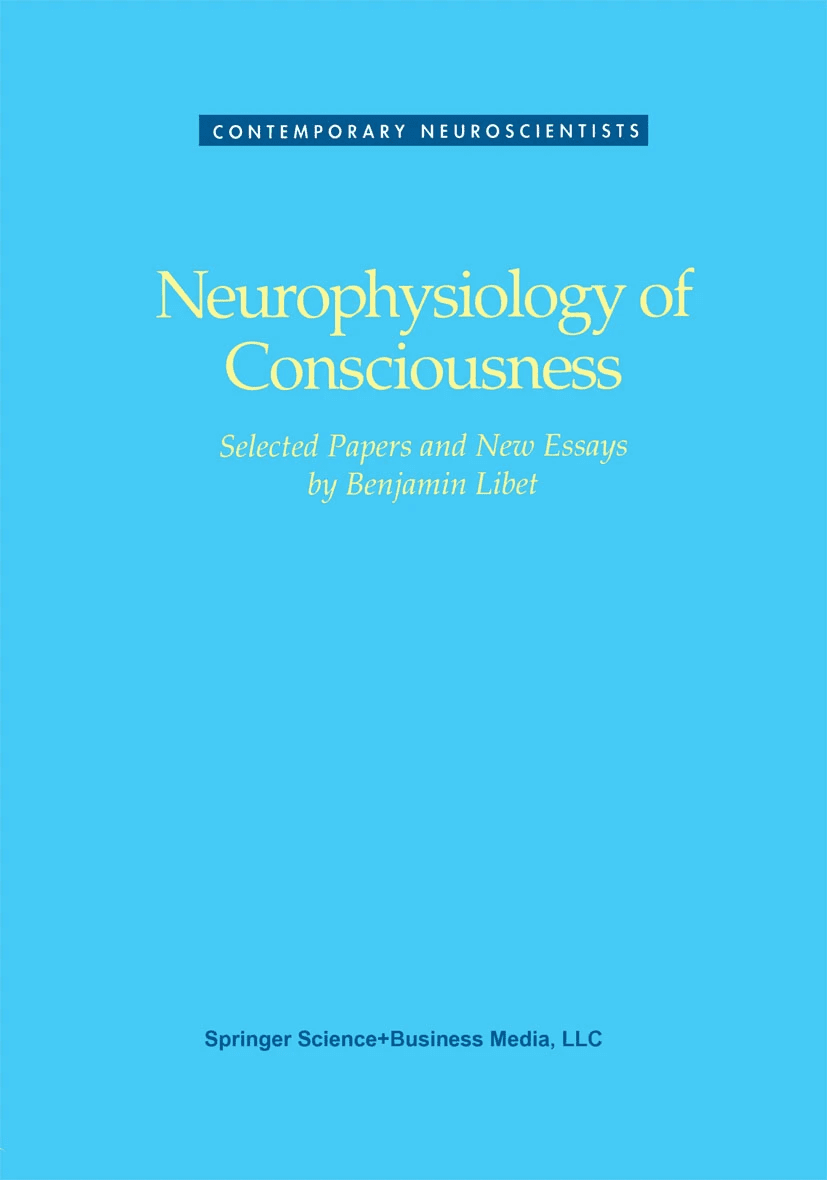
在追随里贝特脚步的当代实验中,存在一个不再仅限于简单的“移动手指”意图,而是涉及更为复杂的高阶抽象意图的研究,[3]这避免了对原实验中运动决策本就只需较低程度意识水平的批评。
在这项新实验中,被试需要就给出的运算数字自行选择“相加”或“相减”,研究者并不能提前知道其选择是什么,但是通过分析fMRI测量的大脑活动模式,研究者能够以约60%的正确率“读”出被试选择的运算方式,也能解码出那些可预测被试运算行为的大脑活动模式在何时出现。[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意识的决策出现的时间要比被试报告的有意识决策早好几秒。
这样的实验结果是否颠覆了我们对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的直觉,也撼动了我们对道德责任的信念呢?这不只是哲学家关心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将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但举起反对旗帜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比如,一些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支持者会认为,量子力学挑战了物理世界的确定性,因此那种完全被因果决定的世界观本来就是错误的。相容论者(compatibilists)则会认为,一个被因果决定的世界与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不矛盾,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对“何为自由”的定义。更有甚者认为,从自由意志到道德责任的理论跳跃是不合理的,无论人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都不能对道德责任构成挑战。本文将暂时搁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把目光聚焦在与读心术相关的质疑上。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可以有意识地“撤回”(veto)箭在弦上的行动,那么这是否保住了一种反向的自由意志(free won't)?里贝特本人就支持这条思路。他认为,行动前无意识的大脑活动的启动掩盖了一种内隐的自由选择,即到底是在启动之后继续行动,还是取消行动。在有意识的行动意图与无意识的大脑活动之间的几秒时间,足以给一次可能的“撤回”留下余地。
在一些实验[5]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看见绿灯后自由地决定何时按键,但如果绿灯转为红灯,则必须停止一切行动。结果显示,在无意识决定后较早期的时段内(行动前数秒),如果红灯出现,被试完全可以做到停止行动。但如果红灯出现在行动前200毫秒以内,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在一系列神经电位和肌电反应之后,被试仍有可能撤销自己的按键行动(BP)。图源:SCHULTZE-KRAFT M, BIRMAN D, RUSCONI M, et al.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Vetoing Self-Initiated Movemen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2016, 113(4): 1080-1085.](https://i.aiapi.me/h/2022/11/09/Nov_09_2022_20_54_34_7785938770233022.jpeg)
存在“撤回”已经启动的运动的可能,似乎说明了准备电位确实能预测后续行动,但未必能决定后续行动。或许我们可以后退一步,将解读从决定论式转向概率论式。根据后者,人们的决策与行动并不会被那些先于行动的无意识脑信号决定,但会受其影响。这些无意识脑信号更像是一种推力、一种能对后续行动进行某种限制的倾向,它们能改变行动的概率,但不能因果地决定行动的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里贝特类型的实验在设计与技术上是否真正反映了我们关心的问题?尽管涉及加减法的实验相较于仅涉及手指运动的实验已经“高阶”了许多,但相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复杂决策,它依旧非常简单。自由意志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超于此。
正如前文所述,简单粗暴的模式识别是目前破解大脑密码的主要技术手段。为了将大脑活动模式翻译为相应的想法,它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结,而此种联结需要测量被试不断思考某一想法时的大脑活动。但在现实情况下,某一想法与其心理状态的映射关系可能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任意的、无限多的,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前文实验中读心术不尽如人意的正确率。目前的读心术只适用于一些极为有限的心理状态,而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模糊多变、即兴随意的想法时仍然捉襟见肘。
与之相关的是,目前的技术也难以应对极大的个体差异。人们的想法通常由过往的经验塑造,而不同的个体经验所产生的与同一概念相关的联想和引申则天差地别。或许正因如此,不同大脑之间解码心理状态的细节完全不同,不具有跨个体的可迁移性。
此外,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个体,读心术也不具备跨时间的可迁移性。目前的解码过程预设了心理活动与大脑活动模式之间的静态联系。然而,在较大时间跨度与持续学习的塑造下,同一个体对某一想法的相关联想也会发生改变:在谈及“理想”这一抽象概念时,曾经的你与现在的你所注视的还是同一片景象吗?
如此看来,我们或许没必要大惊小怪。强大的通用读心机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人类的自由意志也没那么容易被推下神坛。西比拉系统距离孵化产生还差10086个槙岛圣护,而在三体人入侵地球之时,我们多少还是可以指望一下“面壁计划”。

但且慢,即使我们尚未拥有能够实时、高精度、适用于不同个体且无需长期校准的读心机,前文提到的技术与实验依旧指向了一些需要引起关注的神经伦理学问题。比如,读心机可以被当成测谎仪使用,它无需解码出受测者脑中的所有想法,而只需读取一个意图:说谎了/没说谎。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决策。所以,即使通用读心机无法得知受测者为何说谎、其脑中的小剧场编排了什么剧情,能得出是否说谎的结论也颇为有用。
传统的测谎仪器度量的是一些身体指标,如皮肤电导、心率和呼吸频率。这些指标有效的前提是受测者在说谎时会有较高的唤起(arousal)水平。不过,唤起水平会受到许多其他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过分的紧张会导致误报,而老练的受测者能通过控制自己的唤起水平操纵检测结果。
相比这种间接的度量方式,基于读心机的测谎仪可以克服上述困难。目前大多数用以测谎的读心机都会使用fMRI,也有一些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在实验中,研究者会要求被试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说真话或是说谎,并通过对比两种情况下的神经影像来确定与欺骗相关的脑区。[6]
进一步地,可以在目标脑区使用逻辑回归或一些非线性的机器学习算法,来区分受测者哪次说的是真话,哪次说的是谎言。自2006年起,已经有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将基于fMRI的测谎技术用于法律、商业和家庭生活中。
但是,在我们为技术的进步欢欣鼓舞之前,有必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些更为初步的问题:测谎技术能否从实验室直接跨越到现实生活?首先要考虑的是技术的准确性问题。
在实验室环境下,被试说谎是因为实验者要求其这样做,现实生活中人们说谎则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往往掺杂了复杂的情感因素。很多时候,说谎者的大脑会探测到更高程度的情感波动,而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出来的测谎算法很有可能只能区分出受测者哪次受情绪影响更大。这样一来,在测谎算法应用到新的受测者身上时,人们在想到引发高度心情起伏的事情时说出的真话会被分类为“假”,而更擅长情绪控制的人说出的假话也会被分类为“真”。
与之相关的是基础概率(base rate)带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要区分算法的敏感性(sensitivity)和针对性(specificity)。前者指的是能在受测者确实说谎的情况下正确地识别出说谎情况的概率,后者指的是能在受测者并没有说谎的情况下不发生误报的概率。在一些研究[7]中,敏感性高达百分百的算法却只有较低的针对性,这会导致在并没有人说谎的情况下错怪了很多老实人。我们可以假设人群中存在说谎者的基础概率本来就很低,但即便如此,也很容易发生大批冤假错案。
那么,要达到多高的准确性,测谎技术才能投入使用?如果这一技术被大规模使用,较高的假阳性(false positive)率可能会使受冤枉的人被污名化,在寻找工作时遭遇歧视;而如果为了降低假阳性率选择降低敏感性,也可能要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美国中情局特工巴拉维(Humam Khalil Abu-Mulal al-Balawi)在顺利通过测谎仪测试的情况下,作为双面间谍杀死了七名中情局特工。
这固然是传统测谎仪的疏漏,但这样的问题在神经读心术的技术手段下也难以避免。在敏感性与针对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偏向哪边?这都是神经伦理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论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读心术都已经降临。目前看来,它既不是阿拉丁的神灯,也不至于成为潘多拉的魔盒。神经伦理学能帮我们澄清一些令人忧心的问题,也能帮我们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它教我们在何时保持警惕,在何时无需恐慌,又在何时应当将注意力从令人目眩神迷却只是虚晃一枪的问题上移开,放在那些当下更需要被关注的问题上。
注释
[1] 部分人类个体(“面壁者”)仅在自己的大脑中完成战略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不以任何形式与外界交流, 通过将行为与思想分离, 使敌人无法判断其真实意图。
[2] LIBET B, GLEASON C A, WRIGHT E W, et al.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 (Readiness-Potential)[M]//Neurophysiology of Consciousness. Boston, MA: Birkhäuser, 1993: 249-268.
[3] SOON C S, HE A H, BODE S, et al. Predicting Free Choices for AbstractInten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15):6217-6222.[4] 有趣的是, 在这里能解码出内容的脑区和能解码出时间的脑区是分离的。前额极区与后扣带回(Frontopola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能预测被试究竟想做加法还是减法, 但不能预测决策的时间;前运动辅助区(Pre-SMA)能预测被试做出决定的时间, 但不能预测决定的内容。
[5] SCHULTZE-KRAFT M, BIRMAN D, RUSCONI M, et al.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Vetoing Self-Initiated Movemen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2016, 113(4): 1080-1085.
[6] FARAH M J, HUTCHINSON J B, PHELPS E A, et al. Functional MRI-Based LieDetection: Scientific and Societal Challenges[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2014, 15(2): 123-131.
[7] ANDREW KOZEL F, JOHNSON K A, GRENESKO E L, et al. Functional MRIDetection of Deception after Committing a Mock Sabotage Crime[J]. Journalof Forensic Sciences, 2009, 54(1): 220-23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4期,作者:杨吟竹(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在读),专栏主理机构:神经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