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罗克兰大妹妹,编辑:Rachel、madi,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搞笑,班主任嘴里的不靠谱不正经,相亲对象眼中的有趣灵魂;给观看者播撒乐子,把从业者摁进痛苦;年初一电影院的宠儿,奥斯维辛之后的禁忌。
在喜剧内容制霸本季度的大屏小屏之际,我们想要一起聊聊“你在笑啥”。包含但不限于:一些德艺双馨的老笑料,一些冉冉升起的新笑点,把搞笑作为职业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喜剧创作者一定有趣吗?我们如何一步步为梗正名?这是一篇关于“脱口秀弄潮儿”小水的故事,小水是个化名。说不准,小水就是你我。
尽管小水(化名)的经纪人多番阻挠,我终于在一次单口演出结束后,直接去后台“抓人成功”。小水知道有个烦人的无证“记者”要采访他,看我锲而不舍,也就同意坐下来聊聊。我朴实无华地阐述了对他的兴趣 —— 在非常沮丧的时候靠刷他的视频度过;他年少成名,是行业里最先“红”起来的一批人。我好奇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以及,喜剧本身。
即使刚高强度表演完,小水还是话不落地,虽然姿态非常放松,但实际上像一个素质超高的 MC 在掌控着对话,正如我在所有他的视频里看到的那样。直到后来再去 shadow 他的时候,才发现生活中他其实不是个话多的人,沉默而且冷脸。不过他告诉我,最最开始并非如此。
在他以及其他一些喜剧人身上,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混乱中自洽。这种矛盾有具象的,比如不想念的广告词和想挣的钱之间;也有非常抽象的,比如形而下的语言和形而上的快乐之间。
好了,下面是小水的故事,挺励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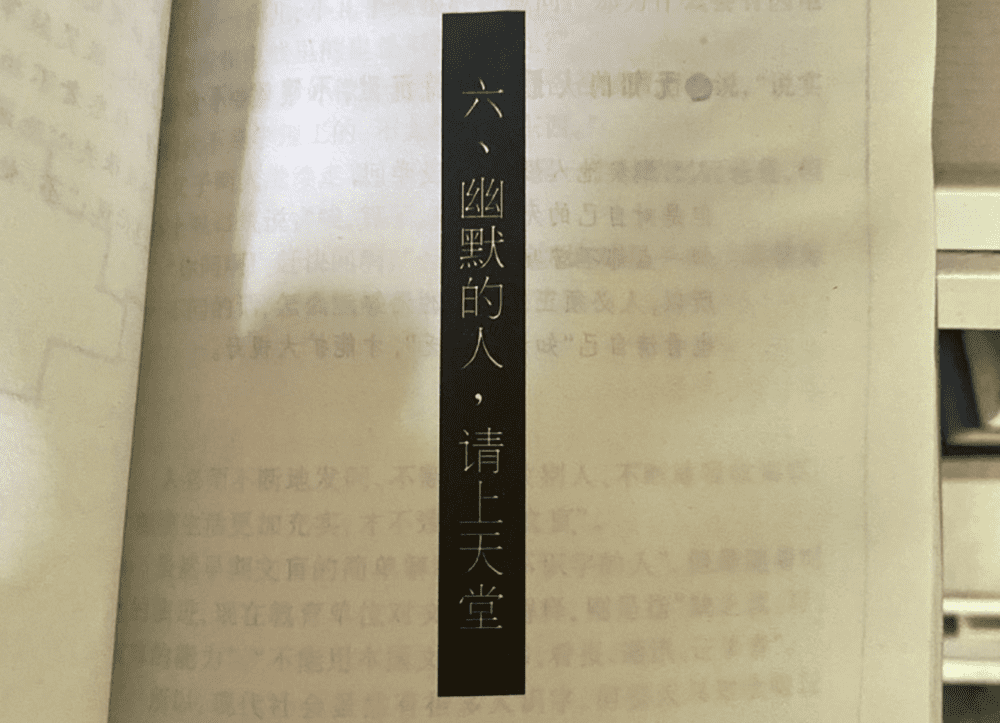
1
人之所以是唯一会笑的动物,就因为他遭到骇人的折磨,迫切需要发明此等安慰剂,以应对痛楚和煎熬。
这话好像是尼采说的,小水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但深以为然。而且他不仅要自己开心,也想逗别人笑。
这也是为什么他周末大清早(快10点)坐到了一个教室里,昨晚的酒精和刚吞咽下肚的包子好像在胃里打架,他还没缓过神来,不得不用手支着脑袋。
是堂单口喜剧课。
其实研究幽默可能是最不幽默的事儿了,所有人都想浑然天成。
但是动了要上台讲单口的念头之后,小水意识到,这是门技术活儿。
问了报名开放麦的事儿,一个酒吧主理人说,门槛不高,提供一段表演视频或是一篇完整的能说 5-8 分钟的稿子就能报名。他私以为是个搞笑的人,但是当坐下来琢磨写点什么的时候,只听见脑子里晃晃荡荡,全是水。“既要冒犯又要好笑,既要表达又要好笑,既要真诚又要好笑”,小水默念着大师们的喜剧信条,一个字都憋不出来。
于是他报名了一俱乐部的培训,免费的,交几百块定金,上完课之后去讲开放麦才能被退,多聪明的机制。二三十个人的座位陆续被占满,还有几个人装模作样地掏出了笔记本。
老师叫蛋钢,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单口喜剧演员,小水在线下看过他的演出,当时在场的观众数量,一双手差不多就能数完。一个关于打工却被老板骗钱的笑话落地,只有两个人笑了,不包括小水。蛋钢在痴迷老美脱口秀节目后入行,说了两三年单口,在酒吧以及各种小场地转悠,偶有商演,生活来源主要是收租,却自诩饥饿艺术家,总把自己带入《路易不容易》的男主角。现在蛋钢走上台,分明还带着睡意,开始放幻灯片,第一张——“单口喜剧是什么?”
怎么又是这样的陈词滥调。别科普了。此时此刻,坐他左边的同学已经准备举手抢答。
小水想起来小时候的课堂,他话多还喜欢跟老师顶嘴,当俏皮话引起一阵“小暴乱”, 他能同时获得一种造反的快感和被瞩目的虚荣。作为一个体格瘦小,成绩也不怎么样的小男生,他只能靠一张嘴,拉帮结派,呼朋唤友。
他是个聪明小孩无疑,但也肯定不是个考试天才。青春期的时候,小水没觉得这是什么大难临头,试卷不断重复,不会做的题不断翻新,但这跟他的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自习时候偷偷看了一堆科幻小说(aka 宇宙修真),《基地》、《三体》、《群星,我的归宿》……宇宙那么大,亿万光年之外还有亿万光年,至于考试?不重要。
他习惯用过于宏大的世界观和搞笑去消解眼下真实的问题,以及它们有可能包涵的严肃意义。理性和规律的构建太大费周章,只有笑话能突破防线,进入一个冒犯和反崇高的安全地带。笑话给他渺小的生存带来安全感,不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说笑话可以是个谋生的手段。
幻灯片变了 —— “段子的类型”。OK,原来段子还有分类,观察式、观点式、故事型、one-liner……小水努力拉回一点儿思绪,听蛋钢一本正经地扯。
界限又是另一个问题。小水不喜欢泾渭分明,模糊地带是他的最爱。定义、分类、条款、纪念日、国界线、逾期账单、正确答案,类似这样的东西,总是让他烦躁,人都没弄清楚上帝掷不掷骰子,就要扼杀随机性。但是当他要表达的时候,“模糊”是个太明显的退缩姿态,不清晰就是空洞。自己都没想明白,凭什么让别人竖着耳朵听?
所以有时候,他又想,单口喜剧演员真是一个又自卑又自负的角色。既要“扮演”生活中的 underdog,又要在台上想得到所有人的关注。
蛋钢结束了“教学” ,开始放视频素材充时间,Lenny Bruce、George Carlin、Dave Chappelle, 经典的段子小水不是没有看过,但是他学不来。回家地铁上,一个小时,小水拿起笔记本,脑子里想着刚才蛋钢说的“技法”、“人设”、“Punchline”… … 还是犹豫着下不了笔。
可能理论和实践就是各自为政吧。先上台好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在地铁有点困,柳暗花明又一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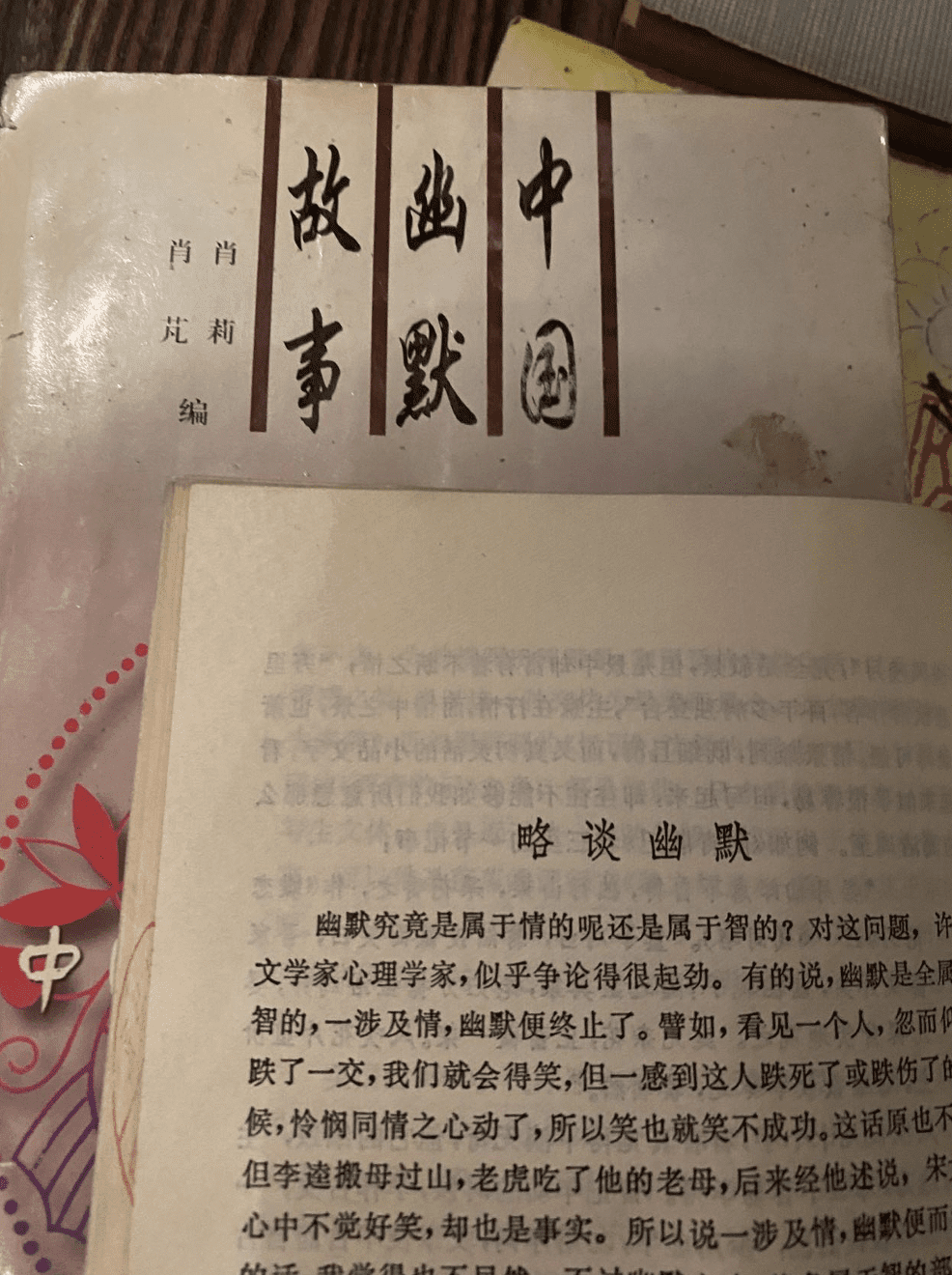
2
“朋友,听说你被打了”微信群里已经有人开始幸灾乐祸。
“牛逼啊,兄弟”—— 这是表扬。
小水刚下台,还沉浸在刚刚的舞台风波里,说实话心里还有点洋洋得意。刚才的演出(商演!100 块一场!),他插了个河南人的段子—— 200 个井盖被一夜失窃,政府号召归还,小偷良心发现,掏出库存,结果还回来 400 个。包袱还没落地呢,第二排一大哥被点着了,蹭的一下站起来,涨红了脸抄着椅子就要往台上冲。大哥被边上两个眼疾手快的热心市民拉住, 嘴里不停嘟囔着,“河南人怎么你了,河南人怎么你了。”
小水这一下也懵了,他就一喜剧新兵涉世未深的,哪儿见过这个阵仗。跟小时候一样,小水只能靠张嘴。“河南人怎么我了?河南人生了我。” 诶唷,一句现挂 punchline,一场由跳脚观众参与的单口。这下,笑声和掌声一块儿来了。
要说圈子也是真的小,这一传十,十传百(其实估计全勤也没一百个),就在当晚,全北京的单口圈都知道了小水演出差点被人打了的事儿,广东和上海的消息灵通人士也发来贺电。他这虚荣心一下膨胀了,将此当成军功章。很多年之后,当他得知偶像 Dave Chappelle 在演出时被人打,还窃喜,他走在了时代前沿,实打实的喜剧弄潮儿。
来简单回顾下,参加完半吊子培训的一周后,小水终于鼓起勇气上了次台,不知道是当晚卖给观众朋友们假酒生效了,还是他实在天赋异禀,用别人的描述就是,“炸了”。虽然当时他还在极度紧张中晕晕乎乎的,手心直冒冷汗,但也深受鼓舞,自此开启了快乐穷鬼的开放麦生涯。
他住五环外,每天在上班族回家的晚高峰时才上地铁,往城市正中心去,越往前坐车厢越挤,他就是那个最美逆行者,要奔赴夜晚取悦那些滞留在鼓楼和三里屯附近的人们。大大小小开单口喜剧开放麦和演出的场子都在那边,喝了两杯的观众朋友们情绪被放大,要不就是听到啥都笑,要不就是听到顶级笑话也默默流泪。他在聚光灯下,越来越收放自如,甚至能一心两用,一边说着临上台前还在琢磨的稿,一边观察着大家的即时反应,下台了好继续琢磨。
小水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无偿酒托,做着助兴表演。说着说着,脑海里就浮现出婚礼司仪和二人转吹瓶表演的画面。但是他高兴,观众卸下防备毫无顾忌地大笑的时候,在当下全盘接受了他的表达。
他骂那个待他很薄的应试教育,他骂官僚主义盛行的大学社团,他骂神神叨叨的概念艺术家,他骂那些觉得出门不占便宜就是吃亏的小市民,他骂热衷于赚快钱却口口声声“长期主义”的资本家,他骂庸人自扰的中产,发起狠来,无产阶级同胞也骂。
他也赞美,不过很少。他赞美一些现实中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纯洁无瑕的爱情。
小水进入了一段与单口喜剧的蜜月期。根本没什么“行业”的概念,这个舶来品,生长在零零散散的酒吧里,这群同行说实话也就是群背景各异的爱好者。很小的圈子,很苦的日子。他们在胡同和脏街占地为王,总是因为扰民和粗俗言论举报被迫“流窜式”表演,接着玩语言的游戏。
有一次小水白天阴差阳错来到了金融街,看着高楼大厦、西装男和女白领,他浑身难受,好像起了红疹。那时候还没有“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的概念,他就是觉得,有些人就是说不了脱口秀的。当一些人的逻辑就是靠数字搭建起来的时候,唯一让他们快乐的就是银行卡入账。被任何体系驯服,都是背叛忤逆单口喜剧的精神。
听起来很傻吧,原谅小水,他那时候只有 23 岁,没有 quarterlife crisis,天天自作聪明不可一世,还在对失败免疫(不用打加强针的那种)。
转变很快就会来的。
3
来的不是失败,是迅速的成功,谁能想到。
行业起飞了。从线下到线上,从地铁到工作室,从酒吧到电视台,从一场一百的商演到一句十万的商务,冲击来得势如破竹。第一次有专业化妆师给他涂粉底画眉毛的时候,小水看着眼睛里环形灯的白影,觉得自己不会是个外星人吧!第一次有公司请小水进行跨省商务会谈包机酒的时候,他以为对方是骗子,痛骂人一顿,最后还苦口婆心劝别人从缅北回家。第一次在某社交平台粉丝数破百万的时候,他开始自我审查,害羞地删除了三年前的一张腹肌自拍。
现在,小水躺在五星级酒店两米的大床上,心中苦不堪言。床太软,腰疼;网太慢,掉线;空气太香,鼻炎。“山猪吃不了细糠”,他觉得由俭入奢好像也没那么简单。
他这是来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录制,节目组别出心裁地把他们一群人拉到海口边上的一个县。一个拔地而起的摄影棚和一个五星级度假酒店和周围景观显然格格不入,凭空来了一点厚腺带的意味。录制明天才开始,他准备去周围转转。
不得不说,小水还挺喜欢这个地方。潮湿的空气咸咸的,但又不像个与世隔绝的海岛或是度假胜地,反而市井气很重。他转个弯就走到了夜市,到处是海鲜烧烤和水果冰沙摊,手上捧着一个椰子,他莫名其妙走进一间网吧。这熟悉的味道让他心驰神往,梦回少年时代,YY 语音聊天室充满队友们的欢声笑语。
走回酒店的时候都快 12 点了。不对,怎么门口全是人?他正想过去凑热闹,就有尖叫声传来,“哥哥!哥哥!!”,然后是一阵长枪短炮闪光灯,原来敌军是站姐们。
刚平静下来,他就听到旁边有人窃窃私语。
“不对,认错人了,这是另一个明星。”嘿,原来等的不是他。
“谁啊这是?看着眼熟,没认出来。”嘿,原来根本不认得。
“哎呀,先拍了再回去查。”然后又是一阵快门声。
一个大胆的女孩凑上来说话,“哥哥你刚走路回来呀,刚录制结束辛苦了。”
小水愣了一下,然后摆出亲切的笑容,确实,他刚才上山入海搞枪击抢装备是挺辛苦的,粉丝们真的太贴心。这更厚腺带了。
回到房里他还在消化,想着想着就乐了。
自从半只脚踏入演艺圈之后,他觉得不可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喜剧和喜剧行业分明就是两回事儿。签了的公司从松散的组织变成了国企,做点什么都得走流程,不仅节目在线上,审批也得在线上。想说的话挺多,能说的话却很少,稍有不慎就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最怕的之一就是完整的表演被剪得支离破碎。
最怕的之二的是性别议题,身为男性就是原罪,支持女性权益也会被贴上“吃红利的女权男”标签人人喊打(这里是在讽刺 cancel culture,无意冒犯)。同行们现在还有贫富差距了,长得不错的阳光男孩竟然有奢侈品代言找上门来。而小水说着酱油广告,也自得其乐。
为了赶上节目排期,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密集熬夜,写稿子、过审、彩排、表演。大晚上的,他盯着电脑屏幕,文档里的光标有规律地跳动,他什么都想不出来。撒把米在键盘上,鸡都比他会写。也有写的快的时候,交差就像做完形填空,模板就在那儿,他知道观众会为什么笑,就往里加料。睡不着的时候就刷短视频和梗图,觉得好好笑啊,甚至自愧不如,一专业搞喜剧的,不如人在广场斗舞的。 多狂野、多有生命力!
摄影棚的光总是很足,灯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小水突然觉得观众面目可憎,他们在安全的滑稽戏中理智地笑,却无法参与到他失谐的狂欢里。他甚至开始思念那些个在他努力逗乐时哭泣的观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那一刻达到了同频。
骂观众,只是最懒惰的办法,所以他也骂自己。当他成为了那个拥有流量和粉丝的建构者,身上被赋予各种意义,却不太敢解构自己(这都什么跟什么,好像没必要)。还能骂什么?那可不敢瞎说。地大物博的,啥的土壤没有。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是幸运的,天赋和机遇都砸来了,摆出抱怨的姿态更像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到底什么堵住了?小水逐渐变得安静了。因为他一贯赖以生存的安全体系正在瓦解,从前因为身上这点幽默得到了朋友和自信,还靠着说话混了口饭吃,但是现在张嘴却如履薄冰。
在生活中,小水他笑的也越来越少很少。上一次爆笑是他小水跟风去参加一个冥想课程,studio 主理人曾是省理科状元、史丹福高材生,鼓励人们抛却烦恼向内探索,寻找 spiritual 的力量,预约席位有限,收费不菲,小水捡漏了免费体验。坐在美丽宁静的课堂,精油的味道充斥鼻腔,状元突然开始抑扬顿挫地吟唱。就一瞬间,小水抑制不住大笑出来,直接被请出了教室也停不下来,灵力世界被一扇门隔在对面。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骂过的一切。
正如某位伟人所说,人生就是要给你两斤(可能是两公斤)大粪,有些人大口大口吃,有些人小口小口吃,但反正你得吃。也如一句俗语所说,人生就是一口蜜糖一口屎。总而言之,他现在可能即将得开始是吃屎了。
这未必是件坏事儿。毕竟,那天真的到来之后,笑将必然成为必需品。找魔鬼诉苦也能得到嘲弄的笑。祝福幽默的人,会上天堂,或腆着老脸上,或青春正茂上。
(以上内容纯属意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罗克兰大妹妹,编辑:Rachel、ma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