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是田埂上的诗人,是现代李清照,是余秀华第二。
她说,我只是个农民,满身黄土,两爪子泥:韩仕梅。


1971年,河南省淅川县,某农户。
一位农妇胎位不正,婴儿趴着出生,脊背朝天,脚朝地下。
屋内的人惊掉下巴,面面相觑:这是不祥的征兆,意味着孩子长大后不孝。
农村人深信不疑,妈妈想都没想,反手就要将她塞进尿桶溺死,反正是个女儿,不心疼。
可千钧一发之际,爸爸将她救了下来。
这便是她一生痛苦的起点。

她叫韩仕梅。
因为登记失误,身份证上的名字被潦草改成了韩花菊。
她失语的前半生,就像这个写错的名字一样,由不得自己掌控。
可她身上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常见了。
若要细数这些年的苦难,一言难罄,但拉到村上一问,个个都习以为常。
而她,也不过是最平凡的一位农妇罢了。

她从小就喜欢读书,成绩很好。
但每次交学费之际,就是她最为煎熬的时刻。
因为交不起学费的学生,都会在课堂上被点名站起来。
韩仕梅一次都没落下。
挣扎到初二下学期,实在拿不出18元的学费,最终还是被迫辍学了。

辍学后,她再也没有了学习的机会,只能在家做些针线活,下田耕地。
再不然,就是等着出嫁,讨彩礼钱补贴家里。
这是每个落后农村里女孩子的宿命。


在妈妈眼里,女儿就像猪圈里待价而沽的猪崽。
只要男方愿意出钱, 她就愿意将女儿嫁给他。
大姐以400元的彩礼嫁了出去,后来爷爷去世没钱安葬,家里又匆忙给三姐说了婆家。
19岁那一年,命运的魔爪终于落到了她的身上。

妈妈带她去镇上见了邻村一个大她六岁的男人。
那男人其貌不扬,木讷寡言,是村里公认的“糊涂蛋”。
韩仕梅爱读书写字,可那男人却只读到一二年级,大字不识,是个半文盲。
话不投机半句多。
韩仕梅不情愿,可是妈妈却扯着嗓子骂道:就你这鳖样还捣蛋呢?
这句话就像一把带着诅咒的利刃,直直捅进韩仕梅的心中,将她的灵魂撕得破碎。

她很清楚家里情况,一贫如洗,没钱盖新房,而弟弟也马上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
嫁她过去,收下彩礼,万事如意。
她想,村里的人不都这样过来吗,反正眼一睁一闭,人生这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
那就嫁吧。
用她美好的青春,去换那3000元彩礼,皆大欢喜。


出嫁当日,她哭着,爸爸也哭着,可他们都没有能力改变这局面。
很多年后回望过去,她才明白这场出嫁意味着什么。
曾自以为短短的几十年,竟这么难熬。
她在作品中写道:
金箍一戴已定型,必保西天去取经。上有公婆八十多,下有儿女要上学。怎能跳出三界外,乐得逍遥又自在。
穿上嫁衣,如同带上金箍,从此九九八十一难,再无回头路。
她没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唯有肉身硬扛,上养公婆下养儿,中间拖着不靠谱的丈夫,硬生生撑起一个家。



丈夫有多不靠谱呢?
嫁过来后她才知道,那3000元彩礼,全是外债。
彩礼一分没落到她的口袋,她却背上了4800的外债,更别提其他零零碎碎的欠款。
“娶媳妇的钱是借的,要账的人要我还,等于我自己花钱买了我自己。”

她也想过一走了之,可终究心太善良,不忍心丈夫一家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怎么办?
只能还呗。
硬着头皮去还。

丈夫游手好闲,不是去理发店消遣,就是去茶馆赌博。
赌输了钱还得靠老婆还债。
所有养家压力都压在韩仕梅的身上:
农忙时要下地,农闲时要打工,一年到头没个清静日子。

那时候她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一直干到晚上9点多。
一天下来浑身都累垮了,腿脚发肿,胳膊酸痛。
可回到家却连句暖心的安慰话都得不到。

丈夫从来不懂得心疼人,还好吃懒做,连晚饭都要等韩仕梅下班回来做。
有一次,韩仕梅去走亲戚,出发前在家轧好了面条。
丈夫却懒得连灶头都不肯去,宁愿饿着等韩仕梅回来伺候他。

干农活时,韩仕梅默默憧憬着:要是丈夫多锄一下,她就能少锄一下。
她是女人,她渴望爱,渴望依靠,渴望被保护。
可现实却是,丈夫一天到晚不着家,只有她孤零零下地干活。
为了挣钱还债,搬砖、拌水泥、抬钢筋这种粗重活,她也抢着去干。
刚嫁过来一年,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又要干活,又要挣钱,又要还债,还要上地...
后来怀着孩子,她还大着肚子去打零工,一直做到孩子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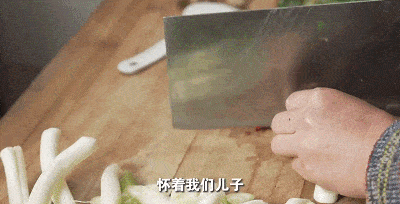
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离婚?
她说,我就像一根空心菜,受的气从这头进,那头出。如果一直在心里憋气,那我早就疯了。
她的字典里没有“反抗”两个字。
她从来不会抱怨,因为长久以来接触的环境只教会她两个字:忍耐。

她在作品《厨娘》里这样写道:
灶台前后转悠,腰酸背痛难受。菜勺碰锅响,盘子叮当歌唱。忍着忍着,又是一年到头。
万家灯火,饭菜飘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生活。
可背后是无数个像韩仕梅一样的女人,在默默付出,默默忍受。
她用自己的腰酸背痛,换来阖家团圆,欢声笑语。
她不够先锋,不懂女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她不过是万千农村妇女的缩影...


韩仕梅就这样忍啊忍,忍到孩子出生,忍到孩子上学,一直忍了十几年。
直到2007年,丈夫突然开窍了。
虽然依旧不理家事,但至少不赌博了,也愿意踏踏实实找份工作,补贴家计。
村里人都说:韩仕梅将他教得更好了。
就这样,韩仕梅撑住一头家,兢兢业业供出了2个大学生。
她也成为了村子里公认的,“3000元娶回来的能干媳妇”。


日子,似乎越过越好了。
但是,不对。
哪里不对?
说不出来。

只有韩仕梅自己知道,深夜流下的泪水有多么苦涩。
丈夫,不过虚得其名。
在她眼里,丈夫就像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她伺候他吃,伺候他喝,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样样操心。
家里盖房子,一砖一瓦,全是韩仕梅跑前跑后。
公婆生病,公公葬礼,也是韩仕梅忙前忙后。
还有儿子的婚礼,更是韩仕梅一手操办。
后来儿子婚姻失败,村里的人都对韩仕梅指指点点:他们家的事全都是她一手操办,这事不成功,那不是乱了套了。


没有人在意过韩仕梅的感受。
如果有的选,她也希望有个宽广的肩膀,希望有人替她遮风挡雨。
然而回到现实,周围都是依靠她的人,却没有她可以依靠的。
丈夫只会索取,从来不懂她的情感需求。

她写诗宣泄痛苦:
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
丈夫是树,是墙,偏偏不是一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
她的内心翻滚着汹涌澎湃的欲望。
她半辈子没走出过薛岗村,可她的脑海里却藏着山川湖泊,日月星辰,百花盛放...
而这些,丈夫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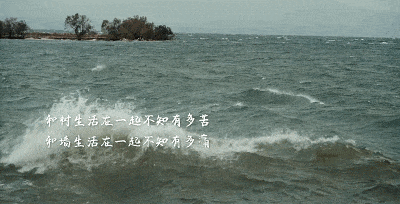
她有一颗向往美好的灵魂,可丈夫那木讷的神色向她泼了一盆冷水,浇灭了她对世界的热忱。
她就像孤独无助的聋哑人,在自己的世界拼命呐喊,呼唤,却始终得不到半点回应...



然而,互联网给了她新生。
一次偶然,她发现有人在快手上写诗,她仿佛看见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她敞开。
于是,她也摸索着用智能手机,在上面发布诗词。
生活的苦闷,婚姻的痛苦,催促着她将千万愁思揉进诗句里面,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渴望。
惊喜的是,那些诗句竟然得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的回应。
她内心里滚烫的情绪,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别人稳稳当当地接住了。

除了情感得到共鸣,她还发现她的诗词,有了医治他人的魔力。
有被父亲家暴的女孩找她倾述,有同样悲苦命运的人向她求助,还有学生跟她分享不愉快的经历...
很多人从她的诗词里,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攫取了活下去的勇气。
她意识到,尽管自己微不足道,却也能成为拯救别人的光。
这也让她找到了人生新的坐标和意义。

渐渐地,她就像上瘾一样,热衷于在网络上写诗,表达自我,跟人交流。
她说:诗歌也拯救不了什么,只不过从中找到一点自我,一点快乐,一点成就感。
这是她漫长人生中,极其微弱的一点烛光。
它点亮了她的人生,支撑着她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咬牙趟过人生的苦难...




可是,丈夫不乐意了。
工厂的人挑拨离间,说韩仕梅长成这样,还好意思发网上...
丈夫生怕韩仕梅跟人跑路,极力限制她的爱好,时刻紧盯她的一举一动。
他还时不时查看她的手机,将上面有交流的联系人删除,拉黑。
有记者去采访韩仕梅,丈夫有时会突然大发脾气,动手赶人。
韩仕梅首次学会了反抗,她说:我一生就这么一个爱好,你还给我掐了,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


如果她不曾见过光明,或许可以忍受黑暗。
但当她通过接触到更宽广的天地以后,她不愿意再将自己束缚在那个冰冷的家里。
曾经,她像个发不出声的聋哑人,有无数的情绪无处宣泄。
如今,她成了丈夫的“囚犯”,时刻活在他的监视下。
这一次,她不愿再沉默。
她想反抗,想逃离,想抗争,她写道:
我想挣脱身上的缆绳,让窒息的灵魂得到喘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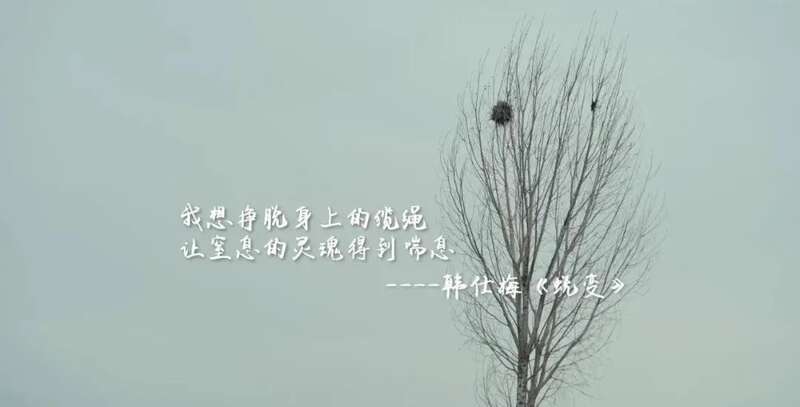
她向丈夫提出离婚,丈夫不同意。
他说: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为什么要离婚?
他不懂她的渴望,不懂她的追求。
更不懂,越过越好的日子,其实是以她无底线的退让为代价的。

当一位辛勤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妇女,意识觉醒,她该何去何从?
她又将会面临什么?
没有人理解她。
没有人帮助她。
越来越多的流言蜚语砸向她,说她不要脸。
家里亲戚轮番给她做思想工作。

2021年5月,因为担心影响女儿高考,她最终撤销了离婚诉讼。
如今,女儿已经顺利考上大学。
韩仕梅说,无论女儿读到什么程度,她都会支持她读下去,因为她不愿意成为她母亲那样的人。
“母亲让我失去了选择婚姻的权利,扼杀了我的幸福,两个孩子牵绊了我的一生,最后丈夫连我这一点点 (写诗的) 爱好也要扼杀,我是他们每个人的牺牲品。”

在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她受到联合国妇女署的邀请,去北京参加活动并发表演讲。
她穿上唯一一件大红棉袄,登上联合国大楼的演讲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她说:希望所有被性别暴力对待过的人,都可以反抗暴力。

这是她第一次去北京,为此她甚至丢失了,已经做了5年的工厂厨娘的工作。
但她不后悔。
她的大半辈子都窝在薛岗村,少有的出远门,也不过是送孩子去上学。
唯有这一次,她是为自己。
完完全全作为韩仕梅而活着。


她来到了曾经遥不可及的天安门广场。
她见到了她诗词笔下的山河大海。
过去,她只在书画里看过,只在脑海中幻想过。
如今,人来人往,微风拂面,海浪翻滚。
真好,原来人生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
她说,我已不再沉睡,海浪将我拥起。



